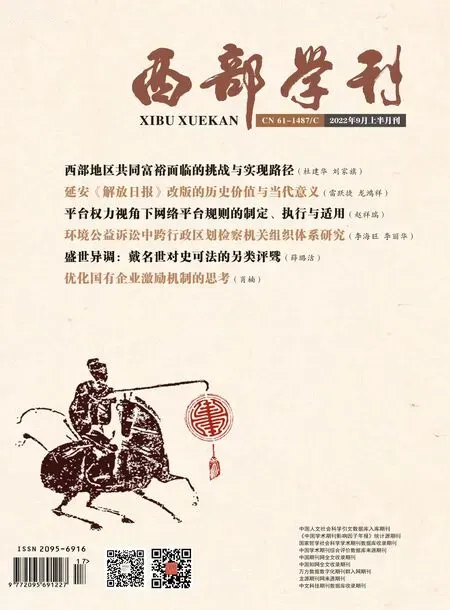盛世异调:戴名世对史可法的另类评骘
薛璐洁
弘光朝廷作为南明朝廷的第一个政权,虽然旋立骤灭,但对南明时局的影响却格外深远。史可法(公元1602—1645年)作为弘光朝廷的督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必然与南明政权的存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是明季以来史学家笔下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在张廷玉主修的《明史》、应廷吉的《青磷屑》、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以及史可法幕僚阎尔梅日记等时人著述中都有涉及史可法言行的记载,近代史学家顾诚在著作《南明史》中提及史可法对于维系衰微南明所做的不朽贡献。但众人对史可法的评价却因褒贬殊途,而难定公论,这一现象引起了热衷搜集南明史料的清初桐城名士戴名世的关注。
戴名世(公元1653—1713年)作为桐城古文的先驱人物,不仅因他清正典雅的文风受到后学推崇,更凭借其在史学方面的极高造诣,在南明史料的编纂过程中倾尽心血,“综其终始,核其本末,旁参互证”“虚其心以求之,平其心而论之。”然由于时局和历史等诸多因素,其保存下来的仅有数十篇人物传记和史论杂记。现将戴名世付诸笔墨较多的史可法这一人物作为研究切入点,管窥戴名世的论述对研究史可法乃至整个南明史带来的重要意义。
一、抑扬霄壤:《明史》与《南明史》对史可法的两种评价
崇祯自缢后,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参与建立的弘光朝廷被时人期许满怀,却在清军的汹汹铁骑面前土崩瓦解。对于史可法的评价,后世的史书抑扬霄壤。《明史》多处提及史可法,在此试举几例:
可法每缮疏,循环讽诵,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感泣。
为督师,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
素善饮……进数十觥,思先帝,泫然泪下,凭几卧。
这些呕心沥血之举颇有当年蜀相诸葛亮之遗风,“思先帝”“泫然泪下”的字眼将舍命报答先帝知遇之恩的史可法之伟岸身影展现出来。再如:
史可法悯国布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卫,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
这段评价指出弘光朝廷的败亡是“权臣掣肘”和“悍将跋扈”造成的局面,史可法作为鞠躬尽瘁的忠臣义子不能为南明政府所用,反倒成为“权臣”与“悍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其人“忠义奋发”,最终不免“志决身歼”,诚可悲矣。可以说,代表着清廷官修史书的《明史》编纂者们对史可法的道德品质推崇备至、满怀敬意。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顾诚教授(1934—2003年)在《南明史》中对史可法的评价与《明史》褒贬对立、不啻霄壤。
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份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
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顾诚的分析中,史可法是“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民族罪人。作为近代史学家的顾诚,具有将明季以来官修史书和私修史书收罗殆尽、征览察验的得天独厚条件,他在纷繁芜杂的史料中将抗清斗争作为研究的主线,力求突破藩篱,极大地拓展了南明史的研究视野。
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从表面上看是官修史书和私修史书的固有差异导致的,实际上官修和私修之间也有互动和征引,如《明史》馆正式开馆后,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张岱的《石匮书》等私家修史的著作都被陆续地送入馆内,戴名世曾在书信中提及“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这些送入史馆的私家修史在经过筛察保留、加工整理后荟萃成编。有鉴于此,将史可法放入清初学术背景中考察,在官私修史的对照中,结合戴名世的相关史学著述评骘这一重要历史人物,以求还原历史现场,展现人物全貌。
二、回避·褒扬:戴名世论述与《明史》等同时期著述的异同
据学界目前收集的戴名世著述可知,戴氏未对史可法单独作传,相关记录散见于《孑遗录》和《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等篇中,以纪事为体例的编纂方式和顾诚的《南明史》是相同的,顾诚在书中第二章“弘光朝廷的建立”、第三章“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以及第五章“弘光政权的瓦解”中的部分篇幅中涉及史可法。以纪传为体例的《明史》对于史可法的记述主要集中于《史可法传》中,两种体例各有春秋、不分轩轾。
《明史·史可法传》和戴名世著述中都提到史可法为官勤政爱民,为将与士兵同甘共苦。《孑遗录》云:
驰驱江淮间,衣不解带辄至十余日。军行不具帷幕幞被,当天寒讨贼,夜坐草间,与一卒背相倚假寐,须臾,霜满甲胄,往往成冰,欠伸起,冰霜有声戛戛然。
敬士爱民,所募健儿侠客,皆得其死力,虽古名将莫过也。
《明史·史可法传》中提到可法身材“短小精悍”,目光烁烁有神。
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
这说明史可法深受士兵爱戴,史可法祭告凤、泗二陵后呈给皇上的文书和劝谏皇帝发布讨贼诏书的上书,表达了他为先皇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诚之心。这里选录如下:
愿慎终如始,处深宫广厦,则思东北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则思东北诸陵麦饭之无展;膺图受禄,则念先帝之集木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罢,则念先帝之克俭克勤,何以卒隳大业。
先皇帝死于贼,恭皇帝亦死于贼,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诸臣,死节者无多;在南诸臣,讨贼者复少。此千古未有之耻也……臣愿陛下速发讨贼之诏,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阙,悬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责成效,丝纶之布,痛切邻里,庶海内忠臣义士,闻而感愤也。
《明史》在修订过程中几经删削,唯独对史可法的两篇上书给予了相当多的篇幅,这不能不说是清廷的刻意偏爱,乾隆帝作为《明史》的最终定稿人,不仅为前明的“抗清”英雄史可法追赠“忠正”的谥号,还在主持编修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称“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及遭时艰,临危受命,均足以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在“一代完人”的褒扬基调中,史可法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隐词回护、曲笔讳饰的现象,这些不光彩的细节隐藏在幽隐婉约的笔触下,为史可法的光环罩上了一层迷雾,这给清初史家戴名世拨云推雾留下一定空间。
史可法的仕宦生涯以崇祯自缢作为划分前后的时间界点,这是学界的共识。前期他几经升迁调动,但是都以镇压地方农民起义军为主要职责;后期作为弘光朝廷的最高军事长官担任兵部尚书并督师淮扬一带,直至殉节扬州,这段经历总共不到一年,即(1644年5月—1645年4月)。这一年史可法真正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在卷入朝野内外纷争的漩涡时,也走进亲历者的史书,因此后世的文集关于史可法的记述主要集中在这一年的经历。史可法因误判局势,导致延误军情,酿成大错与前期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九年军事生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却较为空乏,相比之下,戴名世的记述显得易览循宗、详尽丰赡。
戴名世在《孑遗录》中指出史可法前期军事指挥能力堪忧,为了抵挡起义军的侵犯,提出“两营一寨”的以守为攻策略,但面对居无定所、随处劫掠的起义军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史可法第一次担任军事职务是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五月,“上命史可法监安庐军”。
八月,贼众万余人自豫逼凤阳,颖、亳大震。史可法命总兵许自强率兵五千守桐,而自引兵三千至庐州当贼。贼自颖亳入英霍山中,出舒至桐。可法回军驻北峡关,与许自强为犄角。贼复从英霍走黄麻。十月,贼由黄麻走郧阳,又转入太湖、潜山。史可法率潘可大等御之于潜山,贼又入英霍。十二月,许自强率吴淞兵三千与史可法驻北峡关。
从八月到十二月,史可法面对起义军四处逃窜、劫掠啃噬的行径束手无策,没有和起义军进行过一次正面交锋,两次驻扎北峡关都没有起到抵挡敌军的作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眼皮子底下恣意妄为。在与桐城县令杨尔铭彻夜商议后,史可法决定在安庐一带实施“两营一寨”的计划:设立桐标营、栏马营和堡寨。
一立桐标营,立官主之,贼去则侦,贼来则守。
一筑栏马营,远城外筑土墙,使避难之民居之,内以护城,外以防贼。
一立堡寨,以远乡之民无可守之险,无可战之人,輙至屠灭,乃相视险隘筑堡立寨,立长主之,贼去则耕,贼来则守,而于城四隅各筑炮台。
实施“两营一寨”计划的落脚点在于协调近城、远城、远乡的军民关系,相互配合形成有效的策应——防御机制。史可法的军事策略从两次驻守北峡关改为利用军民力量共同守卫“两营一寨”,是以守为攻战术细致化的体现。但以劫掠为目标的起义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他们避开守备森严的安庐一带,流窜到没有来得及修筑城郭的潜、太两地继续抢掠。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闰四月“贼自英霍出掠潜山,可法御之,贼小却,凡十余日,贼来益众,而官兵止两千余人,贼围之数重”,史可法急忙请求凤阳总兵牟文绶救援,牟文绶率兵拒之,仍不能退敌。桐城县令杨尔铭令百姓“夜持火炬,鸣金鼓”壮大声势,“贼疑救兵且至,遂解围去。”看似严谨周密的“两营一寨”的计划,实则漏洞百出,可见史可法在与起义军周旋时屡屡处于被动局面,也反映了在军事思想与指挥能力上的欠缺。
同样的史实在《明史》中记述得较为简省,史可法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至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的守备经历,史书著者仅用了百余字概括,原文如下:
八年,迁右参议,分守池州、太平。其秋,总理侍郎卢象升大举讨贼。改可法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黄梅贼掠宿松、潜山、太湖,将犯安庆,可法追击之潜山天堂寨。明年,祖宽破贼滁州,贼走河南。十二月,贼马守应合罗汝才、李万庆自郧阳东下。可法驰驻太湖,扼其冲。
其中涉及史可法的部分只有“可法追击之潜山天堂寨”和“可法驰驻太湖,扼其冲”这两处,接着补充道“可法东西驱御,贼稍稍避其锋。十一年夏,以平贼逾期,戴罪立功”,点出了史可法军事防备和指挥能力的欠缺。如果说对史可法前期军事生涯简省记述是出于详略有序的考虑,那么后期的军事能力应该作为重点凸显出来。虽然作为督师的史可法受制于“权臣掣肘”和“悍将跋扈”而难有作为(前者是马士英等人阻挠干扰,后者是高杰等将领不服指挥),但1644年冬弘光政权握有江苏、浙江、湖南、江西、福建、两广、云贵以及湖北和河南的大部分,其远远多于清廷占领的领土。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史可法却经常流露消极抗敌的情绪,心灰意冷的他过早地产生放弃山河的想法,不肯再有一番作为。戴名世在《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中记录了史可法消极心态以及这种心态带来的两种负面影响:其一在于继续贯彻错误的以守为攻方针,其二在部下有投降倾向时“不强其志”,加速了己方全局的瓦解。书中记载有:
是冬,紫微垣诸星皆暗,公屏人夜召应廷吉,仰视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独明。”公曰:“辅星皆暗,上相其独生乎?”怆然不乐,归于帐中。明年正月,饷缺,诸公皆饥……有顷,高杰凶问至,公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建武,绍兴之事,其可望乎!”遂如徐州。
1644年冬应廷吉夜观天象,认为“上相独明”,激励史可法赶紧振作起来,重整军队,史公却因“辅星皆暗”而心情沮丧。次年年初,史公面对高杰的质问仅用“流涕顿足”回应部下,并退徐州以求自保。这样的细节在《明史》中仅用一句话概括,史可法听闻高杰被害死后,“流泪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遂如徐州。”“流泪顿足”是痛失爱将高杰引发的,“遂如徐州”则高杰之死导致军队实力受损,史可法在考虑大局后不得已退回徐州。事实上高杰死后,他的幼子拜史可法为义父,迎来了“自是高营将士愈皆归诚于公”的局面。《明史》巧妙地调整了事件的因果关系,既保留了部分史实,又将史可法爱民如子、有大局观的特点凸显出来,回避了“遂如徐州”是在长期消极情绪主导下做出的军事行动。
史可法为缓和因高杰之死引发诸将争雄内讧的局面,不得已将高杰在徐州的大部分兵力撤至扬州,命高杰外甥李本身为扬州提督,命高杰部下李成栋为徐州总兵。当清军压境之际,李成栋慌忙弃徐州而奔扬州,“而高营兵既引还徐州,于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徐州在史可法的默许下被彻底放弃。史可法的幕僚阎尔梅在回忆录中不无遗憾地写道:“余力劝史公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竟用左右言,去之扬州,且招余行,余哭此歌别之。”阎尔梅认为史可法既然不肯收复山东、河南,那么退到徐州还可以谋求河北,然其一退再退,退到了无险可守的扬州。在消极情绪的影响下,史可法在与清兵对峙中又一次错误地贯彻前期与起义军作战中以守为攻的方针,区别在于起义军不愿攻城掠地,清军却怀有吞并中原的野心。
退守扬州的史可法愈加消极,在听到精通奇门遁甲的部下应廷吉分析“今岁太乙阳局,镇坤二宫始系关提,主大将囚。且文昌与太阴并,凶祸有不可言者……大势已去”的言论后唏嘘不已、感慨万分。他的部下高岐凤、李栖凤二人眼看每况愈下的局势,遂生投降之意,劝史公一同投降清军,“公曰‘扬州死吾所,君等欲富贵,各从其志,不相强也。’李、高中夜拔营而去,胡尚友、韩尚谅亦随之以行。”应廷吉在《青磷屑》也记载此事,原文如下:
二十二日李、高有异志,将欲劫公以应北兵,公正色拒之曰:‘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高见公志不可夺,逐于二鼓拔营而出,并带护饷川将胡尚友、韩尚良诸兵北去……自此备御单弱,饷不可继,城不可守矣。
在兵临城下的危机关头史可法只想着“扬州死吾所”,没有及时约束手下,随着更多的士兵出逃投降,城中“备御益单弱矣”。史可法纵容部下变节的行为无疑帮了清军大忙,致使扬州不到旬日即破。
《明史》记录了部下高岐凤、李栖凤投降的事实,却没有提及史可法对下属投降后做出的回应。这就从侧面烘托了一个孤立无援的英雄拼尽全力守备城池的艰难场景,也符合“一代完人”的形象塑造。
作为一个集三代帝王、数百位明季以降史学家智慧于一体的《明史》,在史可法传记中,有意识地遮盖和回避传主那些不光彩的细节,美化和放大标榜千古的品德。反观同时期的戴名世在史可法的威望如日中天之时能够据实而录,冷静指出史可法性格、军事部署和指挥能力的缺陷,认为其以守为攻的错误策略和个人消极情绪对抗清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为后世研究南明史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排斥·争夺:官私修史在忠臣叙述上产生分歧的原因
《明史》对史可法有关史实的记述存在诸多缺漏,这背后反映的原因有很多,曾有学者认为是修史时将记载清朝入关前不光彩行径的书籍进行了淘汰和过滤,但史可法这样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士人作为清廷褒奖和宣教的对象,对和其有关的史料搜罗殆尽、掇菁撷华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分歧的焦点则集中于搜罗殆尽后怎样取舍才符合清廷的利益。
修史作为历朝历代的政治行为,是“新朝”加强自身合法性的手段。一直以来清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入关是替明朝复仇的正义之举: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66年)曾有“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宇内,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的记载。此处的“贼”自然是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在一点上,南明朝廷和清廷的敌人是一样的,这就给史书编纂者在修订口吻上留下了发挥空间。
史可法在1644年年底之前一直将清廷认为是盟友,并派遣左懋第作为北使前往清廷准备和谈,直到和谈梦的破碎让史可法意识到此时清兵才是真正的敌人。1645年初,高杰被降清的许定国所害,史可法在万分沮丧后做了一些军事部署,二月便从徐州退到扬州。清兵四月初抵达扬州,四月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史可法英勇就义。这意味着史可法在1645年之前一直将以李自成、张献忠代表的农民军队视为敌人,这和清廷一贯以来的主张是一致的,《明史》洋洋洒洒摘录史可法两次上书给弘光帝的文字就是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为背景下创作的。这样史可法后期军事部署能力的缺陷、消极御敌情绪、纵容下属变节等问题都指向了反清不力的事实。
《明史》编纂者正是抓住了反清不力这样一个显著事实,将史可法这些以农民起义军作为敌军的明朝烈士浓墨铺陈,同样的叙述口吻在永历朝廷的股肱之臣何腾蛟、瞿式耜身上也得到了体现。瞿式耜、何腾蛟在殉国后都被选入乾隆主编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更被赐予“专谥”之荣,“瞿式耜定诬立君,竭诚奉上,义全忠孝,节贯存亡,今谥忠宣。”同样为永历朝廷做出贡献的堵胤锡,与瞿式耜相比,在出身、地位、气节上均毫无欠缺,不但没有“专谥”的待遇,甚至连“入祠”都不可得。究其原因,何腾蛟与瞿式耜都看不惯堵胤锡借助农民起义军屡屡立功,这些遭清军重挫的农民起义军在投靠永历朝廷后被改编和重组后继续抗清,并给清军以沉重打击。当何腾蛟将这些投靠的起义军从湖南抽调走了之后,清军火速压境,因实力悬殊,南明军队一触即溃,何腾蛟本人誓死不降,以身殉国,遂入忠孝。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刊布后,被后来的官私撰述奉为丰臬,频频征引。如后来改办钦定《明史》,其后不仅附录考证之文,还吸收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的“成果”,将清朝赐予殉节诸臣的谥号胪列其后,从而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与《明史》“嫁接”在一起,结束了他们“相附而行”的“艰难”岁月。此后,各级政府所修地方史志之书,凡涉明末清初史事、诸人谥号,皆以此书为准。这些反清不力的明末英雄,一次又一次被抬高地位,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与农民起义军势同水火,而与清廷的矛盾却并不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将这些人的名字和事迹千秋传诵,宣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孟程朱之道,达到安抚人心、教化子民的目的是不言自明的。那么掩盖这些殉节诸臣不光彩的事迹也是理所应当的,而这些不符合官方书写殉节诸臣口吻的文献资料,则注定藏于深宫,埋于地下。
在官方如此细致缜密的安排下,戴名世的文集不可能因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南山集》案”的结束而解禁,在乾隆帝对舆论和书籍的严密控制下依然被禁止私藏。
康熙年间戴名世私刻《南山集》,悖逆不法,方式济代作序文,曾经审明治罪,并将书籍版片销毁,但阅时久远,恐伊子孙亲族尚有私自收藏者。该犯等籍隶桐城。著传谕书麟密行访察。如其族姓中尚有留存者,即行据实具奏,送京销毁,务期收缴净尽。但须不动声色,妥为查办。
随着道光年间文禁渐弛,戴名世的文集得以重见天日,桐城后学戴钧衡整理和出版的《潜虚先生文集》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道光年间完稿的《续修桐城县志·杂记·兵事》记载从“崇祯七年八月县人黄文鼎汪国华反”到崇祯十六年桐城的守备情况和《孑遗录》中戴名世一万多字的论述几乎一字不差,只在开头和结尾稍稍修改。《孑遗录》结尾有:
大清豫王遣将卜从善、张天禄至桐城,擒九武、孙得胜等……于是斩九武等于市。
《续修桐城县志·杂记·兵事》结尾为:
顺治二年乙酉闰六月豫王遣将卜从善、张天禄领兵抚桐执罗九武、孙得胜等诣江宁杀之。
道光年间修订的史集大幅度地摘抄戴名世著作的原文,意味着认可他的撰述客观公正,也承认史可法在桐城一带的守备情况是存在诸多问题的。
戴名世对史可法的情感是颇为复杂的,一方面,他承认史可法清廉为政、敬士爱民,在朝廷和百姓中都有极高的声誉,对于他就义前说“吾死,当葬我于太祖高皇帝之侧,其或不能,则梅花岭可也”深感敬佩,作为一个忠臣为国殉节固然可歌可泣;另一方面,出于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尊重,戴名世在冷静客观分析之后并没有一味给史可法唱赞歌,他不仅记录下史可法作为主要将领在敌军兵临城下时徘徊犹豫,用曲笔指出史可法的计划虽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实际执行时却困难重重,并且指出他驭下无能,常常左支右绌的窘迫心境,这体现了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责任和担当。这一点与清末史学家孟森的论断不谋而合。孟森先生有一段鞭辟入里的分析:“史公之可传,以纯忠大节,千载景仰,然其治军之才甚短,虑事之智亦不特殊。若用其德量诚信,辅君当道,进贤退不肖,以端政本,岂不为拨乱反正之大助.而乃使之治兵,正用其所最短……世人读《青烤屑》《幸存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尚为不平,谓诸野史不免翘公之短。吾独谓天使公不得不用其短。而公之纯忠大节,丝毫不能掩蔽于其间,则道其短正所以存其真。但当为公痛哭流涕,惜明祚之与公俱为天夺,而不应以此求多于公也。”孟森先生“道其短正”以“存其真”是秉事直书、不作佞史的体现。
四、结语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中,史可法是书写南明史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他与弘光政权以及内部党争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他的评骘不可不慎重。史可法被捧为英雄是因为他与同时期那些因私废公、贪赃枉法的官僚相比,具有公正无私、廉政爱民、愿与士兵同甘共苦等优良品德,在天崩地解之际成为士大夫追忆的精神领袖。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背后,不难发现清廷借机利用了士大夫的心理,在士大夫群体已有的记忆基础上进行添补和删削,以完善和重塑史可法形象。
经过史家一番拨云推雾,那些掩埋已久的真相逐渐浮出历史的天空。戴名世顾虑毁誉失当会妨碍一个史家对褒贬矜慎的追求,将史可法的功与过一分为二地看待:一则能维护史可法作为民族记忆上的精神载体,具有凝聚人心的价值;二则指出史可法的过失以及对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能够警醒世人,反省明朝灭亡的真实原因,其史德史才,一时无两。在《明史》的编纂如火如荼之际,戴名世不符圣调的文字在盛世同音的口吻下敲出了“不和谐”且强有力的音符,这为我们思考当下如何书写南明史的重要人物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