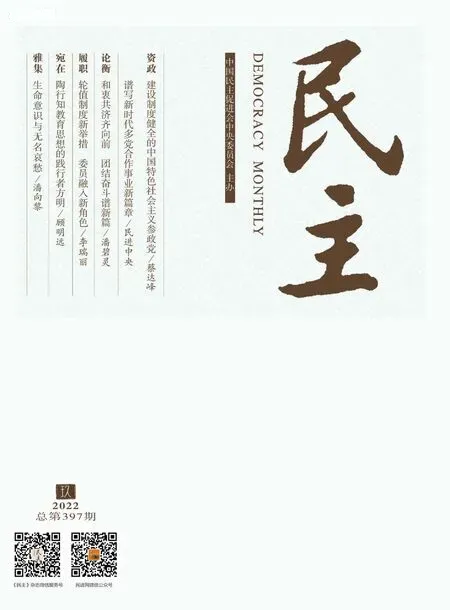生命意识与无名哀愁
□潘向黎
家里挂着一幅文瑜兄的画。墨色写意的山,一叶小舟在水上,舟上一个蓑衣船夫,一个红袍乘客,题诗是:“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倚枕犹听半夜钟。”我查了一下,是宋代孙觌的《枫桥》。最后一句的“听”,大多数版本作“闻”。
最后两句显然来自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曾独自在寒山寺门口,细细读了这首诗,在那个“唐诗现场”,真切地感到这首诗真是怎么都读不厌。但同时,心里再次翻起了一个迷团:“愁眠”的“愁”,到底能不能当真?真的是通常意义上的“愁”吗?若真的有“愁”,所“愁”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解释,自古大多是把这个“愁”字当真的。“愁”什么?
大部分人认为是羁旅之愁,荒凉寥寂,甚至苍凉欲绝。“目未交睫而斋钟声遽至,则客夜恨怀,何假明言?”(明·周敬《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全篇诗意自‘愁眠’上起,妙在不说出。”(清·沈子来《唐诗三集合编》)“愁人自不能寐,却咎晓钟,诗人语妙,往往乃尔。”(清·何焯《笺注唐贤三体诗法》)“‘对愁眠’三字为全章关目。明逗一‘愁’字,虚写竟夕光景,转辗反侧之意自见。”(清·王谦《碛砂唐诗》)“尘市喧阗之处,只闻钟声,荒凉寥寂可知。”(清·沈德潜《唐诗别裁》)“此诗苍凉欲绝,或多辨夜半钟声有无,亦太拘矣。且释家名幽宾钟者,尝彻夜鸣之。如于鹄‘遥听缑山半夜钟’,温庭筠‘无复松窗半夜钟’之类,不止此也。”(清张南邨语,见《唐风怀》)“此诗所写枫桥泊舟一夜之景,诗中除所见所闻外,只一‘愁’字透露心情。半夜钟声,非有旅愁者未必便能听到。后人纷纷辨夜半有无钟声,殊觉可笑。”(近代·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
当代的许多学人、作家也认为是“客舟孤苦”,“满怀愁绪”,有人猜测“愁”的内容是科考不顺的失意,也有人推测是大时代由盛转衰后的离乱荒凉引起的愁苦。
虽然不能说这样的理解背离了张继原意,但是我总觉得解释得小了,实了,板了。
确实,张继明明白白写下了“愁”,而我总觉得这“愁”是不必当真也当不得真的,此诗情绪基调是清冷中的宁静——顾随说辛弃疾词“月到愁边白”时云:“此所谓愁,岂棼如乱丝之焦心苦虑哉?静极生愁,静之极也”(《苏辛词说》),正可移来说张继此诗。主要是写“静极”。生出些许愁意,也是淡淡的。催生这首诗的,应该是一种清旷的自在,是出神、忘我甚至若有所悟的状态。
前人也有认为张继不“愁”的:“写野景夜景,即不必作离乱荒凉解,亦妙。”(清·宋宗元《网师园唐诗笺》)
“作者不过夜行记事之诗,随手写来,得自然趣味。诗非不佳,然唐人七绝佳作如林,独此诗流传日本,几妇稚皆习诵之。诗之传与不传,亦有幸有不幸耶!”(近代·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
评价都有道理,但是,仅仅是因为写野景夜景写得妙,或者“夜行记事,随手写来,得自然趣味”,这首诗就有如此魅力吗?难怪这样说的人,自己对这首诗的流传之广有几分想不通了。
也有与众不同的意见。如刘学锴认为,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里所写到的一切“都和谐地统一于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孑清寥感受中”,“这里确有孤孑的旅人面对霜夜江枫渔火时萦绕的缕缕轻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幽美风物的新鲜感受”……“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唐诗鉴赏辞典》)
骆玉明认为——
张继到底是在哪一年、为什么原因,在一个夜晚泊舟在苏州城外的江面上呢?或许,他是为了自己的前程离开家乡在世路上奔波。人生总是有很多艰辛,除了对自己,没有人可以说。
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这个夜晚,张继长夜无眠。世界是美好的,江南水乡的秋夜格外清幽,作为诗人,张继能够体会它。但世界也是难以理解的,你无法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催逼着人不由自主地奔走不息,孤独地漂泊。这时候钟声响了,清晰地撞击着人的内心。深夜里,张继听到一种呼唤,他找到近乎完美的语言形式把这个夜晚感受到的一切保存下来。寒山寺的夜钟,从那一刻到永远,被无数人在心中体味。(《诗里特别有禅》)
骆先生暗示诗中包含了某种禅意,似乎是张继来到了一个顿悟或至少很有利于顿悟的时刻;刘先生则揭示了清冷中的幽美和孤寂中的愉悦,同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词“轻愁”。
似乎越到晚近,对张继诗境的读解越倾向于宁静、发现和愉悦。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现代都市的兴起和发达吧。正如葡萄牙诗人、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在《不安之书》中所写到的那样:都市人之所以对郊野夜晚的宁静“满含渴望”,是因为平时总是处于“那些高楼大厦和狭窄的街道之间”。“在这片旷野里,无论我享受着什么,我享受是因为我并不在这里生活。从未被约束过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
都市文明越发达,人们越向往自然的宁静和空旷,于是《枫桥夜泊》那样的孤舟静夜渐渐变得越来越美好而珍贵,对孤独倾听夜半钟声的际遇的感情砝码,也渐渐从“同情”的那一边,移到了另一边:珍视与羡慕。
张继的原意属于张继,我的阅读感受属于我。我觉得《枫桥夜泊》的情感基调,不是通常意义的“愁”——不是客舟孤苦,不是离乱荒凉。它是一种宁静,彻底的宁静。似乎天地间只有这一叶孤舟,这一个人;这个人面对这样无边无际的清寥幽美,他无法入睡,好像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渐渐地,他“忘我”了,这个人不见了,似乎天地间是只有江枫、渔火和黑暗中的流水了。这时,震撼心灵的钟声响起来了,似乎是茫然人生中的一个棒喝,这个人从“出神”中醒来,于是“我”重新出现了,觉得这个时刻有无穷意味,于是记取下来。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人在一个秋夜里,无意中发现一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清幽境界,受到一种偶然而略带神秘的启示,产生了一种若有所悟又难以言传的感觉。甚至,这个人有透彻顿悟,但又归于“欲辨已忘言”的物我两忘之境。
愁,纵然有,也是轻愁。它不是因为世俗世界上的某个具体事由(或刺激)而生出的那种具体的、扎实的愁,而是和现实世界、日常生活相对有距离的一种愁绪和愁意,是在人相对安静、松弛、闲适的情况下才会浮现的,往往是和某种深刻的审美体验交融在一起的,是超越功利得失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心灵体验,是艺术的愁意,诗性的愁意。因此,又叫闲愁。
在愁的程度上,轻愁、闲愁是最弱的,只在第一级台阶上。“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是第二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愁一些了,第三级;“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又更愁一些,第四级;“一寸相思千万缕,人间没个安排处”,“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无?”是悲愁了,第五级;“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心碎了,对人生局部无望,第六级;“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愁得厉害了,而且对人生整体失望,第七级。对人生,这是烈酒了,但李清照写来,这样的愁苦还是小杯的;“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第八级,愁得猛烈,却阔大,是大觥的烈酒了,一般人难以抵挡,除非是辛弃疾这样的好汉子。“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天下大事,家国命运,除非心死,否则实在放不下,而时光无情,心愿未了,人生价值没有实现,人生却即将结束,这愁苦,到了第九级;“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独自莫凭栏,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亡国、破家、失去自由、难免亡身的李后主的愁,是彻底心碎、无望、无奈的愁恨,是最强烈的,到了第十级。
回头来看第一级的轻愁与闲愁。在意境和审美上,它有着烟水云雾的飘忽和飞花迴雪的轻盈,极富美感。
极爱冯延巳的《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那抛掷不去的闲情,那年年来袭的惆怅,是伤春?是春愁?是念远?是怀人?是叹息韶华易逝?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就是一个敏感的心灵在春天里感受到的莫名伤感,这种“新愁”,就是轻愁、闲愁。
同样的情绪和美感出现在另一位写暮春闲愁的高手——晏殊的笔下。
晏殊《踏莎行》: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还有他的名作《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一段隐隐孤寂和淡淡愁意,是居官显赫也不能“抛掷”的“闲情”,亦是“年年有”的“新愁”,闲意沁人、清芬四溢。这是属于诗性心灵的,若有所失,复若有所思,看似发自无端,却深挚动人。
秦观的名作,一般首推声调激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我却最喜欢《浣溪沙》,认为不但是少游的代表作,而且也是宋词巅峰杰作之一: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诚如缪钺所言,此词“取材运意,一句一字,均极幽细精美之能事……故能达人生芬馨要眇不能自言之情”。
这阕词的主角是情绪:凄迷的心绪,淡淡的哀愁,无处不在,但依然是轻盈的,清雅的;发自无端,难以自言,但很美,非常美,而且始终是美的。这便是真正的“闲愁”。
说到“闲愁”,自会想起“试问闲愁都几许?”这出自贺铸的《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最后四句,黄庭坚非常欣赏,周紫芝《竹坡诗话》中提到“人皆服其工”,罗大经指出(烟草、风絮、梅雨)“盖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赵齐平则洞悉了贺铸连用三个比喻(博喻)的妙处:“烟草”连天,是表示“闲愁”的无处不在;“风絮”颠狂,是表示“闲愁”的纷繁杂乱;“梅雨”连绵,是表示着“闲愁”的难以穷尽。抽象的“闲愁”被描写得如此丰富、生动、形象、真切。
这些诗词中的孤寂、失落、惆怅、无名哀愁,来自何方?曹丕《善哉行》所言“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愁来无方,人莫之知”,曹丕说对了一半,所有的轻愁、闲愁、新愁,都是与生俱来的,是与生命意识联袂而至的。人生如梦,浮生短暂,花开必谢,月圆即亏,遗憾多而如意少,愁闷长而欢娱短。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克尔凯郭尔则认为“世上无人不为某种原因而绝望”,人的不自由、局限、缺憾是生命本质的一部分,更何况人生一切戏剧的背景,是死亡的黑色幕布。
因此,轻愁与闲愁,并不是什么“消极情绪”“灰暗心态”,更不是“无病呻吟”,也不需从历史年代、作者生平中苦苦追索“历史原因”“个人原因”,因为这样的愁绪和愁意并不来自于具体的一个原因、一件事,而是来自生命本身。“深知身在情长在”,人生的局限、生命的缺憾永在,心中的愁也必定长存。
李清照和柳永都是抒写愁绪的高手,但是他们的笔下较少出现真正的闲愁。他们的愁,往往来自于心事:不是“求不得”苦,就是“爱别离”苦。他们的愁,是有具体因由的。这种愁,甚至在他们的某些人生阶段,是有解决的可能的。比如,赵明诚回来团聚,比如,易安能够结束被迫归宁的日子回到丈夫和自己的藏书身边,比如,赵明诚不因为易安无出或者年长色衰而纳妾,那么李清照的愁苦是可以排解的。
苦苦思念着一个人,或者心中有强烈恋情,整个人便处于奥尔罕·帕慕克《纯真博物馆》中所写的状态:“我的胃里有午饭,脖颈上有阳光,脑子里有爱情,灵魂里有慌乱,心里则有一股刺痛。”这时候的愁,是情愁,是浓愁——心里有“人”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伊人的影子,只见那片特殊的树叶,不见整个森林,愁因伊人起,整颗心置于相思的磨盘中;灵魂里没有慌乱、心里没有刺痛的时候,才会安静地看见整个世界,发现世界辽阔,安静,蕴含着生机、美、神秘和启示,但,依然惆怅。依然哀愁。这便是闲愁,是轻愁,也是清愁。
清愁,这两个字真美。这个词,和青瓷器物,是我心目中“纯中国的美”的典范。雅致而含蓄,静谧却深刻,单纯中有许多微妙,丰富却又远离尘嚣,能同时带给人轻灵(向上)和沉静(向下)的感觉,美得极富灵魂性。
“有不可一世之慨”的辛弃疾,在他24岁的立春日,写下他南归宋朝后的第一阕词《汉宫春》,后半阕里便有“清愁”:
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清愁不断,而且纠缠成结,如玉连环般无法解开。这样的“清愁”太有力量,只属于辛弃疾。
最初是在《红楼梦》里读到“清愁”的,曹公用“风露清愁”的芙蓉来代表林黛玉。一身不食人间烟火的脱俗和一缕带着诗性幽芬的愁意,令她美得不同凡响。从而和代表宝钗的花王牡丹形成对比。黛玉多愁,其中有身世的悲愁,有相思的情愁,有高洁者与世疏离之愁,也有颖悟者敏感于生命本质的闲愁与清愁。
刘晓蕾在《醉里挑灯看红楼》中写道:“谁能孤独而自由?……是黛玉,让孤独开出了诗意的花。”说得好极了。
新愁、轻愁、闲愁、清愁,是高级的精神活动,与感情的丰富、感知的敏锐、内心的独立、个体生命的觉悟相伴相生。能深刻体味这种愁的,都是敏感而安于孤独的人,是在孤独中思考生命本质、细细体会人生况味的人。
“孤独而自由”的心灵,才懂得轻愁和闲愁。
深刻地体味它,以灵隽之笔抒发,方能令人“似置身于另一清超幽迥之境界,而有凄迷怅惘难以为怀之感”(缪钺语)。
“人世生活的本来状态就是不如意、不完美的,从来如此,也会永远如此。不但不该厌弃,正当细细品尝这人生原本的滋味。”(朱刚《苏轼十讲》)
只有真正挚爱生命的人,才会甘于担荷如此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甘于细细咀嚼,深深品味如此苦涩幽微、黯然神伤的情怀。
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
身在情长在,愁也长在。闲愁最苦。闲愁也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