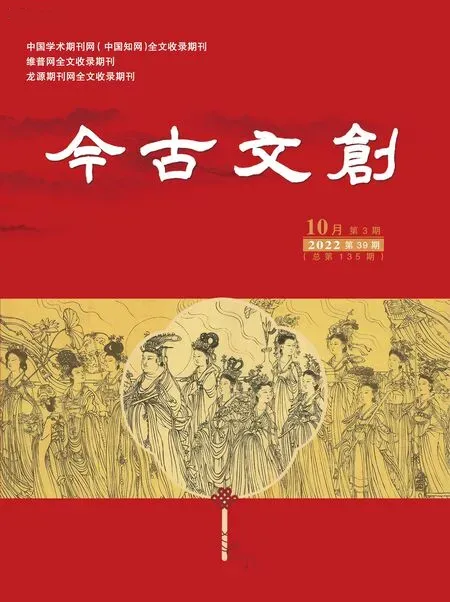《儒林外史》之僧道书写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突破
◎孙 晴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儒林外史》写作于乾隆年间,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以江南地区士绅的生活百态为基点创作的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小说着力于展现社会风尚与伦理观念,其中关于僧道的宗教书写占据了相当的篇幅。
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经过汉化的佛教与本土的道教早在唐宋时期就进行了密切的交流,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明清时期,儒、释、道呈现出了三教合流的趋势。从上古神话的叙事萌芽开始,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在明清戏曲、小说中大放异彩。宗教文化对传统叙事文学发展的参与,促生了传统叙事文学中复杂的宗教书写。
《儒林外史》在传统的依托宗教干预现实的模式下,在僧道形象的塑造上对原本的“仁者”“哲人”形象有所颠覆,并且通过超自然性、传奇性与强现实性结合的方式,将宗教与元素带来的落差感放大。
一、《儒林外史》中的僧道书写
(一)《儒林外史》中的僧人职务
为了便于对佛教事务以及寺庙僧人的管理,清代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僧官制度。僧官最早是佛教僧人团体内部自治的产物,到了清代被纳入了行政管理体制。僧官由封建统治阶级授权的僧人担任,管理一定行政辖区内的僧侣以及相关佛教活动,有相应的品级。《儒林外史》第四回“荐亡斋和尚契官司”中因为田产纷争而陷入官司的和尚慧敏就是僧官,佃户何美之称其为“慧老爷”,恭恭敬敬地请他喝酒吃饭,除了慧敏是田主人的缘故,也有对其僧官品级的忌惮。
作为佛教事务的管理者,僧官在各种佛教仪式中担任主持。僧人与道士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宗教活动的参与者,而其中与世俗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替亡者超度的仪式。小说第四回范母死后,范进“请大寺八众僧人来念经,拜梁皇忏,放焰口,追荐老太太升天。”第二十六回鲍文卿死后,和尚、道士与吹打手一同为其送殡。
除了作为宗教仪式的参与者,僧道还承担食宿提供者的角色,原本的宗教活动场所也具备了为不同阶层人士的临时住所。小说开头申祥甫等人请周进到观音庵作学堂老师,并每月向和尚支付食宿费,同一回中,王举人也宿在庵内,第二十二回牛玉圃和牛浦宿在道观中。除了驿馆和租房外,僧寺道观还是游玩和宴饮的场所。第二十八回和尚骂小和尚道:“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模样!”同回中,僧官留萧金铉、诸葛天申和季恬逸三人吃饭、陪同他们游览寺庙,打破了佛门清修之地的固有印象。
(二)《儒林外史》中的僧道形象
《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对僧道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
在作者笔下,大多数的僧人都并非清修者,他们的“人性”是多过“佛性”的,且并无向“佛性”修行的趋势,人性之恶在他们身上占据了压倒性地位,宗教的戒律清规在小说中形同虚设。
慧敏和尚在何美之的一只火腿引诱下便“口里流涎,那脚由不得自己,跟着他走到庄上”,可谓是丑态百出。到了何美之家中,慧敏和尚竟居于上座,何美之及其太太居于下坐作陪,饮酒作乐,乃是破了不饮酒之戒。在头上抹盐引牛来舔,谎称牛是自己父亲转世,欲将牛占为己有者是犯了妄语、贪财之罪。请季恬逸等人来家摆酒唱戏者,是破了不歌舞及旁听之戒。与喇子龙三有过非正当关系,被其男扮女装上门敲诈,丑闻险些败露者,是破了不邪淫之戒。恶和尚吃人脑浆,是破了不杀生之戒。更有甚者,他们成为僧人的动机就并非为了修行。王惠入仕之初仕途顺利,被举荐为“江西第一能员”,实质上却是个贪财的酷吏,宁王之乱时投降,害怕被治罪便隐姓埋名出家为僧,拒不承认千山万水赶来相认的亲生儿子。陈和甫的儿子仅仅因为生活琐事和丈人吵架,就一气之下做了和尚,“无妻一身轻,有肉万事足,每日测字的钱就买肉吃,吃饱了就坐在文德桥头测字的桌子上念诗,十分自在。”他出家为僧,不是为了苦行,反而是为了躲避俗世生活的责任,以僧侣生活的自由为享受。书中详细描写的道士来霞士,最喜结交官吏名士,以抬高自己身份。
吴敬梓笔下大多数的僧道都是欲念与恶的化身,但也存在一个例外,那就是甘露庵的老和尚。吴敬梓在书中并没有提到老和尚的法号,但却在多回中出现,占据了相当的篇幅。老和尚第一次出场是第二十回中,牛布衣病故前将后事托付给老和尚,并嘱托他将自己的诗集交给有才之人。老和尚因为牛布衣与自己萍水相逢却如此信任自己而感到过意不去,悉心照顾他,亲自到自己房中做了龙眼水喂给他喝,并在他亡故后大哭一场。前文提到小说中多次提到僧人为亡者举行超度仪式,但大多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并不作为重要情节展开。然而此处,老和尚在牛布衣身死后为他安排后事,是作者少有的对丧葬仪式场面的详细描写。老和尚亲自买来棺木装殓,请邻人帮忙,“百忙里,老和尚还走到自己房里,披了袈裟,拿了手击子,到他柩前来念‘往生咒’。”“取一张桌子,供奉香炉、烛台、魂旛;俱各停当。老和尚伏着灵桌又哭了一场。”老和尚与牛布衣仅仅是房主人与借宿者的关系,却因为牛布衣的信任和嘱托而尽心尽力地安排他的丧礼,周到妥当,可以说,老和尚是至善的象征。
他的“至善”同时也体现在对牛浦郎的态度上。牛浦郎偷钱买书,每日来庵里读书,老和尚却认为这是极上进的表现,借他油灯读书,将牛布衣的书传送于他。吴敬梓在这里有意颠覆遇隐贤传书的传统,老和尚所授者并非张良式的上进人才,而是一个沽名钓誉者,他不能识人,所托非人,是因为他用“善”的眼光去看待世间种种,无条件地信任世人。然而人性之恶无法因为善的存在而被忽视,他对牛浦郎的善举自然没有得到善果。他用广泛的善对待万物苍生,对众生有着“菩萨低眉”式的仁慈之心,具有普世的慈悲,在此基础上,他收了郭孝子两个梨,便要广传僧众一人一碗梨水,不独占分毫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
除去甘露僧,郭孝子在寻父途中遇到的另一位老和尚就颇有些神话色彩了。吴敬梓在此处安排了与“罴九”的奇遇.那罴九在山上,长了一只角、一只眼,“任你坚冰冻厚几尺,一声响亮,叫他顿时粉碎。”如此可怖的异兽,老和尚却笑称其为“雪道兄”,与其称兄道弟,十分熟悉亲近。这一场奇遇,与传统的志怪主题有些类似,这一情节的安排,衬托出老和尚的“仙风道骨”,将其奇异化、神仙化。
二、《儒林外史》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宗教书写的突破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的宗教书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以鬼神为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以神仙精怪故事为主体框架。这样的模式常常出现在志怪小说中,其中以东晋干宝的《搜神传》中的部分故事为代表,其序言中直言“明神道之不诬”,即以证明神仙鬼怪的真实存在为创作目的。此类范式下的作品以宗教教义为主旨,想象奇特瑰丽,富有浪漫色彩,但其创作往往出现类型化倾向。
(二)以鬼神为依托,抒发现实诉求。这样的作品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占据了相当比例,或通过“人鬼之恋”“人神之恋”的模式追求现世婚姻爱情的自由,例如汤显祖《牡丹亭》、郑光祖《倩女离魂》乃至后世蒲松龄《聊斋志异》;或通过宗教形象的塑造表现作者的理想人格、精神追求或对人生哲理的思索,例如《西游记》。
(三)宗教弱化为情节推动或人物衬托的工具。这样的书写模式往往出现在一些现实性较强叙事文学作品中。例如王实甫《西厢记》中普救寺只是作为男女主人公相会的地点存在,《水浒传》中五台山与大相国寺诸僧,只是起到衬托鲁智深的人物形象和安排其归宿的作用。这样的宗教书写往往是背景化、工具化的。
以上的三种书写模式下宗教的参与度是逐渐减少的,宗教元素也逐渐由直接的神鬼精怪转向普通人与超自然因素的中间人、媒介。除第一类为纯粹的鬼神传说外,第二类、第三类往往都是通过“遇仙”的模式,使人物与宗教元素相遇,展开一段奇遇。
《儒林外史》对于第二种、第三种模式有部分继承。宗教元素在小说中仍然承担了一部分合理化人物、情节的功能。这一类宗教元素以风俗、习俗的方式出现,最具有典型性的就是作为驿馆的僧寺道观以及作为群像出现的无名僧人道士。小说的宗教书写仍然存在第二类范式下干预社会现实的目的。然而,相较于以往的宗教书写,《儒林外史》在各个方面都有所突破与创新。
首先,在形象塑造上,《儒林外史》颠覆了传统的“清修者”和点化世人的“哲人”“思想者”形象。“三藏禅林”成为游览玩耍的娱乐之处,原本远离世俗的佛寺道观承担起了娱乐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僧道从出世的修行者变为世俗生活的参与者,是清代社会风俗画中的一笔。他们的宗教活动沾染了世俗的色彩,最不该沾染世俗欲望的群体却反而成了欲望的具象载体。然而,他们并不是《水浒传》中的“义僧”,他们更像是俗人,行为中带有很多功利化的色彩。小说第二回中,本该用于佛前供灯的香油全被和尚贪污,中饱私囊。本不该参与尘世纷争,却替人说媒,又参与田产买卖,绞进了一场官司。本应当远离俗世的人情世故,却在匡超人考中后前来奉承。僧人道士们追逐利益,欺软怕硬,与各种官员士子结交,上赶着讨好高位者。佛教的清规戒律、教义教旨一概抛弃,取而代之的是金钱至上、利益至上,追逐声色犬马,更有极恶者到了要“吃人”的地步。争名逐利的不仅仅是儒生,纵情声色的也不单是世人,竟还有僧道,可见现实社会这股不正之风浸染至深。作者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反映整个社会的风尚,以最远离世俗者的入世来彰显社会的功利性以及进行道德批判。
如果说,僧道之“恶”在《金瓶梅》中还有所体现,那么同样作为强烈现实性的小说,《儒林外史》在超自然因素上的运用便可算独树一帜。《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实写清代南京杭州的文人生活图景,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真实的地名,例如燕子矶、清凉山、西湖等,描绘了大量的江南风土人情,并且,在人物塑造上,往往有其原型,或姓名字号相关,或性格相似,经历相关,无不给读者以强烈的真实感。然而,作者在着力渲染其真实性的同时,于宗教书写上又安排了一些超自然的因素与传奇性情节,乍看十分突兀,却有其深意。
宗教的神秘性及其起源的传说性使得超自然因素与传奇性情节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儒林外史》少有的奇幻色彩与传奇惊险的情节主要集中在小说第三十八回。正是在这一回中,郭孝子寻父途中遇到与凶兽“罴九”称兄道弟的老和尚,而甘露僧遇到了曾被赶出禅林的恶和尚。这两出“奇遇”的安排,需从全文来看。第三十八回位于整部小说的中后段,小说中较为精彩的段落、刻画出彩的人物大多已经登场,也就是说,这卷社会风俗画已经展开大半,图未穷而匕将现。这一回中出现的两位僧人与小说中其他在世俗名利欲望中翻滚的僧人和道士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于可以说,甘露僧与郭孝子所遇老和尚,更符合传统认知中的僧人形象。甘露僧是超脱的,是去功利化的,从甘露庵到京师报国寺做方丈,本是平步青云,却因厌京师热闹而离开,他趋向于个人的清修,躲避尘世的纷扰,吴敬梓在第二十一、二十二回中,利用反讽的手法,将甘露僧与牛浦郎一正一反置于一处,意在反衬讽刺牛浦郎急功近利冒名顶替,但也同时表现了甘露僧之至善,他的善举在牛浦郎身上虽然未得善果,但却在自己遇到恶和尚、身处险境时得遇萧云仙逢凶化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者肯定了因果轮回,但其目的并非宣扬佛教教义。在甘露僧的身上,有一种普世的慈悲,他的悲悯之心近乎佛性,应当是作者理想化的产物,是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理想人格。作者在小说第四十一回描写了清凉山地藏胜会点香花火烛的习俗“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这无疑是掩菩萨耳目、粉饰太平、自欺欺人的行径,将社会之黑暗与人性之丑恶尽数掩去。而吴敬梓想做的,就是揭开太平的表象,将欲望与人性的真实赤裸地展现出来,同时又呼唤对理想人格的趋近。而郭孝子所遇老和尚,更倾向于世外高人的形象,他居于深山,仿佛一位隐者,与异兽来往,称兄道弟,颇具名士之风雅。
无论是甘露僧,还是老和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都象征着一种回归。吴敬梓刻画功利化的僧人群体确为一种对传统的反叛,然而并非为了反叛而反叛,为了颠覆而颠覆,反叛的最终目的依旧是为了“扳正”,是对一种对原初朴素的真善美的回归。这种似乎已经逝去本该是人性中的美好,放在作者所描写的社会中显得非常突兀,显得近乎“神性”这种落差感、突兀感恰恰是一种反常。
三、结语
传统叙事文学在演变的过程中,部分作品与宗教文化发生了密切且复杂的联系。《儒林外史》由多元化的僧道形象和宗教对社会的参与进行宗教书写。在继承以宗教映带现实模式的基础上,从僧道形象层面和强现实性中的超现实性融合层面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的宗教书写进行了突破,通过一系列的颠覆来进行一种对本初美好的人性和健康的社会风气的回归。
①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②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7页。
③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2页。
④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页。
⑤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0页。
⑥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