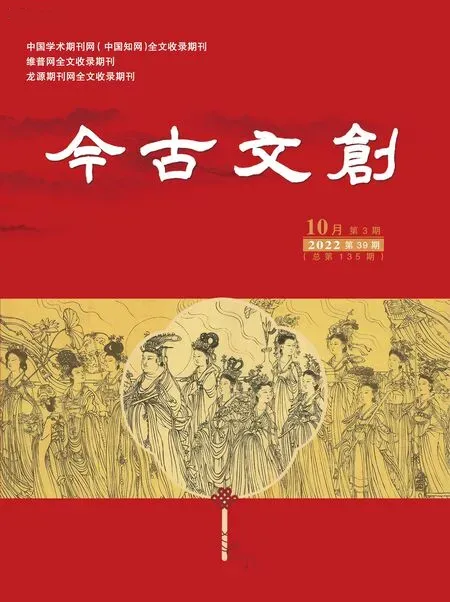不可忘却的创伤记忆
——试论“流言” 之下鲁迅先生的精神世界及其创作
◎李 静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 100083)
一、鲁迅先生文章中的“流言”
“流言”作为一个普通的日常汉语词汇,它指的是一种广泛传播但却缺乏事实依据的说法,同时它也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乎某种社会现实问题的不确定消息。流言一般被认为是未经考证的、非正式的话语,它在很大程度上与谣言相似,即为有人故意散布,甚至恶意捏造,以此来蛊惑人心,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未经证实其准确性,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曾在其著作《谣言》一书中强调过此特点,他认为:“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辟谣的信息。”
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流言”二字共在51篇文章中出现128次、“谣言”二字共在102篇文章中出现143次、“闲话”二字共在57篇文章中出现99次,这三个词都有在背后议论他人是非之意。从这三个词出现在鲁迅先生文章中的数量与频率来看,一方面表明了鲁迅先生饱受流言的困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鲁迅先生对于流言的介怀,因此频繁地在文章中提及。
“闲话”除去在背后议论他人是非之意,亦有在生活中随意而谈的闲趣之意,其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并非像“流言”“谣言”一样情感倾向明确,因此在本文中对于“闲话”并未做进一步地分析阐释。同时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流言”二字相较于“谣言”二字出现的频次更高,所以在这里本文将鲁迅先生文章中“流言”二字的出现次数做了一个数据统计(数据来源:北京鲁迅博物馆在线检索系统)。

集名 次数 时间《坟》 7次 1925年《彷徨》 3次 1925年《朝花夕拾》 8次 1926年《华盖集》 31次 1925-1926年《华盖集续编》 49次 1925-1926年《而已集》 2次 1926年《集外集》 3次 1925年《集外集拾遗补编》 1次 1927年《中国小说史略》 1次 1924年《译文序跋集》 2次 1927年《两地书》 10次 1925-1927年书信 11次 1925-1935年
从上表中数据可见,在1926年左右鲁迅先生频繁地在文章中写到“流言”,并且在其杂文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在鲁迅先生的写作中,其笔下的杂文论战色彩最为浓烈,而在此,流言的发出者、散布者更是为其攻击、痛斥的对象;同时书信集中出现“流言”的频次也较高,书信是鲁迅先生与最亲近的爱人、友人之间的对话,在此他并不设防,可以尽情地倾诉自我及其内心的困扰;此外在篇幅短少的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中也多次出现“流言”,这是中年的鲁迅先生对于年轻时的回忆,此时的他身陷世俗的纷争不免又想起曾经流言对其的中伤。
“流言”二字作为鲁迅先生在文本内的用词,其在文本外产生的语境也是不可忽视的。鲁迅先生一生为流言所困,这不免也成了他的生存状态,可以说其生活饱受流言与世俗纷争的侵袭,而作品的创作语境必然与作家本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文本内外,在过去与当下两端之间,我们不得不审视作家自我的精神世界。
二、无法忘却的创伤记忆
鲁迅先生曾言,“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我们由此可见流言对于鲁迅先生精神世界留有的阴霾之深、伤害之大,使得其在成年后的写作中频频提及,无法忘却,这已然成了他脑海中的一种创伤记忆,在个体付诸语言和文字的行为之下将压抑的创伤记忆唤起。
创伤性记忆又被叫作精神创伤或心理创伤,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引起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的记忆。创伤记忆会对人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对于当事人的行为与情绪,并且它是一种会被持续唤起的记忆。“流言”之于鲁迅先生,从幼年到中年在其生命中持续留存,成为其不可忘却的创伤记忆的同时也成了其创作话语。
一般人在幼年时受到的伤害容易对其一生产生持续性的不良影响,鲁迅先生最初所受流言的损害便是在青年时期。在鲁迅先生的儿时生活中有这样一个人,她代表着一种令鲁迅先生最为厌恶的人性,即瞒与欺,并且她以自己的言行着实给予了青少年的鲁迅以精神损伤,她就是鲁迅笔下的衍太太。衍太太曾经教唆不谙世事的鲁迅偷母亲的钱物,并且散布鲁迅变卖家中东西的流言,在此流言之下使得年纪尚小的鲁迅变得怯懦、羞愧,不敢直视他人的眼睛与接受母亲的爱抚,仿佛自己真的变成了小偷。
可见年少时的流言带给鲁迅先生的是一种精神伤害,他幼年在故乡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给他留下了痛苦的内心体验。相较于物质的匮乏,精神上的折磨对一个人的灵魂是更具有侵蚀性的,它侵犯了鲁迅先生作为独立个体的健全人格,给幼小且单纯的心灵以沉重打击,并且这种伤害根植于心,在世事面前时常被唤起,同时这种少年经历也给了他清醒认识社会与人本来面目的敏锐双眼。
还有曾在日本学医时鲁迅先生在解剖学这门课拿到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成绩,却被同学散布是受老师恩惠所得的流言。这些在其年轻时所受的精神伤害鲁迅先生于后来的回忆中才提及,而写作时正是1926年,我们便不得不思考当下之于过去——“旧事重提”的意义。
黄子平教授关于鲁迅先生旧事重提的一看法值得我们注意,其言:“为回忆而回忆的事是没有的,旧事重提必是为了镜照现在,即所谓‘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将过去收纳于现在’。一旦为了解释当前,而将旧事反复重提,使之成为现实的一项注解,旧事也就‘故事化’‘寓言化’了。”“流言”经由过去来到当下已然成了一种创作话语,而现实与过去是在相互作用,当下的语境是对过去的影射,过去的语境则是对当下的确认。
除却年轻时的流言阴影,回到当下,1926年左右鲁迅先生频繁地在文章中写到“流言”二字,此时的他更是陷在流言的漩涡中。1923年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便是因羽太信子捏造流言所致;1926年“女师大学潮”事件被陈西滢散布谣言是鲁迅所鼓动发生的;1925年与1926年间陈西滢又发文称鲁迅所做的《中国小说史略》存在抄袭之嫌;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鲁迅先生因顾颉刚要到中山大学任教而离开却被谣传是亲共而逃亡。细数1926年左右有关鲁迅先生的流言,从生活到学术到政治,这些都是令其无比愤然的事件,在他的笔下被反复言说,可见流言对他的伤害之大以及鲁迅先生对于流言中伤的在意。
然而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尤其是杂文中,那些散布谣言的人被比作“媚态的猫”“趴儿狗”“跳梁的老鼠”等等,鲁迅先生以最有力的文辞以回击,他在叙事中参以杂论,极尽反语、讽刺、比拟,给流言发出者以抨击,揭露他们的险恶用心与故弄玄虚。
作为流言下的受害者,鲁迅先生表现了作为民族战士的一面,他的奋力反抗与不屈不挠,显示出他看待流言的自我原则,即“一是鄙视,不理不睬;二是适时反击,揭穿卑劣无耻的谰言”。他绝不会任听流言为自己冠上莫须有的罪名,他在《并非闲话》中就曾指出:“‘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
当下与过去的交织,流言的不断侵袭,其成为鲁迅先生无法忘却的创伤记忆,损害了他的独立人格与尊严,使他的精神世界饱受纷扰。然而鲁迅先生的自我意识始终高扬勃发,在流言的侵害下仍然保持着斗士的警觉,他将笔锋指向小人与黑暗的统治,在流言话语中揭示谣传的杀人诛心与国民的麻木,这便是他对自我人格最好的证明。
三、流言之下鲁迅先生的创作
流言可畏是以一种特殊的声音形态存在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也被看作是一种叙事话语,它的频繁出现证明其在鲁迅先生的创作中占有举重若轻的地位。身陷流言侵扰中的鲁迅先生在与奸佞小人论战的同时也显露出了作为一位思想家的深刻性,他把“流言”当作叙述话语,使之承担叙事功能,以此来阐释对于国民性的思考。
作为叙述话语的“流言”在文本中的表现,朱崇科有一观点值得我们借鉴,他指出:“流言话语在此处显然不只是娱乐或流言的简单指代,而更多是富含了权力关系的运行机制。易言之,流言话语更要探讨的是流言在小说中的权力运作结构和轨迹。”鲁迅先生受流言伤害之深,所以他更能洞见流言在社会中产生的巨大破坏性,他把这种思考具体置于书写中,落实到对笔下人物的描写中,以此来表达对于那个时代人性与社会的批判。以下将略选鲁迅先生的几篇文章来解读流言话语在其笔下的意义。
《阿Q正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鲁迅先生塑造了阿Q这一人物典型,从这一人物出发,小说中充满着民间极度无聊的并毫无根据的八卦流言,包括对于革命的传言,对于假洋鬼子的揣度,还有阿Q入城再返回后的“卖货事件”,尤其是邹七嫂对于阿Q的造谣更是决定了阿Q人生的起落等等一系列流言事件,都体现出一种流言在言说中成了集体无意识指认下的“真相”。著名学者李欧梵曾在其著作《中西文学的徊想》中写道:“鲁迅在作品中对中国的民族性讽刺得最厉害的就是《阿Q正传》,它是鲁迅最长的一部作品,而‘阿Q’也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成了一个讽刺的象征和习惯用语。”因为正是他以一种典型的象征性印证了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早已将流言变成了日常话语。
《理水》是一篇极具社会现实讽喻性质的文章,它是鲁迅先生改编自我国传统神话故事大禹治水而写作的,在这洪荒之野下的文化山上无疑也是充斥着流言的国度,学者与民众都是流言的制造者与发出者,有关于禹的传言比比皆是,他们不知谁是真正的治水人,知晓后却又对他予以另类的揣测。其实鲁迅先生在这样的流言话语中揭示的是国民的愚昧与无知,启蒙者被遮蔽,被困于流言的围城里,而受启蒙者则愈加成为权力中心话语的牺牲者,大众的言说指向的是社会群体的无意识。
更甚者是《药》,在这篇小说中流言“人血馒头可以治肺痨”成了杀人的隐形刀刃,无法辨别流言还是箴言的国民正在以自我个体无法负责的言论杀着人,喝着血。愚昧与麻木的国民,他们是庸众,是无聊的看客,他们将道听途说当作是自我言语表达的权力,这是麻木的国民们共有的特点,以此又进一步衍生为一种群体文化特征,所以我们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又何尝不是为大众集体无意识的流言所杀呢?
普通民众作为社会的下层,他们必定是无法掌握中心权力话语的,而流言的存在则能够扮演一种“代偿”的角色,弥补大众丧失权力话语的缺憾。所以说流言的存在的形态其实可以用《叫魂》一书中所言的“妖术”来指认,“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一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通过流言话语的言说,大众以此能够对自我话语权力进行确认,而流言的杀伤力则根本不在他们的顾忌范围之内,甚至可以说“流言杀人”是他们意识不到的,殊不知他们本人早也已成了被流言所杀之人。他们不仅是这种权力游戏的帮凶,也更是权力运作之下的牺牲者,放任自我主体意识一步步滑向平庸与贫瘠的所在,彻底陷入非自住型人格的悲哀之中。“鲁迅把专制权力下的国民人格概括为羊与兽的二重特征。而这二重特征就像传递权力的接力棒一样,在受支配被阉割的同时也让你具有支配和阉割他人的权力。”说到底民众们本质上仍是权力运作机制下的他者。
“谣言的可爱之处在于能让人听从它的摆布,即便没有那些不论在自己的事情还是在看法和观点上都不受影响的人的帮助,它也能在善与恶中继续滋生。究竟谁会成为流言的交换载体纯属偶然。不光被议论的人,就算所谓的目击者也不在场,最后在文学惯例期待各种辩词代理人的地方出现了空白。这种严重的缺省构成了听传。”麻木的国民们早已将主体性尽失,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流言的肆虐不仅考验的是人性,更是人性背后存在的社会文化机制。
四、结语
从青少年开始便深受流言侵害的鲁迅先生,流言沉入他的内心并成了他心底的创伤记忆,而在其创作中他又将这种创伤记忆转化为具体的叙述话语,使之承担叙事功能。一方面我们看到鲁迅先生以他高昂勃发的精神面貌持犀利的笔锋通过论战来建构自我以抵御流言,另一方面他又能够以人文学者的悲悯之心与心系国家社会的使命意识来审视国民,不仅仅是把流言当作小我的创伤,更是将其放置于民族与社会之中来进行书写。
此外,流言话语的呈现也进一步显现出鲁迅先生对于民族文化的自省意识。对于流言背后所隐含的权力文化运作机制与国民的集体无意识,他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流言的杀人威力,但是鲁迅先生的书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正以一种自省的思考来建构他的叙述话语,不只是单纯地批判国民性,而是让国民在自我主体的缺失中重新拯救自我。
①卡普费雷著,郑若麟等译:《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②⑤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第81页。
③黄子平:《故事新编:时间与叙述》,《中国文化》1990年第1期,第125页。
④刘家鸣:《鲁迅:在流言伤害中挺立不屈——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6年版,第18-19页。
⑥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38页。
⑦李欧梵:《中西文学的徊想》,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版,第11-12页。
⑧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85页。
⑨薛毅:《无物之阵:语言游戏的迷宫——论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第43页。
⑩诺伊鲍尔著,顾牧译:《谣言女神》,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