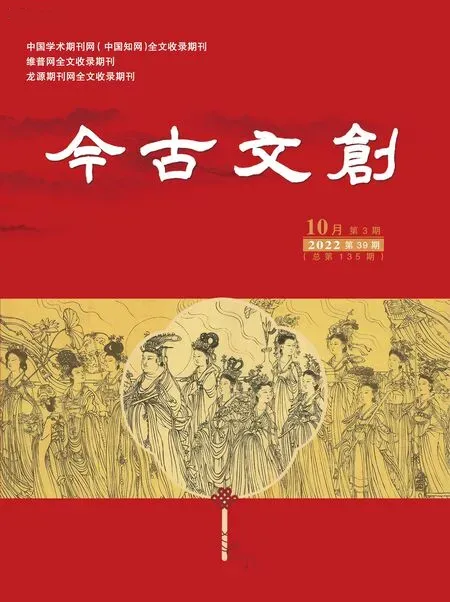盛世影像 : 唐传奇中的都城长安书写
◎王文婕
(中山大学 广东 广州 510275)
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长安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都城是最主要、最典型的国家形态,它既是象征权力中心的“都”,又是人们日常居住生活的“城”,是汇聚了物质与精神的多为载体。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的特殊地理空间,唐人传奇对都城长安多有书写。一方面这些传奇的作者大多为士人,一方面他们亦常常选择士子为主人公。“士子”这一特殊身份便于出于雅俗之间:他们既可以官运亨通,登上宫城中朝拜的大雅之堂。亦可不受拘束地频繁穿梭于外郭城的众多里坊。既仰望又感知长安,书写出长安的独特风貌。
因此,作为都城的长安,其个性如何生成,在文学视域中具有怎样的面貌与独特性。尤其是在真正意义上拥有自觉叙事的唐传奇如何塑造出历史中长安的都城形象?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有助于重新认识都城与文学的关系。
一、都城个性:长安格局中的盛世想象与市井风情
长安城按照宫城—皇城—外郭城顺序依次建造, 宫城与皇城一北一南,外郭城则以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不但一改“城郭”混居的旧制,于宫城之南专建皇城设置行政衙署, 并大大扩展外郭城面,明确各自界限与职能并形成了棋盘式的整齐格局。且不同于汉长安“皇城”的功能定位,唐长安外郭城的面积远大于皇宫城,其布局更以便利为前提,里坊内平民、官吏、显宦乃至皇亲国戚间杂居住,甚至官员在上朝路上可买蒸饼并之藏于帽底。长安是唐传奇创作的重要人文环境之一,其整饬规范又繁复多样的空间布局为传奇小说提供了纷繁多彩的生活素材,使其书写中显露出盛世想象与市井风俗的双重特征。
(一)皇城中的盛世想象
象征着皇权的宫城与皇城坐落于城内的中心位置,是长安的布局核心,所展现的王朝盛世气象令无数往来者在驻足时惊叹不已。卢照邻在长安大道上平视来往交通,骆宾王仰视巍峨的长安气派,王勃于高台登高俯视望帝乡之佳气,皆穷尽辞藻绘写皇宫之雄伟华丽,开启书写都城长安的先声。而以士人为创作主体的唐传奇,对长安雍容气象则较少直接描写。《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以皇宫宫闱之事作品重点在于旧事重述,而非皇城气派书写。其他作品中的“长安”多出现于梦中或比附神仙世界。如《周秦行纪》中牛僧孺梦中“至大殿,殿蔽以珠帘,有朱衣紫衣人数百立阶陛间”,《南柯太守传》中淳于棼见到了槐安国皇城之气派,“彩槛雕楹,华木珍果……几案茵褥,帘帏肴膳”,恢宏胜似宫城,《柳毅传》中描绘龙宫时“山有宫阙如人世……前列丝竹,后罗珠翠”,比附人世皇宫。可见唐传奇在塑造皇宫意象时,区别于诗赋写实化的铺陈,通过异空间的架构或想象使得其高置于人间之上,充满强烈的虚空感。且做梦之主角多为赶考或落榜之士子,他们难以触及真实的中心,只能在梦中勾勒皇宫面貌,想象着自身飞黄腾达。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倾注于长安的想象与神往之情,蕴含着追逐功名、渴望进入政治核心圈的理想抱负。
(二)外城中的市井风情
同时,长安作为城市也是人们的居住空间。外城郭汇聚着贵族与市民、本地与异邦人,是各个社会阶层共同分享的空间。如果说长安中心作为皇室核心区,是广大士子盛世想象的载体,那么外城郭则是众士子最熟悉活动空间。前文所举的初唐诗在盛世歌咏之中亦有市井风情的渗透,“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的狎妓风情,“歌屏朝掩翠,妆镜晚窥红”的青楼寻欢,初步凸显出长安在壮阔气象之外喧嚣繁华的市井风情。而唐传奇的大部分作者或多或少有过长安生活的经历,故有能力对长安城独特的管理制度与都市风貌的进行写实的细致描写,加强了长安在城市功能上的世俗化。
首先,长安作为都城,在外城郭的治安与管理上呈现出严谨而有序的特征。一方面是唐长安的都城治安,其中宫殿城门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城门的进出入审查尤其得到重视。唐传奇《无双传》中动乱发生时,仙客携带金银罗锦二十驮“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而无双一家却被拦截在启夏门。开远门是向西域出使或经商的起点,故人目混杂,往来人群密集,成为长安严密都城治安下的“盲点”,也无怪乎唐僖宗能在安史之乱中从此门顺利逃往骆谷。而启夏门位于城南,郊外有天坛圆丘及众多郊祀之坛,是众多郊祀的官员进出之处,故有严格的审查管理,刘氏一家难免受到门司阻拦。另一方面是城市街鼓制度,不仅标志着城门开启关闭和,是维护禁夜制度中的重要法律依据,完善长安坊市的管理。《任氏传》中二人欢度良宵后,任氏因姐妹“名系教坊,职属南衙”早一步离去,郑生想要返程,却因解除宵禁的街鼓声并未敲响,行至里门而“门扃未发”,不得不“憩其帘下,坐以候鼓。”《李娃传》中荥阳生与李娃相谈甚欢,而日暮时的“鼓声”意味着城门将关。本住于布政坊的荥阳生谎称自己住在“延平门外数里”,就是借助城内外的宵禁制度为自己的留宿创造机会。为了避免鸨母劝语中“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的后果,便顺理成章暂宿于此。因此,从唐传奇对城市治安与管理着意描摹中,可以看出外城生活区具体而翔实的制度设置,极贴近市民生活,加强了世俗化的特征。
其次,“城市既是一种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也是一种生活中心和活动中心”经济与商业的繁荣,长安的城市化进程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对内主要表现为商业景观的繁荣,各式经营行业层出不穷。《东城老父传》中天门街处设有鸡坊,《任氏传》中的郑生游入的西市衣肆亦在《两京新记》中有“市署前有大衣行”为证。《李娃传》中有“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的凶肆,《唐六典》中有关于葬业经营方式的记载。至旗亭南偏门所见的“坟典之肆”能“尽载而归”,可见书肆规模之大,《大唐新语》中徐文远之兄以书肆鬻书助力弟弟科举,《新唐书》中吕向“即市阅书,遂通古今”也反映了长安书肆众多的经济现象。以及《霍小玉传》中的寄附铺,《李娃传》中的典当铺,《三梦记》中西市帛肆的张氏女,都反映了长安商业景观的丰富种类。对外“世界首都”的地位体现在长安经济中时时出现的胡人经营者,《任氏传》中“门旁有胡人鬻饼”,《太平广记·原化记》中亦载有相关事件,以及《韦弇》《崔书生》《陆颙》数十篇等小说都有关于胡商识宝、寻宝、进行珠宝交易的描写,皆反映出唐帝国由于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对外域商人的强大吸引力。
小说中对长安城独特的管理制度与都市风貌的进行写实描写,不仅是作为单纯的背景介绍,体现长安小说强烈的地域色彩,更与情节安排、人物刻画联系在一起。如城门的管理制度引发了仙客与无双的分离、李娃与荥阳生的欢好,商业的繁荣为荥阳生的仕途发展、任氏郑生的偶遇、小玉对李益消息的寻觅等带来了机遇。小说人物在这长安外郭城中具体场景中演出无数的悲欢离合,以生动的故事饱满了喧嚣外城的立体感与世俗性。
因此,唐人小说一方面通过虚置的想象勾勒出长安的王朝气象与盛世想象,一方面以真实的笔触描摹出长安的城市风貌与世俗生活。这两种景观不仅并不矛盾,反而可以在双重并置中相互补充,塑造出统一王朝的都城气象——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辐射功能,是无数人的向往之地。兼有皇城与居住城市的两种角色身份,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一个繁华的长安气象。既是王权的象征,巍峨中充满着盛世之想象,又是市民的生存空间,具体生动中充斥着世俗喧嚣之音。
二、小说场景:里坊空间中长安个性的展开
作家在呈现地域性时,需要将小说情节在一定场景中展开,以物质空间作为矛盾与事件的空间载体。唐传奇的叙事以母体史传文学为基础,继承“言匪浮诡,事弗空诬”的传统,选择以真实空间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所。如新昌、平康、宣阳等长安里坊,以及坊间的东西市、干福寺以及曲江乐游原等场所,给人以历史般的真实感与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同时,场景是城市个性最集中的体现。同一场景的反复出现,不但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也通过空间次序与逻辑的安排推动小说叙事的产开。且真实的空间与情节相关联形成特定的空间隐喻性。其中唐人小说中士子的长安之旅往往在投宿空间与公共空间中切换,其中公共空间又以间杂于坊间的娱乐场所和寺庙道观为主。本文将通过考察这三种长安场景,从中探赜其与长安个性的对应关系。
(一)士子投宿空间:仕途理想与及时行乐
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长安城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并作为选拔与任命人才的枢纽,籍科举与铨选制度的展开掌握着官吏升迁与人事任免,牵动着士人的命运。“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望秋来,乌聚云和”,进京应举的举人与赴京参与等待拔萃之人从各地赶来,荟萃于长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投宿于何处。
据妹尾达彦统计,《太平广记》中街东为官僚街,以高官为主。街西则以商人和下层官员为多,呈现出“东贵西富”的特点,而士子的投宿空间恰恰呈现出这样的特征。
第一类是以乡贡进士、明经为主的应举团体,由于身份的不确定性在城市空间分化中多被置于街西。“家徒甚殷”的荥阳生赴京赶考时投宿于街西“布政坊”。布政坊位于西侧第三街从北向南第四坊,旅店较多且东邻皇城。向东仰望便可见“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的皇城气象。使得赶考士子们在焦灼等待中,更增一分对帝都的向往之情与金榜题名的热烈渴盼,加强了士子们的仕途想象。而巍峨的皇城是如此遥不可及,容易实现的世俗情感也就因此催生,故荥阳生横穿半个长安城来到了繁华的东市,此处的歌舞升平与美酒佳人令他完全忘却“一战而霸”的政治理想与居所东侧的气派皇城。其投宿之处由布政坊转移至鸣珂曲深处,意味着赶考的政治想象被风流情调与世俗享乐彻底掩埋。
第二类是赴京参与吏部、兵部铨选的人,以获得官职为目的。其身份较之未考中的士子更为明朗,拥有官运禄命的可能性较大,与官僚的接触也就更多,故此此类士子多集中投宿于街东官僚街。其中以“新昌坊”为典型,其处于高爽的乐游原区域,为高级官僚文士居住与娱乐的理想区域。且位于东市东南,左侧为城内交通干线,右侧紧邻通向城外的延兴门,邻近宫城及众多娱乐休闲区。它既紧邻繁华喧闹的闹市区,又是环境宜居的官僚权贵的聚集之地 ,双重特征隐喻着士子抒张政治抱负与排遣世俗娱乐情感的矛盾张力。居住于此的士人常常表现出迥别于政治理想的世俗情感。闲情者有之,如白居易《吾庐》《题新昌所居》等诗流露出享受生活的闲适情感。风流享乐者亦有之,《任氏传》韦崟与郑生欲“会饮”游宴之地即位于新昌里。《霍小玉传》中主角李益更是怀揣着积极进仕的政治理想投宿于新昌里。此时他须等“拔萃”登科后方能委任参军等官。所居处紧挨纸醉金迷的世俗享乐之地,于是等待中不甘寂寞的他,受空间影响被激起了“自矜风调”的才情,博求名妓的行为更是世俗情感压倒了理性的表现。李益与小玉在胜业坊欢好是政治理想实现过程中,必定会面临的纸醉金迷的世俗挑战。而当他以“书判拔萃登科时”,政治抱负彻底淹没世俗玩乐的身体快感,为跻身仕途他遵循了良贱不婚的社会约定并为迎娶高门女奔走,狠心负约。
可见,无论是赶考士子还是参与铨选者,他们赴京的投宿之处被放置在特殊的地理位置,或紧邻皇城,或毗邻风流渊薮区,这一特定的场景往往成为情节开始的契机,催化了政治抱负与世俗享乐之情的激烈碰撞。且唐代文士普遍存在行为与内心脱节的表现——唐朝注重诗赋,追求巧丽的科举之风助长了文人佻薄的性格,使得他们行为上不拘小节、崇尚风流。但在心理上,儒家仁义孝道、入仕忠君繁荣伦理道德标准仍是他们时刻铭记的人生价值取向。这样的矛盾心态与“投宿空间”的交叠成特定的隐喻性特征息息相关,并为后续的矛盾对峙埋下伏笔。因此,他们有的在皇城西侧因理想遥远而选择了眼下享乐,有的繁华坊西侧博求名妓并沉醉温柔乡,士子们都使得长安政治性与世俗性的个性张力得到强化。
(二)宴饮娱乐空间:世俗享乐与信息交流
充满仕途想象的士子投宿空间蕴含着与世俗享乐的张力,而升平欢愉、觥筹交错的北里享乐空间又因“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与密集的人口成为各种信息汇聚交流空间,政治性于其中潜藏涌动。
一方面,“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的平康坊三曲、“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崇仁坊与“四方珍奇,皆所集积”的东市联结成长安城盛极一时的繁华地带,使得男子的艳遇得以在喧嚣奢靡的场景中展开。李益在胜业坊与小玉日夜相从,荥阳生与李娃在平康坊情意甚笃,柳氏与韩翊于游筵中彼此倾心,凤帅家子寓居平康坊时梦美妓起舞作《阳春曲》等。这些在奢靡浮华的都市空间中编织出男女间的艳丽情事,无一不强化了长安的“世俗性”特征。
同时,都城中的世俗享乐中又无可避地成为信息交流的核心地带,间杂着交错的政治关系。平康坊中坐落着许多达官贵人的府邸。一街之隔的崇仁坊更是进京参与科举与选调的士子集中地,人口的稠密使得其成为重要的信息空间。首先,士人由于共同的政治利益或文学志趣往往形成固定的交友圈,常常在宴饮之际切磋创作,并因特定的立场将某种文学作品传播开来。《李娃传》《莺莺传》《长恨歌传》等诸多作品,皆是在长安宴游的觥筹交错间得以传播。且除了有一定政治色彩的集聚性文学创作外,宴饮游赏的政治性集中体现在籍聚会进行站队结党。《北里志》中载 “左谏王致君、右貂郑礼臣、夕拜孙文府、小天赵为山皆在席……互相造诣,互结朋党”可见赴京的句子通过行卷名人、请谒权贵等方式,在不断充实自己的根基,投靠站队便成了一种必然的分内之事。
可见,士子在风流渊薮之地沉浸于世俗享乐时,又无可避地受到长安政治性的渗透。士人们因相似的文学或政治倾向聚集于浮华的美酒佳筵中,自觉地开展政治社交活动,充分地在世俗性中彰显出属于帝国中心的政治特征。
(三)公共寺庙空间:宗教信仰与世俗游赏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表现为大量的设斋仪式与寺院兴建。统治者以大量钱财支持佛寺中供奉与祈福修活动,以此来保佑王朝的繁荣与稳定。长安里坊中建有大量的佛教寺院,如清禅寺、庄严寺,是佛教传播的核心。
而直接与皇权相关联的寺庙空间,由于在坊间分布密集,与民众生活接触频繁,又呈现出世俗化特征。除寺院外,道观的功能亦在泛化中与普通民众密切关联,成为世俗生活中的重要文化娱乐场所。最初高宗为母祈福所建的“大慈恩寺”成为俗讲俗戏的演出地点;皇室族戚为高宗献福而兴建的寺院“献福寺”,在《秀师言记》成为民众崔晤与李仁钧预测未来的算卦之地;为纪念功德深厚的楚金禅师所兴建的“千福寺”,在《任氏传》中成为刁将军女婢吹笙的“张乐之地”,和韦崟与友人在寒食节的艳遇之地;崇敬寺是高宗为安定公主迁葬和追福所立,却凭借“牡丹”成为踏春时节的赏游之处,《霍小玉传》中静居的李益一反常态地与同辈五六人至此赏玩牡丹花,闲步吟诗。间接反映了踏青季节居民便倾城出动,游寺院、访花圃和赏牡丹的盛况。“京城贵游……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其中崇敬寺牡丹尤为著名,白居易诗“应过唐昌玉蕊后,犹当崇敬牡丹时”亦对其大加赞赏。以及著名道观“唐昌观”凭借一丛玉蕊花成为“观者如堵”的市民游乐之地。
可见,唐代由统治阶级兴建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佛道寺观,在人口稠密、多个阶层共享的公共空间中,呈现出强烈的世俗化特征与居民游观活动的娱乐色彩。
三、都城的回响:长安的模糊与其他都城的显现
中国古代都城与文学间的双向建构,对我们认识都城形象与深刻理解文学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唐长安城的皇城宫城与外郭城层层环绕的格局,使文学中的长安书写呈现两个向度——在具有政治色彩的皇宫想象与世俗性的外城风情中,共同构成了丰满长安个性,并且作家真实的场景设置中得到集中体现。唐传奇中大量真实的长安里坊空间作为场景,其中士子投宿空间、宴饮娱乐空间、公共寺庙空间从不同的功能形态构成对长安个性的具现,构成某种特定的场景意义。唐传奇之前的志怪小说多之穷山恶水或异空间中展开,而拥有自觉叙事意识的唐传奇在都城视域中受到长安特色与帝国都城的感召影响,有意选择以其作为背景或书写对象,在长安里坊空间的聚焦性书写中展开了文学视域中长安形象重塑。反观后世延续长安背景进行改编的戏曲作品,如《霍小玉传》的同题戏曲《紫钗记》,在地域内容却上选择尚冠里、章台街等汉长安街道地名,与唐长安城的真实情况脱节。原因在于明朝与唐朝相隔数百年,都城地理位置变化,无法具备唐人当代书写“亲临现场”的写实之感。
且文学与都城的关系并非单项维度,长安城的格局影响着唐传奇的创作,且其一经完成,便以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身份影响着后世对长安城文化内涵的理解。其通过具体场景展开的都城个性书写成为后世都城书写不断模仿参照的范式,有着广泛回响,如宋元话本中关于东京与临安的双城书写,南宋遗民不断追忆着旧时的繁华都城,集中于金明池、樊楼、相国寺等场景书写出城市个性。明清小说中则通过南京与北京的书写展现出强烈的京都情结,不断回应着都城与文学间双向建构的意义关系。
①参见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之一有关“西京”的描述。
②③④⑧⑨⑩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1页,第85页,第63页,第170页,第43页,第101页。
⑤卢照邻:《长安古意》,载《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22页。
⑥王勃:《临高台》,载《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77页。
⑦关于唐五代小说作家在长安完成的作品数量,具体统计表格参见张同利:《长安与唐五代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⑪法国地理学家潘什美尔语,转引自梅新林、赵光育主编:《现代文化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⑫韦述著,陈子怡校正:《校正两京新记》,1936年版,第13页。
⑬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58-5759页。
⑭本文沿用刘勇强对“场景”的定义,区别于 “场所”,场景在指称人物活动或事件发生的环境上更为灵活,可超脱于单纯的空间维度,与一定的文化背景联系。
⑮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页。
⑯李世民:《帝京篇十首》,载《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页。
⑰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⑱⑲宋敏求:《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页,第291页。
⑳丁如明等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7页。
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㉒白居易:《自城东至以诗代书戏招李六拾遗崔二十六先辈》,《全唐诗》卷四三六,第10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