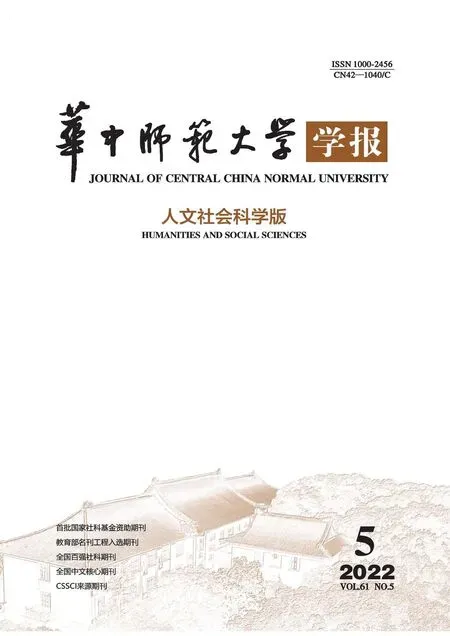成长型思维能有效提升青少年学业素养吗?
陈纯槿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上海 200062)
一、问题的提出
培养青少年成长型思维以增强其心理韧性和自适应能力并促使其心智系统更加健全完善,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提高青少年核心素养的重要策略和路径选择(1)参见OECD, Sky’s the Limit: Growth Mindset, Students, and Schools in PISA,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1.。成长型思维干预的随机实验和准实验研究随着脑科学与教育的融合发展而蔚然兴起,并逐渐延展到教育政策议题,以助力青少年尤其是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获得积极思维支持系统和更高的学业成就(2)参见A. Rattan, K. Savani, D. Chugh and C. S. Dweck, “Leveraging Mindsets to Promote Academic Achieveme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erspectives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10, no.6, 2015, pp.721-726.。然而,有关成长型思维干预有效性的科学证据仍相当模糊,而且已有的经验证据大多聚焦西方国家,来自中国的自然实验和准实验研究近乎阙如(3)参见V. F. Sisk, A. P. Burgoyne, J. Sun, et al., “To What Extent and under Which Circumstances Are Growth Mindsets Important to Academic Achievement? Two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29, no.4, 2018, pp.549-571.。与经合组织迥异的是,成长型思维对东亚地区青少年学业素养的影响大都未显现出强烈的正向效应(4)参见Z. Yan, R. B. King and J. Y. Haw, “Formative Assessment, Growth Mindset, and Achievement: Examining Their Relations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vol.28, no.5, 2021, pp.676-702.。在此背景下,探寻成长型思维干预无效的根源并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扎实推进中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极具现实意义。
从固定型思维向成长型思维转变能否实质性提升青少年学业素养,成为当前国际上广泛关注的热点议题,但相关研究结论仍颇具争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心理学领域一直在讨论成长型思维,因为它解释了为何一些学生在逆境中茁壮成长,而另一些学生则萎靡不振的情况(5)参见D. S. Yeager, P. Hanselman, G. M. Walton, et al., “A National Experiment Reveals Where a Growth Mindset Improves Achievement,” Nature, vol.573, 2019, pp.364-369.。卡罗尔·德韦克在界定成长型思维的开创性论著中指出,人们对于自己大脑的内隐信念——无论是将才智视为与生俱来的抑或是可以变化和成长的——对长期认知技能和社会情感发展都具有深刻影响(6)参见C. Dweck and D. Yeager, “Mindsets: A View from Two Era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14, no.3, 2019, pp.481-496.。早期的经验研究也表明,成长型思维可以显著预测与学习相关的重要结果。此类研究中被引用最广泛的布莱克威尔等人对青少年四期追踪调查表明,成长型思维与学生在数学、阅读等学业测验中更高的成就轨迹高度相关(7)参见L. Blackwell, K. Trzesniewski and C. Dweck,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Predict Achievement across an Adolescent Transi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and an Intervention,” Child Development, vol.78, no.1, 2007, pp.246-263.。从异质性角度看,克拉罗等人验证了成长型思维对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改善学业成就的助益更大(8)参见S. Claro, D. Paunesku and C. Dweck, “Growth Mindset Tempers the Effects of Poverty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13, no.31, 2016, pp.8664-8668.。施莱德等人综合了17份研究报告的45个效应量做进一步元分析发现,成长型思维既与挫折后的建设性应对、积极的失败归因密切相关,又与低学业焦虑、学习适应性心理等积极情绪有着显著关联(9)参见J. L. Schleider, M. R. Abel and J. R. Weisz, “Implicit Theories and You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 Random-Effects Meta-Analysi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vol.35, 2015, pp.1-9.。
然而,新近的实证研究未能真实重现成长型思维显著提升青少年学业素养的经验证据。在复刻了穆勒与德韦克的实验研究后发现,成长型思维与青少年对于学习目标的追求、将失败归因于努力抑或是失败后的坚持信念之间均无显著相关性(10)参见Y. Li and T. C. Bates, “You Can’t Change Your Basic Ability, But You Work at Things, and That’s How We Get Hard Things Done: Testing the Role of Growth Mindset on Response to Setback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Cognitive Abi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148, no.9, 2019, pp.1640-1655.。西斯克等人综合了273项研究近36.6万名学生样本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成长型思维对学生学业成就总体影响甚为微弱,其中一些研究甚至显示出成长型思维对学生学业素养存在负向效应(11)参见V. F. Sisk, A. P. Burgoyne, J. Sun, et al., “To What Extent and under Which Circumstances Are Growth Mindsets Important to Academic Achievement? Two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29, no.4, 2018, pp.549-571.。另一项纵向研究进一步表明,成长型思维仅对富裕家庭的学生学业成就有正向预测作用,对于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却不具有同等效应(12)参见R. B. King and J. E. Trinidad, “Growth Mindset Predicts Achievement Only among Rich Students: Examin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Mindse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vol.24, 2021, pp.635-652.。
来自中国的少量经验证据同样结论各异。新近研究表明,成长型思维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低龄学生的积极心理知觉和学业表现(13)参见刁春婷、周文倩、黄臻:《小学生成长型思维模式与学业成绩、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心理与行为研究》2020第4期。。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成长型思维的正向效应并未广泛地存在于东亚社会儒家文化圈中。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青少年群体具有成长型思维的比例偏低,且对学业素养的影响并未显现出强烈的正向效应(14)参见陈纯槿:《PISA 2018中国四省市学生阅读素养研究新发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5期。。造成上述发现相互矛盾的可能原因在于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成长型思维的干预效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且难以准确地识别成长型思维对青少年学业素养的因果效应(15)参见B. N. Macnamara and N. S. Rupan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Mindset,” Intelligence, vol.64, 2017, pp.52-69.。因为持有成长型思维或固定型思维的个体在特质、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学校文化环境等诸多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也同样影响着青少年的学业发展。
综观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大都忽视了处理组与控制组协变量的组间差异可能造成的自选择偏差,以致无法得到精确可靠的因果推断(16)参见G. M. Walton and D. S. Yeager, “Seed and Soil: Psychological Affordances in Contexts Help to Explain Where Wise Interventions Succeed or Fail,”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29, no.3, 2020, pp.219-226.。成长型思维干预效果的异质性讨论已逐步转移到何种环境下可以反复重现成长型思维干预有效的问题,但对于成长型思维在何种环境下更有助于促进青少年教育与心理发展亟需进一步循证探微。
鉴于已有经验研究的缺憾,本文利用准实验研究框架下的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Inverse-Probability-Weighted Regression Adjustment, 简称:IPWRA)来克服潜在的自选择偏差,并针对来自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的微观数据,细致地验证了成长型思维在不同成长环境下对青少年学业素养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故此,本文重点讨论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相较于固定型思维,持有成长型思维的青少年在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方面是否获得明显更高的收益?二是成长型思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来自不同成长环境下的青少年学业素养?在综合考虑上述问题以及潜在的自选择偏差后,本文基于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中国四省市学生测试数据进行检验。
二、数据说明和计量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经合组织2018年进行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简称PISA)。该项目旨在评估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以后所获得的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必要的关键知识和技能。PISA测试的目标人群为在校接受正规教育、年龄在15岁左右(15岁3个月至16岁2个月)的中学生,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限定在该年龄区间的青少年。抽样设计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方法从抽样框中选择学校,各学校被抽取的概率与该年龄段学生人数成正比;第二阶段从第一阶段选择的学校中随机选取学生,每个学生都有相同的被抽中概率。学业素养测试内容涵盖了阅读、数学及科学,且在每一轮测试中重点对其中一门学科进行精细化测验。为全面收集学生与学校层次信息,本研究以学校编码为匹配基准,采用一对多匹配方式与学生层次数据进行合并,构建多层信息精准匹配数据库,并从中选取我国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四省市共361所学校12058名学生测试数据进行分析。
(二)变量说明
1.结果变量
本文的结果变量是由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门学科组成的学业素养测试得分。PISA测评的阅读素养不再是主要从教科书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而是在单一文本和复合文本的多元情境下对数字文本进行信息定位与检索、整合与运用、评价与反思的能力。PISA测评的数学素养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数学”,而非“脱离生活的抽象数学”,也即为了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而激活其具有的数学知识和应用技能来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7)参见陆璟:《PISA测评的理论和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科学素养的评估重点则聚焦学生运用科学知识发现和分析问题,并科学地解释现象,以及针对相关问题和现象做出基于证据的科学判断的能力。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的综合测评内容,集中反映了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现代社会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在PISA测试数据库中,本文选取了由10个似真值组成的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测试得分来衡量总体的学业素养,并基于学生抽样权重进行了加权。
2.处理变量
本文的处理变量为受试者是否具有成长型思维的二元变量。支持成长型思维的增量理论假设能力、智力等品质具有可锻造性,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并得以持续发展。而支持固定型思维的实体理论假设智力和能力等内在品质是与生俱来的,且具有固定不变、不可控制的特质,这些特质即使经过后天努力也是无法改变的。与固定型思维不同,成长型思维遵循的是“才智可塑性”的基本逻辑(18)参见C. Dweck and D. Yeager, “Mindsets: A View from Two Era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14, no.3, 2019, pp.481-496.。根据成长型思维的基本内涵,本文认为以个人才智是否具有可塑性为依据可以区分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在PISA调查问卷中有测试题询问受试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说法:“你的智力是你难以大幅改变的”,选项包括“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四个选择。如果受试者回答“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表明受试者认为智力具有可塑性,可被视为具有成长型思维,赋值为1,反之则为固定型思维,赋值为0。该项测试题准确地捕捉到区分成长型思维与固定型思维的关键点,即“才智是否具有可塑性”这一核心问题,这是PISA衡量成长型思维的主要度量方式,而且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单项测量的有效性(19)参见OECD, Sky’s the Limit: Growth Mindset, Students, and Schools in PISA,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1.。
考虑到单项测量可能存在测量误差问题,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了多指标计量方法测量成长型思维。鉴于成长型思维的根本要义在于相信个人才能是可以改变的这一内隐信念,尤其是在面对困难、挫折乃至失败时仍然坚持改变和努力的成长信念,故而在前述指标的基础上本文又选择了另外四道测试题:“当遇到不擅长的事我会努力克服它,而不是转向我可能擅长的事”;“我在做事时得到的乐趣,部分来自于能突破自己过去的表现”;“当身处逆境时,我总是能找到出路”;“当我失败时,我会担心自己天分不足”。其中前三题为正向评分,而最后一道测试题为负向,对此本文采用反向计分方式将之转换为与其他三题作用方向一致的正向评分。
根据上述筛选的指标,本文采用K-均值聚类法(K-means cluster)进行聚类分析(20)参见C. H. Lee and D. G. Steigerwald, “Inference for Clustered Data,” Stata Journal, vol.18, 2018, pp.447-460.:首先确定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两个类别;然后确定各类别的初始中心,进而计算每个样本到中心点的欧氏距离,按照距离中心点最近的原则,将每个样本分派到各中心点所在的类中去,形成新的类别,再根据生成的类别计算每类中各变量的均值,并以均值作为新的聚类中心;最后重复上述步骤,直至达到指定的迭代次数或达到终止迭代的条件。本文还使用K-中位数聚类法计算各类中心点,结果与K-均值聚类基本一致且保持稳定,表明K-均值聚类结果是稳健的。
3.协变量
本文的协变量共分为三类:一是学生个体特征,包括学生性别、年级、自我教育期望、元认知策略、同伴竞争氛围以及努力信念。其中,性别和年级均界定为虚拟变量,自我教育期望分为高中及以下、大学专科及以上两类。元认知策略是控制、组织和评估认知的高级认知集合,是学业素养最具影响力的预测指标之一(21)参见B. Odell, M. Cutumisu and M. Gierl, “A Scoping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ICT and Performance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n the PISA Data,”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vol.23, 2020, pp.1449-1481.。元认知策略由受试者在从1(“完全没有用处”)到6(“非常有用”)的六点李克特量表上对特定阅读任务的策略有用性进行评分,涉及信息理解与记忆策略、信息概述策略和信息可信度评鉴策略(22)参见陈纯槿:《PISA 2018中国四省市学生阅读素养研究新发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5期。。同伴竞争氛围衡量的是同龄人在多大程度上相互竞争的风气,包含三道测试题:“学生崇尚竞争”;“学生之间相互竞争”;“学生似乎都觉得相互竞争是重要的”。努力信念是学生对在校学习重要性的感知和判断,基于以下三道题目测量:“在学校努力学习有助于我将来找份好工作”;“在学校努力学习有助于我将来考进好大学”;“在学校努力学习很重要”。本文根据受试者对上述测试题的响应情况逐项计分并进行主成分分析,进而计算得到标准化指数。信度检验显示,元认知策略、同伴竞争氛围和努力信念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77、0.83和0.76,说明上述量表具有良好信度。
二是家庭背景特征,包括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指数和父母情感支持。已有的经验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是影响青少年学业成就和教育发展最重要的先赋性因素(23)参见岳昌君、周丽萍:《家庭背景对我国重点高中入学机会的影响——基于2014年高等教育改革学生调查的实证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指数基于家庭财富、父母最高职业地位和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三个指标来衡量;父母情感通过受试者对“我父母支持我在学习上的努力和成绩”“当我在学校遇到困难时我父母会支持我”“我父母鼓励我要自信”这三道测试题的应答来衡量。对这三道题的回答情况进行逐项计分,之后分值被转化为以经合组织为参照系的标准化指数。
三是学校环境特征,包括教师适应性教学、学校性质以及学校地理位置。以学校地理位置为划分标准,倘若学校坐落在乡村,赋值为1,否则为0;以学校性质为划分标准,分为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两类,其中以中等职业学校为观测组。教师适应性教学通过四道测试题进行度量:“老师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当学生需要时老师会提供额外的帮助”;“老师帮助学生学习”;“老师会一直讲解直到学生理解为止”。信度检验表明,教师适应性教学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达到0.85,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已有研究表明,教师教学实践中采用适应性教学与学生成长型思维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因为因材施教的教师乐于助力学生形成积极的成就归因,并激发学生学习与发展的能动性(24)参见雷万鹏、李贞义:《教师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综合以上观测变量,从总体样本中剔除了相关变量的缺省值,最终得到11703个有效样本。本文将总体样本划分为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两个子样本并进行比较,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调查显示,我国四省市约有55.6%的学生表现出成长型思维,相较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明显低7个百分点。由表1中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对比结果可知,持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在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均值上明显低于持有固定型思维的学生,且上述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少年显现出成长型思维的倾向性不同,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比优势家庭的学生具有成长型思维的比例显著更高。此外,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在自我教育期望、元认知策略、同伴竞争氛围等方面均显著低于固定型思维的学生,但是在努力信念、父母情感支持以及教师适应性教学等方面均显著更高。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初步说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个体特征、家庭背景以及学校环境等诸多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有必要控制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初始条件使其尽可能相近,以消除潜在的自选择偏差。
(三)计量方法
为避免自选择偏差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了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调整后的加权回归系数来计算实际接受干预的事实结果,然后外推到具有相近倾向值的其他组群,为每个组群估测如果受试者接受干预可能出现的反事实结果(25)参见E. F. Halpern, “Behind the Numbers: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 Radiology, vol.271, no.3, 2014, pp.625-628.。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过程共分为三步:第一步,估计接受干预的概率预测模型参数并计算逆概率权重;第二步,利用估测的逆概率权重,拟合各个观察组的加权回归模型,并获得每个受试者的干预预测结果;第三步,计算干预预测结果的均值,得出处理组的事实结果与控制组的反事实结果,两组结果之差异提供了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值。相比于其他计量方法,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的最大优势在于结合了基于回归模型的估计与逆概率加权估计的双重稳健属性,从而极大地减少了变异性并显著提高了模型估计效率(26)参见X. Bai, A. A. Tsiatis and S. M. O’Brien, “Doubly-Robust Estimators of Treatment-Specific Survival Distributions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with Stratified Sampling,” Biometrics, vol.69, 2013, pp.830-839.。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的平衡性检验
使用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潜在的自选择偏差,以达到处理组和控制组初始条件近似平衡的准实验效果。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之后,若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初始条件的差异不再显著,也即协变量的分布是近乎一致的,则表示自选择偏差得到有效控制。为满足上述假设的前提条件,本文首先针对处理组与控制组协变量是否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进行了平衡性诊断,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所示的结果表明,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协变量的标准化差异相较于加权之前更接近于0,说明处理组与控制组初始条件的差异已不再显著;与此同时,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之后,协变量的方差比总体上更接近于1,上述这些结果一致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初始条件差异得到了有效控制。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后,样本整体上满足了协变量平衡性假设条件的要求,从而有效克服了自选择偏差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二)成长型思维对青少年学业素养的影响效应
由以上平衡性诊断结果可知,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后的样本已满足了条件独立分布假设。在此基础上,本文构造了成长型思维概率预测模型,以探查青少年具有成长型思维的倾向性,并分别以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测试得分作为结果变量进行逆概率加权估计,并计算得到成长型思维影响学生学业素养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值,估计结果见表3。
表3呈现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克服了自选择偏差之后,持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在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均值上相比固定型思维的学生分别显著低0.054、0.050、0.042个标准差,并且上述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成长型思维对青少年学业素养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却显现出与预期相反的负向效应。无论是对阅读、数学素养抑或是对科学素养,成长型思维均未产生有效的提升作用,反而显著降低了总体的学业素养。

表3 成长型思维对青少年学业素养的影响: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估计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学业素养不同分位点上,成长型思维影响程度及影响方向不尽相同。随着分位点的不断提高,成长型思维的影响效应整体呈现出由正向负的变动态势。具体来看,成长型思维对阅读素养的边际效应从10分位点的0.043个标准差,减至25分位点的-0.034个标准差,之后在50分位点降至-0.063个标准差,直至90分位点下降到最低。对比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的估计结果,其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最低点落在75分位点,但总体的变化趋势呈现一致性,即随着学业素养分位点的不断提高,成长型思维的负向影响逐渐趋于上升。
相较于固定型思维,持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在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的最低10分位点占据微弱优势,亦即对最低分位点的学业素养呈现出正向效应,但是在25分位点之后,成长型思维的影响方向发生了明显转折,而且在90分位点与10分位点上两者之间的差异极其显著,因此成长型思维的影响在学业素养不同分位点上存在异质性效应。
(三)成长型思维影响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上述发现未必适用于所有青少年群体,因为并非所有群体受到成长型思维的影响都是相同的,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不同环境下成长型思维影响效应的异质性问题。根据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元认知策略、同伴竞争氛围以及教师适应性教学等变量,以最高四分位和最低四分位进行分样本估计,分样本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成长型思维影响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分样本估计表明,成长型思维对在不同家庭背景下学生的学业素养存在异质性影响。如表4所示,成长型思维对家庭处境不利学生的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的影响均显著为负,但这种负向效应要明显低于处于优势家庭的学生,可见成长型思维的负向效应主要存在于处境有利家庭的组群中。对于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来说,成长型思维对其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56、-0.037和-0.051个标准差,且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成长型思维并未有效地提升家庭处境不利学生的学业素养,反而起到与预期相反的负向效应,可见,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未能在成长型思维的调节作用下获益更多。
从元认知维度来看,元认知策略较高的青少年群体中成长型思维的负向效应更大,而对于元认知策略较低的学生并无显著影响。在低效的元认知策略作用下,无论是成长型思维学生还是固定型思维学生,其学业素养均处于相似的低水平,然而当其使用的元认知策略不断提高时,成长型思维的边际效应转而趋于下降,说明成长型思维与学业素养之间的关系因其使用的元认知策略不同而出现了明显变化,元认知策略在两者之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就同伴竞争氛围而言,成长型思维对学生学业素养的影响仅在高竞争氛围下显著为负,而进入低竞争氛围则并无显著影响。从教师教学实践层面来看,无论是在最高分位点还是最低分位点实施适应性教学,成长型思维的影响皆为负向,且未因教师适应性教学方式不同而出现显著变化,可见,教师适应性教学在成长型思维与学生学业素养之间未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综上所述,成长型思维对青少年学业素养的影响因其家庭背景和元认知策略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为探查成长型思维的边际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局域效应,本文进一步比较了在不同家庭背景下成长型思维对学生学业素养各分位点的边际影响,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成长型思维对学生学业素养的异质性影响:分家庭背景
从图1左侧可以看出,对于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来说,成长型思维仅对最低分位点处学生的学业素养呈微弱的正向效应,系数约为0.286个标准差,且上述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进入25分位点之后,成长型思维的负向效应逐步显现,从25分位点的0.045到50分位点的-0.110,直至95分位点达到-0.231个标准差。这意味着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并未从成长型思维中获得显著更高的收益,只有在最低分位点处,成长型思维才显现出微弱的正向效应。
相较于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成长型思维对家庭处境有利学生的学业素养在各分位点上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伴随着分位点的不断提高,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结构(见图1右侧)。无论是在低分位点还是高分位点,成长型思维的负向效应都极为显著,且在35分位点处,这种负向效应最为突出,两者相差0.476个标准差,足见成长型思维整体上难以显著地提升家庭处境有利学生的学业素养。上述估计结果表明,成长型思维对青少年学业素养的影响在学业素养各分位点有着明显差异,而且因家庭背景不同而显现出异质性的特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前述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将单项测量指标的成长型思维,替换为多项指标测度的因变量。与前述的基准模型设定一致,本文根据家庭背景以及总体样本进行分位数回归。如表5所示,对于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而言,成长型思维仅在最低分位点具有微弱正向影响,其负向效应在90至95分位点更为突出;而对于家庭处境有利的学生来说,不管是在低分位点抑或是高分位点均显现为负向影响,且负向效应在20至50分位区间尤为凸显。总体样本中,成长型思维仅对10分位点的学业素养呈现正向效应,但紧随着分位点的不断提高,其负向效应逐步显现出来,直至75分位点处达到峰值。平均而言,成长型思维的影响系数仍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成长型思维对青少年学业素养难以起到直接的正向推动作用。扩展模型的实证结果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前述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
四、结论与讨论
成长型思维能否实质性提升青少年学业素养,这一议题引起了国际脑科学与教育学界的广泛关注,但迄今仍缺乏来自中国的自然实验或准实验研究的经验证据。本文利用准实验研究框架下的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在克服了自选择偏差之后,使用2018年PISA中国四省市学生测试数据,循证探查了成长型思维对学生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的影响,并检验上述影响在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异质性效应,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持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在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测试得分均值上相比固定型思维的学生显著更低。研究发现,在克服了潜在的自选择偏差后,无论是对阅读、数学素养还是对科学素养,成长型思维均未能带来预期的正向效应,甚至显著降低了总体的学业素养。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持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在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得分上分别为546.1、584.4和583.0分,相较于固定型思维的学生明显低21.2、16.3和17.3分;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和学校环境后,两者间差距依次缩减至9.2、6.0和6.3分;在矫正了自选择偏差的情况下,持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分别低0.054、0.050和0.042个标准差,且均具有统计上稳健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成长型思维干预不仅助益微小,甚至可能损害基础教育质量。所以大规模推广成长型思维干预之前,需要审慎评估其适用情境以及有效干预的必要条件,以避免陷入逆向成长的思维陷阱之中。
导致成长型思维对青少年学业素养呈显著负向效应的根源在于:其一,致使成长型思维干预无效的可能根源在于儒家社会文化情境下学生秉持的努力信念的“天花板效应”甚为凸显,且甚于成长型思维本身的影响。在参与PISA测试的78个经济体中,只有4个教育系统(其中包括我国四省市)显示成长型思维对学生学业素养均未有显著正向效应。为试图找出不同地区在成长型思维影响效应上的差异来源,本文基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28)参见G. Hofstede, G. J. Hofstede and M. Minkov,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New York: McGraw-Hill, 2010.,使用数据可及的74个经济体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成长型思维与个人主义维度呈正相关性(r=0.57),而与权力距离指数呈负相关性(r=-0.67),且上述关系均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成长型思维在不同地区的影响效应部分来源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其二,在中国异常激烈的学业竞争风潮下,努力信念的“天花板效应”更为凸显,这极大地削弱乃至扭转了成长型思维应有的作用。在社会竞争文化熏染下,借助成长型思维干预试图激励已经足够努力的学生不断强化成长信念,抑或促使原本高负荷状态下的青少年持续层层加码以延长学习时间,不仅难以有效地改善其学业表现,甚至可能起到与预期截然相反的负向效应(29)参见D. S. Yeager and C. S. Dweck,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Growth Mindset Controvers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75, no.9, 2020, pp.1269-1284.。
第二,持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更多地使用了低效的元认知策略。微观调查数据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在我国四省市学生样本中,持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在阅读理解与记忆策略、阅读概述策略以及阅读评鉴策略上的均值相比固定型思维的学生分别显著低0.082、0.063和0.149个标准差,且上述差异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机械化地使用低效的元认知策略致使持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在学习效率和学业质量上显著更低。
第三,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处于劣势的学生比优势家庭的学生更有可能发展出成长型思维。比较而言,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持有成长型思维的比例相较于优势家庭的学生显著更高。究其根源,由于家庭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匮乏,相对贫困的家庭环境更易于激发抗逆能力和心理韧性,走出困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更为强烈,故而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更有可能在逆境中发展出成长型思维。然而从另一维度来看,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在努力信念上却显著更低,说明持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未必具有更高水平的努力信念。
第四,成长型思维对最低分位点的学业素养显现出微弱的正向效应。究其根源,处于最低分位点的学生往往是接受成长型思维干预的主要对象,更有机会因改变思维而直接受益。但对于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来说,成长型思维未能起到持续而显著地助力其改善学业成就、缩小学业差距的“补差效应”,故而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未能在成长型思维的调节作用下受益更多。从教师教学实践层面来看,成长型思维对学生学业素养的影响并未因教师适应性教学方式不同而出现显著变化。成长型思维在不同环境下的干预效果并不一致,其可能的解释是成长型思维本质上是才智可形塑的内隐信念,其最大功能更多的是激发潜能和心理韧性的精神价值,而非旨在提高学业成就的工具价值。
上述发现蕴含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在于,倘若成长型思维对青少年学业素养的负向影响是既定事实,那么教育系统应该通过加强脑科学与教育宣传,引导家长和学生客观地审视对于才智可塑性的科学认识,特别是理性地看待成长型思维的真实效度。同时我们要重点关注不同群体、家庭和学校环境中成长型思维干预的异质性,避免过度放大成长心态在青少年教育与心理发展中的重要性。导致对成长型思维干预效果存疑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试图将成长心态及思维转换刻画成化解所有教育弊病的灵丹妙药,过度夸大“心态”因素而对于导致青少年发展差异的家庭社会经济“结构”因素却视而不见(30)参见R. B. King and J. E. Trinidad, “Growth Mindset Predicts Achievement Only among Rich Students: Examin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Mindse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vol.24, 2021, pp.635-652.。为了矫正上述偏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个体成长心态与其家庭社会经济结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这就迫切需要学校管理者建立一个与学生个体成长特征和家庭背景紧密结合的内生发展机制,以更好地了解成长型思维如何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的学生群体,并为学生发展和践行成长信念创造有利环境。
鉴于致使成长型思维呈负向效应的重要制约因素是青少年群体中努力信念日益显现出“天花板效应”,故而对于成长型思维的干预不宜简化为单纯地强化青少年的成长信念而忽视了成长的正确路向(31)参见D. S. Yeager, P. Hanselman, G. M. Walton, et al., “A National Experiment Reveals Where a Growth Mindset Improves Achievement,” Nature, vol.573, 2019, pp.364-369.。无条件地夸大成长型思维的精神价值可能会起到反向作用,让学生在实质上并未取得显著进展时盲目地相信自己的禀赋,以致陷入逆向成长的思维陷阱之中。尽管个人才智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独特个体都具有相同潜能。因此,提高成长型思维干预有效性的关键在于扎实推进重在增强和嵌入内源性发展能力而非脱离现实的外生驱动,尤为关键的是注重运用有效的元认知策略激发内隐潜能并遏制自我挫败感,这对于缓解青少年因深陷激烈的学业竞争带来的焦虑是大有裨益的。
——郑州市创新实验学校成长型课程体系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