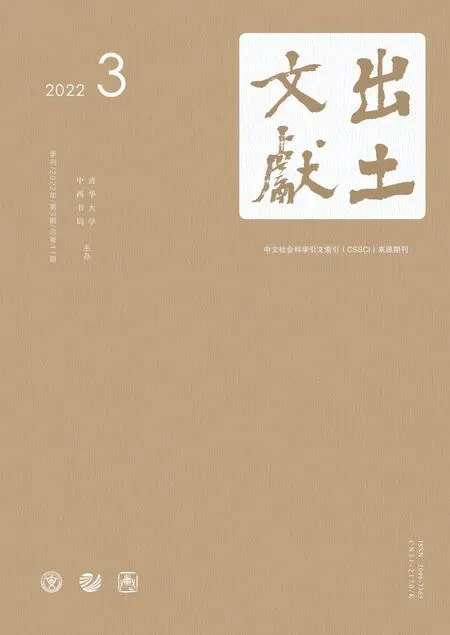都吏新解
单印飞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汉书·文帝纪》:“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律说,都吏今督邮是也。”(1)《汉书》卷四《文帝纪》,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114页。西北汉简中的都吏,多根据律说被解释为督邮的前身。(2)劳榦: 《居延汉简考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上册,1959年,第346页;陈槃: 《汉晋遗简识小七种》,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5年,第87页;陈梦家: 《汉简缀述》,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第121页;陈直: 《居延汉简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第187—188页。后来,秦至汉初的简牍中的都吏多被解释为二千石官(郡守)的直属官吏。(3)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76页。此外,亦有学者提出都吏是泛称,指“主管某项职能或承担某项使命的掾史”,(4)吴礽骧: 《说“都吏”》,《简牍学研究》第4辑,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9—225页。或指“大吏”,(5)刘军: 《两汉督邮新论》,《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或指“一郡之长吏”,(6)姜维公: 《汉代郡域监察体制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6期。或指“郡吏”。(7)黄今言: 《西汉“都吏”考略》,《简帛研究 二○一五(春夏卷)》,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0—111页。可见,都吏的性质仍有较大分歧。本文利用新出简牍材料,拟就都吏的性质再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里耶秦简8-461是一木方,内容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的正字形、正用字、正用语的汇编,(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里耶秦简(壹)》,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8页。关于此简的性质,可参见张春龙、龙京沙: 《湘西里耶秦简8-455号》,《简帛》第4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15页;胡平生: 《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性质刍议》,《简帛》第4辑,第17—25页;游逸飞: 《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选释》,《简帛》第6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7—104页;田炜: 《论秦始皇“书同文字”政策的内涵及影响——兼论判断出土秦文献文本年代的重要标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3分,2018年。其中有关于都吏的规定:
1. ……
郡邦尉为郡尉。
邦司马为郡司马。
乘传客为都吏。
大府为守□公。
毋曰邦门曰都门。
……
(8-461)
如是,都吏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前乘传客的改称。了解乘传客的性质有助于认识都吏的性质。
先秦文献中未曾出现乘传、乘传客,而乘驲、乘遽等辞例则较为常见。驲、遽与传意思相近。《尔雅·释言》:“驲、遽,传也。”(9)郭璞注,邢昺疏,王世伟整理: 《尔雅注疏》,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7页。《说文解字》马部“驲,传也”;辵部“遽,传也”;人部“传,遽也”。(10)段玉裁撰: 《说文解字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3年,第473、76、381页。注家多将驲、遽解释为传车。(11)《尔雅注疏》,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第4036页。所以,乘传应与乘驲、乘遽一样,指乘坐传车。
既名为乘传客,那么先将其理解为秦国乘坐传车者应无误。但是,从乘坐传车者的实例来看,并非所有的乘坐传车者均是乘传客。所以,乘传客与乘坐传车者的区别应在于“客”。
先秦时期“客”有使臣、使者的内涵。《国语·晋语》:“秦景公使其弟鍼来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员。’子朱曰:‘朱也当御。’叔向曰:‘肸也欲子员之对客也。’”(12)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 《国语集解》,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428页。“欲子员之对客”中的“客”指的就是秦景公的使者“鍼”。《国语·晋语》“郑简公使公孙成子来聘,平公有疾,韩宣子赞授客馆。客问君疾,对曰……”,(13)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 《国语集解》,第437页。子产作为郑简公的使者来到晋国,被安排在“客馆”,而且“客问君疾”中的“客”指的就是郑国使者子产。乘传客可能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类型,即乘坐传车的使者。秦汉时期的文献中频繁出现乘传,乘传者中确实有一部分群体的身份为使者。《汉官旧仪补遗》“奉玺书使者乘驰传”,(14)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 《汉官六种》,北京: 中华书局,1990年,第31页。即传递皇帝玺书的使者得以乘用驰传进行传递。这里的驰传是传车制度化后的第二等传车。(15)《汉书》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57页)根据传马的数量和速度将传车分为置传、驰传、乘传和轺传,四者等级依次降低。《汉旧仪补遗》“十月涸冻,二月解冻,皆祭祀。乘传车,称使者”,(16)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 《汉官六种》,第100页。即涸冻、解冻时,祭祀官员被皇帝任命为使者,而且得以乘坐传车前往祭祀。这是从制度层面显示出使者得以乘传。在具体实例中亦有展现,《史记·蒙恬列传》:“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17)《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8—2569页。这里的“使者”即乘传至代的曲宫。《汉书·王莽传》:“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18)《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第4158页。“乘传使者”亦直接地显示出这里乘传者的身份是使者。都吏是乘传客的改称,从下文所举的都吏实例中亦可以看到都吏的使者身份。所以,笔者认为乘传客(都吏)可能是指乘坐传车的使者。
然而,使者的群体仍较宽泛,凡是受某人委派为其代表或以其名义行事,皆可称为某人之使者。(19)廖伯源: 《使者与官制演变: 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北: 文津出版社,2006年,第1页。并非所有乘传使者都是都吏。那么,哪些人派遣的使者可以称都吏呢?
秦代,皇帝的使者可以称都吏。里耶秦简“从人”简中多次出现“都吏”一词,简文如下:

令且解(?)盗戒(械)。卅五年七月戊戌,御史大夫绾下将军,下令叚御史往行
(8-532+8-674+8-528)
(8-532+8-674+8-528背)(20)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173—174页。释文及句读参杨振红《秦“从人”简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合从”》,《文史哲》2020年第3期。
其中的“都吏治从人者”即负责处理“从人”事务的都吏。李洪财认为这里的都吏是地方官员,吴雪飞认为是御史大夫绾派出的假御史,(21)李洪财: 《秦简牍“从人”考》,《文物》2016年第12期;吴雪飞: 《〈岳麓简五〉所见“从人”考》,简帛网简帛论坛,2018年4月13日。二说不妥。《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中有数枚与“从人”有关的律文,学者们多认为其与这里的代地从人相关。(22)李洪财: 《秦简牍“从人”考》,《文物》2016年第12期;吴雪飞: 《〈岳麓简五〉所见“从人”考》,简帛网简帛论坛,2018年4月13日;杨振红: 《秦“从人”简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合从”》,《文史哲》2020年第3期。其中一条律文是“诸治从人者,具书未得者名族、年、长、物色、疵瑕,移讂县道,县道官谨以讂穷求,得辄以智巧谮(潜)讯”。(23)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45页。“都吏治从人者”应该属于律文中的“诸治从人者”。“诸治从人者”要将“未得者”的相关信息移送给县、道,由县、道进一步审讯、抓捕。可知,“都吏治从人者”至少不是县、道的地方官吏。除了代地从人外,岳麓秦简律文中还见齐从人、魏从人、荆从人、赵从人等。岳麓秦简整理者指出,“从人”都出自故六国,其身份特殊,级别较高,不是普通的伙同从犯,这种特殊的犯人应该是文献中所说的主张合纵抗秦之人。(24)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74页。杨振红先生亦指出,这些从人都是秦灭六国时参与过反秦斗争的旧六国人。(25)杨振红: 《秦“从人”简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合从”》,《文史哲》2020年第3期。可见,“从人”案件不是一郡、一县内发生的普通司法案件而是涉及国家安全、涉案人员非常广泛的特殊系列案件。所以,处理“从人”案件的官吏应该不会是郡县的地方官员。例如,岳麓秦简中在讨论将代从人、齐从人“论输”何处时,先是“假正夫”请论输“巴县盐”,后是“御史”请论输洞庭郡、苍梧郡。(26)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43—44页。整理者注释:“叚(假),代理。正,疑为廷尉正。夫,人名。”(27)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74页。从文意来看,整理者的意见可从。请论是重大案件或犯罪身份较高的场合,治狱官吏在作出判断后,需上请,向上级部门提出请论建议。(28)杨振红: 《秦“从人”简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合从”》,《文史哲》2020年第3期。假正夫“请论”、御史“请令夫论”说明该案是由廷尉一级的中央官员审理的,奏请流放地的廷尉正、御史均为中央官员而非地方官员。所以,将“治从人”的都吏理解为地方官员并不妥当。从简文来看,虽然“叚御史謷往行”与“下书都吏治从人者”之间的内容已经残缺,但是可以看出“下将军”“下令叚御史謷往行”“下书都吏治从人者”都是御史大夫绾的指示。如果假御史是都吏的话,御史大夫已经派“假御史謷往行”,就没有必要再说“下书都吏治从人者”。所以,都吏是假御史的观点亦显不妥。廖伯源先生曾指出,秦汉时期的普通司法事务由县令长、郡国守相、中央廷尉负责,但是对于某些特殊案件皇帝经常会派遣使者进行干预,比如使者奉诏调查案件、缉捕嫌犯、治狱、理囚、释囚、监护特殊犯人、诛杀等。(29)廖伯源: 《使者与官制演变: 秦汉皇帝使者考论》,第13—33页。“从人”案件是旧六国人参与的、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系列案件。简文的第一部分为皇帝的制诏内容,再结合“从人”案件的性质、简文内容,可知这里的都吏应该是皇帝派遣的专门案治代地“从人”事务的使者。
都吏作为皇帝使者的现象在秦律中亦有体现。例如《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其都吏及诸它吏所自受诏治而当先决论者,各令其治所县官以法决论之,乃以其奏夬(决)闻。”(30)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65页。这条律文中使用都吏一词,说明该条律文的时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史记》中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后改“命”为“制”,改“令”为“诏”。(31)《史记》卷五《秦始皇本纪》,第236页。那么,这条律文中“受诏治”的“诏”指的应该是皇帝的诏书。“都吏及诸它吏所自受诏治”透露出这里的都吏是奉皇帝的诏书在执行某事。所以,这里的都吏也是皇帝的使者。
秦代,执法的使者亦可以称都吏。岳麓秦简中有以下简文:
3. □□坐一□,丞、令、令史、官啬夫吏主者夺爵各一级,无爵者以(?)官为新地吏四岁,执法令都吏循行案举不如令者,论之,而上夺爵者名丞相,丞相上御史。(32)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187页。
4. 亡不仁邑里、官,毋以智(知)何人殹(也),中县道官诣咸阳,郡县道诣其郡都县……咸阳及郡都县恒以计时上不仁邑里及官者数狱属所执法,县道官别之,且令都吏时覆治之,以论失者,覆治之而即言请(情)者,以自出律论之。(33)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46—48页。
例3中,执法派遣都吏巡行案举违令者并进行论处,最后将夺爵者姓名上报给丞相,丞相上报给御史大夫。例4中,如果遇到不知原籍及所属官署的逃亡者,中县道官将其送至咸阳,郡县道官将其送至郡都县,咸阳和郡都县在上计时将这类逃亡者的名数、卷宗上报给所属的执法,所属执法派都吏进行覆治,论处错判者。可见,秦代都吏的派遣者也可以是执法。关于执法,彭浩先生认为,在中央政府是和御史、丞相并列的官署;在郡或和监郡御史相似,独立于郡府;执法机构似未再向下延伸至县级。(34)彭浩: 《谈〈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的“执法”》,《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6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92—94页。亦可参见土口史记著,何东译《岳麓秦简“执法”考》,《法律史译评》第6卷,上海: 中西书局,2018年,第50—72页;王四维: 《秦郡“执法”考——兼论秦郡制的发展》,《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曹旅宁: 《说岳麓秦简(伍)中的执法》,简帛网简帛论坛,2019年1月26日。例3中执法要将夺爵者姓名上报给丞相,丞相上报给御史大夫,从文书传递流程来看,这里的执法或为中央执法。例4中郡都县要将“不仁邑里及官者”的名数、卷宗上报给所属的执法即郡执法。所以,无论是中央执法还是郡执法均可派遣都吏案举、覆治相关案件。
西汉初期史料中都吏的派遣者多为二千石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二年律令·具律》:“气(乞)鞫者各辞在所县道,县道官令、长、丞谨听,书其气(乞)鞫,上狱属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及郡各移旁近郡,御史、丞相所覆治移廷。”(35)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139页。关于这里的二千石官具体所指,学界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最初,学者们认为是指郡守,例如彭浩等先生在解释都吏时注为“都吏乃二千石官(郡守)的直属官吏”,(36)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140页。程政举、土口史记等先生亦将其解释为郡守。(37)程政举: 《张家山汉墓竹简反映的乞鞫制度》,《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土口史记: 《岳麓秦简“执法”考》,何东译,《法律史译评》第6卷,第64页。后来,郭洪伯提出这里的二千石官指的是郡守府和廷尉府,前者是针对外地属县而言的,后者是针对京师属县而言的。(38)郭洪伯: 《“郡守为廷”——秦汉时期的司法体系》,第八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论文,2012年。游逸飞同样指出郡下辖县道官上呈的乞鞫案件由郡守覆审,内史下辖县道官上呈的乞鞫案件由廷尉覆审。同时,他还提出不宜完全排除郡尉覆审乞鞫案件的可能性。(39)游逸飞: 《战国至汉初的郡制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2014年。也就是说,他认为这里的二千石官不仅包括廷尉、郡守,可能还包括郡尉。近来,杨振红先生在解读此简时指出,复审乞鞫案件的中央机构中除了廷尉府外,还包括御史大夫府等二千石府。(40)杨振红、王安宇: 《秦汉诉讼制度中的“覆”及相关问题》,《史学月刊》2017年第12期。由此知道,汉初都吏的派遣者也可以是御史大夫、廷尉、郡守、郡尉(?)等二千石官。
在西汉中后期的西北汉简中,仍有二千石派遣都吏的文例。例如“甘露二年五月己丑朔甲辰朔,丞相少史充、御史守少史仁以请,诏有逐验大逆无道故广陵王胥御者惠同产弟,故长公主盖卿大婢外人,移郡大守……书到,二千石遣毋害都吏严教属县官令以下……”,(41)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 《肩水金关汉简(一)》,上海: 中西书局,2011年,下册,第1页。句读参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居延新简释粹》,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9—100页。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二千石与秦至汉初的二千石已经有所不同。二千石在汉文帝时分为了中二千石和二千石上下两个秩级。(42)杨振红: 《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一》,《文史哲》2008年第5期。所以,西汉中后期的都吏派遣者即便称二千石,也应将其与秦至汉初的二千石区别开来。从文意来看,该简中的二千石指的是郡太守。西北汉简中都吏的派遣者更为常见的是郡太守,例如“永光元年六月丙申朔,甲渠鄣候喜敢言之。府移大守府都吏书曰……”“毋得贳卖衣财物大守不遣都吏循行……”,(43)商志、李均明: 《商承祚先生藏居延汉简》,《文物》1992年第9期;简牍整理小组编: 《居延汉简(叁)》,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6年,第7页。其中的“大守府都吏”“大守不遣都吏”皆显示出西汉中后期的都吏派遣者可以是郡太守。(44)西北汉简中的“都吏”主要出现在西汉中后期,东汉很少出现,所以后一例无纪年简可能也是西汉中后期的简牍。
此外,在西北汉简中还出现护羌都吏、监领悬泉置都吏(监置都吏)、五官都吏、察事都吏等辞例。(45)胡平生、张德芳编撰: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吴礽骧《说“都吏”》,《简牍学研究》第4辑,第221、222页;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 《悬泉汉简(壹)》,上海: 中西书局,2019年,第144页。关于护羌都吏,胡平生、张德芳先生认为是护羌校尉派遣之巡行官员,(46)胡平生、张德芳编撰: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60页。此说可从。《汉官仪》:“护羌校尉,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节,以护西羌。”(47)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 《汉官六种》,第154页。护羌校尉的具体设置时间主要有武帝元鼎六年说、宣帝神爵二年说,(48)参见丁树芳: 《两汉护羌校尉研究评述》,《南都学坛》2014年第2期。目前尚难以定论。护羌都吏的出现时间自然在此之后。由此可知,西汉中后期的比二千石护羌校尉亦可是都吏的派遣者。监领悬泉置都吏可省称为监置都吏,是敦煌郡太守府派遣至悬泉置的都吏。五官都吏、察事都吏的资料较少,目前难以确定其派遣者。
总之,目前的材料显示,都吏的派遣者有秦代的皇帝、中央执法、郡执法,西汉初期的御史大夫、廷尉、郡守、郡尉(?),西汉中后期的郡太守、护羌校尉等。派遣者中除了皇帝之外主要是二千石(含比二千石)的高官。
至此,我们对秦汉时期的都吏有了新的认识。首先,它源自秦统一,是秦国乘传客的改称。其次,它既非一个具体官吏,亦非大吏、长吏、郡吏,而是一种泛称,指乘坐传车的使者,派遣者主要是皇帝和二千石(含比二千石)的高官。当然,这是基于目前所能见到的都吏的相关材料所得,至于乘传客在改称都吏时其内涵是否发生了细微变化,都吏的派遣者在不同时期是否发生变化等问题,有待新材料的补充论证。
附记:本文初稿蒙杨振红、蔡万进先生审阅教正,秦史青年学者论坛与会师友、匿名评审专家亦惠赐宝贵意见,谨致谢忱!唯文中疏失,皆为本人之责。待刊期间,梁鹤先生《秦代“都吏”研究——从里耶秦简8-461“乘传客”谈起》一文发表于《简帛研究二○二一(秋冬卷)》(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侧重点与拙文不同,请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