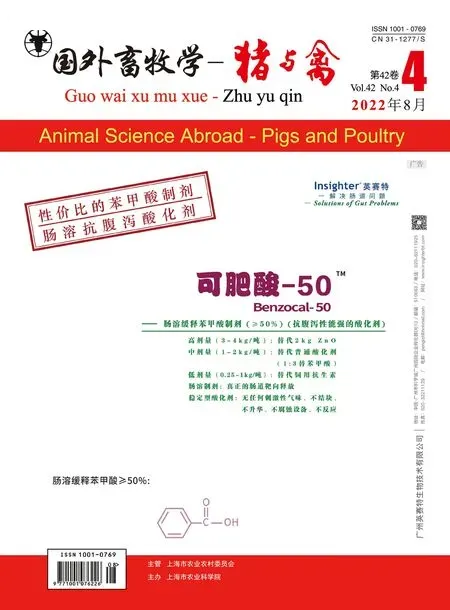非洲猪瘟的临床症状、病理形态学病变和流行病学
林子怡 译自,Vol.287(2020),10月
范美红 校 李红 审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一种病毒性、出血性疾病,对家猪和欧亚野猪具有极高的致死率。2007 年,起源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森林循环(sylvatic cycle)中的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 传入格鲁吉亚,随后跨高加索地区侵入俄罗斯,2014 年传入欧盟,2018 年8 月传入世界生猪生产大国——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中,ASF 的传播范围空前绝后,目前的大流行已经影响到了许多毫不相关的行业,不仅肝素以及用于食品和糖果生产的明胶的供应受到了影响,而且动物的脂肪、皮和毛的利用也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根据现有的数据,特别是在过去5 年中获得的知识,阐述了非洲猪瘟的临床症状、病理形态学病变和流行病学,并就主要的知识空白进行归纳和总结。
1 非洲猪瘟的临床症状、病理形态学病变
1.1 易感宿主的临床症状
ASF 造成的临床症状变化很大,取决于毒株的毒力、感染猪的年龄及其所处的免疫状态。发病猪除了会出现类似于出血热的急性型症状外,还可能会出现慢性型和亚临床型症状。
欧洲(除撒丁岛外) 和亚洲的ASFV 致病毒株属于基因Ⅱ型,两者高度相关,该毒株在实验条件下对家猪和欧洲野猪都表现出高致病性。高致病性ASFV 毒株会引起急性或亚急性临床症状,感染后7~10 d 内的死亡率达100%。临床症状通常呈非特异性,包括高热、厌食、呼吸道和胃肠道症状、发绀、共济失调,以及急性死亡。妊娠母猪会因为病情危重和高热而流产。少数发病猪会出现出血症状。实验感染的猪临床症状见图1(家猪) 和图2(野猪)。最近两篇论文对这些实验性研究进行了综述和总结。

图1 家猪感染高致病性ASFV 毒株后的临床症状

图2 野猪感染ASFV 后的临床症状
中等毒力的ASFV 毒株会使感染猪出现急性临床症状,如高热、厌食、疲乏和非特异性呼吸道和胃肠道症状,妊娠母猪出现流产,死亡率为30%~70%。低毒力的ASFV 毒株会使感染猪出现亚临床症状,病程发展缓慢,无特异性临床症状,死亡率低。7~10 d 后发病猪会产生抗体,但无法根据这些抗体预测疾病的结果,抗体也不能完全中和病毒。
1.2 病理形态学病变
病理解剖的结果取决于疾病的病程,同时反映了上述临床表现的差异性。在感染欧亚ASFV 毒株的发病猪上观察到的病理变化中,发病猪的肝脏和胃部淋巴结出血性肿大,脾出现不同程度的肿大。此外,肾脏、膀胱和胃壁有出血点,肺水肿,胃发生出血性胃炎。有时仅观察到少数淋巴结出血,这种情况也不是太罕见。为了协调发病机制研究和疫苗试验的病理调查,Galindo-Cardiel 等开发了一个评分系统,可以使这些试验更具可比性。
差距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影响ASFV 相关疾病结局和病程的因素仍知之甚少,研究应围绕宿主出现的主要有益和有害的反应。
○必须对有争议的幸存者和病毒携带者在ASFV 流行病学中的潜在作用进行更详细地研究。
○改进临床和病理评分方案,使用最先进的诊断技术,将对比较发病机制和疫苗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应为家猪和野猪开发一个统一的标准ASFV 攻毒模型。
2 现状和流行病学
2.1 现状
当ASF 于2007 年传入格鲁吉亚,随后又传入高加索地区进入俄罗斯时,外来疾病成为欧盟养猪业和野猪种群切实的威胁。如今,多个欧洲国家受到影响,ASFV 已蔓延到亚洲,自2018 年秋季以来,该病毒在亚洲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除欧盟的比利时、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的猪群正在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外,乌克兰、摩尔多瓦和俄罗斯仍然报告有疫情发生。到2020 年4月初,中国、朝鲜、韩国、老挝、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印度均报告发生了ASF。
2.2 流行病学
ASFV 的宿主范围非常狭窄,野猪是其唯一的脊椎动物宿主,钝缘蜱属的软蜱是其唯一的节肢动物媒介。ASF 无人畜共患的可能性,也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不太可能出现人畜共患病演变的原因包括:DNA聚合酶和病毒编码的碱基切除DNA 修复系统的精确校正导致病毒基因的突变率较低,同时缺乏可能的重组伙伴(在野猪和家猪中没有已知的病毒可与ASFV 重组)。
ASF 起源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疾病在疣猪和钝缘蜱属软蜱之间以古老的森林循环方式传播,使ASFV 成为唯一由节肢动物传播 (arthropod-borne,ARBO)的ASFV 的DNA 病毒。这种循环在疣猪环节不会引发明显的疾病或死亡,因此会被忽视。其他非洲野猪(特别是丛林猪种) 也表现出对ASFV 的抵抗力。然而,任何通过蜱虫或寄生虫传入家猪的疾病都会引发上文撰述的严重的多系统疾病和极高的死亡率。软蜱的另一个种群[游走鸟壁虱(Ornithodoros erraticus)]导致了非洲猪瘟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暴发。对于目前非洲猪瘟在全球的暴发,蜱虫的参与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然而,随着新发病国家的出现和新栖息地中蜱虫物种的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ASFV 一旦传入家猪群,不需要借助节肢动物就能够在猪群或猪场间传播。ASFV 可通过感染猪和易感猪之间的直接接触,以及与被污染的物体或饲料的间接接触进行传播。被污染的猪肉(泔水饲喂)和被用作蛋白质来源的猪血液制品,在非洲猪瘟的传播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受污染的衣服、卡车和兽医设备(特别是疫苗接种枪和类似的器具)等可能会成为健康猪的感染源。在野猪的栖息地,病死猪的尸体是猪持续感染ASFV 至关重要的因素。此外,持续感染的带毒猪已被认为是ASFV 在猪群、猪场或地区中持续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疫情流行的情况下。这种持续感染的猪在疾病长期传播中的作用仍存在争论。围绕ASFV“持续性存在”的一些争议可能是一个定义问题。Petrov 等指出,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存活的猪身上检测到ASFV,特别是病毒基因组。在没有真正的中和抗体的情况下,大约60~70 d 内仍然可以从存活的猪上分离出ASFV。病毒基因组可检测到的时间甚至更长(大约100 d)。然而,根据现场经验和长期研究来看,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携带者在ASF 的传播或流行中发挥了主要作用。Nurmoja 等和Petrov 等指出:a) 非洲猪瘟病毒没有传播给哨兵猪,b) 没有在超过100 d的幸存猪体内检测到非洲猪瘟病毒。
对于监测行动,应该明确界定不同类别的猪(目前数据库未区分病原体和抗体的检测)。病原体检测方法呈阳性的猪应被视为感染早期的猪(根据实验数据,这个阶段应该是介于感染后第3 天到第10 天之间)。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猪可以传播ASFV。同时检测到病毒和抗体的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排毒和传播病毒的可能性。从感染后的第7 天到第10 天,再到感染后的近100 d,感染猪会出现这种行为。由于无法根据抗体明确预测疾病的进程,这些猪仍可能会因ASF 而死亡,但它们至少已经存活了一周或更长的时间。最后一类猪是只能检测到抗体的猪。这些猪是真正的长期存活者,不应被称为ASFV 的持续感染者,因为在相关样本中没有检测到ASFV。这些猪很可能受到了免疫保护,不会再感染,因此非常安全,但不能排除在其淋巴组织的某个地方仍然存在ASFV 的几个基因组拷贝。鉴于口服感染通常需要相当高的剂量,即10 000 个血红素吸附量(heamadsorbing units),这种猪的影响应该很低。然而,免疫力的持续时间和潜在的重新激活情况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虽然非常清楚软蜱对目前ASF 的流行没有起到主要的作用(至少到目前为止),但包括食腐肉的食肉动物、鸟类和吸血性节肢动物在内的机械性媒介在ASFV 的传播上所起的作用也有争议。目前还没有关于食肉动物和鸟类在ASFV 传播上所起作用的详细研究,但鉴于ASFV 无法在胃肠道的条件下存活,这些动物不应被认为是ASFV 的宿主。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它们在ASFV 机械性传播上的作用,但在评估了猎物射线摄影机收集到的视频数据后,可以认为这些动物是导致ASFV 传播的一个很小的风险因素。鉴于在多个国家观察到了ASF在夏季出现发病高峰,节肢动物成为ASFV 流行病学调查的重点。波罗的海地区野猪感染ASF,研究人员收集了苍蝇、虻科昆虫、蚊子和硬蜱。结果发现,在这些动物中没有检测到病毒基因组(未发表的结果)。在实验条件下,尚未有任何迹象表明,蜻蜓幼虫在ASFV 的传播上会发挥主要作用。其他研究发现,猪摄入蜱虫和厩螯蝇后会感染ASF。确切地说,这些研究表明高度污染的物体可以是感染源,这并不奇怪。其他任何物体的表面,如棉球,都可能会起到同样的效果,除了软蜱外,并没有表现出特定节肢动物物种的特殊载体功能。厩螯蝇本身与ASF 的研究有关,因为只有这种苍蝇在多年前被证明在一定时期内携带传染性病毒,并可以机械传播病毒。这种叮人苍蝇的喙足够大,可以暂时储存足够数量的血液用于感染(对于肠外感染,至少需要0.13 个半数血红素吸附单位)。对ASF 而言,相关时间为24 h。然而,厩螯蝇通常不会远距离飞行。Herm等在来自受感染猪舍中的节肢动物上检测到了ASFV 基因组。研究认为,节肢动物在疾病跨猪舍或跨地区传播上所起的作用似乎相当有限。然而,在同一家猪场的一个猪栏或猪圈内,或一个较小的受影响区域内,不能排除它们在ASFV 传播上的作用。
为了了解不同传播周期的疾病动态,需要详细了解行为者和传播链。这对家猪的生产周期来说尤其重要,由于饲养方式多变,目前还没有适合所有情况的方案。Dixon 等最近详细论述了ASF 的流行病学和控制。以下部分章节采用了其中讨论的一些要点。
在缺乏疫苗的情况下,生物安全是防止ASFV 传入和传播的关键。不幸的是,往往不能确定ASFV 的传播路径。这导致人们形成了一种错误的看法,即生物安全终究没有起到作用,没有必要改变养猪生产的习惯。良好的沟通策略是有效预防ASF 所必需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这样一个事实:ASFV 在环境中以及猪肉产品中持续存在很长时间,即使经过更长的时间,它仍然会给猪群健康构成风险。不幸的是,一切并非黑白分明,许多传播途径只有通过高频率的接触才会变得重要。这些事实使人们无法进行精准的预测。
社会经济因素对ASF 的预防也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上仍有许多地方采用小规模的养猪生产方式,通常自产自用。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安全性较低,通常采用泔水饲喂。世界粮食与农业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已经起草了在这些情况下如何减少疾病风险的手册,控制战略应为传统的养殖业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养猪业生物安全规范,http://www.fao.org/3/a-i1435e.pdf;非洲猪瘟应急计划的准备,http://www.fao.org/3/a-i1196e.pdf)。
差距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必须进一步研究机械媒介在ASFV 传播上的潜在作用,如节肢动物、鸟类和食肉动物等。
○需要进一步详细研究各种环境因素对ASFV 在野猪栖息地流行所起的作用。
○对ASFV 幸存者和潜在带毒者在ASF 流行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免疫力的持续时间和母源性抗体的持续时间都没有充分研究。
○有必要继续进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以监测圈养猪群、野猪群以及软蜱,从而了解ASFV 和相关病毒的系统发育和进化。
原题名:African swine fever-A review of current knowledge(英文)
原作者:Sandra Blome、Kati Franzke和Martin Be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