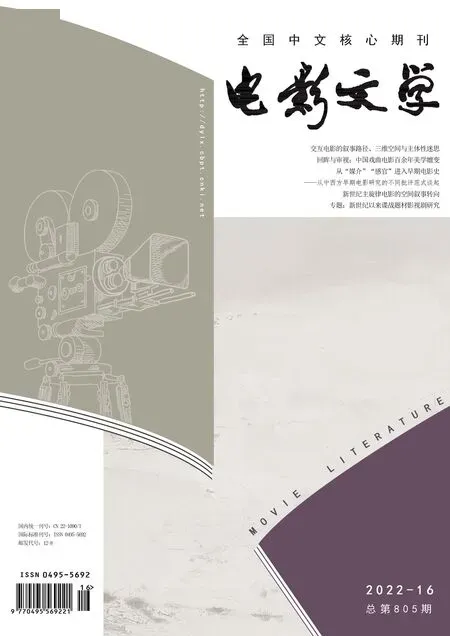融戏入影:《柳浪闻莺》的叙事伦理透视
袁智忠 司金冉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中国电影自诞生起就不断从戏曲中汲取养分,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便是对戏曲的电影化搬演,碍于彼时电影观念、电影技术等因素制约,戏曲与电影的融合还较为生硬,仅限于对舞台戏曲表演的“记录”。此后出现的诸如《生死恨》《墙头马上》《穆桂英挂帅》等影片突破了舞台限制,将部分戏曲场景实地化,加入了电影制作者的主观意图和艺术构想,但仍以戏曲为主导,本质上仍是对戏曲的搬演。电影并非只是传播戏曲的载体和工具,《霸王别姬》《人·鬼·情》《夜奔》以及《柳浪闻莺》等影片为戏曲与电影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戏曲从“绝对主角”演化为电影的一部分,戏曲的情节、人物、音乐、脸谱、程式不仅存在于戏曲文本内,更在整个电影文本内有了更复杂的意蕴与功能。
电影《柳浪闻莺》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江南水乡,这里是越剧的诞生地,越剧以表现抒情性的才子佳人故事为长,《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探》《五女拜寿》都是越剧的代表剧目。与《霸王别姬》《人·鬼·情》等影片分别将京剧《霸王别姬》、河北梆子戏《钟馗嫁妹》作为互文本相似,《柳浪闻莺》同样选取了经典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作为互文本,台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恨情仇映照着生活中垂髫、银心、工欲善等人复杂的情感纠葛,台上台下、戏中戏外,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柳浪闻莺》的叙事伦理都极为复杂和耐人寻味。从伦理角度看,“叙事伦理”这一模式研究的核心特征就是“讲故事的策略”和抽象的伦理思考的结合,换言之,即只有将道德意图和叙事方式结合起来考察,才可视为完整的叙事伦理研究。在叙事方式上,《柳浪闻莺》将戏与影融为一体,电影中的角色还要扮演戏曲中的演员,双重身份、双重情感彼此交杂、互为指涉;在道德意图上,两女一男的情感多重叠印,在情感与理性的博弈下影片人物走向了表面的“和”与深层的遗憾,影片则在“中和之美”的指引下避免了对人物的道德审判和“大团圆”式的俗套结局;在发展方向上,戏曲元素在电影中的灵活运用昭示着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和本土化色彩更加浓厚,为实现电影叙事伦理民族化提供了本民族的伦理精神和民族品格支撑。
一、戏影交融:双重身份与情感的相互映照
数千年来,糅合悲情与浪漫的梁祝传说被各种文学作品、各类剧种曲目改编,电影诞生后也得以接连不断地呈现于银幕。与“白蛇传”“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爱情传说一样,“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早已在历代中国人之间实现了“饱和传播”,无论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还是目不识丁的山野村夫都对其耳熟能详。长于抒情传意的越剧更是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演绎得婉转悠长,可歌可泣。单就“梁祝”二人的爱情传说来看,祝英台女扮男装到杭城求学,与同窗三载的梁山伯情谊深厚,芳心暗许梁山伯,而梁山伯却对其女儿身一无所知,获知祝英台女性身份后,急忙赶往祝家庄以求与祝英台结成连理。不少评论家认为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情感转化可能涉及同性之恋,实则不然,如果以纵览全局的目光再审视梁祝故事,就不难发现梁山伯既对以男性身份出现的祝英台爱护有加,也未因得知其女儿身而改变心意。足可见,两人既非传统的异性恋,也非评论家所说的同性之恋,而是超越了性别与俗世的纯粹情感。
如果说“梁祝”只涉及祝英台一人的性别流变,那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则更为复杂,除了祝英台隐瞒女儿身以男性身份在书院求学这一文本内的硬设定外,越剧中扮演梁山伯的演员并非现实生活中的男性,女小生的行当增加了性别流变的复杂程度,越剧中的梁祝故事变成了戏里戏外两个女扮男装的女性的故事。基于对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体味电影《柳浪闻莺》中人物的情感纠葛。戏台下,银心和垂髫自少女时期便一起学戏,银心胆小怯懦,垂髫英气无畏,两人一柔一刚,形影不离;戏台上,银心是满怀柔情、芳心暗许的“男性”祝英台,垂髫则是不解其意、照护贤弟的“男性”梁山伯。戏内,祝英台倾慕梁山伯;戏外,垂髫同样以保护的姿态多方照顾“胆小心慌”的银心。垂髫之于银心正似梁山伯之于祝英台,两者虽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在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等方面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电影《柳浪闻莺》提供了文化预设。
电影《柳浪闻莺》用20分钟左右的时长对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舞台表演进行直接呈现,又对银心和垂髫二人戏台上的角色身份以及垂髫对戏的执念一再强调,其实已经暗示了戏台下银心和垂髫朦胧而又浓烈的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既有因入戏太深而将戏内梁祝的情感投射到戏外,也有经年累月里两人朝夕相处而凝结的深厚情谊。相较于银心戏内戏外明显的女性特质,垂髫不论是戏内还是戏外的性格都透露出明显的男性化特质。正如梁祝二人超越性别的纯粹情感,垂髫与银心之间的情感同样超越了性别,工欲善说女小生是“第三性”,垂髫亦认识到自己对传统男女性别的超越,自称是“白马非马”。从银心的角度来看,垂髫扮演的梁山伯是她倾慕的异性,垂髫本身则是她无法超越的同性。电影运用戏曲片段和情节,生动地塑造出舞台上下的人物形象,借古代传奇诉当下离殇,戏曲文本与电影文本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在整部影片里,戏曲情节与电影情节水乳交融,戏曲角色与电影人物浑然一体,电影情节与戏曲情节相互推动。
粗略来看,戏曲文本是“套”在电影内的一套叙事,如果将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视为一个自足的文本,那么电影《柳浪闻莺》展现的便是“真实/戏外”故事和“虚构/戏内”故事形成互相平行的两条故事线索。如在第二场会演的《十八相送》片段,银心扮演的祝英台唱道,“我心又慌胆又慌”,垂髫扮演的梁山伯唱道,“愚兄扶你过桥去”,而现实生活中,少女时期,垂髫便对胆小怕雷的银心照顾有加,成年后,当银心遇到茶叶老板搭讪不知所措时,也是垂髫毫不犹豫地将银心从中拉出;又如垂髫邀请银心再次和自己唱梁祝,虽然眼睛已经看不到,但垂髫还是准确感知到了银心的到来,于是借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台词表情达意,饱含无限深情地唱道:“贤妹妹,我想你。”
二、诗性正义:道德情感自觉下的绵绵咏叹
西方哲学认为情与理是彼此对立的,西方的哲学思维也常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思维,因此,作为哲学下位学科的伦理学也长期注重“道德”而忽略“情感”。然而,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是情感动物,道德意识的确立以及道德行为的发生都离不开道德主体的情感参与,中国哲学以“人”为中心,特别是儒家学说认为情感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命意识,“情”是人一切行为的源头,是应该正视和满足的,但关键在于“情”需要有所节制,而节制的规范便是“礼”,“礼”最终规定着人的社会地位和行为,越礼之情受到社会礼教的极大压制,这种压制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渗透到人的内心深处,成为难以摆脱的对人性的桎梏。情与礼的复杂关系不仅扎根于社会土壤,电影也反复对其进行探讨和表达。
“欲”为“情”的一种,这个欲既指欲望也指情欲,本身无所谓善恶,但情感具有可变性,既可以上提为情理,也可以下滑为私欲。《柳浪闻莺》呈现的不仅是银心和垂髫的情感关联,还加入了工欲善这个男性角色,围绕两女一男三个人物情感纠葛的电影很容易制造戏剧冲突,但《柳浪闻莺》对情感和冲突的处理却是以一种细腻手法隐晦呈现。直接将情感外化为行动的只有银心这个角色,银心最初的欲望是把戏唱好争取留在杭州,这是正当的、合理的、无可指摘的,然而,她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却将垂髫眼睛看不见这一秘密散播出去,为了自己的私情私欲而伤害了垂髫,并对垂髫的演艺生涯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情感上,银心对画扇师工欲善一见倾心,而工欲善则对气质独特的垂髫念念不忘,工欲善对银心的示爱不拒绝不接受,垂髫同样对工欲善的情谊欲迎还拒,三人这种胶着难分的情感联系与德勒兹所提的“情状”概念极为契合,感情无所谓对错,但在具体伦理情境设置下(银心已知晓工欲善对垂髫的爱意)就会生出道德判断,道德判断以判断人的行为善恶为目的,这类判断属于伦理命题,追溯的是人类行为的道德意义。
银心的欲望与情欲带有自私自利的色彩,但《柳浪闻莺》并未引导观众对电影中的人物进行道德评判,意在展现作为“人”的复杂性。电影内的人事物并不全然与现实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原则完全符合,因为电影对正义的伸张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电影的正义在特定意义上是一种诗性的正义, 它是在象征的意义上完成对伦理法则的归依。出于对垂髫的同情和愧疚,银心再一次将自己置于道德旋涡,公开与尚有家庭的于老板交往,而目的只是让垂髫有戏可唱,无私与自私交杂在一起,很难以单一的“善”或“恶”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柳浪闻莺》的可贵之处体现为其在唤醒观众共情的同时又让观众时刻保持理智旁观者的身份,以一种中立的目光见证电影中人物的情感与行为,最终指向“诗性正义”,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诗性正义”是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情与理融为一体,影片中的人物以个人情感和幸福为中心的同时又受到社会现实和良知的约束。
尽管我们很难以单方面的道德去定义电影中的人物,但基于“情感”的“诗性正义”还是能够带给我们伦理层面的感召,或被垂髫视戏为生命的执着所感动,或从银心的世俗与善良中体悟人生。影片结尾,银心选择和于老板一起去美国,除了对工欲善心死,还隐含着对垂髫的成全。看似“圆满”的结局实则蕴含着无限的缺憾,两个热爱舞台热爱戏曲的人却再也不能一起唱戏,银心在自己爱和爱自己之间选择了一个爱自己的人,垂髫虽和工欲善相伴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祝英台”,与《小城之春》“言有尽而意无穷”相似,《柳浪闻莺》中的人物也在无限的时间与空间中沿着符合情理、各自隐忍的命运之路前行,让观众在绵绵咏叹中回味、思索。
三、民族化叙事:构筑具有本土特色的电影景观
民族化是电影叙事伦理的重要指向,即通过运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艺术思维来表达具有民族性的人、事、情,进而使影片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柳浪闻莺》在影片形式、影片内容、影片风格三个向度都具有明显的民族化特色,将戏曲这一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融入电影之中,不仅使电影文本与戏曲文本交相辉映,观众可以从中获得双重审美体验,而且在满足观众对道德层面善的要求的同时又不落窠臼,以带有缺憾的结尾诉诸中国人早已在各种戏曲、话本、传说中塑造的“悲情传统”。影片还承续了中国电影的“尚诗”传统,以“意境”为主要显在形式导入影片的叙事风格过程中,赋予影片以民族诗情,绘就了中国电影民族化诗意表达的特色图景。
戏曲与电影分属于两套不同的艺术体系,虽都以叙事为主要目的,但戏曲重“写意”而电影重“写实”,这与它们各自的艺术属性相关。戏曲要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内完成曲折且跨越时空的叙事,因此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程式化和假定性的表演方式,而电影则可以重塑时空,对现实进行描摹与复刻。两者在表演方式、叙事手法、场面调度等方面各有侧重,电影《柳浪闻莺》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内化为戏中之戏,一方面令影片的本体故事和戏曲故事产生内在的呼应,另一方面也充分运用传统戏曲文化丰富了电影自身的意蕴。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种类繁多、各富特色,不仅承载着中国文化精神,更体现着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在戏曲舞台上,“境随象生,天马行空”,“扇子”作为戏曲中的道具,不仅能够传达出人物身份、人物性格、人物情绪等信息,也能够展现戏曲的假定性美学,比如梁山伯在得知祝英台是女儿身且要和马家公子完婚时,舞台上的梁山伯“化扇为马”,通过摇扇的动作来表现快马加鞭赶路的情形。延伸到电影中,“扇子”不仅是戏曲舞台上的道具,也是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物件,垂髫、银心和工欲善的结识便是因为扇子,作为一个画扇师,工欲善虽不懂越剧,但对扇子的见解颇为独到,也是利用扇子和垂髫暗传情谊。因此,《柳浪闻莺》不仅在情节上与戏曲相互交织,也将戏曲中的道具从台上挪到台下,生出多重意蕴。整部影片最核心的矛盾点就是如何处理“情”与“理”的关系,若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出发,凡不符合秩序、人伦的情感都是需要被压制和阻止的,人必须摆脱最原始的生理欲望从而符合所谓的“礼”,但《柳浪闻莺》显然没有把道德至善作为最终的追求,无论是工欲善还是银心都有着各自的人性缺点,这些缺点暗示了影片人物命运的走向,一向胆小的银心选择和于老板去到陌生的异国,把戏看作生命的垂髫再也无法和银心同台,爱慕垂髫的工欲善永远不会理解垂髫对银心的感情……
影片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始终营造出淡淡的落寞与哀愁。与西方成熟的悲剧美学不同,中国可能从未诞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只有对“悲”这种意境的营造,即延续至今的“悲情传统”。中国的悲没有强烈的对抗与冲突,受儒释道文化的长期浸染,中国的悲似乎被稀释、中和了,如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跃入祝英台墓碑后两人化作蝴蝶从中飞出,有情人无法结合本是悲剧,但最后比翼双飞的蝴蝶似乎又冲淡了这种悲,反而带有一种浪漫色彩。《柳浪闻莺》承续了这种悲情传统,绵绵不绝的细雨从视觉层面传达出悲凉的情绪,垂髫和银心的分别正如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十八相送一般,虽依依不舍却再也无法相见,两人的遭际也从侧面表现出戏曲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衰落和边缘处境。
戏曲作为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历史文化,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美学资源,“才子佳人”戏是传统戏曲中的一个重要母题,许多戏曲故事讲述的都是落魄书生和富家小姐、才子和名伶之间曲折且动人的爱情故事,戏曲母题既是中华民族情感的想象性外化,也是民族语言的寄托。一方面,熟悉的情节设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审美观念,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审美心理,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期待;另一方面,电影创作者也根据时代发展,适当改变情节、人物设定,在满足观众审美期待的同时又突破母题本身,实现一定的“陌生化”,满足观众求异心理。将中国独有的戏曲文化融入电影创作环节,不仅可以为中国电影树立独特标志,而且为传承和发扬戏曲文化也大有裨益。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视,他说:“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戏曲在千百年的流传中早已刻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带有显在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京剧、豫剧、越剧、粤剧、黄梅戏、梆子戏等)。在电影中,中国的影视创作者应该找到属于本民族文化特质的表述形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者开始有意识地从成熟的戏曲美学中汲取营养,虽不像《柳浪闻莺》一样将故事主角设置为戏曲演员,也没有反复长时间的戏曲片段,但《过昭关》《八佰》等影片都“挪用”了部分戏曲片段,在现实场景的叙事中插入“超现实”的戏曲表演,非但没有破坏电影本身的叙事节奏和叙事线索,反而将原本封闭的文本变为开放的和富有多重解释空间的场域。足可见戏曲艺术的生命力不只在于戏曲实体自身,而在于对(足以传递出戏曲意蕴的)戏曲元素的创造性运用与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