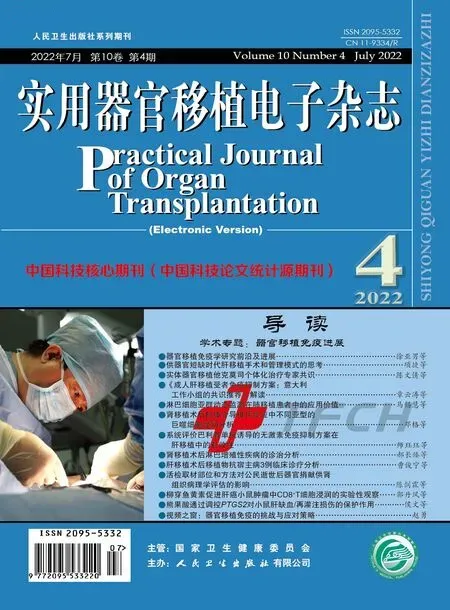供器官短缺时代肝移植手术和管理模式的思考
项捷,厉智威,张微,梁廷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肝胆胰外科,肝移植中心,浙江 杭州 310003)
自20 世纪70 年代我国开始肝移植的早期探索,中国肝移植事业已经过50 余年的奋斗与发展,一代代移植人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特别是近10 余年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和器官移植改革不断推进深化,肝移植得到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道路和取得的成就,被称为“中国模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
在器官移植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发展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越来越为国内外学者们所关注。在各种制约移植事业发展的问题中,供器官短缺,供需矛盾突出,已成为中国与世界移植领域共同面对的紧迫问题[2]。活体器官移植存在伦理瓶颈,异种器官移植遭遇的伦理束缚,都限制了供器官来源的扩展。积极倡导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对移植技术健康开展有决定性意义。目前中国每年的捐献总量已趋于稳定,如何利用有限的捐献器官,使更多的供器官等待者获益,是移植手术医生需要思考的问题。
1 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现状
自2015 年1 月1 日起,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献(Chinese donation after citizens’death,CDCD)全面取代司法途径供器官来源,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供体来源。此后中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数量逐年增长,器官捐献数量长期列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3]。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截至2022 年3 月,全国累计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461 万,实现捐献超过39 000 例,共计捐献器官超过11 万个。2019 年,中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5 818 例,每百万人口器官(per million population, PMP)捐献率从2015 年2.01上升至2019 年4.16[3]。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每年完成器官移植手术超过1.5 万例,其中,2019 年中国共完成器官移植手术19 454 例[3]。
然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器官捐献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开展。2019 年器官捐献PMP 最高的5 个国家分别是西班牙(49.6)、美国(36.1)、葡萄牙(33.7)、克罗地亚(32)和法国(29.4),而中国为4.07[3]。2019 年器官移植(包括活体)PMP 最高的5 个国家分别是美国(123.4)、西班牙(117.4)、法国(90.2)、韩国(83.8)、加拿大(82.9),中国为13.6[3]。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PMP 均与世界主要国家存在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虽然总体器官捐献与移植规模已居世界前列,但在人口平均层面仍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此外,在我国,脑死亡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比例较其他国家低,但近年来随着脑死亡概念的推广,脑死亡判定技能培训的持续开展,各地医疗机构开展脑死亡器官捐献实践经验的不断累积,以及卫生行政政策的推动,在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脑死亡捐献比例由2015 年的16%上升至2019 年的32.7%[4]。DBD 数量的增加,将有效促进每供者平均捐献器官数量的增加,以及心脏、肺脏、胰腺等脏器的利用。
由此可见,供器官短缺仍然是制约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据统计,2019 年共有81410 例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然而,最终仅19 454 例(23.9%)接受器官移植手术。而在肝移植中,2019 年共有14 399 例患者等待,只有6 163 例(42.8%)最终完成肝移植(包含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和活体器官捐献)[3]。而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来,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经历重大影响,虽然在全国共同努力下疫情得到控制,但全年器官捐献数量由2019 年的5 818 例下降至2020 年的5 222 例,而肝移植完成数量由2019 年的5 332 下降至2020 年的4 954 例。由此可见,在供器官短缺时代,器官捐献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移植的需求,只有大力推进器官捐献与器官最大化利用才能促进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
笔者所在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20 年完成各类肝移植432 例,较2019 年的280 例上涨54.3%。究其原因,除大力开展活体肝移植以外,针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展开技术创新,发展多项肝移植新技术,最大化利用有限的供器官,拯救了更多的患者,在肝移植数量快速上升的同时质量同步提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应。在目前器官捐献数量趋于稳定的阶段,以创新求发展,通过移植技术创新最大化利用捐献器官,将成为今后阶段中国肝移植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2 移植技术创新使器官利用率最大化
自2010 年我国积极推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以来,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逐步与国际接轨,2015 年1 月1 日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唯一合法器官来源。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得到快速、健康发展,近年来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已稳居全球第二位。随着社会公民捐献意识逐渐普及、各地器官获取组织建设日趋完善,社会器官捐献数量在今后一段时间会趋于平稳,因此,器官移植的持续发展需要移植外科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为克服供器官短缺问题打开新的窗口。
2.1 劈离式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是将供肝最大化利用的一种方式。1988 年,德国Pichlmayr 等[5]首次完成劈离式肝移植,将1 个供肝的左外侧叶和扩大右三叶分别移植给1 例儿童和1 例成人受体。2001 年,Azoulay 等[6]将供肝进行完整左-右半肝劈离,分别移植给2 例成人受体。此外,也可为2 例儿童受体进行劈离式肝移植。供肝劈离的主要方式为体外劈离和原位在体劈离,其中体外劈离是通过供肝整体获取后,在体外进行修整劈离,而原位在体劈离是在不阻断供肝血流的条件下进行两部分肝脏的劈离。不管是离体还是原位在体劈离,均需在术前须仔细评估肝血管和胆管的走形和解剖变异。不同劈离术式的肝血管及胆管分配方式不同,但都需保证不影响移植手术完成,以及保持移植物功能完整。
随着活体肝移植不断发展和技术进步,劈离式肝移植也在供器官短缺时代得到越来越快的发展和应用。目前的研究表明,劈离式肝移植可以取得和常规肝移植一样的预后效果。然而,劈离式肝移植在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等情况仍有待改善。劈离式肝移植应用中主要的困难和挑战包括:① 供受体选择标准。② 供肝劈离和重建技术。③ 小肝综合征等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自2006 年开展劈离式肝移植以来,不断创新,2020 年起单中心年劈离式肝移植完成数量超过90 例,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劈离式肝移植中心。针对劈离式肝移植的技术挑战,笔者单位有以下经验供参考。
2.1.1 供受体选择标准:根据近年研究报道,劈离式肝移植与全肝移植预后已十分接近,但不管在哪个国家,除了劈离式肝移植技术,严格的供、受体选择标准也是手术成功的关键。劈离式肝移植供体的选择标准相对全肝移植而言更高。目前各国对劈离式肝移植供体选择标准均做了一定规范(表1)[7]。笔者单位在基于大规模劈离式肝移植开展实践中,提出以下符合我国肝移植实践的劈离式肝移植供体选择标准:年龄<60 岁且血液动力学稳定,没有或仅一种小剂量血管活性药物,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治疗时间<5 d,预计冷缺血时间<10 h,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1.5 倍正常值上限,肝脏脂肪变性<15%和血清钠<160 mmol/L (表1)。而受体选择标准包括无手术史、MELD 低于25 分、体型小、评估GRWR 大于1%、术前无腹腔感染高危因素(肾衰竭、腹膜炎等)。

表1 各国劈离式肝移植供体选择标准
2.1.2 供肝劈离和重建技术:常用的供肝劈离技术包括体外劈离与原位在体劈离技术。两种技术各有其优缺点。供肝原位在体劈离技术优势主要在于能更确切地对肝断面的血管和胆管进行处理,减少断面出血和胆漏的发生,同时由于不阻断血流,可缩短供肝的冷缺血时间。但供肝原位在体劈离技术也存在局限性:需要手术医生到供者所在医院切取肝脏,延长了手术时间,同时影响了供者体内血液动力学的稳定性,体内供肝的劈离需要一定手术时间,势必影响其他器官组的器官切除。且供肝一旦出现胆道或血管变异,一般较难在获取同时再对供者做侵袭性胆道或血管造影。但供肝原位劈离术的劣势却恰恰是供肝体外劈离术的优势,体外劈肝不但对其他取器官组的影响较小,同时供肝体外劈离术可以更好的进行解剖,胆道和血管造影,这不但为合理劈离肝脏提供依据,更为移植后移植物拥有良好的血液供应,避免胆漏等并发症打下坚实的基础。供肝劈离过程中针对肝动脉、门静脉、肝静脉以及胆道的分配目前仍然存在争议,特别是在存在管道变异的情况下,需要特别小心,保证两个供肝的安全。笔者单位供肝劈离方式以体外劈离为主。
针对左半肝-右半肝方式的劈离式肝移植,常规的操作是将肝后下腔静脉归于左半肝,通常需完全重建右半肝的V5、V8 静脉回流,但对于其他细小的肝短静脉回流无法重建,术后常常出现右半肝流出道回流异常,影响术后移植肝功能恢复。笔者单位创新性的应用供肝肝后下腔静脉劈离技术,并联合肝中静脉属支重建,可保护完全左右半肝劈离后两个半肝的静脉回流,促进移植物回流,防治淤血所致的功能丧失,不影响肝功能恢复。
对于移植后淤血(缺血)肝段,存在术后坏死感染的可能,特别是扩大右三叶的供肝,其残余的Ⅳ段肝脏容易发生缺血,因此在肝移植血流再灌注后需考虑切除残余的Ⅳ段肝脏。
2.1.3 小肝综合征的防治措施包括:① 提供足够的功能性肝体积。② 脾切除或脾动脉结扎调节门静脉压力,但脾切除后可能出现门静脉血栓形成等,而脾动脉结扎仅在脾脏巨大情况下有一定的作用,调节范围为2 mmHg(1 mmHg =0.133 kPa)。
2.2 多米诺肝移植:多米诺肝移植是将1 例接受肝移植的遗传代谢性肝病患者切除的非肝硬化病肝作为供肝移植给另1 例肝移植受体,其原理是代谢性肝病患者的肝脏虽然存在某些代谢中间通路缺陷,但其他肝脏功能基本正常,后者接受移植后通过本身其他途径代谢通路互补完成相应代谢产物合成。最早于1995 年在葡萄牙完成第1 例多米诺肝移植[8]。
目前,多米诺肝移植多应用于不适合长时间等待的肝癌患者和高龄患者,符合多米诺肝移植供者的原发病包括家族性淀粉样变多发性神经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枫糖尿病等。目前临床上多米诺肝移植面临主要的问题包括:供者面临更复杂的外科手术风险以及疾病传播的伦理问题以及多米诺肝移植手术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难点。多米诺肝移植手术的技术难点主要是多米诺供肝的切除与修整,包括流出道、肝动脉合适的大小长度,以保证多米诺供、受体两方面都能顺利完成肝移植血管重建。目前多米诺供肝切取过程中多采用保留多米诺供体下腔静脉的方式,可以减少多米诺供体的下腔静脉阻断,进而减少手术时间、出血量、热缺血时间等。但在这种方式下,多米诺供肝的流出道重建显得尤为重要。此外,由于多米诺供肝是高质量的供器官,具有良好的肝功能和活体肝移植的特点,包括稳定的供体状态和较短的冷热缺血时间。因此,多米诺供肝也可应用于劈离式肝移植。
笔者单位创新性地开展了多种新技术,如:多米诺-劈离式肝移植联合心脏移植、多米诺肝移植联合辅助肝移植小肠移植等,均取得了优异的成果。笔者单位的经验是,在常规肝移植手术技术的前提下,针对多米诺供肝,需要更加精准地规划肝动脉、门静脉以及流出道。对于多米诺供肝的流出道,常规通过流出道血管成形、肝静脉补片成形等方式进行流出道重建。在多米诺供肝劈离的情况下,肝静脉重建更为重要,特别是断面的第5、8 段静脉需要进行重建。
2.3 辅助性肝移植:辅助性肝移植(auxiliary liver transplantation, ALT)是指保留肝移植受体原有全部或部分病肝,同时把部分或全部供肝移植到受体体内。其优点在于相对原位肝移植不需要完整切除受体原有病肝、创伤相对小、没有无肝期、供肝体积要求低等。ALT 主要应用于急性肝衰竭、遗传代谢性肝病及终末期肝病等患者。
目前限制ALT 开展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腹腔空间缺乏、门静脉的血流竞争以及急性排斥反应的早期诊断等。其中,最为困扰的是原肝与移植肝之间门静脉的血流竞争。肝脏的血流约75%来自于门静脉系统,因此,足够的门静脉血流是肝脏正常生长的关键。而在ALT 手术后常会发现受体病肝能获得较多门脉血流而出现增生,反而移植肝因门静脉血流减少则出现萎缩。因此,如何调控病肝与移植肝之间门静脉的血流成为了ALT 难点问题。目前,解决办法包括结扎门静脉、缩窄门静脉、门静脉动脉化等,但都存在相应的缺陷[9-10]。笔者单位创新性地将异位移植肝门静脉与原肝门静脉左支矢状部相吻合,保证了移植肝稳定充足的门静脉血流,术后恢复顺利,术后移植肝再生且功能正常。
2.4 边缘性供肝拓展应用
2.4.1 脂肪性供肝:供肝脂肪变性是供体常见的病理改变[11-14],一般认为,小泡性脂肪变性对供肝质量无明显影响,而大泡性脂肪变性则是供肝质量的重要危险因素。目前认为重度脂肪肝的使用会导致移植肝初期肝功能不良和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发生率升高,而轻-中度脂肪肝对于肝移植远期预后无明显差异[15]。有报道表明,25%的供肝遭弃是由于肝脏脂肪变,但目前对于何种程度的脂肪肝不能作为肝移植供肝尚无统一定论[16]。中国香港大学Wong 等[17]研究19 例重度脂肪供肝肝移植,术后未发生原发性无功能或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3 年生存率高达94.7%。笔者单位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度脂肪肝DCD 肝移植组的移植肝功能恢复短期较无脂肪肝DCD 组慢,但长期无显著差异。而在术后并发症及90 d、1 年、3 年生存率之间无明显差别[18]。在等待者多而供肝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中度甚至重度DCD 脂肪肝仍可尝试在急诊肝移植中应用,甚至可以作为再次肝移植的过渡治疗。
2.4.2 乙肝病毒阳性供肝:我国是乙肝大国,对于乙肝阳性供肝的拓展应用研究可大大扩展供器官来源。对于乙肝核心抗体阳性供肝,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其生存率与接受乙肝阴性供肝的患者无显著差异[19-20]。目前研究的焦点主要是针对乙肝表面抗体阳性供肝的应用。Loggi 等[21]采用1O 例乙肝表面抗体阳性供肝,其中6 例受者为乙肝相关肝病,4 例受者为非乙肝相关性肝病。1O 例术后均予高效抗乙肝病毒治疗,平均随访时间42 个月,结果无1 例感染乙肝病毒。
笔者所在单位的多篇研究结果表明,拉米夫定联合乙肝免疫球蛋白可显著减少肝移植术后乙肝病毒复发[22]。此外,本单位多项研究[23-24]表明接受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供肝也是安全有效的,长期预后与接受乙肝表面抗原阴性供肝的受体无显著性差异,对于移植术后乙肝病毒复发,可通过抗乙肝病毒核苷类似物和乙肝免疫球蛋白进行预防和治疗。
2.4.3 丙肝病毒阳性供肝:随着新型口服抗丙肝病毒药物的出现,丙肝彻底治愈成为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之前被视作禁忌的丙肝病毒阳性供肝也成为扩展供肝来源的一大方向。在缺乏抗丙肝病毒药物的时期,丙肝病毒阳性供肝被认为只能移植于丙肝阳性肝病受体。限制丙肝病毒阳性供肝应用于丙肝病毒阴性受体的主要因素是考虑病毒传染的伦理问题。目前研究证明接受丙肝病毒阳性供肝的受体在经过口服抗丙肝病毒药物预防后可显著减低新发丙肝的风险[25-26]。因此,考虑到目前新型口服抗丙肝病毒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对于丙肝阴性的器官等待者而言,丙肝病毒阳性供肝不失为一种选择,可显著减少等待时间。
2.4.4 高龄供肝: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供肝年龄也成为扩展供器官来源的一大突破。高龄供肝一般是指大于65 岁以上的供肝。早期有研究提出高龄供肝的术后早期病死率和供肝无功能发生率较年轻供肝显著增高[27]。高龄供肝不管在尸体或活体肝移植中都表现出较差的预后,且高龄供肝常存在高血压、糖尿病等合并症,进一步影响供肝质量进而影响预后,因此,高龄供肝被认为是边缘性供肝[28]。但随着研究深入,近来对于高龄供肝的研究显示,在严格选择标准下,不管是60 岁、70 岁甚至80 岁以上供肝都可以取得与更加年轻供肝相似的预后[29-30]。欧洲肝移植注册对于高龄供肝的选择标准包括:转氨酶正常或<3 倍正常值上限、ICU 治疗时间<4 d、循环系统稳定、无肝纤维化、无糖尿病史。接受高龄供肝的受体选择标准包括无丙肝病毒感染,MELD 评分<24 分。
2.5 异种移植:尽管同种异体移植技术在不断创新发展,但器官短缺仍是限制移植发展的最大瓶颈。异种移植作为增加器官供应的途径之一,可以解决供肝短缺的问题。随着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异种肝移植在近10 年来得到迅猛发展,异种肝移植术后超急性排斥反应得到了有效控制[31]。而随着多种基因编辑小型猪愈加成熟,在动物实验不断取得进展,异种移植临床研究与应用逐步展开。2021 年10 月,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在一位脑死亡患者上将基因工程猪肾脏以体外连接的方式进行移植,并在观察54 h 后终止实验,期间移植肾未出现与排斥反应有关的表现。此后,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研究显示[32],将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猪肾脏移植到1 例脑死亡的患者体内,替代其原有肾脏,猪肾脏在植入体内大约23 min 后开始起作用并排尿,并持续74 h 后终止实验。在此期间没有观察到超级排斥反应和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感染迹象,肾脏可以产生尿液,但肌酐清除能力没有恢复。此外,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进行了全球首例猪心脏移植手术[33],患者在接受原位猪心脏移植后2 个月左右去世。异种移植的先锋临床研究获得了在患有终末期肾衰竭疾病的患者身上开始临床试验所需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数据,为今后逐步开展临床试验奠定了基础。
3 结 语
随着医疗技术发展、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供器官短缺仍是长期困扰全球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笔者所在单位经验表明,在短期内供器官短缺常态化情况下,通过移植外科技术创新、管理理念和模式创新,尽最大可能利用现有器官资源,才能为更多患者获得治疗机会。新型技术如肝细胞移植、异种移植的进一步发展成熟,这将是全球移植领域不断研究和探索的方向,人类终将跨过供器官短缺的鸿沟,迈入移植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