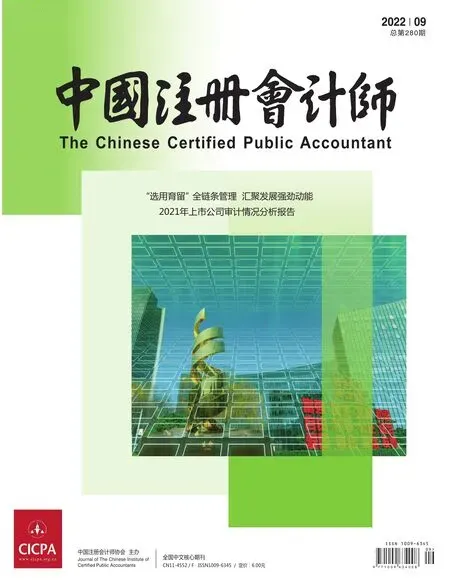“国际四大”研究述评与展望:影响因素、审计行为与经济后果
高新梓 孙艳阳
一、引言
二战后,国际资本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带动了审计行业的跨国界发展,形成了一批从事国际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伴随着国际审计市场的竞争与演变,至上世纪80年代,形成了“国际四大”的前身,即当时的国际八大。经过数十年的演变,经历了合并破产重新组合后,80年代末合并为六大,90年代又合并成为五大,2001年安然安达信事件后合并为今天的“四大”,即普华永道(PWC)、德勤(DTT)、毕马威(KPMG)以及安永(EY)。目前,“四大”在世界范围的很多国家的审计市场中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其审计行为对于全球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乃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对于“四大”而言,进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国际惯例做法是发展成员所。但1992年获准进入中国内地时,双方采取了中外合作的方式,合作设立有限责任制的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合作期满,“四大”陆续开始本土化转制,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在过渡期内逐步实现本土化目标。但“四大”与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存在管理理念和文化理念的本质差别,本土化转制并非一蹴而就,并且成为“四大”国际成员所后,如何发挥“四大”在中国的品牌优势,成为其他国家审计监管部门认可的、高质量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依然任重而道远。其中全面理解“四大”的审计需求、审计供给,以及审计市场结构、制度环境等对“四大”审计行为的影响尤为重要。鉴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目前国内外文献中关于“四大”研究的主要领域和角度,理论上总结“四大”研究体系,发掘潜在研究机会;实务上为监管部门优化现有政策提供依据。
二、“国际四大”审计需求与供给
(一)“国际四大”审计需求
从对“四大”的审计需求角度,国外文献大多从审计需求的委托代理观入手,研究结论大多支持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的公司,对“四大”审计服务的需求动机更强。一方面,“四大”独立性更高。从管理层与股东的委托代理问题入手,Lennox(2005b)以非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是否聘请“四大”负相关;也有文献从债权人与股东、债权人与管理层的委托代理问题入手,选取资产负债率作为代理变量,结论同样支持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与聘请“四大”显著正相关(DeFond,1992;Blouin et al.,2007)。另一方面,“四大”专业胜任能力更强。部分研究支持会计总应计项目高(Francis et al.,1999)、经营情况复杂的公司(Godfrey and Hamilton, 2005)更倾向于聘请“四大”。
也有部分文献从审计需求的信息观入手,研究结论大多支持当公司的外部管理人,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等治理机制力量较强时,会更倾向于聘请“四大”(Engel et al.,2010; Cassell et al.,2012)。原因在于这些高质量的监管者有更强动机寻求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降低与公司内部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程度(Beasley and Petroni, 2001)。
国内关于“四大”的审计需求的研究与国际文献基本类似。国内文献的研究结论也支持审计需求的委托代理观以及审计需求的信息观。如王烨(2009)从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角度,孙铮、于旭辉(2007)从国有企业中政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角度,以及陈德球、叶陈刚、李楠(2011)从家族企业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角度入手,也有不少学者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是否存在外部监管机制入手,研究结论支持审计需求信息观。如宋常、陈胤默、赵懿清(2018)中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步丹璐、屠长文(2017)中外资持股的上市公司,杜兴强、谭雪(2016)中外籍董事等均与是否聘请“四大”显著正相关。
(二)“国际四大”审计供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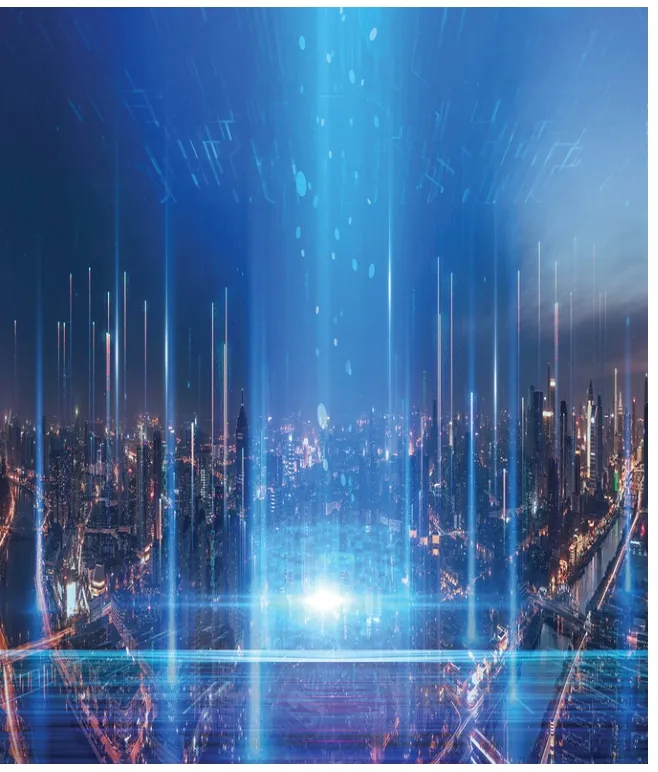
从对“四大”的审计供给角度,国外研究普遍发现“四大”的审计质量较高,且存在收费溢价。从财务信息质量衡量审计质量的角度,“四大”审计的客户非标审计意见的比例较高(Francis and Krishan, 1999),操纵性应计项目较低(Becker, DeFond, Jiambalvo,and Subramanyam, 1998),财务报表重述的概率较低(Francis et al.,2014),盈余稳健性更高(Francis and Wang, 2008),并且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准确性更高(Clarkson,2000)。国外文献普遍发现“四大”存在收费溢价,但“四大”的收费溢价源于较高的审计质量、垄断定价还是风险溢价,并没有明确结论(DeFond and Zhang,2014)。其中如Basioudis and Francis(2007)发现有行业专长的“四大”收费溢价最高;Bandyopadhyay and Kao(2001;2004)研究结论并不支持“四大”的收费溢价源于垄断租金,反而可能是由于品牌效应产生的;Ghosh and Pawlewicz(2009)研究发现“四大”的收费溢价与法律风险密切相关。
“四大”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溢价效应不仅在事务所层面存在,亦有学者研究发现,“四大”审计质量以及审计收费溢价在“四大”分所层面也存在系统差别。规模大的分所由于具有更丰富的内部经验而审计质量更高,表现在规模大的分所会出具更多非标意见以及客户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Francis and Yu, 2009)。并且由于分所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监督,同一事务所内部分所联系紧密程度与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表现为较少的客户重述以及更低的操纵性应计(Seavey et al.,2018)。Basioudis and Francis(2007)以英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四大”中某一地域特定行业领导者的审计收费溢价高于其他地区的“四大”。Whitworth and Lambert(2014)研究发现“四大”地区分所特定的行业专长与审计延迟显著负相关。
虽然多数文献支持“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且存在收费溢价,但是亦有少数学者指出“四大”的高审计质量以及收费溢价存在内生性问题。如Lawrence, Minuttimeza and Zhang(2011)研究发现考虑了客户特征之后,“四大”与非“四大”在操纵性应计项目、资本成本以及分析师预测准确性三个审计质量代理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别。Chaney, Jeter and Shivakumar(2004)研究了非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问题,发现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四大”并不存在收费溢价。
从“四大”审计供给的角度,国内多数学者研究发现“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所,且存在收费溢价。如:潘克勤(2011)认为“四大”对日后遭受监管处罚的客户会出具更为严格的审计意见;林永坚、王志强(2013)在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发现“四大”比国内所审计质量更高,表现在“四大”审计的公司正向的操纵性应计更低;王艳艳、陈汉文(2006)研究发现“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显著高于非“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朱松、夏冬林、陈长春(2010)认为“四大”相对于非“四大”而言,由于声誉等预期损失较大,因此在风险控制上更加谨慎,客户的会计稳健性更高;张奇峰(2005)认为经“四大”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盈利更具可信性;米春蕾、陈超(2018),祝继高、王春飞、尤可畅(2015)发现“四大”审计能够显著提高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真实性。关于“四大”的审计收费溢价国内亦有不少研究成果。张立民、丁朝霞、钱华(2006),戴文涛、刘秀梅、陈红、翟航(2017),田利辉、刘霞(2013),李连军、薛云奎(2007)等学者的研究均支持“四大”在我国审计市场中存在收费溢价。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必然高于国内所。如刘峰、周福源(2007)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出具的概率、可控应计的数量和会计盈余的持续性三个角度来看,“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从会计盈余的稳健性角度来看,强烈的证据表明“四大”甚至比非“四大”更不稳健。李江涛、何苦(2012)认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真实盈余管理强度显著大于非“四大”事务所审计的公司,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具有采用真实盈余管理逃避高质量外部审计的动机。
三、审计市场结构与竞争对“四大”审计行为的影响
(一)审计市场结构
除美国审计市场外,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德国、比利时、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均有文献支持“四大”在该地区的审计市场中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Quick and Wolz, 1999;Beattie et al., 2003; Willekens and Achmadi, 2003)。已有文献研究审计市场结构与竞争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大多从“四大”的市场集中度入手(如赫芬达尔指数),而且并没有统一结论。部分研究发现“四大”的市场集中度高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Newton et al.,2013),也有学者发现“四大”的高市场集中度会损害审计质量(Boone et al.,2012)。除了“四大”总体的集中度外,“四大”内部集中度也会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Francis et al.(2013)以42个国家的审计市场为研究样本,发现“四大”总体的集中度有利于审计质量,但“四大”内部集中度会损害审计质量。
“四大”的市场集中度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情况类似,部分文献研究发现“四大”市场集中度与审计收费溢价显著正相关(Ferguson and Stokes,2002),部分文献发现“四大”的高市场集中度也可能会降低收费溢价(Carson,2012),也有研究认为“四大”的市场集中度与收费溢价关系不显著(Bandyopadhyay and Kao, 2004)。
导致上述研究结论不统一的原因可能是用市场集中度指标衡量审计市场结构与竞争理论上并不全面,高集中度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程度低。Dunn et al.(2013)在市场集中度之外,引入“四大”市场份额的均等程度来衡量审计市场结构,研究发现国家层面“四大”市场份额均等程度与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与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
(二)“四大”与非“四大”之间竞争
目前研究非“四大”与“四大”之间的竞争的文献大多以区域竞争理论为基础,研究某一地域内非四大分所与四大分所之间的竞争。Keune et al.(2016)认为非“四大”领导者会加剧地区审计市场竞争,存在非“四大”领导者的地区,总体上审计收费较低。Bills and Stephens(2016)研究发现在某一地域内,非“四大”与“四大”的市场份额越接近,“四大”的审计收费溢价越低。
四、制度环境对“四大”审计行为的影响
(一)法制环境
法制环境对“四大”的审计质量及收费的影响也受到广泛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诉讼风险以及管制风险存在差异,Francis and Wang(2008)考察了不同国家法律环境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在法律环境严格的国家,“四大”在执业过程中更加保守,审计质量更高。Ke et al.(2015)以“四大”在中国的执业情况为研究对象,发现由于受到香港资本市场的监管,“四大”所审计的AH股公司比A股公司更可能获得非标意见,具有更低的可操纵性应计以及更可能报告亏损。Choi et al.(2008)对“四大”的审计收费溢价进行了跨国研究,发现总体上“四大”的审计收费高于非“四大”,随着国家法制环境的增强,“四大”的收费溢价降低。
(二)监管干预
2001年安然安达信事件后,美国政府出台了萨班斯法案(SOX)。SOX涉及一系列关于公众公司、外部审计师的监管新举措,产生了广泛的经济后果。已有文献普遍发现,SOX出台后,“四大”的审计收费溢价上升。Asthana et al.(2009)研究结论支持SOX颁布后,“四大”收费溢价上升,且对于规模大、风险高的客户上升程度更加明显。Charles et al.(2010)研究了2000至2003年间财务报告风险和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发现SOX出台后财务报告风险与“四大”审计收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增强。除了审计收费溢价上升之外,Ghosh and Pawlewicz(2009)还研究发现SOX实施后,小所依然存在低价揽客现象,而“四大”低价揽客现象消失。
SOX实施的最基本的变革是在审计市场的自我监管中引入政府监管,成立PCAOB。PCAOB监管对于小所的审计质量有正面效应(Gramling et al.,2011),但对于“四大”的审计质量的影响不明显。2007年12月,德勤遭遇PCAOB处罚,德勤的客户表现为负面市场反应,但其他“四大”的客户市场反应并不明显(Dee et al., 2011)。处罚后3年内,德勤审计质量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客户转换风险显著提高,审计收费的增长率显著降低(Boone et al.,2015)。Boone et al.(2017)进一步研究发现,德勤的地区市场领导地位、与最近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差距以及行业专业化并没有减轻客户流失风险,但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审计收费增长率的降低程度。
五、“国际四大”审计的经济后果
从资本市场认知的角度,已有文献普遍支持,聘请“四大”具有正向的经济后果。“四大”审计的客户比非“四大”审计的客户盈余反映系数ERC更高(Teoh and Wong,1993),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更高(Behn et al.,2008),并购标的定价更高(DeFranco et al.,2011),股价同步性较低(Gul et al.,2010),权益/债务融资成本较低(Khurana and Raman 2004;Mansi, Maxwell, and Miller 2004;Pittman and Fortin 2004),并且在法制环境较弱的国家更容易对外筹集资金(Choi and Wong, 2007)。Fan and Wong(2005)研究发现在新兴市场中,“四大”作为一种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减轻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降低由于这种委托代理问题而导致的价值低估。
国内也有不少文献支持“四大”在新兴市场中可以起到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如魏明海、黄琼宇、程敏英(2013)研究指出“四大”审计师可以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对关联大股东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王烨(2009)同样发现,聘请“四大”能够降低控制性股东的资金侵占程度,减缓公司的代理冲突。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外部审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曾姝、李青原(2016)认为“四大”审计作为企业的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对税收激进行为具有监督和抑制作用。
六、评论与展望
(一)总结与评论
1.国内外关于“四大”审计需求的文献大多支持审计需求的委托代理观和信息观。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的公司,包括管理层与股东、管理层与债权人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的公司,都有证据表明更加倾向于聘请“四大”。公司治理结构中,境外股东、审计委员会以及独立董事等外部治理机制力量较强时,都会更加倾向于聘请“四大”。国内外现有笼统研究“四大”审计供给,包括“四大”的审计质量、审计收费溢价等一般特征的文献已经比较成熟,国内外文献普遍发现“四大”审计质量高,且存在收费溢价。
2.审计市场结构与竞争对“四大”审计供求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审计供给(1)“四大”内部竞争程度与审计质量正相关,而与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2)非“四大”与“四大”竞争程度强时,“四大”的审计收费显著降低。
3.法制环境对“四大”审计供求的文献也主要集中于审计供给。普遍接受的结论包括:(1)法制环境强的国家,“四大”的审计质量更高;(2)SOX以及PCAOB监管对于“四大”的审计质量效应不明显,但已有文献普遍支持SOX实施后,“四大”提高了审计收费。而受到PCAOB监管处罚对于审计收费有负效应。
4.国内外文献普遍认为,聘请“四大”审计师会产生正向的经济后果。包括正向的公司治理效应、正向的投融资效应以及正向的估值效应。并且这些正向的效应在法制环境较差的新兴市场中表现更加明显。
(二)未来研究展望
1.虽然笼统研究“四大”审计供给、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溢价的文献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四大”的高审计质量源于专业胜任能力还是独立性尚且不够明确;同样的“四大”的审计收费溢价源于法律风险、品牌效应还是垄断定价尚需要进一步研究证据。关于“四大”审计供给的文献目前主要集中于审计质量、审计收费,虽有少量文献涉及审计效率,但并没有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关于“四大”的合伙人与非“四大”的合伙人特征以及行为的差异研究证据更少,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补充相关证据。
2.从审计市场结构与竞争的角度研究“四大”的审计质量、审计收费溢价等审计行为的文献尚且存在不足,而且结论不统一。(1)衡量审计市场竞争的代理变量大多采用“四大”的市场集中度指标,而该指标并不能全面衡量审计市场竞争程度,因此缺少更加严谨的指标或研究设计来有效考察审计市场的结构与竞争;(2)关于“四大”与非“四大”之间竞争的文献更少,这是由西方审计市场的特征决定的,“四大”的市场份额占有绝对优势,非“四大”与“四大”难以进行有效全面的竞争。因此国内外该部分文献尚缺少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以及有效的实证研究证据。
3.国内关于“四大”的审计供求文献大多为对国际研究的进一步验证。世界上很少有国家的审计市场类似于中国,在政府的扶持下本土所迅速发展,“四大”从最初享受超国民待遇到逐渐面临本土大所的有效竞争。目前国内文献不仅没有全面体现中国审计市场的特殊性,而且没有有效利用中国审计市场的背景为国际上相关文献做出贡献。未来研究可以利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以及审计行业发展特征,为国际上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检验的,但又缺乏客观条件的文献提供理论以及实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