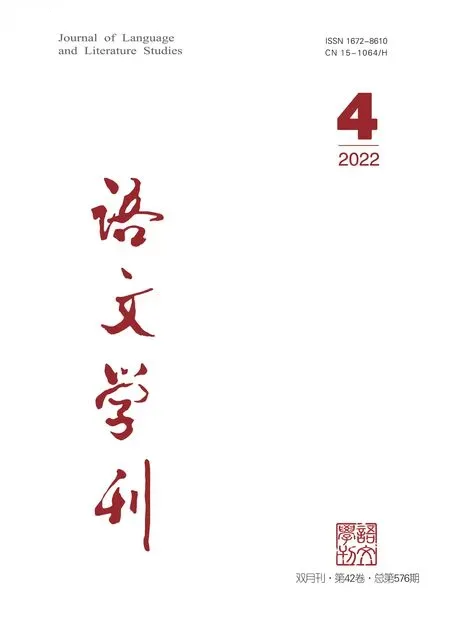《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俗字考释九则
○ 迟苏倩 闫艳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文化生活愈加丰富,为满足社会文化的需要,民间书坊所编刻的书籍通常以通俗易懂的读物为主,加之社会思潮转变、图书商品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于宋元之际的民间日用通俗类书在明代达到了高度的繁荣。明代是中国俗字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通俗类书是在书坊编写出版并供中下层民众翻阅的,书中往往蕴含数量丰富且类型多样的俗字字形,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字的实际应用情况,对于研究文字发展演变情况有着重要的价值,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而目前对于明代通俗类书中俗字的研究成果寥寥。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余氏三台馆刻本《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下文简称《三台万用正宗》),由三台馆主人余象斗编刻。全书共计四十三卷,每卷为一个门类,内容基本涵盖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是明代至今刻印清晰且保存完整的一部综合性质的通俗类书。本文选取“”“”“”“”“”“”“”“”“”共九个俗字进行考释,根据目前的考察情况,这些俗字暂未在宋元时期的通俗类书中出现,而在明代其他通俗类书中可见,通过分析这些俗字的产生原因,以期为明代通俗类书俗字研究提供借鉴。
(卷三〇风鉴秘旨)
曾良《明清小说俗字研究》中将这种代替原部件的“又”称为重文符号,称“这种重文符号,俗写又拿来作为省略一字里面相同的部件”,并举“”(谈)、“摄”“轰”三例,其中“摄”所举为明刊本字例,其余二字均在清代小说刊本中可见。用“又”来表示重出部件是一种简省规律,只不过“轰”“聂”等字形简省后保留了下来,成为现代通行的简化汉字,而“”虽在明代通俗类书中可见,但流传和使用的范围不够广泛,未能成为通行的文字,字典辞书失收,在规定简化字时未被吸收采纳和留存下来。

“瓦”原为“土器已烧之总名”,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实际生活中的运用,逐渐用以表示“屋瓦”这一具体的概念,后成为“瓦”字约定俗成的含义,至明被《字汇》《正字通》等字书收录。但在明代其原意又未完全消失,《字汇》仍载,因此要在原字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给本不需要意符的“瓦”加上“石”部件,专门用来表示后起的“屋瓦”意,以区别于原意。回到文段本身,“”即指“屋瓦”,杨贵妃夜里梦到后宫屋顶上的瓦片飞起来,魏征认为此梦代表宫人相殴至死,贵妃回宫后果见此象。
(卷三四营宅备览 营造宅兴 井灶)
凡人家厨下头锅,遇夜须刷洗净,满注水,不可令干,如空,则使主人心焦。
(《养生类纂》卷一一屋寓部)
《字学三正》《三台万用正宗》里的这些“壽”字均是由“九”“十”“百”“千”等较大的数字和汉字“工”“口”“寸”构成。这可以反映出当时朴素的造字理念,受到民间习俗观念的影响,民众在造字时将对词义的理解加到其中。后起的这些字形寄托了造字者美好的心愿,即数字越大寿命越长,而数字“九”和“工”“口”“寸”等主要起到维持字形稳定的作用,让新造字大致维持“壽”字的基本形态。
《说文解字》瓦部载“瓨”是“从瓦工声”的形声字,又缶部:“缸,瓨也。”段玉裁注曰:“缸与瓨音义皆同也。”《正字通》瓦部:“瓨,与缸同。”“瓨”与“缸”实为一字。《三台万用正宗》中俗字“”当为形声字,明代“音冈”,则由“冈”表音。“”由“瓨”而来,《正字通》山部:“冈,居康切,音刚。”工部:“工,孤烘切,音公。”《中原音韵》中“工”属中东部,“缸”“冈”均属江阳部,将声符“工”换为与明代“缸”字音更为接近的“冈”,是将形声字的声符换用更能表音的部件形成的俗字。
阴和阳本身就是对立的概念,俗字换用“水”“火”来表示更加体现二者的对立性。水火不容的观念自汉便有,东汉王符《潜夫论·慎微》:“且夫邪之与正,犹水与火,不同原,不得并盛。”用水与火比喻邪与正的相对。《汉书·郊祀志下》:“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此处指水火不相及。既然官修正史中有水火不容的理念,底层文人编纂的通俗类书中有所体现也不足为奇,其他综合性质的通俗类书如明万历刊本《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卜筮门也有此类内容。可见这种阴阳对立、水火不容的观念已经深入民心,俗字“”“”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
三十五大江上水、由洞庭湖东路至云贵:……阳陵矶、道人矶、穿湖口、旁蠏,象湖巷,共六十。(卷三地舆门 两京十三省路程)
日用通俗类书中的俗字数量不容小觑,尤其是书中新见俗字,更能反映明代民间用字特点,是对通俗类书进行俗字研究的重点所在。明万历刻本《三台万用正宗》中保存着丰富的俗字材料,本文仅涉及书中一小部分,或可为研究明代俗字提供新的材料,从而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到通俗类书俗字研究的价值,并展开对文本的多方面研究。期望通过本文对《三台万用正宗》中部分俗字的研究,为通俗类书俗字研究积累经验,为明代俗字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