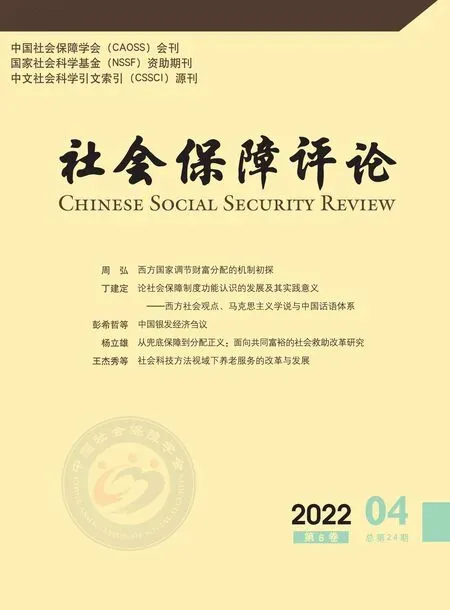从兜底保障到分配正义: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救助改革研究
杨立雄
一、前言
社会救助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在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实现社会稳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回顾我国社会救助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救助“上为政府解忧,下为百姓解愁”,为新政权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90年代,社会救助发挥“最后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救助发挥兜底保障作用,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一个也不能少”地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社会救助在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提升低收入家庭收入、缩小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促进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但是,这一问题尚未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仅有少数学者探讨了社会救助在实现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中的作用,①参见张浩淼:《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救助体系创新—基于成都市的实践经验》,《兰州学刊》2022年第6期;张浩淼:《共同富裕视角下的社会救助》,《中国社会保障》2021年第9期;杨立雄:《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问题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21年第4期。而更多的学者则在研究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改革时提及社会救助改革。①金红磊:《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共同富裕:多维一致性与实现路径》,《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郑功成:《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的逻辑关系及福利中国建设实践》,《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1期;何文炯:《建设适应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1期;熊跃根:《大变革时代的社会政策范式与实践: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江海学刊》2022年第1期;郁建兴、任杰:《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战略目标,分析现行社会救助面临的挑战和未来改革方向。
二、兜底救助的发展与形成
受个体主义贫困观的影响,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呈现“救急不救穷”特征,即:偏重急难救助,国家成为急难救助的主体;家庭和民间社会承担济贫责任,国家只对特定弱势群体实施兜底保障,重在弥补家庭功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社会救助定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安全网”和脱贫攻坚的兜底保障,在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分类济贫制度的形成
中国在几千年前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救助思想,建立了基于社会救助的社会保障体系。②王君南:《基于救助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论纲》,《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在救灾备荒方面,代表性的思想有《周礼》的“十二荒政”思想③“十二荒政”为:“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和《管子》的“德有六兴”思想。④“德有六兴”为: “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十二荒政”思想包含了救灾备荒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人口政策,为历代所继承,并形成由“预弭”政策、“有备”政策和“赈济”政策组成的救灾备荒政策体系。“德有六兴”思想要求在灾害风险发生前“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在灾害风险发生后则“匡其急”“振其绝”。秦汉及以后,救灾备荒思想得到进一步充实,赈济、养恤、安辑、调粟、放贷等救灾制度逐步完善,尤其是仓储后备思想得到广泛认同,先后出现常平仓、义仓、社仓等制度。
在济贫方面,受大同思想和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中国很早就提出了“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分类济贫思想。此后,这一思想不断得到完善和充实。荀子《五制》开篇就指出,对哑、聋、瘸、断手和发育不全特别矮小的“五疾”之人要“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复无疑”。《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说,“收孤寡,补贫穷”。《周礼》提出的“保息六政”(即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以及《管子》提出的“行九惠之教”(即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赈困、接绝),进一步完善了分类济贫思想。对于一般贫民,《管子》提出了“通穷”之措施。分类救助为中国历代所继承。
在制度建设方面,由于救急体制在稳固政权统治、增强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再加上受到“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影响,政府对急难性救助持更加积极的态度,而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又为最大限度调集全国人力、物力,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救灾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①唐传成等:《我国古代政府救助思想探析》,《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在济贫方面,国家认为,每个人需要工作和劳动获得发展,对于无法通过自身劳动、也无法获得家庭支持的老幼病残鳏寡孤独则给予必要的救济。这一思想造就了济贫对象弱势化和济贫实践民间化的特征。
(二)济贫制度的边缘化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救助工作受到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在灾害救助方面,1953年10月,国家确定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辅之以政府必要的救济”的救灾方针,形成主体多元、充分参与的救灾体制。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历经三年自然灾害、海河特大洪水、淮河流域大水灾、唐山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初步建立起中央、地方相协调的减灾救灾领导体制和“生产自救与互助互济”相结合的减灾救灾工作机制,②潘杰、于文善:《中国共产党减灾救灾工作的基本经验(1949-1978)》,《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救灾工作出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局面,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济贫方面,中央政府遵循城乡分治原则,在城市建立了以边缘性群体为主的矫治性社会救助体系,在农村建立了特困户救济和五保供养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救助体系。③杨立雄:《社会救助研究》,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社会救助对象基于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划分,实行了与传统救济相区别的分类救助方式:针对地主、资本家、妓女、国民党散兵游勇、右派人士以及罪犯,采取“改造+救济”模式进行安置;针对流民、贫下中农和手工业者,采取“临时性救助+就业”模式进行救济;针对城市“三无”人员、农村“五保”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采取集中供养方式,保障基本生活;针对失业工人,采取以工代赈、转业训练、生产自救、帮助回乡生产以及发放救济金等办法解决基本生活问题。④刘喜堂:《建国60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这一时期,我国建立起劳动福利制度。在城镇,采取计划安排就业的方式,将绝大多数城镇人口安排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中就业,通过实现充分就业达到摆脱贫困的目的,并获得福利保障;在农村,将绝大多数农民纳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通过集体劳动获得生活资料,并获得五保供养和合作医疗保障。公民通过就业和集体劳动实现自我保障,只有极少数人需要通过济贫制度获得生存保障;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政府认为我国已铲除了产生贫困的土壤,济贫只是出于人道主义而实施的一项补充性制度,由此导致济贫制度的边缘化。从费用支出看,救灾支出远远超过社会救济支出。1959—1979年,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总计268.49亿元,其中救灾支出119.89亿元,占比达到近一半(48.21%);社会救济福利支出64.39亿元,占比只有四分之一左右(25.9%)。⑤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2》计算而得。注:(1)1968-1970年三年数据缺失;(2)1977年及以前各年退休费包括在抚恤支出中;(3)从1976年起救灾支出中包括抗震救灾费。
这一时期,随着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的管控以及在基层建立起“国家-单位”和“国家-集体”制度,民间济贫责任逐步转移到政府,政府承担了社会救助的主要责任,甚至成为唯一主体,社会救助责任开始内化于政府法定职责,并开始成为公民的一项权利。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第34条规定:“人民政府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抗旱......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62年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第三十六条规定:“生产队可以从可分配的总收入中,扣留一定数量的公益金,作为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的费用……”,并规定“生产队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第四十四条规定:“人民公社社员,在社内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福利等方面一切应该享受的权利。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对于社员的一切权利,都必须尊重和保障。”但是这种责任和权利仍然局限于兜底保障,无论是受助人数还是受助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
(三)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在城镇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城镇产生大量隐性失业人员(即下岗人员、冗余人员等)、“工作贫困”群体和就业不稳定人员群体。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员生活于贫困甚至极端贫困状态之中,但又不符合传统的社会救济资格条件,由此产生大量社会问题。1993年,上海市改革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改革得到中央认可,随后在全国推广。与此同时,在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和医疗私有化改革浪潮下,家庭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和住房支出大幅增加,中央政府又相继建立起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并改革五保供养制度和灾害救助制度。2014年,国务院发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确立了包括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灾害生活救助、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教育救助在内的社会救助制度,形成了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基础、以专项救助为支柱、以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体系。
2015年,我国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社会救助承担了兜底保障的责任。2015年11月29日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了“社保兜底脱贫”措施,要求对建档立卡中的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将“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列入“五个一批”。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指导下,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了《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民发〔2018〕90号),明确要求“以应保尽保、兜底救助、统筹衔接”为原则,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制度。为此,各地提高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台账比对工作,放宽最低生活保障条件,对特殊家庭成员按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将部分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这一时期,社会救助改革源于经济改革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城市社会救助定位于经济改革的配套政策,农村社会救助定位于脱贫攻坚的兜底救助,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并为脱贫攻坚任务的如期完成作出贡献。社会救助的兜底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最低限度的公民权利。国家层面发布的多项行政法规,包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划分了政府的兜底保障边界,实现了宪法规定的公民接受救济的权利。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已成为社会救助的基础性制度。从保障人数看,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最高时超过7000万人,远远超过其他社会救助项目保障的人(次)数;从经费支出看,自1994年开始,基本生活保障支出首次超过救灾支出,随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面推广,基本生活支出快速拉开与灾害生活支出的差距。2017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支出1692.3亿元,接近灾害生活支出的11倍;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达到290.6亿元,临时救助支出107.7亿元。①数据来源:参见《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基本生活保障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夯实了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中的基础性地位(即最后的社会安全网)。
三、新形势下兜底救助面临的挑战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在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贫困形态发生变化,社会救助的基础性地位受到冲击;新冠肺炎的爆发和持续流行,为现行应急救助体系提出了新课题;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提出,对社会救助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形势下,社会救助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
(一)贫困形态变化与基本生活救助制度的弱化
中国曾是一个贫困大国,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升至世界第二位,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整体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时,贫困形态发生变化,“吃不饱”“穿不暖”的现象基本消灭,相对贫困成为主要形式。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趋强烈,社会救助需求出现升级:生活救助需求有所下降,专项救助需求快速上升;现金救助方式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服务救助需求快速上升,情感性救助需求稳步增加;社会救助需求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特征。
在新的形势下,基于绝对贫困形态建构起来的基本生活救助人数持续下滑。城镇自2009年的2345多万人减少到2021年第四季度的737.7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30万人以上;农村自2013年的5400万人减少到2021年第四季度的3470多万人,平均每年减少240万人。②根据民政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历年)计算得到。目前,全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受助率不到3%,其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已跌至1%以下。③根据民政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历年)和《民政统计数据(季度)》(历年)计算得到。
而以相对贫困标准衡量,我国还存在大量低收入家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收入五等份划分,2019年的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而根据学者的计算,2020年低收入人口数量为5.1亿人。④李实等:《中国收入不平等:发展、转型和政策》,《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此外,建档立卡已脱贫人口中还有部分群体的家庭生计脆弱,自我发展能力差,面临较高的返贫风险,尤其是受疫情影响,部分低收入家庭已陷入生存困境之中。但是受社会救助资格条件的限制,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无法被纳入社会救助范围。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救助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救助标准的连年增长,受助对象的福利水平快速增长,形成福利的反转,即:低收入家庭的受益水平超过低收入边缘家庭,形成新的不公平。另外,部分地区将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医疗救助、就业救助与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资格挂钩,进一步加剧了“马太效应”,抬高福利悬崖;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各级政府针对兜底保障对象和农村建档立卡户出台了多项保障政策,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部分政策仍然得以保留(即“脱贫不脱政策”),进一步固化了福利悬崖。
(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流行与应急生活救助乏力
2020年,新冠肺炎的爆发和持续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农民工、个体经商户、灵活就业等人群受到严重冲击,部分中低收入群体因疫情陷入贫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1月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多数月份维持在5.0%以上,最高达到6.1%,其中16—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接近20%;居民收入增长放缓,部分季度出现负增长(2020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仅对国家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提出了新课题,也对常态下的生活救助模式造成了冲击。为应对疫情影响,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以及相关部门下发多个文件,要求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工作。各地克服财政困难,采取多种措施缓解疫情对低收入群体生活所造成的冲击,保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如期脱贫,并努力缓解相对贫困下的城市困难家庭的基本生活。但是,从总体上看,现行社会救助措施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疫情表现乏力。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减少的趋势未得到改变,甚至有所加快。比较2019年第四季度(新冠肺炎爆发前)、2020年第四季度和2021年第四季度三个时点的数据,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分别为860.5万人、805.3万人和737.7万人,保障人数稳步下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分别为3456.1万人、3621.5万人和3474.2万人,2020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2021年很快出现回落。①数据来源:参见民政部《2019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2020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2021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受到疫情严重影响且长时间处于封控状况的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也未出现增长。以武汉为例,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最低生活保障83611户、116888人,疫情爆发后的2020年,最低生活保障反而减少了4263户、6330人。②数据来源:武汉市民政局。
从国外应对疫情的做法看,一些国家采取了普惠性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就业补贴、失业补贴等措施应对疫情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冲击,扩大了社会救助覆盖面。世界银行2020年5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针对疫情实施的社会救助覆盖面,马来西亚达到60%,印度和秘鲁接近三分之一,阿根廷接近四分之一,菲律宾和哥伦比亚超过六分之一,泰国达到13%。③ILO.Social Protection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Crisis: Country Responses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ILO Brief,Genève, 2020.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社会救助应对疫情表现乏力。
(三)共同富裕对社会救助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低收入人口与社会平均收入差距维持较高水平,这给实现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提出了挑战。2013-2020年,按五等分划分的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4402.4元、9653.7元、15698元、24361.2元和47456.6增长到7868.8元、16442.7元、26248.9元、41171.7元和80293.8元,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0%、9.4%、9.0%、9.1%和9.2%。尽管低收入组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其他家庭组,但是由于增速差距过小,低收入组与其他收入的差距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2020年,低收入组与其他收入组的收入差距分别达到2.09倍、3.34倍、5.23倍和10.2倍,绝对差距持续拉大(见表1)。

表1 2013—2020年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元/人)
从总体上看,社会救助在提升低收入家庭收入方面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以相对标准衡量,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替代率(即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农村不到20%,城镇长期维持在25%左右。这与OECD国家所采用的相对贫困标准(即中位收入的40%、50%、60%)存在较大差距,也低于OECD国家的社会救助替代率。由于标准偏低,同时受到较多资格条件的限制,导致社会救助受助率偏低。而且,由于受助人数持续下降,保障标准增长较为缓慢,导致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增长过缓,甚至出现下降,由此也导致社会救助缩小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的作用持续下降。
另外,社会救助待遇差距过大也是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改革社会救助管理体制,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抚恤救济事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社会救助待遇的地区差距逐步拉大。1999年,国务院颁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明确规定最低生活保障财权和事权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由此形成几千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局面,标准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近十多年来,政府持续推进城乡一体社会救助建设,部分省市实现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统一,全国城乡社会救助平均待遇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地区之间仍然保持较大差距。2012年,地区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最大差距为3.75倍,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最大差距为2.27倍,绝对差距分别为315.4元和318.71元;到2021年第四季,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最大差距降为3.41倍,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最大差距则上升为2.3倍,而绝对差距则分别达到了每人每月828.8元和753.2元。①数据来源:参见民政部《2012年四季度各省社会服务统计数据》《2021年4季度民政统计分省数据》。
四、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救助改革建议
目前基于兜底保障的社会救助体系存在受助范围窄、保障标准低、待遇差距大等问题,在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满足低收入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方面的作用不明显。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对社会救助理念进行调整,提升社会救助的分配能力,让低收入群体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一)调整社会救助理念
社会救助作为一种再分配制度,对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促进社会分配公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发达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救助受助水平高,受助面广,分配作用更为明显。从社会救助水平看,瑞士、瑞典、荷兰、挪威、丹麦的社会救助的替代率达到50%及以上;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新西兰、葡萄牙、美国部分州的社会救助替代率约为30%—50%;希腊、西班牙、英国、美国部分州的社会救助替代率为30%以下。②Tony Eardley, "Means Testing for Social Assistance: UK Policy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Neil Lunt & Douglas Coyle (eds.), Welfare & Policy: Research Agendas and Issues.Auerbach Publications, Routledge, Taylor &Francis Group, London, 1996, pp.58-78.从受助率看,澳大利亚社会救助受助率达到17.8%,加拿大15.1%,新西兰为25.1%,英国15.3%,爱尔兰为12.4%,美国食品券为10%,补充收入保障(SSI)为7.5%,其他部分欧洲国家也有较高的受助率,如丹麦8.3%,芬兰9.2%,德国和瑞典均为6.8%;从社会救助支出看,OECD国家的平均社会救助支出占GDP的比重已接近2%,其中新西兰达到12.5%,澳大利亚为5.2%,爱尔兰为4.3%,英国3.0%,美国2.7%,加拿大2%。③Ian Gough, "Social Assistance in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1997, 7(1).对发展中国来说,社会救助则是减贫的重要措施。国际增长中心(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re)对123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在所有不同形式的社会保护和劳动方案中,社会救助是惠及人数最多的人并使他们摆脱贫困的工具(社会救助方案惠及27亿人,使其中7%的人摆脱贫困)。④Nidhi Parekh and Oriana Bandiera, Do 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mes Reach the Poor? Micro-Evidence from 123 Countries, IGC Growth Brief Series 023, London: 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re, 2020.
在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政策有效衔接,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2012年每人每年2068元提高到2020年5962元,快速提升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社会救助在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⑤蔡萌、岳希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1期;李实、杨穗:《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作用》,《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5期;陶纪坤、黎梦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研究》,《社会工作》2021年第4期;蒲晓红、徐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效果》,《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杨翠迎、冯广刚,《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效果的实证研究》,《人口学刊》2014年第3期。而且,随着绝对贫困的逐步消除,社会救助人数的持续下降和社会救助财政支出规模的缓慢增长(甚至有些年份出现下降),进一步弱化了社会救助的分配功能。为此,在迈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夯实社会救助的基础性地位,提高社会救助水平,提升社会救助的分配功能,满足低收入群体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然,社会救助的再分配作用应该是适度的。既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强烈否定制度化的社会福利、实行剩余式的社会福利模式和“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理论,①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也要反对国家对全社会资源的强力分配,完全依赖于转移支付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可以基于罗尔斯的正义论原则,在肯定和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及其义务和机会的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对“社会的与经济的不平等”合理性调节和再分配,以使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尤其是要“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79页。市场不能达致平等,政府可以在分配方面发挥作用,而实现再分配的合适方式是收入转移,但是这种转移支付应该是适度的。
(二)社会救助改革目标
基于共同富裕的社会救助改革应达致以下目标。
一是夯实基本生活救助制度。基本生活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制度安排,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基本生活保障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如日本的新生活保护法已实施了60多年,其重要地位一直未变;韩国已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国民基本生活保护仍然是福利体系的核心制度;美国的食品援助计划和补充营养计划在保障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方面,仍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受助率在各项社会救助项目中位居前列。目前,我国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但是仍然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家庭面临较为沉重的生存压力。因此,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救助改革目标之一是夯实基本生活救助制度。
二是形成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我国很早就探索了分类社会救助,早期社会提出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德有六兴”“行九惠之教”成为分类救助的思想基础。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后,上述分类救助对象被整合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在社会救助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最低生活保障往往成为其他社会救助项目的认定资格,由此导致了福利悬崖效应。为了减轻这一现象,部分地区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线(简称低边,通常以最低生活保障线的150%为计算依据),形成了最低生活保障、低边两个层次的分层救助体系。但是因针对低边人群的救助项目偏少,低边人数远少于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这一分层体系的科学性有待提升。因此,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救助改革目标是细化分层社会救助体系,提升精准救助水平,满足低收入群体多元化的救助需求。
三是提升社会救助的包容性和均等化水平。目前,社会救助存在较为明确的社会排斥现象,基于户籍所在地进行申请和救助的制度安排将大量流动人口排除在外,基于城乡分治的社会救助导致城乡差距难以消除,而社会救助事权和支出责任的下移导致了过多的救助标准,且拉大了地区差距;另一方面,对申请者过于严苛的家计调查和资格审核,将贫困边缘人群排除于救助范围。为此,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救助改革目标是提升社会救助的包容性,实现无差别的公民受助权。具体措施包括:整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知》,对基本生活保障进行立法,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生存保障权;打破户籍限制和城乡壁垒,改变以户籍地作为申请社会救助的条件,改为基于居住地(常住地)申请社会救助,保障公民实现平等的社会救助权;明确国家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责任边界和个体应履行的义务,适当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四是提升低收入家庭自我发展能力。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在社会救助日渐强调分配正义,强调社会公民权,强调社会救助的受益水平之时,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受助对象对福利制度的依赖(welfare dependence)。为此,社会救助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减轻对福利的依赖,通过救助达致自立,并融入社会。从发达国家的改革措施看,虽然不同的国家实施了不同的改革措施,改革的理念和发展趋势却基本相同,即采取“无责任即无权利”的积极福利政策,在不削减个人权利的同时,增加个人义务,以此鼓励形成自立的福利政策氛围。实现低收入群体的共同富裕,最关键的措施在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劳动参与率,通过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社会救助则在于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当前困难,助其摆脱发展困境,实现家庭的自我发展。
(三)社会救助改革措施
一是改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夯实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性地位。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救助改革,需要通过“提标”“扩面”两项措施进一步夯实基本生活救助制度。在“提标”方面,改进绝对贫困线计算方法,基于相对贫困理念,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如30%)为计算依据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而较大幅度地提升受助家庭的转移支付水平。在“扩面”方面,改变最低生活保障中“两线合一”的做法,将资格线和救助线分离,将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家庭、抚养未成年人的家庭、赡养老年人的家庭等优先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改变最低生活保障中无差别“差额”补助的做法,以家庭结构为基准,遵循儿童优先、强弱有别和积极福利原则,实行差别化救助,救助标准按家庭等级发放。同时,适应疫情防控要求,扩大非常态化下的社会救助范围。即从低收入家庭、建档立卡已脱贫户、失业人员、因疫情严重影响生活的家庭等扩展到中低收入家庭。根据疫情影响严重程度,将全国划分为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疫情影响一般地区和疫情影响轻微地区,并根据疫情影响等级确定受助对象范围,在实行长时间静态管理的地区,甚至可以将全体居民纳入受助范围。救助资金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分担。同时,积极创新非常态化下的社会救助方式,包括: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给予全额救助,发放持续时间视疫情影响而定;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低收入家庭发放临时生活补贴;对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人员发放临时生活补贴;对困境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及其他有需要的困难群众提供服务救助,对受疫情及防疫措施影响的家庭提供实物救助,对受封控时间长的贫困家庭成员、或因疫情罹患大病、或因遭遇重大变故生活陷入困境的人员提供心理服务。
二是建立贫困分级制度,细化分层救助体系。目前,发达国家通常根据收入的一定比例(如中位收入的40%、50%和60%)将贫困划分赤贫(destitute)、低收入(low income)和贫困风险(at-risk-of-poverty)三个等级。赤贫表现为一贫如洗,生存随时受到威胁,处于贫困的最底层;低收入表现为收入少或者支出超出收入而导致生活困难,其贫困程度稍缓于赤贫状况;贫困风险表现为家庭抗风险能力弱,极易因为灾难性支出陷入贫困境地,其贫困程度稍缓于低收入。我国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后,农村贫困线也退出历史舞台,此后未建立起全面层面的贫困线。为此,建议根据贫困形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要素,以全国中位收入的一定比例(如30%)确定全国统一的国家低收入线;以低收入线的150%和200%,再划分出相对贫困线和贫困风险线,形成低收入、相对贫困和贫困风险三个贫困等级。基于贫困分级制度,对家庭贫困程度进行认定,分析不同贫困程度的家庭特征及救助需求,匹配社会救助资源,形成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见表2)。根据相对贫困下低收入群体救助需求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趋势,建立社会救助个案帮扶制度,针对不同的救助对象,分析其致贫原因和具体需求,制定不同的救助方案,提供持续性社会支持。个案帮扶的重点对象包括社会救助对象、罹患大病或因遭遇重大变故生活陷入困境的人员、困境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及其他有需要的困难群众,对其提供经济救助、心理关怀、社会关系促进、生计发展、危机干预、权益保护等服务。

表2 贫困类型与社会救助项目的匹配
三是改革社会救助管理体制,促进社会救助均等化。将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权收归国务院,由中央政府制定和发布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省(直辖市、自治区)级政府根据中央公布的标准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调整,省级以下各级政府不得再制定当地的基本生活保障标准。调整央地支出责任,由中央财政承担80%的支出责任,根据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划分地方财政承担比例。地方政府承担住房救助、失业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以及面向特定群体的分类救助的主要财政责任和事权责任,中央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对于灾害生活救助,则视灾害等级划分中央和地方责任。视疫情影响程度划分新冠肺炎救助央地支出责任。对于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由中央财政承担主要支出责任;对于疫情影响一般的地区,由中央财政给予地方补贴;疫情影响轻微的地区,由地方财政承担主要支出责任。
四是整合低收入人口帮扶制度,提升受助家庭发展能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通过自身的努力过上美好的生活,社会救助的目标在于助其脱困,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使其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为此,需要采取如下措施:(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贫困发生风险。从社会保障的视角看,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心在于夯实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降低贫困发生率,让更多的人进入到中产阶级的行列。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大幅度提升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升医疗保障水平,完善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福利服务制度,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逐步减轻社会救助的压力。(2)平衡就业与救助的关系,强化家庭生计发展能力。包括:加强人力资本开发,提高低收入群体持续自我发展能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供持续性就业服务;加强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群的就业支持及低收入家庭子女教育救助,提高低收入群体持续自我改善的能力;正确处理就业与救助的关系,构建正向的就业激励机制。(3)消除社会排斥,促进低收入群体的社会融合。构建基于社区的邻里互助、党建引领、志愿活动等为内容的社会帮扶圈,改进服务方式,建立上门探访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将贫困群体融入社区之间;组织贫困群体参加志愿服务、开展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树立贫困群体的责任观念;消除制度性障碍,促进机会平等,让贫困群体获得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
五、结语
我国很早就产生了“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建立了多项社会救济制度,但受到“救急不救穷”理念的影响,社会救济只能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劳动福利制度,社会救济边缘化。20世纪90年代,我国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做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贫困形成的变化,社会救助受助人数持续减少,社会救助的基础性地位受到冲击。而以相对贫困标准衡量,我国还存在数量庞大的低收入人口;受到疫情持续流行的影响,部分低收入家庭陷入贫困边缘境地。而受社会救助资格条件的限制,部分低收入家庭被排除在社会救助之外,导致收入群体的社会排斥感和相对剥夺感日渐增强。
目前,社会救助在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因社会救助在降低低收入群体与总体人群的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救助改革,需要改变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定位,树立适度分配理念,通过夯实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分层社会救助体系、促进社会救助均等化、提升受助家庭发展能力等措施,建立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救助体系,为实现低收入人口的共同富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