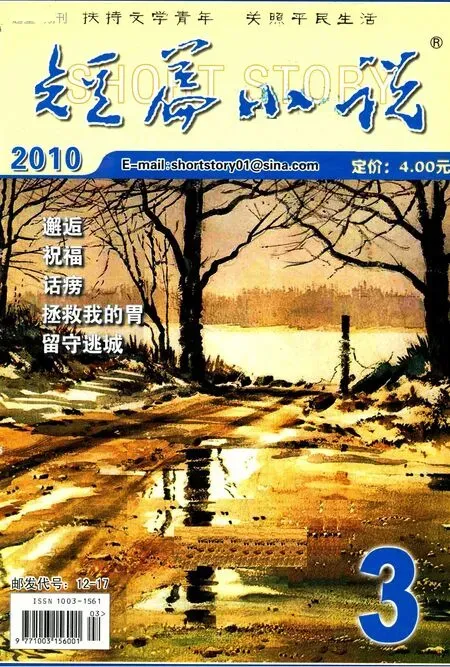飞毛腿
◎冉晴涛
一
早读课放学,徐若虚在初阳之下低着头往家赶,脸埋在阴影里,以为这样父母便不会注意他脸上的红伤。一刻钟前他的鼻子挨了一拳,两股黑血从鼻孔喷涌而出,流进嘴里又腥又咸。右眼则吃了一肘,不大一会儿便肿得像颗油桃,眼皮胀胀的睁不开,他用凉水激了又激,镇了又镇,效果全无。这还只是皮肉伤,至于心里的伤痛,那叫一个没法说!他想好了,到家拿两颗茶叶蛋再捎一包榨菜转身就走,在上学的路上吃——看样子最近三天他都不能大模大样上桌吃饭了,那会暴露脸上的伤情,让家人知道他又吃了败仗。他不想战败。他尽力了。看电视跟陈真和李小龙学的招数他使了一半,边腿、踹腿、扫堂腿,另一半,冲拳、摆拳、勾拳还没来得及用便落败了。他原打算先使拳的,可书上说“手是两扇门,全靠脚打人”,于是就改用腿了,结果边腿被轻松闪过,踹腿则踹了个空,扫堂腿倒是结结实实扫在了毛竹的脚踝上,可人家毛竹非但屹立不倒,还像没事人一样抱起膀子对他嗤之以鼻。徐若虚大惊,他的腿活像扫在了电线杆上,生疼生疼的,忍了一秒钟,到底没忍住,蹲在地上嗤嗤哈哈缓起了劲儿。毛竹岂能容他,趁他痛,不能动,右手一拳砸向他的鼻梁,左手一肘正中他的右眼。

回家路上,徐若虚一边照镜子察看伤痕,想法子遮掩,一边反思败因,他琢磨,“先出拳会不会好一点,好歹可以护住面门;腿嘛,见机行事,有机会就踢一脚,没机会就做个样子吓唬吓唬……”但他马上又否决了这一方案,先出拳估计腿就没机会出了,然而他那两条竹竿一般的细胳膊还不如麻秆一般的细腿给力。显而易见,他太瘦了,空有技术,没有力道,全是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而对手毛竹十分敦实,脑袋圆如球,一身腱子肉,实打实的一拳抡过来,呼的一声,好比一发炮弹,任你花样百出,硬是招架不住,所谓“一力降十会”是也。这次即是,徐若虚撇开两腿,像只蚂蚱蹦跶了好几下,毛都没伤到人家,自家鼻梁反挨了一拳,差点摔个倒栽葱,虽勉强立住身体,但脚下开始拌蒜,一不留神,右眼又受了一肘,青红紫黑,有如戴了一片墨镜。
说起来,他俩原是一对好友,称不上刎颈之交,但相互抄作业的交情也绝非泛泛,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徐若虚抄毛竹的语文,毛竹抄徐若虚的数学,抄得一字不改,抄得家长打、老师骂,那又如何,照样抄得不亦乐乎!追溯二人之冤仇,源自一次吃奶事件。那天,毛竹吃过午饭上门邀约徐若虚一道上学去——学校离家千米,孤悬村外,四周全是田地,一条细细的小路绕过田间地头从家门直抵校门——徐若虚跟着毛竹走出家门,忽然记起有件要紧事没做,丢下一句“等我两分钟”,扭头便回。毛竹好奇,紧随其后,只见徐若虚钻进堂屋,掀起正吃饭的妈妈的衣襟,扑进她怀里像个小宝宝咕叽咕叽吃起奶来。毛竹惊得眼角都瞪裂了,一下午半个字没说,课也听不进,脑子里回旋往复就一句话:“他还吃咪咪?他还吃咪咪!他还吃咪咪……”眼瞅着要放学,毛竹憋不住了,他的嘴巴奇痒无比,不说话磨一磨不行,搞不好能痒死!说点啥呢?“你们知道吗,徐若虚还吃咪咪呢,他都五年级了,十二岁了,还像个小宝宝趴到妈妈怀里就吃。他也吃饭,咪咪是饭后甜点,就像电视里的美国人那样。”
校园里,徐若虚仍在吃奶的新闻倏然间到处流传,有人当面嘲笑他不知羞,大小伙子了还吃咪咪,预备吃到几岁呀?徐若虚抵死不认,说他早就不吃了,两岁就戒了。一群人七嘴八舌指证他,只因道听途说,反被徐若虚呛得直咽口水。情绪特别激烈的那几位实在气不过,顺藤摸瓜将消息源毛竹揪了出来。
“你说,他是不是还在吃咪咪?”一伙人簇拥着毛竹跟徐若虚对质。
徐若虚一见毛竹,脸噌一下白了,但他稳住阵脚,不慌不乱地反问:“毛竹,你啥时候看见我吃咪咪了?”
“毛竹,你倒是说呀……他要是没吃咪咪,你就是个谎话精。”众人指手掐腰,向毛竹施压。
毛竹望一眼徐若虚,徐若虚回望一眼毛竹,两双眼睛里满是乞求,一个乞求别说,一个乞求原谅。
“说呀,毛竹,证死他!”
“他吃咪咪,”毛竹伸出右手朝对面缓缓一指,“我亲眼看见的,今儿中午。”
“你发誓?”众人继续威逼。
“我发誓。”
众人一齐将头扭向徐若虚,个个神气活现,好像刚刚捉了贼,拿了赃。
徐若虚眼泪汪汪,不看众人,只盯着毛竹,咬牙切齿骂:“我操你妈!”
此事之后,二人彻底掰了,作业再不互抄,成绩扶摇直上……不过,两人开始较劲,得手就修理对方一回,修理完,吃亏的不甘受辱,一门心思找回场子,打架动粗便在所难免。
二
他们村名叫望月楼,村子南边有条小河,名为巴清河,上接黄河,下通东海,水至清且有鱼,农忙时口渴,村民们趴河边咕咚咕咚只管牛饮,那情景有点像广告:农夫,水长,有点凉。徐若虚头一回跟毛竹干架就在这条河边,大夏天,毛竹农活干得口干舌燥,跑过来扒开水草埋头就喝。徐若虚溜到上游十米,敞开裤腰往河里撒尿,边尿边感慨:“我这童子尿啊,包治百病!”毛竹也不是好欺负的,上来揍了徐若虚一拳,徐若虚还他一脚,两人你来我往,斗了两个回合,徐若虚身子虚,被一身钢筋铁骨的毛竹撂倒在地,落了个鼻青脸肿。
当时徐若虚不会游泳,洗澡只敢在水浅的地方瞎扑腾,有次不慎玩脱了,滑入深水中,脚下没了底,心里更没底,这回可不是瞎扑腾,是玩命地瞎扑腾。嘴巴好不容易露出水面,刚要喊人,河水立刻涨上来堵了个严实——两年后上了中学他才得知这种情况科学术语叫液封,免得漏气,当然也省得喘气——扑腾吧,少年,每露一次嘴巴就是一次希望,随着咕咚一口水下肚,希望变失望,不过请别绝望,人不死,扑腾不止。
后来自然活着登陆了,不然也就没有后来了。当时一群人在洗澡,只有毛竹发现徐若虚溺水,其他人都玩疯了。待徐若虚抓住岸边的水草颤巍巍地捡了一条命上来,毛竹抢上去嘲讽:“不赖不赖,喝水真快!”
徐若虚肚皮撑得溜儿圆,跪地起不来,抚着水饺一般的肚子刚要骂,无奈腹中水压过大,一张嘴便喷出一道水剑,活似科莫多巨蜥倏忽伸出的长舌,区别在人家的肉舌有去有回,徐若虚的水舌有去无回,他也不想它回。
大难不死,再下河徐若虚就会凫水了,而且无论怎么扑腾再也沉不下去了,至今他都不会潜泳。他寻思,“上一局被毛竹瞧了笑话,不行,得扳回来,脸比钱值钱。”
第二年雨水少,巴清河一下窄了许多,几乎没了深水区。池浅王八多,河浅水蛭多。下河洗澡的赤条条上来大呼小叫:“快看,我背后有水蛭吗?”
机会来了,徐若虚尖声冲毛竹咋呼:“哎哟喂,你左边屁股上趴着一条。”
同伴们心领神会,没人点破。
毛竹前世铁定是吸血鬼弄死的,一听身上附着个吸血的家伙头发都炸毛了,使劲扭头找,双手在屁股上胡抓乱挠:“哪儿呢?哪儿呢?”
徐若虚故作惊恐:“别挠了,水蛭你还不知道,越挠越往肉里钻。”
毛竹带着哭腔求救。徐若虚慢悠悠握紧鞋底:“治水蛭,你懂,就一招绝活,打!”
徐若虚的塑料鞋底结实又柔韧,是件上好的刑具,抽上七八下,毛竹的屁股就成了发酵的白面,肿得老高。
“水蛭呢?”毛竹问。
“掉河里跑了。”
毛竹起了疑心,看热闹的同伴绷不住,纷纷笑出声。“你他妈诓我呢?”毛竹的眼角又瞪裂了。
“我他妈诓你呢。”徐若虚两手一摊,干干脆脆认了账。
毛竹瘸着被打肿的左腿要跟徐若虚算账。徐若虚往水里一窜,施展卓越的泳技奋力朝对岸游去——正是这次占了便宜且成功逃离的经历给了徐若虚灵感——他从家拿了茶叶蛋与榨菜,一边往学校走一边思索,“干吗不学学红军以弱胜强的战争法则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他知道走字在文言文里是跑的意思。
“对,打不赢就跑。”主意已定,徐若虚决定练习跑步——跑得快,不失败。
三
望月楼往北有一条直路,像木工用墨斗打了线一样直,而且路面平整,平整得像天天过压路机。此路宽五米,长五里,直通乡镇,路两旁栽满杨树,杨树之外是农田,放眼一望,满目青翠,是一架天然的跑步机。徐若虚穿了一双新鞋,上来就是一通冲刺,冲了四百米,口干舌燥,眼冒金星,心脏咚咚响,两肋插刀疼,先前憋着的那股劲随着玩命的奔跑箭一般射了出来,释放一空。徐若虚脑袋清明了,扶着路边的杨树一面喘息一面思考:“步不是这么跑的,我太急躁了。”
十分钟后,调息均匀,继续跑,这回徐若虚释然了,既然跑步非一日之功,急又有个鸟用?反正毛竹跑不了,今后跟他较量的日子长着呢。这么一想,徐若虚心里敞亮了,步伐不疾不徐,一口气跑了二里地,刚好跑到这条路的终点,此处左右无村,前后无店,坟墓倒有一大片,分散在两边的庄稼田里,据说是两大家族的祖坟地。这些高门大户的祖宗徐若虚是不放在眼里的,唯东南角上的一座大墓令他肃然起敬,墓主人自己一家,并不身属两大姓氏,称其墓葬为大墓,是因他的坟头着实不小,比普通者大三倍——小了不行,小了埋不住他!他个子很高,两米开外,而且膀大腰圆,天生神力。他叫什么名,徐若虚并不清楚,坟前也没有石碑提示,但他的外号方圆百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称飞毛腿。
飞毛腿的传说很多,说他喜欢追兔子,兔子一步窜三道红薯沟,他一步窜五道,田间地头经常有这样的奇景:他在前面堵,狗在后头追,中间夹着一只沮丧透顶、生无可恋的野兔。传颂最广的是他替村里买石磙,去江苏徐州,全程一百八十里,他早上动身,中午回转,一路风尘仆仆,回来肩上一边扛一只石磙,每只重一百八十斤。传得最神乎的是有一晚他和朋友喝酒,酒喝多了尿急,他出门小解,回屋时满头满身的雪花,他一边拍打一边嘟囔 “下雪了,下雪了”。朋友推门一看,不对呀,月明中天,满地光华,何来下雪一说?哦,他憋坏了,跑着去的茅房,一不留神跑过了,跑远了,跑到下雪的地界去了。
徐若虚佩服死了,好一个飞毛腿,好生了得,冲他老人家的面子他也要好好练,假以时日也来个健步如飞,五道红薯沟一窜而过,把兔子、狗和毛竹全甩在身后,甩得远远的。
坚定了信念,徐若虚开始每日一练,赶早起床,先热身,跑上半小时再去学校,除非下大雨,否则跑不停。坚持了一个月,跑坏了两双鞋,成效初现。再和毛竹斗嘴,徐若虚不由分说上去抽了他一个嘴巴子,然后拔腿就跑。毛竹拼死追赶,发誓要以嘴巴子还嘴巴子,两人相距最近时不过一步之遥,可就是这一步,到底也没追上,白白被扇了一巴掌。初战告捷,徐若虚没有自满,毕竟是险胜,毛竹的手臂再长半尺估计就逮住他了,少不了对他又是一顿胖揍。
谦逊自知的徐若虚又苦练一个月,这次原地踏步竟然没有长进,他不信自己已达极限,他可以跑得更快,像飞毛腿一样贴地起飞。村里有位老人指点他,不妨在腿上绑缚沙袋,锻炼腿部肌肉,增强爆发力。徐若虚从善如流,采纳了高见。天气渐冷,沙袋绑在两条小腿上,外罩绒裤,重是重了点,抬腿也费力,但保暖相当不错。
一夜北风吹,杨树叶黄了,杨树叶枯了,杨树叶落了。那条直通乡镇的直路上行人日渐稀少,尤其早上,风吹得冰冰寒,地冻得梆梆硬,行人就更少了,经常跑到两头徐若虚只碰见他自己一个人。他劲头十足,从不抱怨,从不偷懒,与毛竹的冤仇也被暂放一边,因为他忽然有个更大的想法,他要做飞毛腿,还要向阿甘学习,从国家的这一头跑到那一头。
太阳去了又返,日照由南向北,天气一天暖比一天,转眼开春,冻土融化,杨树长新芽,地里是蜷了一冬如今眉开眼笑的庄稼。这一天,徐若虚一抬眼,不远一辆山地自行车驶来,正是毛竹的座驾。
“听说有人要当飞毛腿,”毛竹刹住车,嘴撇得像裤腰,“看把他能的,有本事先赢了我的自行车。”
徐若虚就地画了一条起跑线,人车并齐,毛竹放了一声响屁,二人闻声而动,一个猛跑,一个猛蹬,人向前,车也向前。初始人占先机,跑起来风驰电掣。车则紧追不舍,换挡再换挡,终于迎头赶上,齐头并进。徐若虚一瞅,“看你还有几挡好换,”脚下发力,不断加速,重新拉开距离。毛竹将挡位调至最大,全速前进,累得呼哧呼哧喘大气,总算又赶了上来。徐若虚正要再次加速,恍然若有所悟,喊了一声停,滑出几步,呼一口气说:“今天就到这里,平手。”
毛竹喘得比徐若虚厉害多了,却老大不情愿:“别呀,你不会怕输吧?”
徐若虚扭头就走,扬扬手:“明天再来。”
毛竹同意:“你不来,你是我孙子;我不来,我是你孙子。”
第二天还是那条起跑线,仍然没有发令枪,徐若虚不等毛竹憋屁,说:“你先。”
毛竹当仁不让,山地车嗖一声飞了出去——骑出老远却不见徐若虚追来,毛竹回头一瞥,只见徐若虚杵在原地尚未起跑。毛竹冷笑:“老子赢定了。”话音落,一条人影哧溜一下从他车旁闪了过去,晃得他两眼一花,回过神定睛一瞧,不是徐若虚是谁!只是——他妈的,他那是跑步吗,分明在跳跃,像袋鼠,脚一沾地立刻弹了起来,斜着向前,一弹就是好几米。
毛竹的车挡已然最高,调无可调,只好从车座上抬起屁股左一歪右一歪全力踩车。踩了两分钟,突然捏住刹车紧急减速,随后车把一扭,掉头就走——毛竹明白,再想追上徐若虚已经不可能。这一点,徐若虚同样心知肚明,昨天当他意识到是时候摘去绑腿了,便料定今天必赢,不过没想到赢得这么轻松,两脚仿佛装了弹簧,不能沾地,一沾地即刻弹起。毛竹虽败,事却没完。一星期后的一天,徐若虚正在那条专用跑道上奔跑,忽然背后传来引擎的突突声,不用看,来了一辆摩托,听动静,马力不小。
“你不是飞毛腿吗,敢不敢再比一场?”毛竹嘴巴撅得能挂住油壶,骑在摩托后座不可一世地发出挑战。驾车人是他表哥,去年刚上大学,一身运动装,理了个寸头,满脸青春痘,像癞蛤蟆皮。
“就以这棵树为线。”徐若虚手指路旁一棵白杨,接下战书。
“你先。”毛竹假客气,他表哥却不肯吃亏,一拧油门,嗡一声飞驰而去。
徐若虚深吸一口气,奋起直追,两只脚尖轮番点地,频率极快,看得人满眼重影。他一步一纵,宛若身怀武当绝技“梯云纵”,三纵两纵便超越了摩托。
毛竹双腿夹紧座位,好似骑在马上,左手抓牢靠背,像握着缰绳,右手挥舞,像挥着马鞭,催促表哥:“加油门!加油门!”摩托喷出一股黑烟,猛然提速,十秒即赶超徐若虚。徐若虚今非昔比,也不是易予之辈,他身躯微躬,将浑身的力气倾注于两腿,足尖一点,再一点,又一点……两耳当中全是破风之声,几乎听不见近在咫尺的摩托轰鸣,十秒不到,他又领先了。
“加油门!加油门!”摩托风阻之大促使表哥极力压低身体,差不多趴在了车上,长满青春痘的脸绷成了酱油色,好像不是在骑摩托,而是背着毛竹在跑。摩托吭哧着追了上来。
“加油门!加油门!”风吹得毛竹睁不开眼,他闭着眼睛趴在表哥背上发号施令。
徐若虚的上身躬得更低了,竭尽全力的对抗已使他感知不到身体存在,全身上下似乎只剩两只脚丫在不计后果地狂奔。被逼至极限,他自觉非常幸福,一种虚空感使他渐渐沉入催眠状态,摩托在旁,一忽儿靠前,一忽儿靠后,一忽儿与他相持不下。车上两人缩成一团,紧贴着,有若两只在寒风中相互取暖的毛猴。
人终究不是机器,拼命跑出四里地,徐若虚的神经疲惫至极,竟回光返照般渐次恢复了知觉,从下往上,先是脚,再是腿,接着是小腹,然后是胸膛,继而是头脑,其中胸膛里的心脏最为清晰,它正隐隐作痛。动力受损,徐若虚脚下稍一放松,摩托便一寸一寸地越过他,弃他而走。他想拉它一把,手伸出,摩托却没影了。它跑掉了,像亡命之徒夺路而逃。
徐若虚摔倒在地,翻了几个滚,他不疼,就是有点难受。
摩托在前方兜个圈,转了回来,毛竹踩在脚蹬上起身冲徐若虚喊叫:“哈,飞毛腿?用台湾话说,‘你不如摩托耐操’,哈哈。”
徐若虚瘫在地上,有气无力。
经此一役,毛竹自以为击垮了对手,徐若虚将萎靡不振,中止跑步,那条五米宽五里长的大路会从此无主,与风寂寞……可他哪里想到,第二天,天刚放亮,徐若虚便站在了路口,与往常一样,杨树立成两排,庄稼一望无边,全都翘首以待,等着一个人从它们身旁飞奔而过,像一股风,像曾经的飞毛腿——不过徐若虚没有跑,他边走边想,跑不过摩托又怎样,跑得赢毛竹就行。除此之外,他还要当飞毛腿呢,还要学阿甘跑步横跨祖国呢。再说他练了三九,却未练三暑,半年就能把一辆摩托比得冒黑烟,他干得不错,不能要求更多了。
走着,想着,东天边开始冒红,太阳就要露头了。徐若虚不停地走,一直走到路的一半,走到飞毛腿墓。太阳升起来了,他望一眼前方,往左右手心分别吐了一口唾沫,然后迈开腿脚轻盈地跑了起来。他身披朝阳,越跑越快,越跑越远,不久便隐身在逐渐消散的淡淡的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