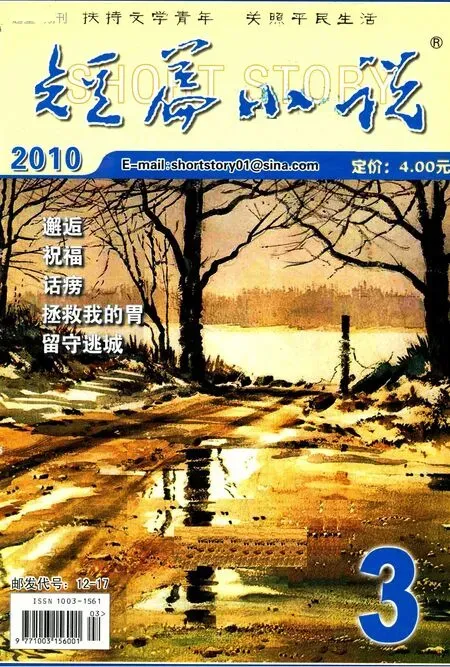锤子剪刀布
◎杨 明

119路公交停靠碧江街站,张青华透过车窗向街对面的五楼和四楼望两眼,习惯地按了三下轻柔的喇叭,两声短暂,一声悠长。
前边两声给五楼,后边一声给四楼。
五楼楼窗明亮,张青华父母家的,四楼垂遮着淡粉色的窗帘,春雨家的。
现在是冬季了,家家窗子紧闭,喇叭声不一定能穿透玻璃传进屋里去。但张青华觉得他们都能听到,因为那是他的心声。
乘客很快乘降完毕,张青华稔熟地把车开走。
在以前,张青华路过这里时是只按两声喇叭的,给父母报个平安。大约半年前吧,添了后边的这一按,绵绵的问候。
半年多以前,有一天下午,张青华跑完了末班车回到总站点的停车场,看到一辆拖车拽着一辆破得稀里哗啦的公交车往外走,张青华忙从自己的车里跳下来扬手追着喊:等等——等等——
张青华跑上那辆破车,从窗边拆下一只破窗安全锤来,拿在手里掂了掂。
哎,青华,你要它干啥?车队长老冯在窗外问。
这锤儿又小巧又轻便,好用。张青华说。
干啥用?
张青华下车,摸出5块钱递给老冯:冯哥,给,帮我给公司上缴一下,够不?
老冯不接,说:我问你干啥用,你给我5块大洋,行贿也不是这么个行法嘛。张青华趴在老冯耳边嘀咕了几句,老冯点头说,哦,这样啊,挥挥手,那还要啥钱,一个报废车上的东西。
张青华把钱硬塞进老冯手里。
下班交了车,张青华拎着小锤儿徒步去了离总站点五站地外的父母家。
张青华离婚好几年,转眼三十开外,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放心不下的只剩年迈的父母。
父母都七十来岁了,不肯和张青华住在一起。天下父母心是一样的,孩子还年轻,有合适的还应当再找一个成个家,享受他自己的幸福,不要拖累他。
碧江家园是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建成的开放式住宅小区,都是些没电梯的老式楼房,张青华父母住的五楼就是顶层。每天晚饭后老两口出门遛遛弯,回来互相搀扶着顺楼梯一级一级往上爬。上次张青华来的时候看见父母刚进楼门,暮色苍茫,楼道里模糊一片,老父亲抬起头喊了两声,可声音虚弱混浊,中气明显不足,连喊两声,楼道声控灯竟然没亮,不知把谁家的小狗惊动了,在门里汪汪欢叫起来,楼道里这才乍现光芒。张青华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忙上前扶住二老。
一般人进楼只要一跺脚灯就亮了,人老了腿脚没劲,跺不动了。
张青华来到小区楼外,转了一圈没看到父母,打了个电话,知道他们今天没下来,都在屋里,忙说我马上就上去。
张青华进了楼道,掏出破窗锤在铸铁的楼梯扶手上轻轻一敲,声音不太大,连小狗都没应声而吠,但比砸鸡蛋壳还脆,感应灯唰地亮了,张青华快乐地一路敲敲点点到五楼,楼上楼下一片光明。
又过了七八天,张青华再来时,还没到单元门口就在夜幕里遥遥听到父亲在楼道里的叫声,张青华心里一翻个,三步并两步跑上前去,搀住父亲紧跺了几脚,先把灯震亮了,说,爸,怎么忘记带锤儿了?却看到破窗锤正握在母亲手里,忙又问,妈,为啥不敲?母亲用手一指,张青华一看,楼梯扶手从下到上缠了一层厚厚的棉布,小锤敲到棉布上只噗的一声闷响,还没有喊声清晰呢。张青华说:啊?这谁干的!父亲说,什么叫谁干的,说话还这么不中听,你以为谁都像你似的一言不合就开干?这是人家四楼那家缠上的。张青华抬腿一步三个台阶就冲了上去,母亲忙叫:哎,小华,小华你回来——
张青华一路看到从一楼到四楼的楼梯扶手都被棉布缠了个风雨不透,心头火更大了,奔到四楼连门铃也没按直接就重重地敲门。
好一会儿,门里传来老年妇女惊疑的问声:谁呀?
张青华说:楼上的,开门。
哦哦,来了来了,门还是没开,里边问,请问有什么事呀?
张青华嚷道:为什么在扶手上缠布,安的什么心,不知道我家老人喊灯吃力吗?张青华听到里屋门响,有人出来走到门后,门半开了,一个老太太和她身后的一个少妇,互相看着不知所措。这时候张青华的父母气喘吁吁地赶到了,老父亲忙向老太太和少妇赔礼,回头对张青华呵斥道:混账,干什么你,还不给我滚回家去。夺过他母亲手里的小锤儿硬赶着张青华回到五楼自己家。
老父亲把锤儿撇到地上喘大气,母亲说:小华呀,楼下住的是一个刚搬来的租户,婆媳俩,人家老太太也像你爸和我似的,身体不好,老太太腿脚没劲,上楼的时候得用手拉着扶手,这不冬天了嘛,这扶手又是铸铁的管子,滴水成冰。上岁数的人出门忘这忘那记了口罩忘手套,人家媳妇怕婆婆拉扶手时手凉,就用棉布把扶手缠上了,你说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去踹人家门呢?
张青华说:我没踹,是敲。老父亲说:天底下的门有你这么个敲法?手比锤子还恶。人家可没像你那样只顾着自己,人家在扶手上缠棉布,也暖了我和你妈的手,人家住四楼,可你没看到从四楼到五楼的扶手上也缠了棉布吗?要照你的想法,那还得是人家坏事做绝,从楼底到楼顶成心不让你爹妈敲灯了呗,哼,小人之心。
张青华急了:爸,您打我骂我我都跪着接,我混我承认,可您说我是小人之心,这小人从何说起?我是小人吗我,我、我可是您儿子,我从小就是有家教的。
“呸!”
老母亲说:天爷,他爸,你那嘴小点劲,这破楼,楼上楼下不隔音呐。
张青华不吭声了,他这才恍惚回忆起四楼到五楼间的扶手确实也缠着棉布。母亲眼里泛光:小华呀,你这炮筒子脾气啥时能改一改呀,你也真对得起你爸,你爸当了半辈子铸型总厂翻版车间主任,造出你这么个孽来,后继有人呐,三年前你这样,现在都走到这地步了你还这样,唉。
母亲的泪戳到了张青华的肺。三年前,他在开车时遇到一个女大学生揪住一个斯文男人不放,高声说:你干啥呀这都一路上了你有完没完呀?斯文男人说:我啥也没干,这是公共场所,不是你们家,你说话做事注意点,懂吗?你他妈神经病,幻想狂,真把自己当格格啦,你那两片臭肉白晾大街上都没人稀罕,烂透了你都,又烂又穷,穷疯了是不是,想讹人你挑错地方了!司机赶快停车,我有急事要下,前边政协礼堂有个委员大会。张青华刹车熄了火回过头。女大学生说:大哥,这个人一上车就挤着我又蹭又拱的,还拽我手硬摸他,您看这车又没站满,这么宽绰,我躲哪他跟哪,他还用手机拍我和别的女孩子的裙底,那不就、就……女大学生一下语结了,她指证的“别的女孩子”蜷在角落座位上深埋头看手机,头不抬眼不睁心无旁骛。张青华再一扫,满车低头族都专注地各自看手机。斯文男人焦躁地说:你到底松开不松开,你都无理取闹快十分钟了。抡起手来猛锤女大学生头顶,张青华怒喝:住手,不许打人,政协委员,耽误一会儿你的会,我现在就把车开到派出所去,她说你骚扰,你说她讹人,你们俩让警察解决好了,这车上有监控,谁违法就办谁。斯文男人又是两记扯头发拳把女大学生打瘫在座位上,一边狠踹车门一边破口大骂。张青华的车有点毛病,远光和转向灯线路老化,扳钮时亮时不亮,斯文男人踹一下闪亮一下,张青华刚把火打着又一把熄了火,开门下车转过来揪住斯文男人兜头一拳蹽底一脚,斯文男人爹了一声妈了一声,张青华青着脸咬着牙说:叫你骂人,叫你踹门!
张青华把乘客打进了医院,把自己打进了刑拘所,斯文男人和他家属还起诉了。满车的乘客竟没一个看清当时什么情景的,那女大学生也只是指证斯文男人对她的骚扰和施暴,至于司机为什么参与进来,后来怎么和斯文男人厮打起来的,谁先动的口,谁先动的手,原因和程度,她不知道。
张青华的官司打成了认定轻伤害,判半年缓一年,加赔偿金额四万五。刑拘期间父母前来探视,他抓住妈妈的手忙不迭地叫着妻子的乳名问:妈,脚丫怎么没来?她好不好?您把我的话带到了吗?律师的分析还是和上次一样,没变,只要我态度端正,我这情况也就六个月,她肯等我六个月吗?父亲先骂他,七尺高的大汉子,看你那德行,公交上给你爹争脸,这时候怎么这怂样?母亲拿出妻子的离婚起诉书给他看,告诉他,脚丫说了,半年好办,缓期不行,需立即执行,敢为别的女人打架,说明女学生在他心里的位置比她更重要。张青华在起诉书上签了字。
缓期期间,公交公司既往不咎,重新聘用了他。
张青华当晚在父母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刚起来要去上早班,门铃响起,开门一看是楼下那个少妇。她手里拿着一把剪刀,点头对张青华笑了笑:大哥,大姨大姨父都在家吧?我在楼梯扶手上缠棉布,没给二老留下敲锤子的地方,欠考虑了,对不起啊。张母忙过来说:看你说的闺女,是我们家小华不好,快进屋坐。少妇说:不了大姨,我已经把棉布扶手改过了,想请你们看看改得还合适不。
啊?一家三口面面相觑,忙跟着少妇出来看。
从一楼到五楼的楼梯扶手上,少妇每隔一米左右,把棉布剪去了巴掌宽的一小截,裸出铸铁让锤头能敲到实处。而老人们拉扶手时,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是不会把手抓到棉布外头去的,这么一改,两全其美什么也不耽误。可以想见,这是今天一大早,少妇逐层精心比测着距离一层一层地完成了这项工作的。
张青华的母亲拉住少妇的手不知说什么好,老父亲瞪着张青华,张青华脑袋快缩到裤裆里,头也没抬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声:对不起。逃跑一样出门上班去了。
打那以后张青华和这母女俩就认识了,听母亲说她们是外地人,少妇叫春雨,好像丈夫去世了,婆媳俩相依为命。
张青华再来的时候,先去超市给父母买含钙营养补品,想了想,又买了一份。刚出超市,就看到春雨的婆婆从不远处的菜市场出来,左右手里拎着装着鸡蛋和青菜的方便袋,张青华忙迎过去叫了声:大妈。春雨婆婆一愣,随即认出了张青华,笑道:噢,小张呀,又看你爸妈来了?见张青华伸过手来,刚要说不用不用,张青华已将方便袋接了过去,一直把老太太送到家门口。
到了父母家,张青华把补品拿给母亲,请母亲也给楼下的老太太送去一份。
张青华再来时,有时候就能看到春雨也在父母家里,或帮着母亲做做饭收拾收拾房间,或给父亲读读报纸。其中一次,看到母亲把自己每次来过夜时盖的被子拆洗了,正和春雨一针一线地缝被子。
张青华了解到,春雨比自己大两岁,张青华就叫她姐姐,常找她聊聊天,春雨微微笑着听,说得不多,让张青华觉得她比自己的前妻脚丫更踏实。有时又见难得下楼的春雨蹲在楼门口和小丫头、小小子们猜拳,笑的样子像个贪玩的大孩子,让张青华觉得她比脚丫更童真。孩子们嚷着锤子剪刀布,春雨却说军舰半岛夏威夷,孩子们哄笑她。春雨却认真地说:美国和日本的小孩子也玩这种游戏,锤子,他们说军舰,你们看拳头像不像军舰;剪刀,他们说半岛,两根手指代表一个半岛被分为了两个部分;布,他们说夏威夷,五个手指叉开象征着夏威夷群岛。游戏规则是一样的,锤子赢剪刀,剪刀赢布,布赢锤子,但说法不一样。春雨给孩子们比画着说:你们看,军舰来了,半岛就输了,代表着甲午战争;半岛赢夏威夷群岛,代表美国认为在一场战争中他们输了;夏威夷群岛赢军舰,代表二战中,美国打赢了日本。美国和日本的孩子不仅玩游戏,还在游戏中记住他们的历史,记住他们曾经的光荣与耻辱。
孩子们听不懂,没兴趣听完早已快乐地一哄而散了。张青华却听痴了,仿佛自己成了一个孩子。满心都是羡慕,真有学识,真了不起!隐隐担忧,人家说的啥想的啥,自己能跟人家唠到一起去吗,时间长了人家能总有耐心听自己那些没滋没味一点含量都没有的话吗?后来张青华试探着问春雨以前是不是当过老师,春雨笑着摇头。
张青华在亨得利精品店里选了一块精美的女表,夹在了让母亲托送的补品里。春雨马上来找张青华,把表还给他。
张青华说:姐姐,我没别的意思。
春雨说:姐知道你的意思。这表怎么也得三四千块钱吧?听姐的话,把它退了,你起早贪黑地跑车挣点工资不容易,能省的地方别乱花,多孝敬孝敬父母。这表一看就是专卖店的东西吧,它不值但你的心值,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个。
清早,119披着晨曦停靠在碧江街站,张青华刚想按喇叭,在监控屏幕里看到后门上来一个人,张青华忙回头去看,绽开笑脸。
春雨戴着口罩太阳镜,用眼睛对张青华弯弯笑眉,投了币安静地在空座位上坐下。
张青华没想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菜都多由婆婆去买的春雨上了自己的首班车,不知道她要到哪去,工作场合不好聊闲话,张青华启动了车子。
别看张青华性子急,但却是个优秀的公交驾驶员,服务态度好,技术也过硬,春雨在车上,张青华把车开得更平稳了。一路上,春雨都没有下车,中途把座位让给了一个孕妇,站到了终点。过一会儿,再坐着张青华的车原路返回去。
以后春雨又来坐过几回车。
张青华要给春雨办个月票卡,向春雨要身份证。春雨说:不用办,投币就行了。张青华说:办卡比投币便宜,你不是说过,能省的地方别乱花吗?春雨说:傻样你,再省还差那一回一毛两毛的啊,听姐的,不用办。
这天春雨又上车了。一路到了终点,她刚要下车,等过一会儿张青华把车倒过来后再上来,听张青华咳嗽一声,对她摇头使眼色,她坐着没动。别的乘客刚一下完,张青华轰地一下就把车开出去,大把大把地打着方向盘,比正常行车快了好几倍。春雨叫道:你干吗呀?张青华说:来不及说了。两分钟就把车开到公安分局门外,开门跳下车就往院里跑,边跑边回头摆手:姐姐,等我。
过了五分钟,张青华跑回来,春雨还静静地坐着,问他,完事了?张青华说:完事了,我的妈呀,可憋死我了。春雨看看没有警察跟在张青华后边跑出来,说:啥情况急成这样?军情呗,水火无情,别提了,停车场的厕所堵了,好几天都不能用,只好到这来蹭厕所,刚才差点把我憋爆了,张青华坐下发动了车子,回头笑说:我也舍不得让姐下车在那干等我呀,天怪冷的。
这天晚上,张青华父母吃过饭又下去遛弯了,约上春雨婆婆一起出去的。张青华和春雨在屋里说话,他们站在窗边,能看到三个老人在楼下小广场上跟着晚练的人们扭广场舞。
张青华对春雨说了自己为帮助女学生伤人惹事及离婚的事,他以前也说过,这次说得更详细些。春雨照例微笑着听完,未予置评。张青华说:姐,听说姐夫去世了,你还在照顾你婆婆,我佩服姐姐。春雨说:这是姐应该做的,姐从小是个孤儿,是婆婆一家把姐带大,你姐夫从小也像哥哥一样疼爱我,人嘛,应该知道感恩和回报。
张青华说:姐……
嗯?
做我的女朋友吧,以后让我来照顾你。
不行呢,弟。
你不喜欢我?
我、我还有婆婆。
那没事,把老人家接来和我爸我妈咱们一起孝敬着。
春雨说:弟,你是个好人,咱们,看缘分吧。张青华忍不住伸出胳膊要来拥抱春雨,春雨食指立在嘴唇前嘘了一声,一指耳朵,张青华听见了门外清脆的敲锤声,张青华也笑了,马上去给父母们开门。
转眼到年底,张青华的工作更忙了,偏赶上老冯又得病住院了,张青华临时顶替车队长职务,替班顶岗无法分身,一连十多天也没抽出工夫去父母家,而且他也忽然发现,春雨已经快一个星期没来坐他的车了。这天总算熬到下班,张青华匆匆忙忙赶到父母家里,刚进屋就听母亲说春雨和她婆婆已经搬走了,走的时候没说什么,父母也不知道她们搬到哪去了。
啊?张青华傻眼了。
母亲拿出那把剪刀说:小华呀,这是春雨留下的,托我带给你。
张青华郁郁寡欢了,他有的时候就怔怔地看着楼梯扶手,抚摸着上边的棉布,有时有意把手握到棉布外头的铸铁上去,让冰凉的温度冰一冰自己的手,冷却一下发烫的心。他握着剪刀叹息,春雨啊,为什么不辞而别?你到底去哪了,去夏威夷了吗?思绪剪不断,理还乱。
车子路过碧江街站时,张青华仍然按下三声喇叭,向车窗外望去,父母的楼窗依旧明亮,四楼的粉红色窗帘开始依旧低垂,过些日子拉开了,间或闪过陌生的身影,再过些日子粉红色不见了,换成了别的颜色。
冬去春来,又很快来到了初夏。张青华觉得父母再拉着那棉布扶手手就有些热了,棉布缠了一冬也有些脏了,张青华想先把它们拆下来,洗干净放着,等到冬天时再缠上。没准冬天里春雨和婆婆就会回来了吧。
张青华拿起剪刀小心地逐层把棉布拆下来,拆到五楼父母门前那最后一段时,棉布下边有东西,是卷在扶手上的几页信纸,张青华忙取下展平了,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娟秀的字迹:
弟,你终于看到这封信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我是个被通缉的人。原来,我在省城的一家银行里当信贷员,也曾有过幸福美满的家庭。五年前,我的丈夫得了癌症,为了给他治病,我们花光了所有积蓄,可还是眼睁睁地看着死神把他越拉越远。到后期他已经不让我再给他治疗了,只想平静而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我不甘心,万般无奈之下,我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
不该走的还是走了,该来的很快就来,我的罪行暴露,只能带着婆婆仓皇出逃,流落异乡,每天躲在不敢见天日的角落里,平时连楼都不下,惶惶不可终日。你第一次砸我家门的时候,我差点没吓死,以为末日来临。
弟,我感谢你给我带来的那些欣慰和快乐,我多么想重新过上正常人在阳光下的生活,我很喜欢你,你那么真诚、纯朴、正直、孝敬,又心细,正是让我敬重又可以信赖的那种男人。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多想投进你的怀抱,哪怕只有一秒钟,哪怕只能给我一秒钟的温暖与安全。
整整躲藏了两年,我不想再这样人不人鬼不鬼地躲下去了,我真的想好了,不管什么理由,欠了,早晚得承担,害怕没有用。你没发现在你把车开到公安局院外时,我就那么坐在那等着你吗?
我唯一对不起也割舍不下的就是我婆婆,她老了,像你的父母一样,我不在她身边就再没有一个亲人照顾她。可她知道我的心事,她更不愿意我天天这样煎熬着,我们这次搬家,就是婆婆的主意。
我给婆婆联系好了在省城的养老院,老人家风烛残年,和我约定,她硬硬朗朗地活着,等着我。这世上,总算还有人能等着我。
弟,千言万语,就先说到这儿吧,今夜给你留言,明早,我去自首。春雨。
张青华去揩眼泪,手里还拿着剪刀,差点戳到眼睛上。
第二天,张青华去了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