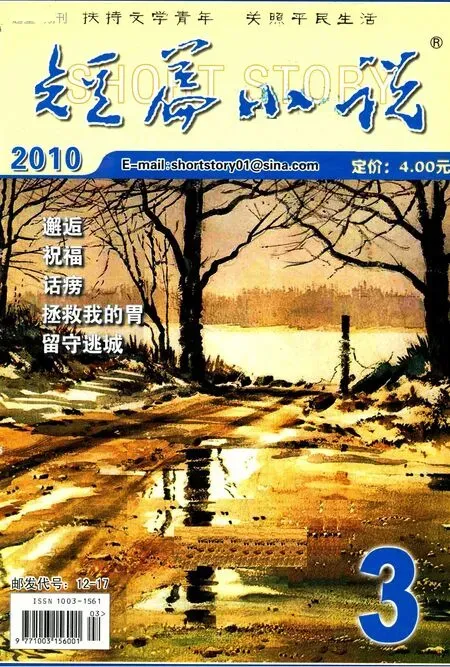杜明的生日
◎王安林

从校长室出来,我马上成了一个快乐无比的人,至于校长刚才说的那些道理,早被我完全彻底地抛弃。
校园里面已经空空荡荡。这让我有点失望。本来应该和我结成一伙的同学都不见了。我一边在心里面骂着那些不守友道的家伙,一边想着是不是还去那个畜牧场。
气候在渐渐入秋,这让我想起那些饱满的果实,这应该是常识。我想着那些成熟的果实生动地挂在枝头,身上涂满诱人的光芒。你根本就无法抗拒。那些光芒会穿过你的眼睛,直达你的肠胃。几乎所有的果实都这样,越是长在高处,越是光芒四射,想采摘到这样的果实就越需要特别的勇气。
这句话好像是刚才校长说的。但他指的不是果实。他的原话应该是这么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勇气,这是我们学校的优良传统”。他指着贴在墙上面的一张照片,“杨——哲——商”,他让我跟着念了一遍。墙上照片上的那个人很年轻,但穿着民国时候的服装,头上的辫子好像是刚刚剪去,像个山民。“我们是哲商小学,杨哲商烈士是我们永远的榜样。”校长一点也不在乎他引以为豪的英雄在照片上的形象。他在那张照片面前,依然保持着他每个星期一上午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做报告时的激情,“这是我们全体哲商师生的荣耀,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他挥舞着双手,很多词语从他的嘴巴里面熟练地跳出来,清光绪、光复会、秋瑾、江南制造局等。
“我知道制造局,就是造炸弹的。”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制造局,“他们攻下了江南制造局,他会造炸弹,他夜以继日地造炸弹,”我得意地用了个形容词,“他造了许多许多的炸弹,多得不计其数。”我挥舞着自己的双手,形容着那些炸弹,完全忽略了面前的校长。
我的想法是真实的,如果我也出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会像杨哲商那样成为英雄。校长宽容地看着我,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我显摆的地方,“他太累了,那些炸弹突然爆炸了,他牺牲了。”我草草地结束了那个故事。校长拍了拍手,似乎是在为我鼓掌,“杨哲商烈士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造炸弹,但你们呢?”校长坐到他的椅子上。
我看到他把一双手摊在桌子上,桌面散乱地堆放着一些书籍、作业本和收缴来的学生物品。我看到了几个不同的果实,两个有点歪的鸭梨,五六颗青枣,还有一个已经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昨天中午,同学们都在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募捐,你们却跑到畜牧场偷摘水果。”校长的声音竟然轻了下去,“有同学说你爬到畜牧场的围墙上,这还不够,你又顺着那棵老梨树往上爬,你只是为了摘到结在最顶上的那只梨子,这就是你认为的勇气?”
我的内心突然产生出一阵羞愧。我回头又看了一眼校长室。我看到校长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在锁门。幸好他没有发现我更加肮脏龌龊的想法。我加快了脚下的步伐,我得尽快摆脱校长的视线。在花坛分叉处,我拐过黑板报栏直接穿过草地,再跨过那排冬青树,那边就是我们自己的教室。教室前面的水泥地面上还留着同学们用粉笔画下的方格,那是女同学用来跳房子的。我希望教室里面还会漏下一两个同学,但我看到教室的门已经上锁了,也就是说,如果我继续要去畜牧场,只能一个人前往。
畜牧场的路虽然有点远,但我一点也不害怕。不要说是白天,就算是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夜晚,我也敢一个人前往。当然,晚上你可能看不到那些藏匿在树叶里面的果实,但我更想看到的是那些更为鲜活的生命,在草地上安静吃草的奶牛,池塘里面的鸭子,养在笼子里面的兔子,最多的应该是猪圈里面的猪了。我想起那只体积庞大的公猪,在猪圈里面横冲直撞,嘴里面发出嘿呲嘿呲的声音,眼睛里面布满红红的血丝,我几乎都感觉得到从它嘴巴里面喷射出来的那种饲料的气味,然而最触目的是那条拖在肚子下面的东西。
我特地绕过整幢教学楼,在教学楼后面的花园里面,我装作是在寻找什么丢失了的东西,低着头,目不斜视,那样东西应该就在某棵树或者某丛花草的下面。校长显然已经走了,但我还是怕碰上某个老师,所以我要装得逼真。我捡起一块玻璃碎片,对着阳光看了一会儿。如果这是一个放大镜,那会怎么样。我将玻璃碎片转向花园。我已经完全进入了自己设置的场景。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透过碎玻璃,我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坐在花坛的水泥边沿上。我放下那块碎玻璃,看清是班里的杜明。他的身体长得太快了,他就算是那么坐着也和我差不多高,他还戴着一副眼镜,我差点将他当成了某个老师。但他是个木头人。也许我说得太委婉了,班上的同学更多的是直接叫他低能儿,甚至叫他傻瓜、笨蛋、呆子。连班主任都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慢半拍”。大家都觉得老师的外号更加有意思。他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慢半拍。老师在课上讲解,所有同学都懂了,只有他仍然一无所知,学习成绩就不用说了,就算是体育课,不管是长跑还是短跑,他总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
“你这是在干什么?”我觉得这句话无论如何都应该是我问他的。我和他虽然是邻居,但我很少会找他玩。和我一起玩的,不仅要手脚灵活,更重要的是要有脑子。他怎么可能有脑子?我如果说,我们去畜牧场吧,他会怎么样?他肯定会说:我得去吃药,我还没吃药呢。我们会怎么奚落他?我们会学着校长的口吻:“你看看人家杨哲商!”
杜明的母亲是个医生。除了杜明,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叫她杜医生。我们并不知道她姓什么,我们只知道她是杜明的母亲。杜医生在校医务室工作,很少有学生会找她看病。除了学生们都很健康,更主要的是杜医生不善言笑。她的脸有点长,又剪了短发,下巴整个裸露出来,那些肌肉绷得很紧,颜色铁青,如果省略去其他部分,与男人差别不大。这样,杜医生就只能够给她自己的儿子杜明看病了。我们并不觉得杜明真的有什么病。如果一定说他有什么病,那就是他的脑子被驴踢坏了。
但杜明会把自己的病说得天花乱坠。“我妈妈说,我如果不去吃药,我的心脏就会分成两半,就像一座房子里面的两个房间,本来应该是相通的,但有人在过道上放了许多东西,在左面房间的人就去不了右面房间。”他说话很慢而且说得很啰唆,我们都没有耐心听下去。但他还是会继续说:“不是我不想与你们一起玩,我如果不去吃药,那些血管就会被堵塞,我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
我们想一个心脏不会跳动的人那就是死人。我们都不愿意和死人一起玩,尽管我们知道他说的本来就是鬼话。他只是为了给自己的低能、胆怯和懦弱寻找借口。
“我想去畜牧场。妈妈说我今天就满十二岁了。”
我看到他站起来,应该是请求我,只是他的个子太高了,否则应该用一只手悄悄地在背后扯着我的衣角。他穿着长衣长裤,衣服上所有的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我想与你一起去畜牧场!”他突然说,“我要像你们一样,做一个勇敢的男人。”
“你说什么,你是说要做一个勇敢的男人?”我笑了。我笑他将我们当成了榜样。如果他知道刚才校长在校长室里面对我说的话,肯定就不会这么说了。
“你知道我们学校为什么叫哲商小学吗?”我模仿着校长的口气。现在我们已经走出校门,我没有往家去的那条路走,我弯上了另外一条路。他的脚步犹豫了一下,但马上跟了上来。他的眼睛看着我的脚后跟,尽量想和我走得一样。他说:“我知道哲商是一个孩子,他的家就在畜牧场那边。有一天他在家后面的山上放羊,山上的树林突然起了山火,他没有跑,而是勇敢地冲上去救火。但火太大了,后来,山火就将他烧死了。”
“你说得不对。”我说。
“说错了,”他很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不能说死了,是牺牲了,老师和校长都让我们学习他。但我妈妈总是对我说,不能去山上玩,如果起火了,也不能去救,那么大的山,那么大的火,就算是全校的老师同学全上去也灭不了火。那不是救火,是送命。”我盯着他的嘴巴。他总是很快地承认错误,但却又总是将更大的错误暴露无遗。我想,也许不应该带他去畜牧场,但一个人去畜牧场也太没意思了。
我们已经走到田野上了。田野不辽阔但很好看,一小块一小块的稻田黄了,有些稻田分布在山坡上,围在稻田边上那些树木有绿有黄还有红的。“我以后会将这些画成画的。”我的口气里面充满了炫耀。我相信自己只要想学,什么都是简单的,不管是数学还是语文,就算是历史、地理以及物理、化学,我只是没兴趣,不像跟在后面的笨蛋。我想,我先将这些画藏在心里面。
路变成了土路,不像回家的路那么平整,我看到杜明的脚步有些跟不上了。我站下来等他。他的脸色本来就一片暗灰,现在更暗了,特别是那嘴唇,都成了紫黑色。我摇摇头,带他出门简直就是一个累赘和包袱。校长经常在星期一的全校集会上说,有那么一个同学,整天说自己有这病那病的,在家里面从来不动手干活,就是倒夜壶的力气都没有。校长说,我们学校不应培养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宝宝书生。校长虽然没有说出这个同学的名字,但当时所有同学的眼睛都盯着杜明。打那天开始,下课后,同学们都会围着杜明,一开始大家都不说话,杜明会奇怪地问为什么围着他。“夜壶!”有一个同学会尖声叫起来,然后,所有人都会齐声地叫“夜壶、夜壶……”这样的叫声一直会延续到上课铃声响起。
杜明终于跟上来了。“还有多少路?”他用两只手轮流擦去那些流下来的汗。由于袖口扣得太紧,让他的动作显得笨拙。“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多的路。”他一边说一边继续擦着不断流下来的汗水。
“远着呢,得爬过那座山。”我想捉弄一下他。他睁开他的眼睛,但没有什么光亮。我想,他看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我突然对他生出一种同情,我指着不远处的两排长长的平房说,那就是畜牧场。我觉得他松了一口气。但他又说:“那些果树呢?”显然,他是为那些果树而来的。我说:“在围墙里面。”他说:“那我们快走吧,再晚,太阳就下山了。”我上下打量着他。我说:“你得将你的衬衣扣子解开。”他很听话,但解扣子的动作同样笨拙。我将他衬衣的袖子往上面卷。我的手指在碰上他的皮肤时有一种碰上橡皮的感觉。袖子卷好后,我再打量了一下,又将他衬衣领子上面的那个扣子解开。
我领着杜明往畜牧场走去。我不回头也知道后面的他利索得多了。“别小看那几只扣子。”我一边走一边说,“你知道孙悟空吗,他为什么怕唐僧,就是因为让唐僧给戴上了紧箍咒。这扣子就像紧箍咒。”
“你说妈妈让我吃药是紧箍咒吗?”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吃药我真的会死吗?”他的表情充满迷茫。“但那些药很贵,我妈妈的医务室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药,全得从国外进口。我妈妈说,如果不是给我买药,日子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在经过畜牧场的大门时,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趴在门卫室里面的桌子上睡觉。他应该是睡着了,我都看到有口水在他的嘴边流出来。但我没有进去。我知道这是一个凶狠的男人。他的床底下藏着很多鞭炮。别看他现在睡得好好的,他的心里巴不得抓到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他会得意地拿出一个铁桶,然后盖在点燃的鞭炮上。他会揪着我们的衣领,将我们的耳朵贴在那铁桶上。更可恶的是他还会让我们脱掉裤子站在门外的阳光下面,他拿那种狗尾巴草来指点着我们的小鸡鸡。狗尾巴草的形状很像我们的小鸡鸡,无精打采地垂着头。“就这么一点点大的小东西,还想来看大种猪交配。”他的话语里面充满了嘲讽,“下次再让我抓住,就让大母猪来咬你的小鸡鸡。”
我带着杜明顺着围墙往后面走,围墙不高,我弓下了腰。杜明也学着我的样子。他的动作明显协调了许多,只是他的个子太高了。我都有点要羡慕他了,我的个子如果像他那么高,这堵墙只要轻轻一翻就可上去。我找到了一个缺口,墙上面的砖是我们扒去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成排的猪舍,而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一块用砖围起来的露天的空地,一头连接着猪舍。我又看到了那只体积庞大的公猪,它在绕着墙转圈,不停地用身体甚至用头撞击着墙体。我让杜明快看。“看什么?”杜明茫然地看着我。“你看它肚子下面的那根东西。”“我看到了。”杜明说,“那是什么?是小鸡鸡吗?有这么长的小鸡鸡吗?”我咯咯咯地笑起来。“再等等,再等等。”我将杜明的头往下摁,“他们马上就出来了,还有母猪,母猪来了才好看。”
果然,两个穿白大褂的人赶着一头母猪出来了。母猪的体积明显小于公猪,走得扭扭捏捏的,似乎有极大的不情愿,两个穿白大褂的还不时地要用手去推它。公猪显然早已经是闻到了母猪的气味,一下子冲过去从母猪的后面将前腿跨了上去,大半个身体都压在了母猪的身上。
“它们打起来了,这样母猪会被压死的。”杜明在为母猪担心。
“你知道什么?”我相信杜明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个,不要说杜明,我们班里面的同学没有几个看到过。“转过来,转过来。”我现在只是埋怨公猪和母猪的角度不对,这样的角度你只能看到公猪那两个大大的睾丸,而我要看到公猪下面那根长长的东西,而且要看到那根东西如何一点一点地进入母猪的身体。
“我不知道它们究竟在干什么。”看来,杜明真的是一个没有脑子的家伙,如此精彩的场面竟然引不起他任何兴趣。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它们在玩什么游戏。”这让我有点恼火,但我又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释这里面的奥妙与乐趣,这确实非常困难。我想寻找一种相似而又通俗易懂的事物来让杜明明白,我马上想起了大人们躲躲闪闪背着我们而又那么热衷去做的那种事情。
我想起自己的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肚子就大起来,然后,我就有了一个小弟弟。过不多久,她的肚子又会大起来,我又有了一个更小的弟弟。只是我不愿意说自己的父亲母亲。“就是你妈与你爸每天晚上都会背着你做的那种事情。”我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杜明想了一下,突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觉得这家伙是存心与我过不去,我生气地说:“就是和你妈一起将你生下来的那个男人。”“我们家除了我没有男人。”他固执地说。他的话让我哭笑不得。但想想他们家也确实没有男人,就是到过他家的男人也是屈指可数。但我还是为杜明找出了一个男人。“去年夏天那个男人,说一口上海话,梳着油亮的头发,在你家住了好几天。”我尽量回忆着那个男人,个子高挑脸形瘦削,在杜明家门口,他从西服口袋里面抓出一大把玻璃纸的软糖给杜明。
“那不是我的爸爸,那是我的舅舅。”杜明一点也不松口。当然,我也没有信心说服杜明。我根本就不关心杜明的爸爸,我关心着里面的公猪和母猪。公猪一直骑在母猪的身上,让人气愤的是那两个穿白大褂的始终挡在公猪前面。我在心里面骂着这两个家伙:“快走开,又不是你们要配种。”他们当然听不到我的抱怨。他们非常认真地说着什么,完全没有将身体挪动一下的意思。
“我们进去吧,”我对杜明说,“进去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我保证你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你会喜欢的。”
“那是我上海的舅舅。”杜明嘟囔着。他的思绪还没有从我们前面的对话中转过来。
“你过来蹲下。”我对杜明说,那堵墙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高。我让杜明蹲在那墙下,我踩着他的背上了墙。然后,我再伸出手去拉他上来。他的身体很沉,他太笨重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拉一具尸体,我使尽了所有的力气还是无法将他拉上来。就在我筋疲力尽时,他的手突然松了。只听到“噗”的一声,就像是一个沉重的麻袋摔在地上一样,我看到杜明趴在了下面的墙根。
“杜明!”我在上面轻声地喊。
杜明一动不动地趴着,没有任何反应。
“杜明!”我将声音提高了一些。
杜明依然那么趴着。但我的声音不能再响了,再响的话,恐怕那边的公猪母猪都听到了。
“行了,你可以起来了。”我从墙上跳下来,“装,你装什么?”我将杜明想象成了那些平时与我一起玩的伙伴,狡猾、诡计多端且爱恶作剧,我得时刻提防着对方会突然间一个鲤鱼打挺,然后若无其事站在你的面前。
杜明没有动。墙下面的草很长,还有厚厚的落叶,他一定觉得这么躺着很舒服,就像是躺在地毯和鸭绒被子上那么舒服。我蹲到他边上,他背对着我仍然是那么一动不动。我想,他不会是装着装着就睡着了吧?我用双手抱住他的脑袋想将这个脑袋扳过来。这时,我发现他的脖子好像是生锈了的阀门,根本就动不了。
“这样就不好玩了!”我对装死的杜明说。我将自己的头也埋进那些荒草与落叶之中。我想看到他的双眼,他一定在偷偷地发笑。但我只看到他的耳朵,连鼻子都看不到。我将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笨蛋,你这样会闷死的。”他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束手无策只好站起来。
这时,我发现围墙里面那两个穿白大褂的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挪动了位置,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整只的公猪,公猪还是那么跨在母猪的身上,但关键的那个时间已经过去。我趴在缺口上看了一会儿。公猪和母猪贴在一起,母猪一动不动,公猪只是偶尔动一下,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我低头看到杜明仍然是那么一动不动地趴着,突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这时我听到了什么声音。我看到有一片树叶落在他的后脑勺上。
我愣了一下,突然浑身不自在起来。我想将手探到他埋在荒草与落叶之下的鼻子前面去,但我不敢。我是突然起身跑起来的。我越跑越快,后来,就感觉自己几乎是飞起来了。我的内心已经被恐惧完全占领,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将它挖出来。我看到了畜牧场的大门,门卫悠闲自得地在抽烟,我当然不敢进去,那只会加强我的恐惧。我继续飞奔,我没有去学校,校长和老师们早走了,就算校长在,我也不敢去校长室。我继续飞奔,我气喘吁吁地飞奔进自己家的院子。这时,我看到了杜明的母亲杜医生。她坐在自己家的窗口往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花,是那种从外面采摘来的野花。以前她都会去买花。她一边插花,眼睛却盯着院子的门。我想避开她的眼光,但她的窗户是打开的。
“你看到杜明了吗?”她站起来,探出半个身子,“我让他早点回家吃药的,今天是他十二岁的生日,你也十二岁了吧?”她好像是在看着我,而她的眼睛分明已经从我边上掠过,“我还说让他叫你晚上过来一起给他过生日。”
我本来想说没看到,但我看到花瓶边上有一个很小的蛋糕,应该是蛋糕店里面最小的一个。这让我想起我们都还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我马上就可以回家了,而那个叫杜明的孩子却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畜牧场后面的围墙下睡觉。院子里面已经没有了阳光,再过一会儿天就会黑下去。应该有人去叫醒杜明。我说:“他在畜牧场后面的围墙下睡觉,我叫过他,但他不肯醒过来。”我真的是认为他在睡觉。
“你是说他在畜牧场那边睡觉?这孩子!”她想将窗户关上,但却碰倒了那个花瓶。她抱歉地冲我笑笑,然后说:“对不起,我得去打个电话。”我觉得她的笑很难看。不过,她的笑本来就很难看。
我如释重负般回到家。吃过晚饭后,我就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我希望不会有人来找我,但我又希望有人来找我。我的脑子里面经常会出现杜明躺在草丛里面的样子,清晰而模糊。
很糟糕,我想,但我毫无办法。我甚至想起我做过的那些梦,梦中的我死了。我为自己设计过各种各样的死法,故事曲折离奇,但我都是英雄无比——我有时候是战斗中被子弹打死的,为了掩护同志;有时候是被铡刀铡下了脑袋,为了保守组织的秘密……我的身上盖着红旗,背后是整齐的军乐队,有许多人向我欢呼,应该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向我欢呼。后来我就睡着了,我还做了个梦,这次我没有死,我是在给杜明过生日,一个很大的蛋糕,比我见过的所有的蛋糕都要大。但杜明闭着嘴,他的眼睛也是闭着的。没有人为他唱生日歌,也没有人鼓掌。
第二天,学校集会。秋天的天气总是那么好,我站在学生的队伍中。今天不是星期一,不知道为什么集会。有阳光照在主席台上,我看到主席台上摆着一排桌子,桌子上放了许多东西,有书籍、衣裤、书包等。校长开始说话,我才知道是在说早一天募捐的事。校长表扬了很多同学,有捐钱的,也有捐物的,桌子上的东西都是同学们捐的。
“但是,”校长在表扬完一大串名单之后,来了一个转折,我知道后面被提到的就是遭到批评的同学了,这其中有我的名字,而且应该是首当其冲。“有个别同学的做法让人不知所措。”校长的这个用词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校长在桌子上拿起一个小瓶子,他一边摇晃着那个小瓶子一边说:“我不知道是应该表扬这个同学,还是批评这个同学?”校长眯起眼打量着那个瓶子,那个动作有点像我昨天看那片碎玻璃。
阳光投射在瓶子上拉出长长的光芒,“这瓶子里面是那个同学自己服用的药片,他要捐献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我不知道这种药片是治什么病的,他说自己是一片一片省下来的。我不知道他省了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贫困山区有没有需要服用这种药片的孩子,就算有吧,等到这小瓶子送到那边,瓶里面的药片恐怕也早已经过期。”当校长的手放下的时候,所有的光芒也就消失了。
我和所有同学的眼光都在人群里面寻找杜明,因为我们知道,全校只有杜明同学每天都在服用这种小药片。但我们谁也没有看到杜明同学。校长又在主席台上面开始说我们是哲商小学的学生,接着说扬哲商烈士的事迹。我想起自己早上出门时从杜明家窗口过时,没有看到杜明,也没有看到杜医生。桌上的花瓶还在,花瓶边上的那块小蛋糕也还在,花瓶边上散落着几枝野花,看来,杜医生一直都没有时间将这几枝花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