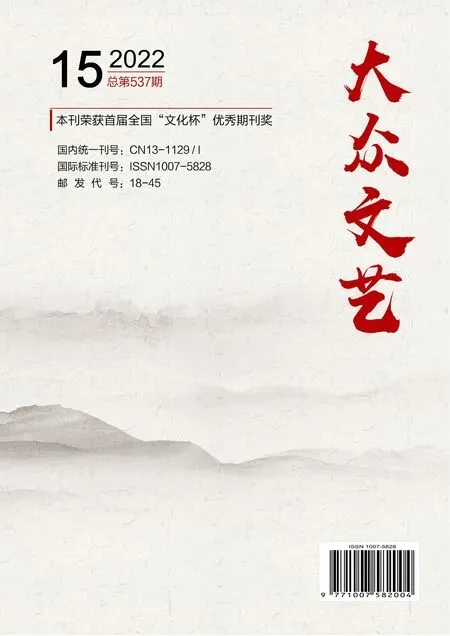创伤,幻灭与静默
——论《千万别让我走》和《长日留痕》中的他者形象
陈娇娇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成都都江堰 611844)
石黑一雄在自己的小说中描述了很多“无法被安慰的人”。这些“无法被安慰的人”往往有着创伤经历,在麻木或者冷漠的环境里,以一种主体性脆弱的状态生活并自我审视着过往以及现在的生活。其中《千万别让我走》和《长日留痕》就是比较典型的作品。本文立足于文本分析,从后殖民主义和创伤理论出发,分析《千万别让我走》和《长日留痕》中的他者形象。第一部分阐述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该理论体系中与本文研究对象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模拟人”概念以及模拟人的生存空间。第二部分分析了两部小说中主人公的视角。着重表述“模拟人”他者在成为叙述主体,反思过去经历时对于主体权威的解构。第三部分从心理学角度对于两位主人公内心的创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试图找出影响他们性格以及重大人生缺憾的内在和外在成因。
一、“模拟人”他者的生存空间
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体系中,他曾经提到过“戏仿(Mimicry)”的概念。Mimicry是后殖民批评的重要术语之一。它汉语中被翻译成多种形式,如戏仿、模仿、戏谑等。在本文中称之为“戏仿”,它是后殖民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身为帝国贵族的男管家,在等级森严的英国阶级社会中,种种言谈举止类似他所服务的英国贵族绅士,但他并不是贵族绅士。他所生活的环境是英国贵族达灵顿勋爵的府邸,与英国贵族相同,但是他自己却并不是这里的主人。小说作者避免以达灵顿勋爵这样的权力来源阶层作为叙事的主体,而选择了在权力机制中被相对边缘化的男管家作为叙事主体。在《千万别让我走》中,同样也是如此。凯西身为克隆人,在各个方面都和真正的人类并无不同,却因为克隆人并不具有人类合法权利而被人类社会边缘化。石黑一雄避免以占据优势地位的正常人类作为叙述主体,而是处于被人类设计和利用地位的克隆人作为主体来讲述,讲述那些优势群体类似又并不真的属于优势群体的人们的故事。这种叙事可以看作一种“戏仿”,而主角从某种意义上又如同模拟实验室中的“模拟人”。
黑尔舍姆学校和达灵顿府邸象征着一座培养类似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中“模拟人”的实验室,凯西和史蒂文斯类似生活在其中的“模拟人”,他们不断模仿自己的控制者,内化权力机制,忽视自身情感需求。在《千万别让我走》中,凯西的就如同生活在一间实验室中。黑尔舍姆学校里的教育是经过精心包装后的灌输。他们被设计为给人类社会提供备用人体器官的机器。克隆人从事服务行业,不能吸烟,不能做伤害自己的身体的事情。凯西和她的同伴在成长中,极力模拟人类生活,迫切希望被人类认可,甚至器官捐献也成为与人类交流的方式。达灵顿府邸也是一个封闭的环境,用机械的规则将人异化,服务于英国社会等级分化严重的权力机制和阶级文化。管家三十年都在走廊,客厅,活动,所见所闻没有变化。史蒂文森执着于管家职责,极力模仿绅士言谈举止,为了职责无视内心对亲情爱情的需求。他们都将自己内化压迫者的一部分,与压迫者有许多相像之处,又不完全相同。“模拟人”生活的空间是被严格限定好的,其中有一系列的规则以保证他们不会超越自己的界限。
“模拟人”生存环境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通常无法拥有或者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在黑尔舍姆学校,孩子们没有自己的原生家庭,在他们成年后,他们也不被允许组成家庭。家庭作为一个人最初的主体性形成、被保护和强化的重要来源,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他们唯一的依靠是学校的老师,但是这些老师大都遵循固有的权力结构,维护固有的规则,不肯将克隆人命运的真相告诉他们,也无力保护他们免于成为器官供体以及帮助他们追求人生的幸福。在达灵顿府邸,管家与男仆的生活有着类似的特征。史蒂文斯也几乎没有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在他成年后虽然暗恋肯顿小姐,但是他工作的环境不允许他分心去追求爱情。男仆与女仆私奔在他们的环境中被视为丑闻。他对于情感的回避也断绝了其追求幸福家庭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权力异化人类,但是真挚的情感等能够使人从异化中恢复人之为人的本质。作为“模拟人”,他们的生存环境以等级森严的权力机制和规则、以家庭、情感等能够有益于恢复人之为人本质的事物的贫瘠为标志,而两位主人公却依然在叙述中表现了对于爱的憧憬和渴望。
二、叙述视角的博弈:从“他者”到“主体”
在许多后殖民主义文学作品中,在历史舞台上长期处在“失语”地位的个人和群体被赋予了表述的权力,来自多样化群体的不同声音汇集在一起,试图取代从前单一化的声音。如此,解读不再是处在优势地位的群体的特权。它重探讨少数族裔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关注差异,允许其寻找自己的声音。因此叙事从原来较为单一的主体转换为多种类型的主体。两部小说均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以追忆的方式进行并在追忆中讲述阶级“他者”,人类“他者”的生涯,主角超出了自身视野的局限,成为另一个凝视的主体,从而解构了原先的主体的权威。作者采取第一人称视角,赋予被边缘化的他者话语权。通过讲述,他们获得一种主动性,分化出实际生活之外超脱的独立自我。凯西和汤米试图用艺术创作证明自己的拥有灵魂,如果他们成功地证明自己拥有灵魂,那么这同时也会证明人类对克隆人的奴役是不合理的。史蒂文森在旅行中的见闻,回忆和反思,也证明了过去关于伟大帝国的幻想不堪一击,自己的付出并无想象中的意义。
在《千万别让我走》中,以学校教职员工为代表的正常人类成了被凝视的对象。艾米丽小姐以及夫人都是这个学校秩序的维持者。他们的初衷是创立一个更加文明的环境,为这些孩子们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们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关怀这些克隆人,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克隆人怀着一丝恐惧。在他们眼中,克隆人与普通人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平等。他们可以自诩高尚博爱之人,会带着怜悯的语气提起这些克隆人,但却无法压抑自己对于克隆人发自内心的恐惧和排斥。在一个克隆人不能被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且不具备人所具有的权利的社会,给予克隆人关怀、尊重以及平等都是困难的。在凯西的凝视下,普通人类面对克隆人的矛盾、脆弱袒露无疑。这些“模拟人”与普通人是如此相似,可以创造艺术、彼此成为朋友以及相爱,但是他们却永远被隔离在普通人的生活之外,永远不能拥有普通人的权利。他们努力模仿普通人生活的样子令人心酸,也更触及普通人类内心对于他们越界的恐惧。而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在旅行中开始审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他的凝视下,以达灵顿勋爵为代表的贵族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逐渐揭开了面纱。以往他将自己看作是帝国运转机器中的一颗小小的齿轮,毫不怀疑这台巨大的机器能够推进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因此,自己也在间接地推进伟大的事业。他从未怀疑过达灵顿勋爵所做的一切。但是在旅途中的反思以及与人们的交谈,使得史蒂文斯看到了这台机器的裂痕。帝国昔日的荣光渐渐消退,新的世界局势正在展开。史蒂文斯意识到,达灵顿勋爵所做的一切并非如自己想象那么伟大。他努力模仿绅士的行为举止,为了更优雅的措辞去阅读英语小说,并且致力于让自己的内心有着和主人一样崇高的理想,为此不惜忽视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甘愿成为帝国齿轮上的一个部件。而在他开始凝视过往,却发现那些真正的“绅士”却并非如自己所想象。这种认真努力的“模拟”对于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的贵族绅士几乎成了一种嘲讽,也引发了史蒂文斯主动的思考和质疑。在这个过程中,“他者”成为主体,成为自己的主人。
三、在静默中幻灭:审视创伤记忆
创伤能够弱化一个人的主体性,使人的主观能动性,批判能力和行动能力都变得更弱,更易受到环境影响。在两部小说中,主人公的创伤记忆与他们所处环境赋予他们的“模拟人”身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创伤往往会导致个体出现感官过载的现象。在生命的早期,个体如果常常缺乏安全感,不能对周围人产生深度的信任和依恋,那么他们就往往难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情感。人类在感知外界信息时会进行一次过滤。而创伤患者的过滤器是敞开的,也就是没有任何过滤。那么这些人就会一直处于感官过载中。为了对应感官过载,他们尝试着让自己变得麻木,或将视野变得狭隘和过分专注。如果他们不能通过自然方式麻木自己,他们可能会用毒品或者酒精来隔绝自己和外界。这一策略的代价是,他们也会把外界愉快的信息过滤掉,也即他们无法全然地感受和追求生活中的幸福。
两部小说中,主人公凯西和史蒂文斯都受到了创伤记忆的折磨。首先,家庭作为一个人出生和成长,建立自我意识和形成健全人格的基础,在两位主人公身上都是残缺的。凯西和史蒂文斯都没有普遍意义上较为正常健康的家庭关系。凯西是被人类“量产”出来作为器官移植备用的克隆人类。在长大成人以后,身为克隆人,也没有机会和权利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凯西成长在全封闭的黑尔舍姆学校里,和无数和她一样的克隆人一样长大。在凯西的生活里,家庭是完全缺失的。她仅仅拥有脆弱的友情和爱情。最初凯西明明知道自己与汤米相爱却选择与其成为朋友,以及在痛苦中选择成为一名悉心且尽责的看护,这些都体现了凯西对于情感的抑制。敏感的凯西早早感受到生活环境的压抑,这种压抑来自她所生活的整个社会。在克隆人整体受到普通人类“奴役”,生命随时可能因为器官捐献而结束的情况下,凯西无法自由释放自己的情感。她不得不学会克制和妥协。而对于史蒂文斯来说,创伤主要来自家庭。首先,其父几乎从不曾给儿子一般意义上的父爱。书中从未出现关于史蒂文斯母亲的描述,其母是生下两个儿子后因故离开了其父抑或是因病离开人世,都全无交代。文中母爱叙事的空白,暗示史蒂文斯母亲的离去可能是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史蒂文斯的父亲和史蒂文斯很有可能共同承受了其母离开所造成的创伤。鉴于他们对此话题绝口不提,那么这份创伤可能在心里造成了较为重大的阴影以致双方都必须默契地缄口不言。史蒂文斯的父亲对儿子缺少温情的陪伴。老史蒂文斯常常给儿子讲述客厅里老虎的故事,核心主题是身为管家的职业素养。而这是一个可以给所有管家男仆们讲述的故事。他对自己的儿子一切公事公办,所有交流似乎都是在公共空间里发生,而不是他和儿子共同构成的私人家庭空间。只有在生命的尽头,他才放下了管家的职业素养和尊严的执着,暴露出了自己孱弱的内心,用颤抖的声音询问儿子:我是不是一个好父亲,对吗?这是书中几处少见的情感流露之一。史蒂文斯的表现也令人心碎。他并没有安慰父亲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在父亲最虚弱且难得真情流露的时候不给予他情感的回应和抚慰。父亲一生极度敬业,尽管客人间接害死了自己的参军的长子,也依然尽职侍奉,并未回避。史蒂文斯同样极度敬业,并未因为父子情而放弃职业要求的体面和克制。这些都暴露了隐藏的家庭创伤。
人在面对创伤时,常常会将自己封闭起来,保持一定的麻木以自我保护。然而,当危机已经过去,却常常难以立刻卸下心防,不再麻木和自我封闭,与周围人产生良好的交流和互动。自我封闭和麻木作为自我保护机制,在危机过去以后,成为新的障碍。从创伤中走出,不再麻木和封闭自己,不再受创伤侵扰常常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处在边缘他者的地位的凯西和史蒂文森,在创伤记忆的压迫下,他们只有选择麻木并依照旧的秩序生活下去,以回避创伤记忆的折磨。凯西可以选择延迟捐献,但她主动放弃了延迟捐献,交出了自己的生命。史蒂文森在质疑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意义后,依然照过去的秩序对待新主人。
结语
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中,“他者”以及“戏仿”都是影响深远的概念。在《千万别让我走》和《长日留痕》中,石黑一雄塑造了两位“他者”形象,分别为凯西和史蒂文斯。他们分别可以看作是普通人类社会中的克隆人“他者”以及古老的英国贵族阶层中的阶级“他者”。尽管他们背负着来自家庭或者社会的创伤,他们仍然在极力模仿“主体”的言行举止,追寻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通过成为叙事主体,他们从一定程度上解构的主体的权威,成了独立的自我。而“主体”也在成为“戏仿”和凝视的对象后,显现出光鲜面目下的重重裂痕。他们受到创伤记忆的折磨,常常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且在故事的最后,依然保持静默。尽管“他者”经历了从天真,顺从,积极合作到彻底质疑和幻灭的过程,但是他们追寻的过程,仍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