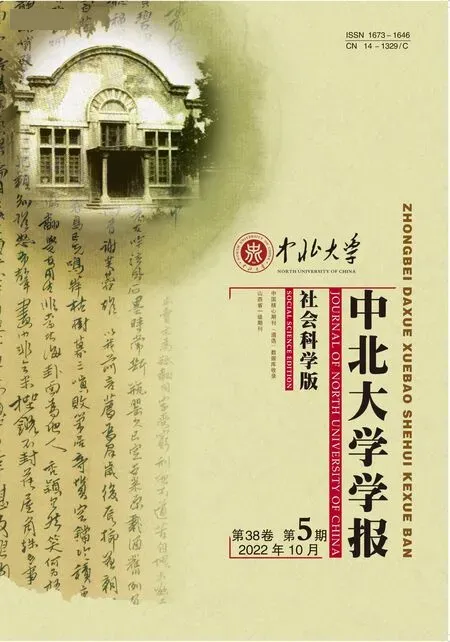山西沁水榼山大云寺史考
赵泽州,侯慧明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大云寺位于山西省沁水县榼山绝顶之上。 寺院始创于北魏,民国时被日军炸毁,曾是晋东南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 寺内历代文人题咏丰富,明代思想家李贽、 诗人常伦都曾留下诗篇; 地方士人,如明代廉吏杨继宗、 晚明重臣张慎言、 清初名相陈廷敬等人亦曾登临揽胜。 目前,关于大云寺的研究较少,部分学者的论著有所提及,如田澍中《梦回沁水》[1]623对榼山大云寺的兴衰、 地域文化进行了探究; 侯志根《沁水佛教史料蒐编》[2]、 贾志军《沁水碑刻蒐编》[3]等书对大云寺碑刻诗文进行了辑录; 仝建平《浅谈山西碑刻书籍的收集与利用》[4]一文论及《榼山寺志》等一批山水志的文献学价值。 本文以《榼山寺志》为中心,探究大云寺的历史变迁以及兴盛原因。
1 榼山大云寺变迁
1.1 北朝始创
关于大云寺的始建年代,据雍正《泽州府志》载:“大云寺,在县东九十里榼山,元魏时建,一名榼山寺。”[5]217宋代《禅院记》载:“窃闻当院古基,有砖浮图一所。 按碑记所述,云是大魏初年,有高僧迁化于阳城县界。”[6]17古记叙述了北魏时,高僧坐化于榼山,被信徒建塔供养的灵验事迹。 榼山寺高僧灵异事迹虽多荒诞,但可能也反映了此时寺院草创,规模较小的状况。
1.2 唐代获敕
隋唐时期,佛教兴盛,榼山寺也获得了官方敕额。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端氏县令张不孤率同僚赴榼山祈雨获应。 张县令撰写了《浮屠赞》称诵榼山寺的灵验:“属县寮寀,尽往祈诚,乃罄腹心,应期降雨……爰因谘议,同为构造……”[6]13按引文之意,应是祈雨成功后,在张不孤等人倡议下,榼山寺得到了进一步修缮。 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该寺“伏蒙天恩赐额,号‘大云禅院’”,并获“敕度僧七人”[6]17。 其时,大云寺获敕,成为有额寺院,表明寺院已获得合法地位,为其进一步发展迎来契机。
1.3 宋元发展
宋元时期,山西境内,佛寺兴盛。 此时,大云寺也有所发展。 宋初,大云寺旧有斋堂“岁时久变,栋宇已坏”,院主道尚禅师率阖寺大众,捐资募化,“重建斋楼五间”[6]15。 宋人傅定基称大云寺:“乃至乡邑川原、 信心男女,归之若晨风之奔北林,百谷之臻东海耳。”[6]15可见,当时大云寺已有相当数量的信徒。 元代,大云寺僧云皓被“敕授都纲”,他曾率众“重修山寺”[6]11。 寺僧云皓既执掌县域内的佛教事务,表明此时大云寺在沁水县佛寺中已有较高的地位。
1.4 明清兴衰
明代是大云寺得到大规模扩建的时期。 从永乐朝至明末,寺内屡有创修。 据《榼山大云寺记》记载,寺院“自永乐二十年,又五六十年来,帑廪克溢,缁徒川涌,突成巨刹,为邑诸寺之首,称主寺”[6]20。 在此背景下,明天顺七年(1463年)至明成化五年(1469年),由僧人全盛住持,寺内完成了一次大规模重修。 其时,寺院住持“大召匠氏,大侈土木”,“先正殿,次法堂,次斋楼,次慈氏,次经阁,次天王、 七佛殿与诸钟楼、 三门、 僧房”,又于“近东南而建伽蓝殿三间,近西南而建牛王殿”,“有余材,而又左右建库庾十二间,廋厨五间,以储日用之需。 化募建塔一驱,高若千丈,以为一寺之镇”[6]21。 此次兴修规模宏大,“视初之制三倍矣”。 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寺僧全彰等人又“同心协力,起造画堂二十有四间,壁绘释氏源流; 大悲殿五间,内大士诸天像; 斋堂六间,厨库各三间,钟楼一所,东西三门二所”[6]23。 其时,大云寺内建筑完备,藏经丰富,接纳四方宾客,教内“道流论法”,俨然成为周边的佛教中心。
明代中后期,大云寺还有多次小规模的修缮,此处不一而足。 明末,社会动荡,大云寺一度遭到破坏。 据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大云寺创修定慧禅院》所载,明崇祯三年(1630年),寺内新修禅堂之时,“土木之工粗毕,彩画未施,兵荒相继,闾左萧然,未终厥役”[6]52,寺内修缮工作因战乱中断。 雍正《泽州府志》载:“崇祯五年七月,贼紫金梁老回回部,自沁水端氏犯县,东入泽州大阳去……十一月,自沁水榼山入境。”[5]1181寺内藏经阁内的经书也被“崇祯年流寇焚毁”[6]5。 社会动乱使寺院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此外,清人张道湜称:“寺有山田数顷,僧徒应差徭。 明末军务旁午,赋额日增,率取办于住持。 人避此席如陷,相率糊其口于四方。 而兴硕、 永祉又相继示寂,方丈室闻其无人。”[6]52可见,过重的徭役使得大云寺僧众四散逃离,寺内主持又相继逝世,寺院往昔的光彩一时不再。
经过清初的社会动荡后,清朝统治者逐渐稳定了统治秩序。 此时,大云寺又有所复兴。 《大云寺创修定慧禅院记》载:“大清定鼎,除繁苛政,以示休息。 一时邑大夫多贤者保护佛法,除僧差,免杂派,而缁流稍稍复业。”[6]53清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1657年)间,为了恢复明末被毁的殿宇,大云寺僧隆翀、 昌觉、 永泽、 昌文等人先后远赴大梁、 荆楚等地募化,将寺内“如大佛殿、 天王殿、 钟楼、 天外楼、 法堂,缺者修,坏者葺,倾者坚整”[6]53。 届时,寺内主要建筑得到修复。
清代中期,见于县志的记载,大云寺有两次修缮记录。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由僧人定乾募化,修德住持,历时4年,将“钟楼而外南殿、 佛殿,以及栖神诸宇,其营建而补葺者,为楹共四十有五”,“计工之费,共银一千五百六十五两有零”[7]976。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清嘉庆二年(1797年),由寺僧修惠住持,寺内“修建春秋阁七楹”,“共费银一千三百余两”[7]975。 从两次修缮的花费来看,此时寺院的财产仍相当丰厚。 清代晚期大云寺的情况,因史料的缺乏,难以稽考。
1.5 民国湮灭
民国大云寺的境况,田澍中老师《梦回沁水》记述:“民国时期,大云寺曾遭到浮山洪汉军破坏。 民国五年(1916年),也曾作为沁水县第二高级中学使用。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后,国民党93军驻扎在窦庄村,在大云寺内办军校。 当时,大云寺遭日军轰炸,大火连烧数日,寺院变成了瓦砾废墟。”[1]701至此,千年古刹毁于一旦。
2 清代大云寺寺院形制及布局特点
结合寺志与学者的民间调查资料,我们可探究清代大云寺的布局特点。 《榼山寺志》卷首绘有榼山总图(见图 1),描绘了清康熙年间大云寺的布局。

图 1 (康熙)《榼山寺志》之《榼山总图》(1)此图由笔者整理拼凑。 参见(清)张鋡:《榼山寺志》卷首附图,国家图书馆藏本。
寺志“寺宇第三”[6]3-8记载了各山门、 楼阁、 殿宇、 僧房、 禅堂的兴建状况。 《沁水佛教史料蒐编》中记有老人对旧时大云寺的回忆:
以东西方向为中轴线,分别建有照壁、 东山门、 钟楼、 厨库房、 天王殿、 禅院、 僧房、 西山门。 中轴线南边,建有法堂、 春秋阁、 诸天护法殿(南殿)、 地藏殿、 天外楼。 中轴线北边分别建有准提阁、 祖师殿、 祖师塔、 禅房、 方丈、 大佛殿、 七佛殿、 藏经楼。 再往北还有弥勒殿、 观音堂、 佛塔。[3]3
中国古代寺院大体分布是坐北向南,主体建筑在南北中轴线上,东西两侧为配殿和生活区。[8]81大云寺不同于这种常规的布局方式,而是以东西为轴线。 轴线上的山门、 钟楼、 厨库、 画廊、 僧房依次排列,这些建筑多为生活设施。 寺内重要的宗教建筑,如释迦殿、 藏经阁、 法堂等坐北朝南,列于中轴线的两侧。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寺院特殊的地形条件。 大云寺所在的榼山为太行山余脉,山麓由南向北延伸,因山形状如“酒榼”,故名榼山。 大云寺坐落于山顶之上,受空间、 坡度等地理条件限制,寺院只能依山势而建,因而形成了这一布局。 这种情况并不稀见,如五台山的佛光寺,“寺因势建造,坐东向西,三面环山,唯西向低下而豁然开朗”[9],永济县的万固寺也是随山势而建,主要建筑并不在轴线之上。
从寺院扩建的历史,可见清初寺院布局的形成原因。 宋代《禅院记》记寺内“初创佛殿三间”[6]17,此佛殿可能为寺院的主体建筑释迦殿。 宋初《斋楼记》记载僧众“重建斋楼五间”[6]15,建于悬崖之上。 又寺志载:“斋堂,金大定丙午,沁水令刘祖寿扁曰‘斋楼’。 明万历乙酉,沁水令赵兰题匾云‘空中楼阁’,又云‘凭栏天外’。 崇祯癸未,张道濬题扁云‘天外楼’。”[6]5-6此斋楼即布局图中的天外楼。 据寺志“寺宇第三”载:“大佛殿,金大定二十五年,沁水令刘祖寿题扁曰:‘释迦殿’,都纲云皓重修。 藏经阁,金大定中,沁水令刘祖寿书扁曰‘龙藏’。”[6]4-5可见,至金代,寺中见于史料记载的建筑有释迦殿、 藏经阁与斋楼。 结合清初的布局图可以推测出,寺院最初的建筑是以释迦殿为中心进行分布,偏向于清代寺院图的西侧。
如上文所述,明天顺七年(1463年)至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两次大修,使得寺院规模扩大了3倍,且明显向东扩展。 其时,清代布局图中部的厨库、 钟楼、 东山门等建筑开始见于寺志的记载。 寺院东山门外的坊表,为“明万历庚辰,寺僧兴晋创建”[6]4。 寺内东北角的定慧禅院由“明崇祯三年寺僧兴硕创建”[6]7。 清初,寺内新增建筑为“康熙二年,张鉁同男道湜创建”[6]7的准提阁,与定慧禅院相对。 这些建筑皆在寺院布局东侧。 随着寺院规模的扩大,寺内建筑由以释迦殿为中心的区域,逐渐向东扩展,至清代形成了布局图中的结构。
综上,清代大云寺的建筑规模宏阔,佛教各式殿宇完备,足见寺院曾经的兴盛之景。
3 榼山大云寺兴盛原因
通过寺志来梳理大云寺的发展可见,天时地利人和对寺院发展的重要影响。 大云寺能成为“沁邑诸寺之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3.1 地理胜景
榼山优美的风景为寺僧提供了良好的静修环境。 明人常軏曾赞叹大云寺的风景:
晋之地,有邑曰沁水。 去沁邑之东百十里,有山曰榼山……其山介乎万山之中,联沁川,接阳、 泽,高数百仞,峰峦秀耸,岩壑万重,望之如画图。 然旁之山,多荆棘杉芑,榼独宜松与柏。 抱岗环谷,如龙蛇状者,皆松柏也。 山有佛寺,处山之绝顶,崇台延阁,甚宏丽,为沁邑之伟观。[6]19
赞词表明了大云寺的几个奇绝之处。 首先,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 大云寺所在的榼山,“东望嵬山,西接琅玕山,北距孤山,南连卧虎山”[6]22,且下有沁河流淌而过,风景秀丽。 其次,榼山的清泉碧巘与怪石奇松乃是一绝。 《榼山寺志》上卷“泉石第二”[6]1-3、 “草木第四”[6]9-10二门,专为记载山寺中的奇景。 历代文人的题诗中也有不少咏叹之作,如明代廉臣杨继宗曾登临榼山,留下了“榼山古刹真奇地,殿下谁栽三大夫”[10]2的美誉,赞叹寺中的“三松奇景”。 李贽的题诗《榼山夜坐》又是另一番心境:“松风已可悲,萝月复飞来。 如何当此夜,万里独登台。”[11]235此外,榼山所在之地,接近沁水县端氏镇。 沁河沿岸坐落着几十个村庄,顺沁河而下更可直达阳城县。 明清时期,随着地方商业的兴起,沁水人文蔚起。 寺院周边的信徒为大云寺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香火,这也是寺院兴盛的重要原因。
3.2 寺僧辈出
宋人傅定基曾记述大云寺兴隆的原因:
粤若助时者教,教重则时平; 存像者宇,宇峻则像尊。 故教借时兴,宇资人立。 其或代之隆替,道之盛衰,亦梵刹所系矣。 然而普天之下,四海之内,山名地灵多矣。 若能全佛宇、 集僧居,历世而不朽者,盖寡矣。 榼山大云禅院者,一居名望,最为胜慨……高僧相继,不计年数。[6]15
傅氏认为寺院能够兴盛,除居于名胜之地外,历代僧人辈出也是关键所在。 《榼山寺志》上卷“释流第五”[6]11-12记载了寺院部分僧人的卓行。 (参见表 1)

表 1 历代僧人事迹表
表 1 中共记18位僧人的事迹。 从僧人分布年代看,明清时期占到2/3,除寺志编撰可能受资料所限,年远僧人事迹失载外,更多反映出此时僧众广大,寺院进一步发展的状况。
以僧人事迹类型来分析,首先,是“修广寺院、 完善殿宇”,约占到僧人事迹的一半。 可见,寺院内部建设、 资金募化、 对外扩展、 寺僧举措都极为关键。 其次,“通晓经典,善辩论说”的僧人有7位,是所载寺僧的重要特质。 最后,以“戒律精严”著称的寺僧有 6人。 寺志所载的僧人,多为历代住持,他们严格戒律,规范僧众行为,是自身职责所在,也为寺院良性发展,提供了保障。 此外,表中所载部分僧人有同外界交往的事迹。 交往的类型可分为佛教丛林内部的交流与士僧交游。 晚明寺僧兴车曾“云游庐山”。 其时,庐山为佛教复兴的中心。 晚明佛教名僧如紫柏真可、 憨山德清、 汉月法藏等人都曾于庐山创立道场。[12]兴车至庐山交流,对于自身研习佛法,应有所裨益,佛门交流亦有助于大云寺的发展。
僧人昌文是大云寺僧与士人交往的一个典型。 张鋡《榼山志序》云:“寺僧昌文请余为志,此余愿也。”[6]1白胤谦《游榼山记》亦称:“诗僧了义,旧刻山志者。”[6]49张道湜《大云寺创修定慧禅院碑记》载:“岁戊申,不佞佐余叔修《榼山志》,今昔名贤碑记,得遍览焉。”[6]51可见,《榼山寺志》即在昌文倡导下,由沁水人张鋡、 张道湜叔侄编篡而成,表明他们的密切关系。 清初,刑部尚书白胤谦,亦有《赠了义上人》 《榼山再赠了义上人》[13]535二诗赠与昌文,可见二人的情谊。 寺内僧人频繁与地方士人往来,可以获取这一群体对寺院的支持。
3.2 士宦支持
大云寺变迁史中频见地方士宦的身影,这一群体在大云寺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他们在政治上往往给予大云寺庇护; 经济上以多种方式给予大云寺支持; 在寺院文化活动与历史传承方面也多有贡献。
3.2.1 历代文人瞻仰大云寺
寺志关于地方士人出入大云寺的记载,最早见于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乃端氏县令张不孤赴榼山祈雨一事,前文已述,兹不赘言。 自唐代以来,寺内文人题咏不断,寺志所收文人诗词共152首,反映了这一群体入寺的行迹。 同时,寺内部分建筑的兴建,也体现了日益频繁与深入的文人活动。 如前文所述,宋初,寺内所建斋楼,即为满足“名流禅子,游憩乎其中”[6]16。 明初《榼山大云寺记》载“先是道流论法,宾客交谈,恒病无其所。 今建东西法堂各十间,斋楼五间……”[6]21,以此供士僧学习交游之用。
相较于寺内修建斋楼,接待士人的举措,明万历年间,僧人在山门外修建坊表一事,更体现了地方士人对寺院的影响。 寺志载:“坊表,在三门前,榜曰‘丛林毓秀’。 明万历庚辰,寺僧兴晋创建。 邑之科第名姓题其上。”[6]4坊表的出现,表明大云寺已与沁水地方文脉相联,这使得寺院更易获取地方士人的支持。 清初,寺内春秋阁的创建,更表明大云寺进一步的世俗化。 据清嘉庆六年(1801年)《修凌霄阁记》记载,寺院原有僧房倾圮之后,寺僧在原址起“春秋阁七楹”,阁内“上层塑关帝像,而文昌、 魁星、 火星诸像,皆附焉”[7]975。 关帝在佛教中被奉为伽蓝神供奉,文昌帝君则是道教与民间信仰的禄位之神,魁星亦为道教中主宰文运的神灵。 寺内供奉以上神灵,显然是地方士绅推动的产物。
入寺观瞻的文人群体中,地方官员的活动可被视为代表。 自唐代以来,域内地方官于任上赴榼山瞻仰大云寺,已然成为了惯例。 他们为大云寺题匾、 作对、 赋诗、 撰写碑文甚至发布禁令来保护山寺。 官员的个人行为不一定能代表官方的态度,但客观上为寺院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庇护。 下表为历代地方官与大云寺相关的事迹记载。 (参见表 2)

表 2 地方官员瞻仰大云寺表
以上官员活动时间,主要集中于明代中期至清代前期,这一时期正是大云寺迅速发展的阶段。 地方官员频繁往来于大云寺,是寺院成为“沁邑诸寺之首”的重要原因。 从官员的活动内容看,多为公务之余,登临榼山,入寺游历。 大云寺俨然成为地方士人聚会之所。 地方官员选择大云寺相聚,一是大云寺的风光绝美,寺院集自然、 人文风景于一体; 二是明清时期,寺院周边的窦庄、 郭壁、 坪上村、 樊庄为沁水县科举兴盛之地。 地方官员出于同本地士人交际的需要,往往将大云寺作为首选之地。 如明嘉靖间沁水令王溱,同樊庄常伦为好友。 王溱入大云寺游历时,常伦曾作诗《游大云寺分韵得然字》[10]3相酬,王溱亦题诗《游大云寺分韵得见字》[10]3与之唱和。 又如窦庄人张錜曾作诗《陪尚子云明府游大云寺》[7]1008,诗中的尚子云乃“顺治乙未进士,沁水县令尚金章”[7]1096。
地方官对大云寺的保护也有一定作用。 清初大云寺重建时,“邑大夫多贤者保护佛法,除僧差,免杂派,而缁流稍稍复业”[6]53。 除免除僧人的杂役外,地方官还发布禁令保护榼山大云寺的树木。 光绪《沁水县志》载:“榼山上有大云寺,佛殿前有白松三株……山木为僧民偷伐,争讼不止。 康熙间,署县事项龙章断为官山。”[7]34
大云寺的奇松一向为地方文人所称诵,被视为寺院重要的文化景观多加保护。 明末沁水人张道濬曾撰写《禁榼山伐树檄》,劝谕乡民、 寺僧不得滥伐树木。 檄文提及“故刘庄靖止尔樵苏,我先宫保严其斩伐”[6]40。 刘庄靖是坪上人刘东星,为“隆庆戊辰进士”[7]1114。 张道濬的先人指张五典,为“万历壬辰进士”[7]1115。 刘张二氏皆沁水地方因科举而兴的大族,可见,地方家族与官府在大云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2.2 张氏家族对大云寺的支持
沁水地方家族对大云寺的支持尤以窦庄张氏最为突出。 关于窦庄张氏家族,清初名相陈廷敬曾感叹:“窦庄者,故沁名区,在榼山下,山绝奇胜,沁水环焉。 所居人多窦氏,里因以名。 然张氏由明以来,为士林华族,实冠冀南,他族鲜可为比。”[5]149据学者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窦庄张氏一门,共出进士7人,举人10人,拔贡生5人,恩荫封赠以及其他途径为官的有20人。”[14]900-902可见其家族之盛。
因居于榼山之下,张氏族人多有出入大云寺的经历。 张五典有《大云寺读书》一诗:“深松开一径,野竹借禅居。 云起龙潜鉢,风翻蠹出书。”[10]10张五典虽浸染于佛寺的熏陶,但称“余既未达于贝叶之书,且不解轮回之说”[6]36,表明他对佛教似无信仰。 其所作《画廊记》[6]34《三松说》[6]36等文,皆为赞叹大云寺风景之作。 五典长子张铨,为“万历甲辰进士”[7]1115,其诗《登大云寺阁眺望》[10]10,亦为题咏之作。
张鋡为“五典第四子,崇祯丙子亚魁,癸未进士”[7]1115。 他有一定的佛学修养,曾撰有《金佛相记》[6]41,多引《金刚经》 《华严经》经义来阐释金粧佛像的意义。 张鋡对大云寺的贡献颇深。 他应寺僧昌文之请,编成《榼山寺志》一书。 全书为上下两卷,上卷分为“本志,泉石,寺宇,草木,释流,文辞” 6门,并附榼山总图2幅; 下卷辑录了历代文人题咏榼山大云寺的诗词。 书中对榼山大云寺的历史沿革、 地理风貌、 建筑形制、 历代僧人、 题咏诗文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 张五典五子张錜,为“顺治丙戌亚魁”[7]1119。 他对《楞严经》多加研习,认为浮屠之说“尤能禁人为恶之心”[6]45。 他曾撰写《募修南殿疏》[6]43,为大云寺僧人募化所用。
张道濬为张铨的长子,他本人对佛教有所信仰。 其文《天外楼记》称:“因忆在南中,欲以跏趺终一生。”[6]40其时,作者身陷明末党争之中,被贬谪后返回故乡,见到大云寺倾圮破败,回忆往昔经历,有感而发。 他亦作《禁榼山伐松檄》劝诫乡民不要滥伐树木,称如此“在佛已干贪戒,于山顿减壮观”[6]41。 张道澄乃张铨第五子,为“崇祯丙子拔贡”[7]1124。 他曾应大云寺僧之请,撰《重修佛殿钟楼记》[6]50,文中对佛教“眼、 耳、 色”与“佛”的关系有一定论述,可见其亦通佛理。 张道湜乃道濬的从弟,为“顺治己丑进士”[7]1116。 他曾于“明季戊寅”,“同职方司李两叔兄少参,共读书于寺(大云寺)之定慧院”[6]45。 他也曾协助叔父张鋡编撰《榼山寺志》,并“发心勉励独创(准提阁)”[6]46,为寺院捐献百余金。 张氏一族与大云寺的联系,直至清嘉庆二年(1797年)仍见于史料的记载。 其时,张氏子弟张心至,“乾隆乙未进士”[7]830,应寺僧慧祥之请,为寺院撰写了《修凌霄阁碑记》[7]935。
此外,沁水县郭壁村王氏、 韩氏也是大云寺的主要檀越。 如王氏家族成员王廷玺,为“崇祯甲戌贡士”[7]511,他写有《禅僧万松圆寂记》[6]38,记述好友僧人祖调的生平。 廷玺之子王度,为“顺治丙戌进士”[7]1116,曾撰《三大士二十四诸天殿募疏》[6]42,供寺僧募化所用。 韩氏家族的韩仰斗,曾为寺院释迦殿题联:“了河沙尘一榼山,来净土证菩提果,三松袛树立丛林”[6]5,给予文学馈赠。 韩张为“顺治乙未进士”[7]1116,其弟韩玙为“顺治己丑进士”[7]1116,韩氏两兄弟也曾出入大云寺,题诗《宿榼山大云寺和韵》[10]17-18两首。 阳城县化源里白氏亦为寺院的香客,如前文所述,阳城人白胤谦与大云寺僧了义交情匪浅,多次入寺礼佛。 其兄长白胤昌有诗《和沁水刘明府宿榼山大云寺韵》[10]19,亦为入寺观瞻的唱和之作。
明万历间至清嘉庆初,正是沁水地方家族因科举显贵的时期,此时亦是大云寺兴盛之时。 由此可见,以窦庄张氏为代表的地方家族,在大云寺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地方士绅不仅为寺院提供经济支持,还予以政治庇护,士人的文化活动更为寺院的发展注入活力。
4 余 论
大云寺历史久远,规模宏阔,沁水境内寺院,无出其右者。 同时,该寺亦为沁水众多寺院的祖庭。 据寺志载,寺之支派有:“嵬山寺(道仁里)、 铁佛寺(端氏镇)、 圣天寺(郎必镇)、 乳窟寺(武安里)、 法隆寺(县东关)、 碧峰寺(县北山)、 十方禅院(王寨镇)。”[6]8
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重修寺宇功缘记》亦载嵬山寺“乃榼山之法,枝同一叶”[15]28,《榼山寺志》“释流第五”记:“全盛,号道隆……兼修法隆、 碧峰二寺,后坐化,三寺分其骨,各建塔瘱之”[6]11,“永哲,号慧光……募修铁佛寺”[6]12,“昌文,号了义……并修王寨十方禅院”[6]12,表明以上寺院同大云寺的联系,由此亦可见大云寺在沁水佛教史中的地位。 大云寺的兴衰变迁,令人叹息的命运,也可看作山西佛教兴衰的缩影。 探究大云寺的变迁过程,可见明中叶至清前期是寺院发展至为关键的一段时期。 其时,大云寺俨然成为域内的文化交流中心,官员、 士绅、 僧人交游频繁。 在三者的共同建构下,大云寺与沁水的文脉联系在了一起。 “丛林毓秀”寄托着地方士子对科举及第的期许,以僧人为主体的寺院也适应了这一需要,寺院内出现了儒学世俗空间,《榼山寺志》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寺志的编撰不仅承载着僧人传承寺院历史的愿景,还包含着沁水地方士人延续本地文脉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