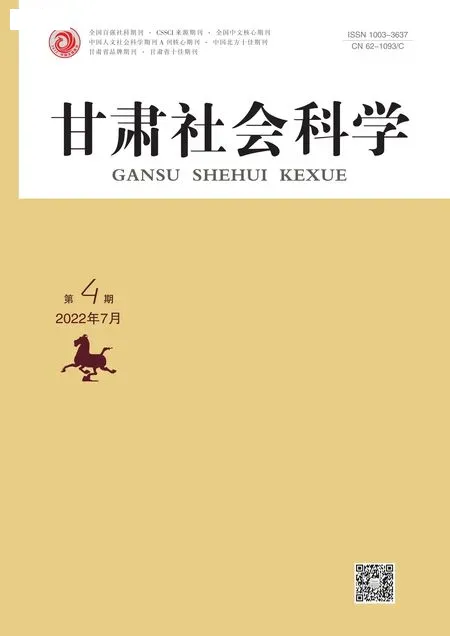勒内·韦勒克对布拉格学派的回忆与评论
昂德瑞·斯拉迪克(著) 杨 磊(译)
(1.捷克科学院 捷克文学研究所,布拉格 11720; 2.云南大学 文学院,昆明 650091)
提要: 勒内·韦勒克早年曾是布拉格学派的成员,且相当活跃。流亡美国后,韦勒克回顾自己在布拉格学派时期的生涯,总体而言,他对布拉格学派及其领袖人物扬·穆卡若夫斯基的学术成就在总体上是肯定的,也针对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梳理韦勒克的相关评论,有助于学界深入理解扬·穆卡若夫斯基以及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文论建树,并客观地理解韦勒克的评介所造成的一些流传甚广的负面影响。
勒内·韦勒克首先以这两种方式知名: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和奥斯汀·沃伦合写的著名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文学理论》的作者。他还撰写了里程碑式的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作为一个学者、教师、编辑和不知疲倦的组织者,韦勒克深远地影响着美国文学研究的方向和形态。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和罗曼·雅各布逊是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这两个学派最好的倡导者和解释者,尽管他不是无条件地支持以上述方式从事文学研究,但在评价、推广方面,仍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①。
这里有两个根本性问题:(1)韦勒克和布拉格语言小组或布拉格学派的关系是什么?(2)他理解和阐释的扬·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学理论和美学又是什么?
一、论结构主义与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
1926年,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以一种非正式俱乐部的方式成立。这一年春天,韦勒克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学院结束了他关于英国和德国的研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小组成立之时,他正在前往伦敦的旅途中。他获得了一份研究生奖学金,将在一年后前往美国。在美国求学时,他访问了普林斯顿、诺坦普顿、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还担任了一年德语讲师。1930年秋,他回到了布拉格,这已经是三年后了。
在此之间,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因为诸多成就获得了国际声誉,也被学界正式承认为一个学术团体。1930年12月,另一个事件——一个国际音位学会议——正在筹办,此时韦勒克27岁,是众多国际和国内会议重要的嘉宾之一。回归之后,由于自己的研究之故,他认识了一些小组成员,也就开始参加小组例行的聚会。晚年时分,在接受彼得·德梅兹采访时他回忆其这段时光:“我参加他们的聚会,这完全在我的兴趣之外,至少我没那么感兴趣。无论如何我没那么优秀。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一个技术性的语言学家。但至少我学会了如何区分元音和辅音。”[1]243
尽管韦勒克在谈起他出席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聚会时会略带戏谑,事实却不像看上去那么富有戏剧性。20世纪30年代,在布拉格举办了诸多关于音位学的讲演,这很容易理解,无论如何,在这一片语言学领域中的研究刚刚经历了喧闹的发展。而且,小组当时正在筹备一个音位学国际会议,这个会议将因为标准音位学术语(学)的建议,以及国际语音学联盟(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的成立而被载入史册。接下来将非常有利于韦勒克,因为穆卡若夫斯基、吉拉特(Vojtech Jirat)和费舍尔(Otokar Fisher)在小组发表了不少讲演,聚焦于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比较文学,这些都是韦勒克关心的。
在20世纪30年代初,韦勒克的学术和文学活动已经收获了赞誉。他研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翻译并探讨翻译理论,撰写他关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康德哲学在英国接受的教授资格论文并于1931年以《伊曼努尔·康德在1793—1838的英格兰》(Immanuel Kant in Enland 1793-1838)为名出版),也为国内和国际的一些杂志撰写短文。此外,从1934年起他受聘于查理大学哲学学院英语教席,以接替马泰修斯(Bohumil Mathesius)。
从韦勒克的回忆中梳理他的人生与工作,可以看到1934年是个转折点。三月,他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发表了第一次演讲,是《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Shklovsky’s Theory of Prose”,1934)。他评点了新近出版的《散文理论》的捷克语译本,这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位奠基者什克洛夫斯基富有开创性的作品。韦勒克不是唯一一个走进此书和什克洛夫斯基展开对话的,在1934年二月初的《行动》杂志上,扬·穆卡若夫斯基做了同样的事,他在《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捷译本序》中,首先勾勒了这本书的理论贡献,又在第二部分中,依据当前文学研究的境况指出形式主义原理需要一以贯之的演进。
依照穆卡若夫斯基,这一演进首先在结构主义中发生了。对于这本书,韦勒克有更多批评的视角。他不只研究形式主义和散文理论,也在和特定文本的关系中评价什克洛夫斯基的作品。他指出,在马泰修斯的捷译本中显示出的和什克洛夫斯基的不一致,是有问题的。在这些方面,韦勒克十分严厉,他很详尽地陈述了作者和译者的错漏。
这里最根本的是韦勒克对俄国形式主义新术语的批评——毋宁说评论。对俄国形式主义者“形式”和“内容”这对术语的用法,韦勒克持保留态度。他要求,对这些术语和他们的用法,要有清晰的界定,要尽可能地精确。如果什克洛夫斯基和其他俄国形式主义者要赋予这些术语新意,就应该在他们的著作中准确地、始终如一地使用这些术语。然而,在这方面什克洛夫斯基做得不是很好。“什克洛夫斯基这样的形式主义者,如果能够一以贯之,内容和形式间的矛盾就会消弭殆尽。”在他的文章里韦勒克这样写道,“作品的形式就是富有艺术意味地塑造出来的一切——是内容的入口。只要以艺术的方式重塑,一切都尽可以囊括在艺术作品中。当然,问题是是否需要把形式拓展到这样的程度”。他更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异见:
尽管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突破了错误的矛盾对立,即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对立;但是“形式”这个概念太容易让人联想到它的狭义所指了,以至于什克洛夫斯基本人也不得不对这种误解负责。出于这个原因,“结构主义”这个新概念就更为清晰,因为它回避了旧的联系。但在结构主义中,我认为内容和形式这对旧的范畴依然是有用的。从传统来看,内容暗示了艺术作品中存有思想、愿望和感受;形式,也就是一切能唤起听觉和视觉形象的东西。显而易见,在那些把传统上基于内容的事物的殒灭归咎于形式主义者的批评家看来,要重塑这样老的、确定的意义并不明智(无论如何,困难在于准确地界定内容和形式的边界)。归根结底,人们在什克洛夫斯基那里,尤其是在富有他个人色彩的程式中,也可以看到这些。他实际上陷入到了被归咎于形式主义者的种种错误中。[2]
现在,我们很容易接受这个引自韦勒克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历史证明了他是正确的,因为把俄国形式主义当作一种只强调艺术作品的“形式”的研究方法,这样令人遗憾的、简化的观点仍然传播开来了——尽管诸多解释者都在努力——但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被托多罗夫这样的法国理论家采用并复活了。
这里有韦勒克以简明的形式评价结构主义的另一个观点,它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韦勒克认为,结构主义这个术语比形式主义更恰当,这可归因于它的创造性,他进而补充道,“内容”和“形式”这对术语在结构主义这里仍然有用。他没有说更多。那个时候,结构主义最终克服了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这样的看法,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内部和在别处一样得到了传播。韦勒克当然清楚知晓这个观点,他重视并坚持这个观点。尽管如此,作为富有经验的史家,他仍然去考虑“内容”和“形式”这对术语的历史,也试图去慎重对待,这很有可能是他对这对术语在结构主义中的有用性(usefulness)的注解。他个人对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一问题的态度,在他和沃伦1949年的名著《文学理论》中有更准确的阐述。在这里,两位作者这样写道:“较之于它们之所是,‘内容’和‘形式’这对术语在更广泛的、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以至于简单地将它们并列起来,并无多大意义;甚至在明晰地界定二者之后,它们仍会简单地把艺术作品一分为二。对艺术作品的一种现代分析方法因之不得不从更复杂的问题着手:它的存在模式,它的层次系统。”[3]18显而易见,在韦勒克的这一观点中,我们能看到他深受英伽登的现象学而非结构主义的影响。
仍然和上文提到的韦勒克和沃伦的理论著作有关,我们应该注意到第十二章《文学艺术作品的存在模式》中提出的建议,要用其他的概念来替代文学研究中对“内容”和“形式”的非系统化的使用。两位作者还建议,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无涉的特征应该称之为“材料”,相反,它们获得审美功效的方式则被称为“结构”。这样的区分不意味着对“内容”和“形式”这对旧概念的简单机械的重命名,相反,这部分是检验艺术作品的全新路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灵感渊源不言而喻了,这在接下来对“结构”这个关键概念的界定中得到了确认,而这个概念明显受到了穆卡若夫斯基(尤其是他的《作为符号事实的艺术》)的深远影响。“结构”,韦勒克写道,“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包含了因审美目的而被组织起来的内容和形式。于是,艺术作品就被视为一整个符号系统,或者符号结构,它服务于特定的审美目的”[3]141。
韦勒克对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的评价十分准确。一方面,韦勒克肯定什克洛夫斯基在文学研究上的创新方法,以及这部书中那令人兴奋的特质。另一方面,韦勒克指出了作者明显的错误和形式主义方法的理论缺陷。尽管文章只在1934年完整地出版过一次,如同上文所提及的,韦勒克对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和《散文理论》的观点的评价,在不同程度上散见于韦勒克所有其他关于这位理论家的著述中。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中有单独的章节可以佐证。
韦勒克的案例中,观点的一致性和持久性在韦勒克的案例中并非偶尔,也不是例外。在他的文本中,令人叹为观止的博学,聚焦于文学作品的内部分析,适当关注历史或文化语境,而且为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一丝不苟地准备,都显而易见。时至今日,这些文本依然有效。因此,即使所有内容都出自已经出版的、自足的文章和评论,都能成为一些研究和著作的一部分。更多的情况可以为韦勒克思想的本质亦即他的彻底性提供更多的证据。数年后,他将回到一些问题上,从不同的角度来调节和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描绘了近三个世纪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转变。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首先关注他在其中首次表达他的想法和态度的早期著作的原因。后来的评价通常只是肯定他最初的结论,最多通过更细致和更简洁的方式重新表述,这适用于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如同适用于其他书、评论和理论——包括穆卡若夫斯基的结构诗学和美学观念。
二、论扬·穆卡若夫斯基
在1930年到1935年间,勒内·韦勒克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一个活跃的成员。他于1930年从美国学成归来,1935年奔赴伦敦“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学校”(the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教授捷克语,这是漫长的五年。他在伦敦呆到1939年,此后他决定流亡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仍打算在战后重返捷克斯洛伐克,但1945年后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当时他受到了捷克政局的影响,也新近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不过,从耶鲁大学收到组建新的“比较文学系和斯拉夫研究系”的消息才是决定性的影响。
即使如此,韦勒克仍然和一些小组成员,以及其他研究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的学者保持联系。他紧密关注捷克研究和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在一些文章里,他对此做了评论。他在捷克研究方面的贡献,被集录为一本名为《捷克文学随笔》(Essays on Czech Literature)的选集,并于1963年出版。韦勒克为《哥伦比亚现代欧洲文学词典》(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1980)撰写了大量有关捷克作家和捷克文化的文章。除此之外,他还是捷克和斯洛伐克流亡学者和作家组织的积极成员,也是捷克斯洛伐克“艺术与科学学会流亡者俱乐部”的成员。在1968到1970年间,他还担任了后一个组织的主席。
让我们先回到1934年。在发表对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的评论的同时,韦勒克这一年还撰写了另外两种著作,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和捷克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原理的思考。其中一种是关于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的详尽报告(“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ilosophy”),罗曼·英加登和扬·穆卡若夫斯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另一种是对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逊关于捷克诗歌史著作的基本的、批评性评价[4]437-445。
即使只是简单一瞥,也可以看出这两种著作中韦勒克同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商谈”的核心,可以看出韦勒克的讨论是以与那些作者和他们表达的观念的开放性对话为基础。韦勒克的研究得益于他所处的位置、一些新的、富有挑战的问题,这样深刻且个人亲历的思想修养,就藏匿在他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背景中。而且他也反复声明,俄罗斯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对他智识的发展影响极深(英伽登的现象学和新批评也同样如此)。在1979年的回忆《展望与回顾》中,韦勒克曾这样写道:“在布拉格的岁月里,我越来越多受到小组中我那些同僚和他们的模式,以及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影响。但我再次抑制了自己的忠诚。”[5]
韦勒克关于布拉格国际哲学大会的报告十分显眼,它不但足够长(10页纸),其观点也细腻且尖锐。这届大会上,扬·穆卡若夫斯基提交了《作为符号事实的艺术》。韦勒克明显被这篇文章刺激到了,因为他的报告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这篇文章的。韦勒克尝试理解穆卡若夫斯基,并为他的观点辩护。这是因为文章引入了一个新术语,自律符号,穆卡若夫斯基想用它来描绘艺术作品,但导致了众多消极的反应。韦勒克写道:
布拉迪斯拉瓦的扬·穆卡若夫斯基教授漂亮地找到了作为符号事实的艺术作品这样一个观念。艺术作品,他解释道,既不能等同于作者的心理状态,也不能等同于它在欣赏主体那里激发的心理状态,这是心理美学的做派。当然,艺术作品绝不是时间和空间中的物,这个物只是符号,也就是真正的审美对象的外部象征。符号是对集体意识的响应。艺术作为自律的符号系统,通过其内部的发展而演变,也和其他文化领域有着持续的辩证联系。[6]17-18


韦勒克发现的第一件令他难以认可的事,是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学史同文学批评间严重的分裂。同俄罗斯形式主义者一样,穆卡若夫斯基相信文学史的唯一标准就是与发展动态相称的新颖的价值。“如果他只接受这个标准”,韦勒克写道,“就不可能再宣称那些处于发展线开端、或单纯外在于某个发展语境的作品的某些成分是历史性的了。并且,把那些伟大的作家(如歌德和莎士比亚)看得比开创者和革新者要低就很有必要了(比如伦茨和马洛)。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离开了它文学史就不再可能。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学和什么不是文学同样是价值判断的问题”[4]442。
韦勒克觉得,把审美对象放到“集体意识”中也很可疑。他追问集体意识意味着什么,但他不满足于别人建议的任何答案,他因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韦勒克之见,一个审美对象“唯有在个人那里才能实现,但没有任何人能将之作为整体来实现”[4]443。每一个个体因此都可以欣赏、经验艺术作品的价值,也可以与之相悖地参与建设它的客观(审美)价值。尽管韦勒克在他文章接下来的内容中承认他缺少符号学领域的能力,他仍使用比勒的符号理论来发展他自己的观点,即穆卡若夫斯基的符号观念太狭窄了。在他看来,同(索绪尔式的)语言学关联太紧密的符号观念是难以接受的,它排除了符号具有绝对根本意义的表现功能,而这跟我们称为艺术个性的事物在原则上是相关的,这种个性不能等同于特别的经验的个性(比如一个诗人或作家)。
在穆卡若夫斯基结构诗学和美学的一系列问题中,韦勒克提到的最后一点是,他觉得去理解艺术作品的思想主题,也就是“作品表达的世界观”的尝试是不充分的[4]444。据韦勒克之见,世界观不是文学社会学的简单议题,毋宁说,它有需要被重视的自己内部的辩证发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把心理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归入到文学研究的恰当的整体方法之中。
韦勒克的研究是非比寻常的:一方面,他力图高度评价扬·穆卡若夫斯基的学术著作,他和穆氏很熟,也与之保持着通信;另一方面,韦勒克的批评是至关重要的。穆卡若夫斯基欢迎这样的对话,他把韦勒克的评论当作一定的挑战。后来,穆卡若夫斯基实际上在多种研究中详细地处理了世界观和艺术个性的问题。韦勒克不仅称赞穆卡若夫斯基对特定艺术作品的分析,也称赞他抽象的、从理论上评价他所考虑的问题的能力。在韦勒克对穆卡若夫斯基的评论的最后,他写道:“在我看来,他的努力还包含了研究的新境况的征候:特殊议题的基础和想要超越的努力,条理清晰的规范,哲学上的深化,与相关领域的鲜活关联,尤其是这样一种新的、但在人文学科中也常见的立场:人文学科有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借自自然科学,也有他们自己的成果和他们自己的秘密。”[4]445
三、布拉格学派:批评、阐释与合作
韦勒克和穆卡若夫斯基最具活力的讨论发生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韦勒克在那里一共做了三次演讲。第一次上文已经提过了。1934年12月,他和俄国文学史家阿尔弗雷德·贝姆(Alfred L.Bem)一起做了第二次演讲,处理的对象是穆卡若夫斯基关于米罗塔·普拉克(Milota Z.Polák)的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三年后,也就是1937年10月,韦勒克在从布拉格前往伦敦短期访问时,做了一个关于英国文学研究之发展的演讲。至此,韦勒克和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合作也就走到了尽头。
1935年《词与语言艺术》杂志创刊,韦勒克在当年就成为该刊的固定撰稿人,这份刊物也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新闻代言。1936年,韦勒克的论文《文学史理论》发表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学刊》第6卷,这证明了他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浓厚兴趣。1938年,诗人马哈的纪念文集《断片,与马哈作品的神秘》(The Fragment and Mistery of Mácha’s Work,穆卡若夫斯基编)在推迟了两年之后由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出版,其中也有韦勒克的贡献——一篇题为《马哈与英语文学》的文章。在这篇广博的文章里,韦勒克恰如其分地使用了比较方法。他越来越认为比较是文学史和批评最为有用的工具。
韦勒克在其众多的演讲、广为人知的论文和学识渊博的论著中,都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捷克结构主义的态度。在韦勒克最重要的著作中——这里列出三种:(1)《近代欧洲文学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反抗》,曾以1943年在耶鲁大学的演讲首次发表;(2)《近代捷克文学史和批评》(“Recent Czech Literary History and Criticism”),最早也是一次演讲,发表于1962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艺术与科学学会在华盛顿的首次大会;(3)《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这是韦勒克关于捷克结构主义的重要著作,后来在经过轻微修订后,作为一章收入《近代文学批评史》。此外,韦勒克还为扬·穆卡若夫斯基的一部文选撰写了导言,这个选集(The Word and Verbal Art,1977)由约翰·布尔班克(John Burbank)和彼得·斯坦纳(Peter Steiner)编选,并译为英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韦勒克的导言只有以删减版的方式才能刊行,因为穆卡若夫斯基著作版权的所有者不希望文中包含有穆卡若夫斯基1948年至1971年间的活动资料。至于(文集中)选取了哪些研究,她觉得无关紧要。
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理应经受一次分析,因为其中充溢着俄罗斯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遗产,这部书直接或间接地参考了不少布拉格学派的诗学和美学。该书的认识论背景和布拉格学派是一致的,布拉格学派的认识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还将更深远地投射到对一些基本术语(如结构、功能、规范和价值)的类比界定,以及研究方法的描述上。尽管穆卡若夫斯基的大名在这部书中只出现在其中一页之上(其余则出现在脚注和参考文献里),但很明显,韦勒克接受和发展了穆卡若夫斯基的一些观点。韦勒克认为穆卡若夫斯基关于审美功能、规范和价值的著作是杰出的,但他还使用了穆卡若夫斯基的其他著作。
在其他的著作中,韦勒克明确地称赞了穆卡若夫斯基的原创性,他的象征形式的整体哲学、艺术和客观主义美学的符号学路径。他个人把穆卡若夫斯基视为最具有原创性和最重要的现代捷克文学学者之一。尽管毕生都在努力向英语国家推广穆卡若夫斯基的思想,撰写关于这些思想学说的导读,但韦勒克仍然认识到,穆卡若夫斯基著作受到的关注远低于理应得到的。从韦勒克和穆卡若夫斯基的通信中能够看到,他们相互十分尊重对方。尽管穆卡若夫斯基高度评价了韦勒克和他的著作,但在穆卡若夫斯基的著作中几乎很难看到对韦勒克的直接征引或参考。
作为一个批判性和原则性都很强的人,韦勒克很难理解1948捷克政权更迭和穆卡若夫斯基随后与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对话,这导致了穆卡若夫斯基公开的自我批评并废除之前发表过的观点。韦勒克把穆卡若夫斯基的自我批评当作公开的切腹自杀:“1950年,大庭广众下他剖腹自杀,那一幕令人不堪,而且,他默许人们重新搬出他的早期成果,这必须作时代的征兆载入史册。”③尽管韦勒克轻视1948年后穆卡若夫斯基个人和学术的发展,他仍关注着穆卡若夫斯基的著作。但无论如何,韦勒克从此都不再那么热情和彻底了。

相反,在韦勒克对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历史的诠释和对扬·穆卡若夫斯基著作的解读中反复出现了他对捷克结构主义起源的追溯。韦勒克拒绝在捷克本民族的霍尔巴特传统中,抑或在捷克美学家奥塔卡·霍斯廷斯基(Otakar Hostinsk)和奥塔卡·齐切(Otakar Zich)的著作中去探寻这些源泉。有别于穆卡若夫斯基,韦勒克相信,这些捷克学者的著作中没有任何预期的结构诗学和美学。韦勒克只在这一点上认可穆卡若夫斯基,捷克文学批评家萨尔达(František Xaveralda)、诺瓦克(Arne Novák)和费舍尔(Otoka Fischer)在一般意义上论述过风格、韵律和诗学,但都没有对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科学原理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穆卡若夫斯基强调国内的文学批评和分析传统,这是对的”,韦勒克写道,“但它绝没有预言小组独特的学识”[9]。按照韦勒克的说法,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俄罗斯形式主义,尤其是罗曼·雅各布逊,他于1920年来到布拉格,并成为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创始者和领袖之一。
在强调俄罗斯形式主义之于捷克结构主义的重要性、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内部俄罗斯和捷克两国研究者通力合作之时,韦勒克显然是对的。但问题依然存在,韦勒克对可能影响过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所有其他因素和方法论源泉的坚决否认,导致了一种不能说是错的、但不幸的是依然广泛传播的观念,即捷克结构主义是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升级版。L.马特耶卡(Ldislav Matějka)在关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及其批评的文章中也指出了这个问题:“韦勒克杰出的影响致使俄罗斯形式主义,尤其是它的早期阶段,在盎格鲁-美利坚文化世界中变得众所周知。在促成这样一个稳固的观点上,韦勒克可能远胜于他人,这个观点就是,布拉格学派为从俄罗斯传来的形式主义严密辩护。尽管韦勒克承认俄罗斯文化的输入在布拉格经历了修正,但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接受并发展了符号学,也就是对符号的研究来看,韦勒克可能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转折点,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很多成员在语言学方面从根本上离开了俄罗斯形式主义,在文学研究、美学和民俗研究方面也同样如此。”[10]马特耶卡后来减少了批评,但捷克结构主义乃俄罗斯形式主义的一个版本,这样一种简化的观点却流传了下来[11]。
结 语
在这样一篇短文里,很难涉及韦勒克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历史语境和这一关系的所有议题。韦勒克常常为他的小组成员的身份而自豪,并且,他既为小组其他成员的实践和理论成就进行辩护,也推广了这些成就。但在他的诠释与解读中,韦勒克主要讨论的是他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那个时期亲历的那些概念。
为了让这些关系对我们至少变得部分生动,很有必要再提一个事实:韦勒克的个人兴趣和个人生活。韦勒克和捷克斯洛伐克有很深的联系。他的父亲一直在这里生活,韦勒克曾于1958年回来探视其父亲。韦勒克和家人的长期分离,拜1948年后执政当局所赐的和祖国的疏离,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早期成员(穆卡若夫斯基)那些无法理解的行动和其他原因一样可能暗示了:在韦勒克心里,他选择的是对他过去的年轻时代,对捷克斯洛伐克当前境遇的不舍。在其对最新捷克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评价中,这仍然发出了回响[12]。韦勒克在美国的流亡生涯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一点。
而今我们仍可以简单回顾一下1946年皮尔科娃(Svatava Pírková-Jakobson)写给B.哈弗瓦内克(Bohuslav Havránek)的妻子泽丹卡(Zdenka)的信。皮尔科娃写到了韦勒克和他的家庭:“韦勒克时不时会来这里(纽约)。他惧怕纽约。他说这里充满了对生命的威胁,小孩子可能在某天用一个瓶子或一块石头杀了他,当地的小孩狂热地相互投掷这些东西。在这里,他在自己的领域中获得了认可,也在美国中西部的爱荷华成了教授。那里很热,有不少沙漠,蛇和蝎子纷纷造访韦勒克夫人(Mrs.Wellková)的花园;晚上8点以后,危险的歹徒则在当地美丽的中央公园中聚集。这里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兴旺发达。韦勒克夫人有个大约两岁的儿子。她仍然那么漂亮。只有到了现如今我更好地了解他的时候,我也理解她和体谅她那神经质的行为。她在那里非常沮丧。她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工作得有点多。”[13]
尽管很不幸地一直未能从他在美国的“外在”流亡中回去,韦勒克从没有进入到“内在”的那里。在他的工作和理论背景中,他一直保持着与捷克的联系。他因此从根本上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了与布拉格学派相关的学说以及它们的发展。
注 释:

②Wellek,R.Czechoslovakia[M]// Wellek,R.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Vol.VII.German,Russian,and Eastern European Criticism: 1900-1950.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420,732.此处引用的是杨自伍先生的译文,参见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修订版第七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③同上,第423页,第7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