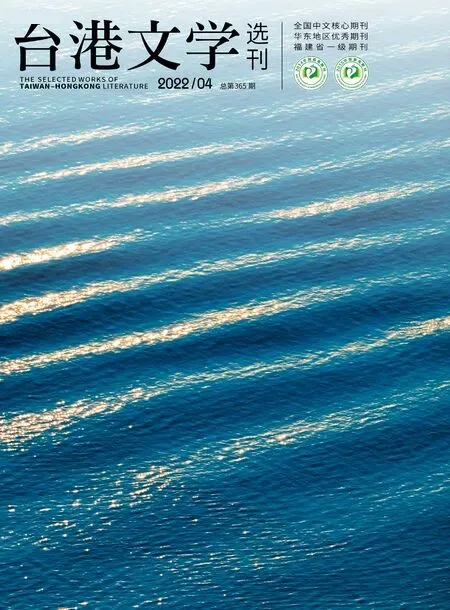安贫知命室读书记
■ 谢 泳(中国山西)
“碑铭”与“原稿”略异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字,较陈寅恪原稿略异。检《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卞僧慧)并比对上海古籍和三联版《金明馆丛稿二编》原文,均未涉及,略述如下:
陈寅恪原稿名为《拟海宁王先生纪念碑文》,因目前未见陈寅恪手迹,此为最近原稿文字。碑文原稿:“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前另有文句:“人类之不同于禽兽者,以其具能思想之特长。能思想矣,而不能自由焉,不能独立焉,则又何以异乎牛马而冠裳。”(刊1929年6月7日第78期《国立清华大学校刊》,见“清华校刊平台”网,吕瑞哲先生提供)
此段文字为碑铭所无,推测是因碑制格式,文字受限,不得已删去。直接以“士之读书治学”起句,略感突兀。另“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且二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句中,已勒碑文“且二”,易为“有”字。
细读陈寅恪原稿,可知结撰此文思路及情感,以思想和自由起笔,止于确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首尾呼应,前后贯通。“又何以异乎牛马而冠裳”一句,更具深意,就文章整体论,似更严谨,应视为碑铭另一版本。
陈乃乾记鲁迅寄书
《陈乃乾日记》对研究中国现代藏书史极有帮助,因作者交游多为书贾、藏家和学者,书中现代藏书史实极为丰富,许多掌故为以往未见,如记唐文治作陈衍墓志、柳亚子登报寻旧情人及处分赵家璧等,因多涉私事,不克抄引,仅录与鲁迅相关事一例,以存掌故。
1951年11月10日记:“晚归,看鲁迅杂文。鲁迅在日,曾经从北京寄赠《小说史考证》一册,自序有‘呜呼,于此谢之’,同人以此为谑笑之辞。其它著作皆从未购阅,后来蒋匪禁鲁迅书,及共产党尊鲁迅,我均莫名其妙。今读散文,其思想自不可及。”(虞坤林整理《陈乃乾日记》第210页,中华书局,2018年)
此处《小说史考证》,指《中国小说史略》,其时陈乃乾在上海编书教书。鲁迅原文:“自编辑写印以来,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或助为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呜呼,于此谢之!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鲁迅记于北京。”“同人以此为谑笑之辞”一语,颇耐人寻味。陈乃乾言论,涉及鲁迅著作流传情况,可作著作传播史料。隔了两天,陈乃乾又记:“《鲁迅全集》误字极多,最显著者‘近代美术史潮论’总目及封面‘史潮’皆误作‘思潮’,初看总以‘思潮’为是,询之通日文徐、林两君,皆以为然。及查阅本书,则当作‘史潮’,盖所论者为‘美术史的潮’。《山民牧唱》原作者‘巴罗哈’,封面误作‘巴哈罗’,卷首有小像签名可据。”
《鲁迅全集》指1938年旧版,后出《鲁迅全集》,这些编校失误,应当都改过来了。近年上海重视鲁迅手稿研究,陈乃乾日记,可助此事。
此日记未作索引。有索引日记,可直奔目标,无索引日记,需细读原书,方能钩沉史料;有索引方便,却也易懒人为文。
顾廷龙记陈寅恪失书事
近读中华书局新出《顾廷龙日记》,见1942年11月3日,记有陈寅恪早年失书事,内容似可补已知史料之不足。
此事最早见于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55年条下。
1938年,陈寅恪转道去昆明时,有两木箱书交由滇越铁路托运,不幸失窃。其中多是陈寅恪读书的批注本。据陈寅恪给蒋天枢的信中说,后来有位越南华侨彭禹铭,曾在海防旧书店意外买到失窃失书中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本想寄还陈先生,无奈越南政府禁书籍出口,此事未成。后彭家失火,所藏古籍数千卷,尽付一炬。信中还提到,有一位梁秩风,也买到失窃书中的一部《论衡》,陈寅恪说这是填箱之物,偶放其中,实非欲带之书。陈寅恪记忆所及,两箱书中是古代东方书籍及拓本和照片。
蒋天枢说:“昔年曾闻友人言,先生此次所失书中,尚有多部批注之《世说新语》,本欲携出据以为文者。是安南丧失大批中外文书籍事,不但影响后来著述,而所谓‘古代东方文书籍、照片、拓片’者,殆皆有关外族史料,如《诗存》中所谓‘尝取唐代突厥、回纥、吐蕃石刻补正史事’者,实先生生平所存文物之浩劫也。”(见该书第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顾廷龙日记说,他和潘景郑曾访叶遐庵,畅谈时提到:“陈寅恪所著《唐书外国传注》《世说新语注》《蒙古游牧记注》及校订佛经译本(据梵文等)数种,装入行箧,交旅行社寄安南,不意误交人家,以致遗失,无可追询,一生心血尽付东流。以此心殊抑郁,体遂益坏,无三日不病。在港沦陷后,米面时向叶氏告贷。”(见该书第273页,中华书局,2022年)
顾廷龙日记去事情发生时间不远,真实性自然亦高,日记所述内容,恰证蒋天枢记忆不误,所列书名为以往未曾提及,更有陈寅恪在港处境的真实记录以及失书事对他精神的影响,对丰富陈寅恪传记史料极有帮助。1950年陈寅恪有一首《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其中最后两句是“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正是叶遐庵和陈寅恪交谊的写照,顾廷龙日记所述,也为理解陈诗多一条材料。
最后附带说一句,《顾廷龙日记》,记钱锺书和冒效鲁事最富,因日记未编索引,有心读者不妨细读后一一钩沉,或可知钱锺书在上海孤岛时期的读书交游情况,另有钱锺书借书及捐赠杂志情况,对了解他的学术兴趣及阅读范围多有帮助,这些均是钱锺书传记的好材料。
陈钱用典
往年曾撰《陈寅恪钱锺书诗共用一典八例》,今又见二例。共用一典,或属偶然,但也见知识背景及心理同构。
1954年陈寅恪《答龙榆生》绝句:“难同夷惠论通介,绝异韩苏感谪迁。珍重盖头茅一把,西天不住住南天。”

林任菁 朝露

“盖头茅”亦称“茅盖头”,佛典,意为无奈中勉强得来贱物。旧版《谈艺录》序言结句:“立锥之地,盖头之茅,皆非吾有。知者识言外有哀江南在,而非自比昭代婵娟子也。”
1964年陈寅恪《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绝》第一首:“慈恩顶骨已三分,西竺遥闻造塔坟。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丰干人名,丰干饶舌是古书常用典故,有言多必失之意。
据网上“视昔犹今”释读钱锺书《中文笔记》,钱锺书曾引梁同书《频罗庵遗集》卷二中诗“丰干莫漫从饶舌,匡鼎徒烦为解颐”,可知钱锺书也留意此典。
陈寅恪引书
新见刘梦溪先生主编《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文辉兄《陈寅恪征引史料未尽之例及其它》一文,举证详赡,见解平实通达,极有说服力。
后人对陈寅恪史学成绩的敬意,其实主要不在史料周全,而在他的“巧”与“妙”(史学亦可视为高级智力游戏)。网络时代,发现陈先生引书不周之处似乎并不很难,但在史学研究中有陈先生的“巧”与“妙”却极不容易,他的“巧”与“妙”,简单说就是“他怎么会想到那样的问题?”“他怎么能把表面完全不相关的事联在一起?”“他怎么能在历史中发现和今天结构、事实极为类似的现象”等等,陈先生研究的是大问题,但从来不失趣味。陈先生早年有一篇文章《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很能见出他的思维习惯,他在已知史料中用自己独特的思维发现问题,然后解释,虽然此文后来因白居易和诗写作时间确定而不成立,陈先生舍弃了此篇论文,但陈先生发现问题的逻辑与视角,也就是他“巧”与“妙”的思维习惯却还是能看得出来。另外,陈先生引书不周,可能还有个习惯问题,明以后的类书,印象中陈先生就不引。
中国老辈读书人对类书的评价一般不高,他们认为这些书都是东抄西抄凑成的。往前的类书尚有价值,如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宋代《太平御览》《玉海》等,因为收古书多,这些古书又没有保存下来,后世只能依赖类书中的史料,明以后的类书则基本不看了。陈寅恪可能也受这个习惯影响,他著作中一般不用明以后类书中的材料,比如郎瑛《七修类稿》是很有名的书,但印象中陈寅恪没有引过(或引过我没有注意到),而《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玉海》等,则是陈寅恪常引的古书。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讲白居易《七德舞》时说过,类书为便利属文,白乐天尤喜编纂类书,可知陈寅恪对类书体例及功用非常留意。
没有引不等于没有看过,因为不引明以后类书中的材料,有时就会出现同样历史现象,陈寅恪的判断和类书史料相类的情况,试举两例:
陈寅恪讲元白诗,经常提到唐代女子很多用叠字为名,如“九九”“莺莺”之类(见《元白诗笺证稿》第113、375页,三联版,2009年),陈寅恪的判断是“莺莺虽非真名,然其真名为复字则可断言,鄙意唐代女子颇有以‘九九’为名者”。
《七修类稿》有《唐双名美人》条,原文如下:
陈寅恪注意到的现象与《唐双名美人》为同一现象,虽强调唐女子多“九九”为名者与《七修类稿》略异,但《七修类稿》举例颇富。
陈寅恪讲《长恨歌》,特别注意考证“霓裳羽衣舞”(同上第26页)。陈寅恪认为“自来考证霓裳羽衣舞之作多矣”,远以宋代王灼《碧鸡漫志》“所论颇精”,近以日人远藤实夫《长恨歌研究》“征引甚繁”。陈寅恪总体认识是重要材料均出《唐会要》和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他依此思路进行了详细举证分析。举证过程未及《七修类稿》,而此书有“霓裳羽衣曲舞”条,抄出如下:
陈寅恪未引《七修类稿》,但所扩展史料方向和《七修类稿》有相合处。陈寅恪解“惊破霓裳羽衣曲”,认为“破”字除一般“破散破坏之意”外,还是一个乐舞术语,但举例时未及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中“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而《七修类稿》已引。最后附说一句,钱锺书常引《七修类稿》,《容安馆札记》中时有所见。
钱锺书喜称古人小名
中国南北习俗,为小孩子健康成长,正名之外,喜以贱名呼之,所谓小名是也,如阿猫阿狗,镢柄狗蛋一类。
《围城》里有个情节:
方鹏图瞧见书上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郎等等,才知道儿子叫“丑儿”还算有体面的。(《围城》第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栾贵明《小说逸语——钱锺书〈围城〉九段》中说,钱锺书提到的这些奇特丑怪小名,其实都是历史真人的真实小名,斑兽是南朝宋战将刘湛,秃头是晋朝的慕容拔,龟儿是唐代白行简,獾郎是王安石。(《小说逸语》第29页,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
《围城》写褚慎明自夸和罗素熟悉,钱锺书写道:“褚慎明跟他亲狎得叫他乳名,连董斜川都羡服了,便说:‘你跟罗素很熟?’”(《围城》第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陈寅恪著作中提到古人,也喜称小名。这个特点凡熟悉陈寅恪著作的人可能都有感觉,他称谢灵运为客儿,庾信为兰成,司马相如为犬子,王导为阿龙,曹操为阿瞒等等,如细检陈书,或可开列一份长长的名单。
《慎园丛集》涉钱锺书史料
天津卢慎之与钱锺书交往事,近年时见有人著文谈及,但多是钱锺书为其诗集作序一事。前几年我读卢慎之《慎园启事》,曾抄出卢与钱氏父子信共七通,其中两通给钱锺书,时在1959年前,收在我前年印出的《钱锺书交游考》中。
《慎园启事》印出后,1964年夏天,卢慎之又在上海戴克宽处油印了一册《慎园丛集》,此册收卢慎之六一年到六四年间各类文字,分为诗、词、文和附录四部分,涉及上世纪五十年代旧文人私下往来事颇多,保存相当丰富的诗坛文坛史料,涉及人物非常广泛。近日偶检其书,见两则关于钱锺书史料,为以往所未见,特抄出如下,以补钱锺书交游史料。
钱锺书与冒效鲁关系极密,二人诗词唱和频繁,友谊终其一生。《慎园丛集》中收卢慎之《小三吾亭诗词序》一文,述及为冒鹤亭遗著写序经过,其中提到:“忽得钱默存书,鹤亭翁三公子效鲁,谋印贺履之遗著,征稿于余。且言效鲁壮游域外,通百国之宝书,夙承家学,工六朝之韵语,续默深海国之编,补愿船朔方之乘,今日之凤毛也。嗣是效鲁书问往还,诚如默存所云。惟余僻处津沽,不问世事,未由读鹤亭名著,徒深向往。效鲁惠贻尊公诗词,读之愉快,不可言喻。”
钱锺书将效鲁学问与魏源《海国图志》、何秋涛 《朔方备乘》并论,虽略感夸饰,但友情至真,令人感慨。
钱锺书与卢慎之交往中,常为人提起的“点绛唇”掌故,书中亦可寻见原始出处,我在网上检索,偶见片言只语,似未见有人完整抄录原词,想是《慎园丛集》为油印书册,翻检不便,现抄录全词,小字夹注一并保留。
卢慎之此时已是八十余岁老翁,巧用绛名恰符词牌字义,“妙谑”暗涉香艳,足见老辈文人机妙诙谐。
知人小名,多从读杂书中来,留下记忆,表明有点幽默和调皮,大学者多有此种趣味,可显读书之杂之博,又见机巧和才智。
施蛰存先生藏书四种
早年在太原时,每见宋谋瑒先生,多要提及施蛰存先生。宋先生总说,施先生中国文学修养太好了,各方面都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宋先生曾邀施先生来山西长治师专讲学,那时我在晋中师专编校刊,还不认识宋先生。宋先生和施先生旨趣相投,同历丁酉之难,后来成了好朋友。我在《黄河》杂志当编辑时,发宋先生文章多,联系很密,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读过施先生的部分小说,还有《唐诗百话》,是经常翻阅的书。施先生中西两面的文化修养如此之好,原因何在?除个人秉赋外,有时候很想知道他青年时代怎么读书,才会有那样的成绩。在他涉猎的范围,如文学、翻译、编辑、诗词、注释、金石等等,今天的人,有一项就算很不错了,而施先生是样样都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有一段时间,《黄河》经常发回忆文章。我知陆灏兄是施家常客,也曾动过托他约施先生写文的念头,但又想施先生年岁已高,不便轻易打扰,后来也就作罢了。但对施先生的敬意一刻也没有消失,很关注他的言动。施先生高龄去世后,看到有那么多人纪念他,心中感到非常欣慰。
2007年5月,得周宁兄关照,朱崇实校长破例,我到厦大中文系,教书数年后,投闲置散,经常在厦门旧书肆闲逛,有次在一堆虫蚀极重的旧书中翻捡,忽见钤有“华亭施氏无相庵藏”“无相庵”“施蛰存”印的旧书,虽已残破且是常见易得之书,本想放弃,但想到这是施先生曾读过的书,福泽尚在,其中或有手批痕迹也未可知,虽无缘得见先生,但能与曾在施家的旧籍相遇,也算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
回来检点,有民国十八年铅印《巢经巢遗诗》上下两册,钤“无相庵”朱文方印;五册中华书局影印“四部丛刊”本《楚辞集注》,钤“施蛰存”朱文方印;五册涵芬楼影印《广韵》,钤“华亭施氏无相庵藏”楷书长方朱印;一册晚清上海鸿文书局白纸石印《竹书纪年》《商君书》《文中子》《山海经》,原装或为两册,现合一册,前后已残破,但在《文中子》那一册封面下方,钤“华亭施氏无相庵藏”印。
“无相庵”是施先生早年用过的一个室名,后来还用“无相庵”印过笺谱,可见对这个室名的感情。“华亭施氏无相庵藏”印,偶然也曾见过。施先生是金石行家,据说他的印章多出邓散木、陈巨来之手,书中钤印,将来可作施先生藏印史料。几种旧书均是中国经典,可知施先生早年读书趣味和他的国学根基。
施先生旧书何以流落厦门?抗战爆发后,施先生离开上海来厦门教书,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当时厦门大学已迁长汀。过去读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知浦江清去西南联大时,经过长汀看望老友林庚、施蛰存的旧事。施先生请他吃饭,一起出席校长萨本栋的宴会,参观图书馆,最后还到车站送行。这几种旧书,想是施先生随身携带的读物,离开厦门时未及带走或是借给朋友未还,流落在厦门,施先生或许早已忘记了。
旧书肆行规是不问来处,施先生在厦门过从最密的朋友是徐霞村,那些年,也曾见徐家旧书散出,未知施先生藏书是不是和徐家有关。虽是几种普通旧籍,但隔了近百年的岁月尘埃,还能重见天日,或可说是施先生与厦门剪不断的情感,一段可永续的佳话吧!
李释戡《苏堂诗拾》
黄裳先生玩古书的时候,清刻本还没有什么地位,黄先生的过人之处是在没有人在意的时候,他看出了“清刻之美”。我们今天看“油印之美”也是一个道理。所谓“油印之美”我想主要是三点,一是诗文集;二是刻印装订要当得起一个“美”字;三是稀见。不是所有刻得好的印品都当得起“油印之美”。
油印时代,说实话,找到会写字的人还不是一件难事,难得是一分骨子里的风雅,就是说油印诗文集时,不能草率为事,而是在有限条件下保持古雅的风度。郑逸梅曾盛赞上世纪五十年代戴克宽在上海主持刻印旧文人诗文集,从设计、刷印到最后装订、题识,都一如古人。我见过李释戡三册《苏堂诗拾》,这种感觉异常强烈。
近两百年来,福建出了很多大诗人,以福州为中心。这些旧文人中年纪稍轻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多聚在上海,积习难改,吟诗作画、拍曲看戏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
李释戡,原名汰书,字蔬畦,号宣倜,原籍福建闽县,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久居京师,精通戏曲音律,曾为梅兰芳编剧。梅派名剧《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黛玉葬花》等,据说皆出于他和齐如山手笔,还编过《鞠部丛谈校补》,他的堂兄李拔可也是近世名诗人,钱锺书对老辈文人时有刻薄之语,但对福州陈石遗、李拔可始终敬重。李释戡喜苏东坡,将自己书室称为“苏堂”。1956年,他印了自己的诗集《苏堂诗拾》,封面是沈尹默题笺,内封再一题笺是苏堂同乡北云即林志钧先生,诗集序言为同乡陈声聪所写,集后跋文则出黄裳之手,刻手是张仁友。李释戡交游很广,诗集中多老辈文人往来史料,同时有相当多上海梨园史料,如果研究当年上海新旧戏曲变革以及名演员的演技等情况,《苏堂诗拾》当是不可少的旁涉史料。
《苏堂诗拾》并不难见,难见的是《苏堂诗拾》后的两册《苏堂诗续》。《苏堂诗续》甲乙两册,封面题笺均是尹石公,1957年在上海油印,刻手还是张仁友。甲集封内题笺、序言都是陈声聪,集后有《赠仁友》七律一首,感谢张仁友为其刻印诗集。乙集内封题笺是潘伯鹰,无序言,集后有作者自跋一则。《苏堂诗续》甲乙两册封面完全相同,甲集乙集二小字,只是用红色朱砂随手拓印,常不为人知,有书贾常将此甲乙二字磨去,让人误以为《苏堂诗续》只有一册。
三册《苏堂诗拾》,刻印都很精善,在油印诗文集中当属上品。我所见《苏堂诗续》乙集内页中的一处毛笔批注:“蔬畦早年即有曲癖,到燕京后,值清末民初,士大夫辈皆以捧伶为事。其尤者,饱食终日,不用他心,耽于曲院中,厥后挂冠下海者亦有。如王又宸、言菊朋等。但当时以捧角最是风行,以金融教育政界为最。蔬畦先生其一也。”
丘菽园《挥麈拾遗》
丘菽园(1873—1941年),名炜萲,字萱娱,号菽园。又有啸虹生、星洲寓公等别号。福建海澄人,二十一岁乡试中试。幼时随父定居新加坡,为著名报人和诗人,享有“南洋才子”和“南国诗宗”之誉,一生以在新加坡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中日甲午战后,康梁倡导维新,他曾深表钦佩,于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自任总理兼总主笔,鼓吹改革。
丘菽园著述甚富,主要著作包括诗集《丘菽园居士诗集》《啸虹生诗钞》;笔记《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麈》和《挥麈拾遗》等。新加坡关于丘菽园的研究很多,如王志伟《丘菽园咏史诗研究》《丘菽园咏史诗编年注释》(2000年,新社出版社,2000年)等。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有对《菽园赘谈》的评价,认为记载中日甲午战争后新加坡情况的笔记当属《菽园赘谈》。谢国桢说丘菽园是“留心时事的有心人”(《明清笔记谈丛》第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一般认为《五百石洞天挥麈》《挥麈拾遗》是两种笔记,其实是“诗话”作品。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最重要的文体形式即是“诗话”。近年专门研究“诗话”的著作不少,如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蒋寅《清诗话考》等。因为中国古代“诗话”著述多在书名中出现“诗话”二字,而对书名中未出现“诗话”二字的著述相对容易遗忘。蒋寅《清诗话考》中虽将《五百石洞天挥麈》《挥麈拾遗》列入书目,但在“清诗话经眼录”章节中,没有提《挥麈拾遗》,可认为此书稀见,而《五百石洞天挥麈》易得。
丘菽园《菽园赘谈》
丘菽园《菽园赘谈》在晚清笔记中虽偶有提及,但尚未得到应有重视。初版《菽园赘谈》凡十四卷,光绪丁酉(1897年)香港铅印本,共八册。书前有曾宗彦短序,由叶芾棠手书上版;叶芾棠短序,则由李季琛手书上版;随后是黎香荪七言排律题词,接着是李琛汝、李启祥、潘飞声序言。接下来是达明阿、刘允丞、邱屏沧、李麟、马子般、曾宗璜、林泽农、林景修、王玉墀、黄镳、浮查客、许允伯题辞,题辞尾有许克家短序一则。此即《菽园赘谈》初版本,流传不广。流传较广的是七卷本《菽园赘谈》,光绪辛丑(1901年)重编七卷,上海铅印本,编为四册。七卷本前有潘飞声、李启祥、许克家、叶芾棠、侯材骥序及作者丘菽园“小引”一则,“小引”后有丘逢甲长序一篇,盛赞该书“上而谈国家政教,下而谈乡闾礼俗,远征三代,近取四国,正襟而谈,骎骎乎与道大适是,盖究心古今中外之书,卓然与先正之善谈者埒。”书后附曾宗璜、谢鸿钧跋两则,另有曾昭琴《刊刻答粤督书缘起》并《答粤督书》,最后刊有丘菽园《庚寅偶存》及短序一篇,系丘菽园诗稿,并附丘菽园《壬辰冬兴》十六首及黄乃裳短序。
《菽园赘谈》十四卷本印出后不久即又刊行七卷本,原因有二:一是十四卷本从香港中华印务总局用仿聚珍版排编,已经散版;二是十四卷本讹误颇多。丘菽园说“赘谈虽属已赀付印,然星、香万里,不能自校,仅以托诸坊贾,草草蒇事,故讹字尤多,亦有原稿本讹,考据未审者,此则急于成书之弊。出书后,屡承闽县曾幼沧侍御师宗彦、番禺李石樵秀才启祥函纠讹字。今又得台湾家仙根工部逐卷校勘。”此本编校胜于十四卷本,后世多以此为正本。
宣统元年,张延华以“清虫天子”笔名辑“香艳丛书”,约三百三十五种分二十集十册,大体包罗隋至晚清间有关女性和艳情的小说、诗词、曲赋等。《菽园赘谈》,以节录本形式收入丛书第八集,近年有上海书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刊影印本,人民中国出版社新刊整理本。除此之外,未见《菽园赘谈》有其他版本流行,在晚清笔记中,尚属稀见。

林任菁 融系列之野蔓
“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大事,但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评价,对于真实历史详情,也认识各异。丘菽园与康有为相识,“公车上书”发生时,恰在京师,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事件发生后不久,丘菽园有两次追忆,虽文字存诸多差异,但由此可窥知此前未知的若干史实,同时对康有为《公车上书记》的刊行也具补正作用。光绪二十年(1895年),丘菽园以福建籍举人身份,北上参加会试。康有为发起联省公车上书,丘菽园亲见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传抄稿,后以《截录康孝廉安危大计疏》为题,大段摘录于《菽园赘谈》中,篇后附有跋语,回忆自己当年参与“公车上书”的情形。丘菽园对康有为一直念念不忘,不仅将康有为所撰《上清帝第二书》收入《菽园赘谈》,附跋纪念,更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林文庆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自任社长,从侧面呼应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举动。“戊戌政变”后,丘菽园主动赠金康有为,并力邀其赴新加坡。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丘菽园与康有为首次晤面,两人一见如故,不仅多有诗歌唱和,更在政治上加强了合作。后丘菽园与康有为绝交。在重编《菽园赘谈》时将《答粤督书》(即《上粤督陶方帅书》)附于书后,虽详述与康有为绝交原因,但依然将《截录康孝廉安危大计疏》收录书内并将跋语大加修正,较十四卷本有“新增”而无“删汰”;对于“公车上书”的描述,也与前稿有较多不同。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菽园赘谈》的重要性早有定评,是研究康有为和“公车上书”的首选史料。
丘菽园虽是传统读书人,但早年游历域外,眼界开阔,善于吸收新知,是中国早期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能将西方知识与中国传统知识对接。《菽园赘谈》中有多篇涉及西方知识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史料,如《化学原质多中国之物考》,将现代化学原素与中国传统事物对应,并寻出其大体来源,可谓中国早期关于科学史的研究文章,今天也不失其参考价值。《菽园赘谈》卷五有《说照像》一文,是较早介绍西方照像术在中国传播的史料。丘菽园说:“西人照像之法,全靠光学妙用,而亦参伍以化学。其法先为穴柜,按机进退,藉日之光,摄影入镜中,所用之化学药料,大抵不外硝磺强水而已。一照即可留影于玻璃,自非擦刮,久不脱落。精于术者,不独眉目分晰,即点景之处,无不毕现,更能仿照书画字迹逼真宛成缩本,又能于玻璃移于石上,印千百幅,悉从此取给,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版,用墨拓出,无殊印书,其便捷之法,殆无以复加者。”
这则史料不但说明照像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同时也将石印技术的要点做了提示,可认为是石印技术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史料,对中国印刷史研究有重要意义。丘菽园在这则笔记中还提到王韬《瀛壖杂志》中一则史料,是王韬咸丰同治年间在上海所见,认为现在照像术“更日异更新,不用湿片,而用干片,坊间有照干片像法之译本,阅之颇可了了,惟不易精耳。”同时谈到新出现的夜间电灯照像法。丘菽园提到,1895年,他在新加坡“曾向德国人兰末氏假得此项机器一试其用,略带黝色,究不如日间所照为妙。计电灯全副十七盏,燃之光耀四射,倘开夜宴,以之照取人物亦颇不俗,今未盛行。”由这个经历,可以判断丘菽园是中国较早试用电灯光照像的人。文章还谈到新出的摄影器具,他说镜箱“亦分数等,佳者贵重不易得”,构造亦各不同,照人物面貌宜用“亮镜”,照山水名胜宜用“快镜”,“各极其妙,而不兼长。”丘菽园还注意到西人又制成供医疗治病用的新镜箱,“以之照人,能见人身骨朵”,“凡遇肢骨损伤,皆可一照而知,此医门卫生法宝也。”这些记述可视为西医造影技术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史料。另外如《日月之食》,比较中西对这一天文现象观察的异同,也具新见。丘菽园对中西医的比较认识,也非常深刻。他在《疾病古今异称附中西医略》中认为“中医善治无形,西医善治有形,则各有所长也。中医化学未明,西医方隅或囿,则各有所短也。西医从考试出身,中医恒师心自用,则不得不让彼善长也,安得以彼之长济吾之短,然后博考其或长或短之故,调济以至于中,则善之善也。”近代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较少专门著述,史料一般多散见于书信、日记及笔记中,《菽园赘谈》中保存了很多这方面的史料线索。
1960年,阿英编纂《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将《挥麈拾遗》《五百洞天石挥麈》《菽园赘谈》及丘菽园发表在其他报刊上有关小说的评论,用丘菽园新加坡的斋名“客云庐”题名,汇编为五卷《客云庐小说话》,可见阿英对丘菽园小说评论的高度重视。
丘菽园喜读晚清小说兼及当时译介过来的西洋小说,在他这一辈旧文人中,对小说形式的关注和评价有非常自觉的意识,特别是对晚清小说在开启民智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重要作用,与梁启超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见解相同,时间比梁启超文章还早一年。丘菽园在《小说与民智关系》中指出:“吾闻东西洋诸国之视小说,与吾华异,吾华通人素轻此学,而外国非通人不敢著小说,故一种小说,即有一种之宗旨,能与政体民志息息相通。”从丘菽园《新小说品》所开列当时新小说的名录可看出,晚清新出的各类小说及新译小说,丘菽园多曾寓目。他对中国小说的许多考证和见解,值得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注意。如丘菽园在《小说闲评七则》中认为:“《红楼梦》一书,不著作者姓名,或以为曹雪芹作,想亦臆度之辞,若因篇末有曹雪芹姓名,则此书旧为抄本,只八十回。倪云癯曾见刻本亦八十回,后四十回乃后来联缀成文者,究未足为据,或以前八十回为国初人之旧,而后之四十回,即雪芹所增入,观其一气衔接,脉络贯通,就举全书笔墨,归功雪芹,亦不为过。”这些认识在《红楼梦》研究中,至今不无参考价值。
丘菽园对《儿女英雄传》的评价是:“自是有意与《红楼梦》争胜,看他请出忠孝廉节一个大题目来,搬演许多,无非想将《红楼梦》压住,直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才多者天且忌,名高者矢之鹄,不意小说中亦难免此,然非作《红楼梦》者先为创局,巧度金针,《儿女英雄传》究安得阴宗其长而显攻其短,攻之虽不克,而彼之长已为吾所窃取以鸣世,又安知《儿女英雄传》显而攻之者,不从而阴为感耶。《红楼梦》得此大弟子,可谓风骚有正声矣。”
丘菽园认为“《红楼梦》彻首彻尾,竟无一笔可议,所以独高一代,《儿女英雄传》不及《红楼梦》正坐后半不佳”。他对《花月痕》的评价是:“亦从熟读《红楼梦》得来,其精到处,与《儿女英雄传》相驰逐于艺圃,正不知谁为赵汉,若以视红楼,则自谢不敏,亦缘后劲失力故也,就使后劲,要也未到红楼地位。《花月痕》命意,见自序两篇中,大抵有寄托而无指摘者近是,人见其所言多咸同间事,意以为必有指摘过矣,亦犹《红楼梦》一书,谈者纷纷,或以为指摘满洲某权贵某大臣而作,及取其事按之,则皆依稀影响,不实不尽,要知作者假名立义,因文生情,本是空中楼阁,特患阅历既多,瞑想遐思,皆成实境,偶借鉴于古人,竟毕肖于今人,欲穷形于魍魉,遂驱及于蛇龙,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七情之发,何境不生,文字之暗合有然,事物之相值何独不然,得一有心者为之吹毛求疵,而作者危矣,得一有心人为之平情论事,而观者谅矣。”
丘菽园对晚清小说的评价,多用中国传统评点形式,但见解鲜明,颇有见地。他对《品花宝鉴》评价较高,而对《金瓶梅》评价一般。《菽园赘谈》保存了丰富的晚清小说史料,研究晚清小说,不可不读。
清人笔记,因作者阅历不同,各有侧重。有专载朝章礼制的,有只记掌故旧闻的,也有多记诗歌唱和的。《菽园赘谈》虽各类兼备,但总体观察,内容除地方风物礼俗外,多涉诗话、科举制度、方言音韵,同时还有一个特点是多地方人物传记史料。
清人笔记本来就是一种自由文体,《菽园赘谈》中保存了丰富的地方人物传记史料,如研究晚清闽地乡绅、文人,可资取材处甚多,因所记多同时代人物事迹,真实性更强。如记林丰年、高雨农、邱萍孙、曾墨农、谢又新、张缵廷、林文庆等地方名人,皆有人有事,栩栩如生。如《林文庆》一节:“林文庆医师者,余同年友三山黄黻臣(乃裳)之快婿也。少日读书英伦大书院,学成考授一等执照,归而售技,即以字行,一时声名藉甚,咸谓林氏有子矣。君居英久,改从西装,及返星州见夫文献遗征,慨然有用世之志,遂弃西服,仍服汉制,然犹未有室家也,或造之谋,则曰蓬矢桑弧,某将为东西南北之人矣,何以家为。强之,则又曰:世无孟光,谁可配梁鸿者,于环岛之中,而求家人之卦,吾终咏雉朝飞乎。友人知其意有在,阴代物色,久之始得,即黄公之女公子也。籍隶榕垣,生而不俗,幼随美国教会女塾师诵习,能通欧西语言文字,熟精医学,平生游踪几环地球之半,李傅相使俄返命,与之邂逅太平洋邮船舱面,手书褒嘉为中国奇女子云。今冬行将南下成合卺礼,适余归舟相左,不及见。闻君夫妇虽俱谙西学,然无西人习气,此尤足多者,故特表而出之。”一般研究林文庆的著作,极少用到如此生动的史料,《菽园赘谈》可称闽地人物传记史料宝库。

林任菁 融系列之红妆素裹
丘菽园见多识广,尤能将中西知识作比较观察,凡遇新鲜事物,常能详细搜集史料,旁征博引。如《缠足》一篇,细述缠足在中国的起源及演变,可谓一篇缠足小史。他从李白、韩偓、杜牧、吴均等人诗中,寻出唐人亦有缠足现象,成为后来研究缠足史者所必引史料。《烟草》一节,最早指出烟草由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传入中国,并指出烟草之害,可视为中国早期烟草传播及戒烟史宝贵文献。《菽园赘谈》在晚清笔记中虽不特别知名,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徐德明《清人学术笔记提要》,均未提及,但其重要性无可怀疑。
许效庳《安事室遗诗》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写当年上海十大狂士,其中有许效庳,叙其生平及趣闻甚详。许无著作,逝世后友人裒其生前诗词,油印一册《安事室遗诗》。此虽一小册,但刻印装璜俱佳。
近年油印书颇受青睐,尤其早年上海戴果园主持油印诗集,可谓一书难求。十多年前我在北京泰和嘉诚拍卖公司购得几册戴刻油印诗集,其中即有《安事室遗诗》,还是天津姚养怡先生藏书。集前有陈病树序言一则,叙许效庳生平及交游,后为友朋为诗集的题诗,先后为严昌堉、何泽翰、蔡钟济、赵祖望、丁淇丁瑗、鲍鼎、梅鹤孙、陆鸣冈、陈文无。诗集未刻目录,附载许效庳十余首词,最后有陈文无跋语一则。
许效庳出身名门,性聪颖,富诗才。集中有《卖书后作》四首,诗作何年,一时不好判断,但表达失书心情,属对工切,用典切要,可见老辈文人读书用力,腹笥之富,文化修养之境界。抄录如下:
沈从文赞周哲文
周哲文是中国当代著名篆刻家,名动海内外,长年居住福州,2001年去世。
有一年我到福州参观三坊七巷,恰好侄子南来在周哲文艺术馆打工,遂顺路而入。艺术馆在光禄吟台旁,为一座三层青砖楼房,据说建于1951年,是专为当时来华苏联专家建造的。我对篆刻只有一般观赏常识,参观后对周先生的篆刻印象极深,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觉得好,当时还曾闪过一个念头,如以后在福州、厦门古玩市场偶然见到周先生的作品,当购存留念。在周哲文艺术馆还见到一封沈从文长信,写得极精,当时也想抄录,看是否为《沈从文全集》中漏收的信札,但因时间匆忙,一时没有动手,只留下了沈先生和周先生关系不一般的印象。
近读新到《新文学史料》,有沈从文1944年在昆明致董作宾三函,其中提到周哲文,对他的篆刻评价极高。沈从文说:“此次字件处理,多得朋友周哲文兄热心帮忙,彼年仅二十余,才气纵横,豪奕可爱,精于篆刻,尤长朱文治印,朴茂雄壮,布置精佳,细线条劲利,奏刀准确,如治玉之‘游丝碾’,将来成就必极大。”(《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第1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文学史料》所刊沈函为沈先生儿子虎雏释读,偶有不确处,后来我在网上看到老朋友贺宏亮先前从嘉德拍卖图录上的释文,似更确切。
周哲文自学成才,青年时一度漂泊西南,与沈从文相识。沈先生对中国艺术的修养人所共知,他对早年周哲文篆刻水平的判断完全出于友朋间的欣赏,无任何功利目的,而当时周哲文篆刻尚不为人知。后来周先生在篆刻艺术上的成就,说明沈先生对艺术的敏感及判断艺术的眼光非常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