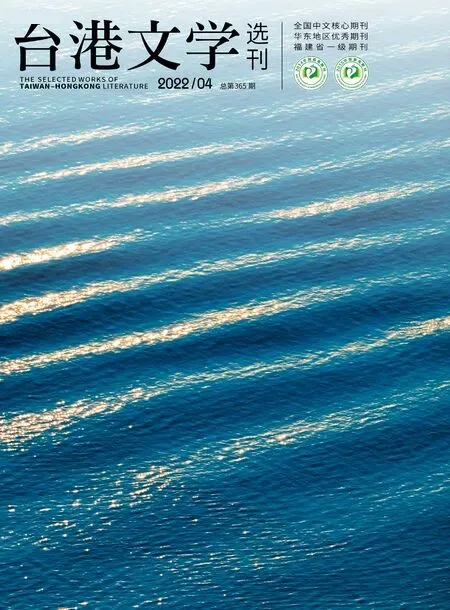论《奇遇》的叙事技法
■ 朱 凌(中国山东) 郑润良(中国广东)
张惠雯是一个创作个性鲜明的“新移民”作家。她的小说没有表现出特别明确的“身份意识”,也不涉及中西文化冲突的模式,而是弱化当前新移民对国外生存的体验与感受。求学、事业、生活只是叙事背景,作家着力描写有个性特色的心路和情绪。对永恒漂泊的深切体悟,对“家”的强烈渴望,蕴含着她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生命体验。与此同时,她又不断拓展叙事空间,尽可能地挖掘叙事潜力,提升叙事技巧。这一特色依然延续到她的新作《奇遇》中。
一、时空位移与精神幻境
《奇遇》如开篇那段文字“火焰已燃尽,洪水消退,戏剧散场”所述,描写了主人公在同一空间不同时间回忆并描述的一段由激情四射到激情燃尽的婚外情感。这种在同一空间的反复回味或者咂摩残存记忆是张惠雯常用的叙事技法。《飞鸟与池鱼》中也是沿用这一叙事技法。往昔印象与当下现实的碰撞,造就了一种极具张力的情景。尖锐的碰撞之下,小说呈现了人物对失意现实、迷惘当下和庸俗中年的抵拒,以及对温暖记忆、轻逸幻想和美好青春的渴求。当激情燃尽之后,主人公落寞地回想往昔的故事,以及保留着空间中固有的陈设,“楼上的卧室里还留着她买来的床具,是她喜欢的图案——格子和花朵”。相同的追忆在文中被与霍桑的《威克菲尔德》进行比较:威克菲尔德是要逃离原来的生活,而男主人公的故事算是对爱的追求,即便是无望的追求。《飞鸟与池鱼》中也是时常掺杂着叙述者从“异乡”到“故乡”的时空位移。作家在这些想象中试图建立起一处精神的隐蔽所。为了对抗沉重的现实,主人公们或沉浸于过往柔软的记忆,或漫游于幻想的虚境,从而一次次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也一次次实现了对委顿生活的逃离。可以说,“回忆”与“幻想”构成了小说人物逃避生活的方式。伴随着记忆被唤醒,一种今昔生活的落差也逐渐被隐蔽地“修辞化”了,于是,剩下的只是激情四射后的孤寂和静谧的幻境。我们在张惠雯小说中感受着“孤独”的气质,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体验着具有共性的人类情感——个体孤独。作为“新移民”作家,张惠雯身为一个远行的移民甚至是漂泊者,深刻体会着现代人的漂泊与无根,关注着他们在面对漂泊和归宿时的心理情感,以及“无家”的忧惧。真实生活本身是乏味、庸俗的,从未有诗和远方,但与“她”的相遇使“我”有了一次恩典般的奇遇,关于她的幻想重新点燃了“我”的生活,也透露出作者对“家”的热切渴望和对无根灵魂的深切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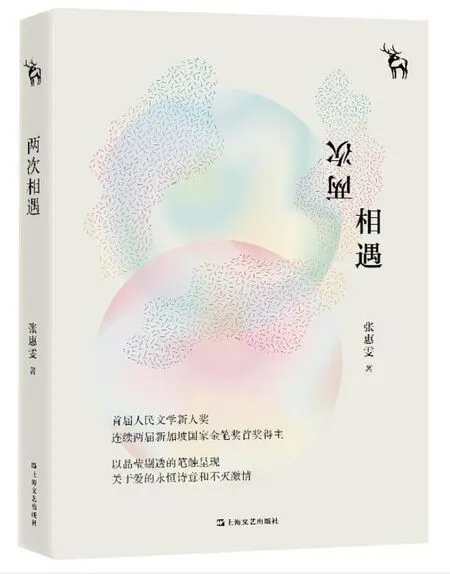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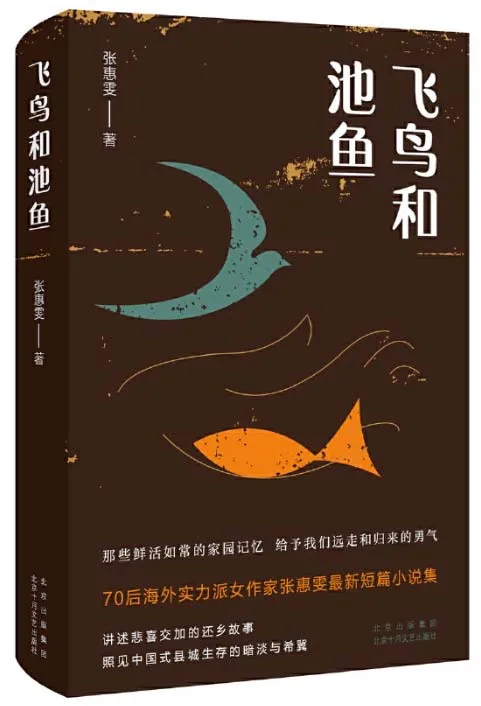
二、感官叙事和性别想象
张惠雯一方面热衷于对人物内心世界与漂泊无依的灵魂的迷恋性书写,另一方面,不断地挑战自己的叙事潜能,寻求新的叙述方式。她说:“我觉得小说的精神就是不断冒险、不断发现、不断超越。” 正是如此,在她的小说中,既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也有对情感世界的深切体验;既在寓言化的叙事中探索人类存在的可能性,也在“怎么写”的领域里探索不同的叙事手法。她尽力使叙事变化多样,不落俗套,并在不断的探索与发现中,赋予小说一种独特的气质。她在人们的情感世界中徜徉,不断剥开生命的内核与困境,以她敏锐的感知,精细的洞察力,笔锋向内探寻复杂而丰盈的内心世界。《奇遇》中不乏通过感官刺激直达内心的书写。比如,想念和焦灼等待使“我”的身心都能感到疼痛,而疯狂的感官刺激又使其陷入欲望、期盼、绝望和嫉妒中。视觉、触觉的联动是小说的艺术个性,时空中的一切细节感受都已自在自恰地成为“处境”的组成部分。在将叙事的焦点由感官刺激下沉到内心感受的过程中,她不断走进生命中的“两难”处境,将人们内心的隐痛,无根灵魂的迷茫与焦虑,缓慢而又细腻地呈现出来。小说中一个小小的眼神,一次不期而遇的邂逅,一场晚餐,一次聚会,甚至是一杯威士忌,一首情诗,一封书信,都成为展示内心世界的源动力。由对感官体验直达内心波澜的精确书写,展示出了张惠雯独特的叙事角度与审美追求。
另外,《奇遇》以非常特别的男女视角互换展现对感官和内心世界的认知和感受。“思想成形于外部世界直接压印在心灵上的感觉印记,心灵把各种感觉印记组合起来,由此开启了思维之程式。”当主人公看到房子时想象到“她怎样布置每个空间角落,怎样在其中生活,然后我也走进去,就像走进自己的家……”在这样一个男性视角下书写女性对“家”的渴望。同时,文中描写到从空置的别墅中走出时,看到了“静谧中,一条条水线在风中摆动、闪烁,细雨般沙沙作响”,“我”想,“真是座漂亮的房子,可惜空空荡荡”。这是以女性视角看到男性对待终将逝去的爱情的感受。实际上这种性别视角的互换在《关于南京的回忆》和《涟漪》中都出现过。张惠雯认为,“小说家的目光不应该只看到那些大而化之的各种人的分类,而是应该看到每一个‘人’的个体,看到这个‘人’的生活的层层面面、形形色色的细节。在我的写作中,我有时甚至会刻意避开那些比较社会性或话题性较强的题材,因为我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小说,仅仅是因为它写得好,或者是它能唤起读者某种普遍的情感和感受力,而不是因为它涉及到他们所关心的某个热门话题。我希望我选择的不同途径,能够为众声喧哗的中国小说界带来一个不同的语调。”对于张惠雯而言,更应该关注的是对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心灵的感知和触摸,是一次次发自内心的个体化叙述的冲动,不是基于常规的道德判断,也不是基于一时一地的社会热点宣传,因此,她以性别角色的替代和互换去体验人物内心感觉,书写生命个体经历的内心隐秘故事。
三、虚实结合与光影交织
虚实结合、光影交织也是张惠雯小说的重要特色。她的作品充满了温柔的光影和线条,巧妙地运用象征隐喻等现代手法,揭示人类心灵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涟漪》里头有一句话:“我身后是稳妥得像是不可能改变的生活,在我前面,是诱惑着我的极大的快乐,类似于光或梦想那样的东西。”张惠雯似乎有一种和现实格格不入的感觉;但是她所想象所谓快乐,又是一种虚幻的、很不可靠的东西——“类似于光或梦想那样的东西”。所以这里头对于记忆的书写或者对于现实的书写,全都有一种“回不去”也“到不了”的感觉。这在小说中就形成了虚实相交、如梦似幻的梦境感受。小说《奇遇》中这种描写淋漓尽致。男主人公叙述的这场香艳的奇遇就像一场梦境,醒来,一切激情归于静谧。男、女主人公从现实生活中逃离,营造了一种美好甜蜜的爱情之境,并且深深沉沦其中。而当女主人公准备和男友回国完婚,男主人公终究离不开事业和家庭,激情过后,就只剩下“回不去”也“到不了”空虚和寂寞。正如主人公所言“爱情、诗歌,那对我来说只是一场奇遇”,“乏味的、没有爱的、充满事业奋斗和金钱运算”才是命定的生活。最终,这段虚妄的爱情死于现实的“计较”。“千万别再找个商人,他们会把感情也放到秤上称称斤两,最后吃亏的总是你。”爱情感受在光影交织的叙述中如梦似幻,漂亮舒适的爱情小屋,诗情画意的邂逅,心灵与肉体的交融在作者笔下如一幕幕艺术画片,精致美好。在这幕布背后却隐藏着人性的嫉妒贪婪,自私丑陋。作家在这段虚幻爱情奇遇背后,通过人物家庭身份的割裂来完成摆脱精神束缚的书写,实现现实世界中人对自我价值的找寻与确认。这种虚实相间的情感张力之下,这篇小说不再是简单的外遇香艳故事,它由梦境穿透到现实世界之中,以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勾连出非常态空间之下的心灵崩裂与治愈。
张惠雯一直认为“故事性是某种东西所具有的那种不甘于被淡忘、不肯在意识里暗淡熄灭、引发你想象与回忆的性质,我们可以说,某个人有故事性,某件事有故事性,或者某个场景有故事性。”(张惠雯《关于〈场景〉》)无论是中国故事还是新移民故事,她都不是致力于情节和细节的真实描写,而是在认真地审视和诉说着感情体验,传递她对人性问题的尖锐与怜悯。“如果你有幸和任何一个生活于幸福模式之家的人深谈,如果你能窥见哪怕一丁点他的内心世界,你几乎都会发现那种无法治愈的、现代的烦闷,那种挥之不去也无所寄托的欠缺与失落。”(张惠雯《关于幸福》)《奇遇》告诉我们:无论成年人多少寻欢作乐的经历或是经济上的极大满足都难以彻底治愈这种“现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