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切伊·佩普日察电影的人文关怀指向探析
齐志辉 王培时
(1.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2.河北美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70)
在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家》之后,波兰电影便渐渐淡出了中国大部分普通观众的视野,直到马切伊·佩普日察凭借《我是杀人犯》(ą,2016),《盲琴师》(,2019)等屡次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后,波兰电影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佩普日察于1964年生于波兰的卡托维兹,亲历了波兰在政治体制以及电影产业上的重大变革,他的电影始终以现实为关注焦点,力求还原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洋溢着浓郁的人文关怀气息。
一、人文主义与波兰电影及佩普日察创作概说
人文主义(Humanism,又被译为人道主义)一词源自古罗马的“Humanus”,即理想充实,在身体与智识上都健全、美好的人。1860年,瑞士文化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彼此间有重要关联的概念,即“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概念也长期为学术界奉为圭臬。在布克哈特的总结中,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是人们走出黑暗、野蛮中世纪的关键。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哲学”开始为人们所关注,个体的尊严、价值以及人生目的被呼吁得到尊重。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对人有着较高肯定与尊重,以人为万物尺度的思潮得以复现,人们在发现世界的同时,也重新发现了“人”。而这一思想遗产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继承,在由欧洲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超越了文学艺术领域,进入哲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尽管数百年来,人们对文艺复兴的定义与得失言人人殊,对人文主义的具体理解也有所不同,但就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关注人的命运、保护人的基本权利这一点却是没有争议的。而电影艺术诞生于1888年,从其出现之日起,人文主义早已深入人心。无论是由卢米埃尔兄弟开辟的面向现实一脉,抑或是由乔治·梅里埃肇始的虚境幻想一脉,人文主义都是衡量电影作品是否优秀的尺度之一。对一辈辈的导演而言,人文主义精神也被其自觉视为自己创作的基本动力与方向。
在谈及马切伊·佩普日察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波兰电影的发展概况稍加梳理,以获得一个较为明晰的、佩普日察的艺术成长环境。长期以来,波兰电影一直以鲜明的现实主义、悲怆沉郁的风格而为人们所熟知。波兰电影最开始为世人所瞩目之际,正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此时的波兰电影人如瓦伊达、卡瓦列洛维奇等,无不自觉地贯彻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主张,以电影来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波兰底层人民造成的种种悲剧故事,如《最后阶段》《华沙一条街》等,莫不如是,他们所建立的“波兰电影学派”也显赫一时。二战后,波兰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苏联电影的影响:“在对某些敏感题材的挖掘上,比如揭露官僚制度、嘲讽极权政治、解释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偶然际遇、反思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以化解英雄主义概念等题材上两国常常不谋而合。”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风云变幻后,需要应对空前市场经济考验的波兰电影依然选择了现实题材,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白》《红》三部曲,霍夫曼的《火与剑》等。新世纪崭露头角的年青一代导演更是不约而同地一起聚焦下层人物琐碎而不无凄凉的生活,如《你好!特雷斯卡》《艾迪》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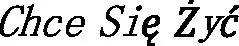
二、佩普日察电影的人文关怀指向
纵观佩普日察的电影创作,我们可以将其人文关怀指向主要总结为以下三点:
(一)关怀弱势群体
首先便是对弱势群体的强烈关怀。弱势群体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由于群体的力量、权力相对较弱,因而在分配、获取社会财富时较少较难的一种社会群体。……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他们受先天或后天条件所限,与他人竞争时处于不利的位置。而电影人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则体现在将后者的际遇搬上大银幕,吸引更多人注意到这一群体,进而接纳他们,改善他们的种种处境。就佩普日察而言,他的电影有着非常明晰的对残障人士的注目。残障人士在生理特征与体能状态上相对健全人而言存在一定区别或弱势,这也就造成了他们在占有社会资源上的困难,不在少数的残障人士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成为消失于大众视野的高度边缘者,而部分残障人士在凭借自身的奋斗脱颖而出后,依然难以彻底摆脱他人的偏见、歧视等。
在佩普日察讲述波兰天才爵士钢琴家米耶特·考什传奇一生的《盲琴师》中,主人公米耶特在度过了无忧无虑的12年后,开始遭遇眼疾,无可挽回地渐渐失去视力,失明所带来的除了直接的生活不便外,还有其社会地位的骤然失落,米耶特从此陷入孤独之中,脾气也越发古怪易怒,直到发现自己在钢琴上的天赋,将生命与音乐融合到一起,功成名就后,米耶特才逐渐重建自己在社会利益格局中的位置,找回了自信。在他一度有希望恢复部分视力时,却要付出牺牲一部分听力为代价,残障始终挥之不去,难以逾越。种种痛苦导致了米耶特最终还是选择在29岁时跳楼自杀。又如在同样基于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生命如此美好》中,佩普日察以马特乌斯这一角色,呈现了脑瘫患者难以言表的巨大痛苦。马特乌斯自幼不能如常人一样说话与控制四肢,甚至不能正常做出点头、摇头的动作与表情,以至于他不仅常年活动范围极其有限,且无法与他人沟通,即使是自己的父母姐弟,也不能真正了解马特乌斯的内心世界。马特乌斯在童年时,就在明明心智与情感都正常的情况下被诊断为智力障碍,而医生甚至尖锐地将他比作一棵蔬菜。随着时间推移,父亲去世,母亲衰老,姐弟也开始拥有自己的家庭与事业,马特乌斯便被送往智障疗养院。他不仅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没有获得安身立命的职业,甚至没有得到合理的看护,在两性情感上也没有得到满足,在年轻貌美的女护工玛格达前来给予他各方面的慰藉,甚至带他去见自己的家人时,马特乌斯一度以为自己得到了爱情,但实际上他只是被玛格达用来激怒父亲的工具。在此,残障人士作为弱势群体其价值是被忽视的,其利益是被全方位侵害的。
(二)检视社会痼疾
其次是对社会中存在的诸多痼疾的省察检视。如与弱势群体福利相关的社会工作的严重不到位。在《生命如此美好》中,护工对马特乌斯的照顾是极为随意的,如他们并不知道他需要坐起来吃饭,在发现他咬破了嘴唇后便不由分说拔掉了他的牙齿,他们的疏漏与粗暴直接导致了马特乌斯的自杀。又如执法部门的黑暗,司法部门的腐败和人们对权力的卑躬屈膝。在《我是杀人犯》中,警方迟迟不能将真凶绳之以法,而在工党第一书记的侄女也被害后,才调来精英雅努什力求破案。然而雅努什依然束手无策,为此不惜制造了大量伪证来做实一个无辜者沃尔克就是真凶。雅努什为此得到了如房子、彩电等奖赏,尽管他一度良心发现,但警局高层与法官等沆瀣一气,力保铁案做成。更为讽刺的是,沃尔克入狱后,杀戮其实并未停止。与奉俊昊的同样以真实连环杀人案为原型改编而成的《杀人回忆》类似,在《我是杀人犯》中,佩普日察并未试图给观众一个关于真凶的确切答案。佩普日察只是将相关情况一一展示给观众,让观众对整个事件乃至时代进行自己的理解与评判。当部分观众笃定自焚的精神病人就是真凶时,实际上也如电影中的某些执法者一样犯下了轻率定罪的错误。而电影中知识分子们排队与领导合影领彩电、雅努什作为英雄给谋杀展览馆剪彩的情形,更是极具讽刺。詹明信在阐释“民族寓言”说时提出了“政治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他认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political intellectual),“文化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是政治斗士,也从事政治的实践活动(praxis)”。奉俊昊与佩普日察实则就是始终对社会现状,对国家伤痕保持敏感的知识分子。
(三)思考人际创痛
最后,佩普日察也思考了底层人之间存在的互相伤害。佩普日察在对底层人抱有深切同情的同时,也能冷峻地注意到,这些难以对上位者造成伤害,与上位者生活间存在隔膜的人,往往也是自己同类苦难创痛的制造者,这是十分可悲的,也是当下人们需要避免的。例如在《盲琴师》中,米耶特罹患的实际上是一种遗传疾病,他的父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他不幸的来源,何况父亲本人也存在发病致盲的可能,然而父亲在知道米耶特将药石罔效地变为盲人后,竟产生了杀害亲子以摆脱这一“累赘”的念头。父亲将米耶特放在马厩里并鞭打马,寄希望于马将米耶特踩死,这一段经历以及随后母亲将他送往盲童教会后关门离去的一幕,给米耶特的心灵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后来父亲果然也变为了盲人,尽管百般思念儿子,抚摸着无法再看到的登载儿子出国演出新闻的报纸,他也并未对米耶特道歉。
类似的还有在《生命如此美好》中,马特乌斯在自己承受了来自他人伤害的同时,也因终日只能坐着凝望窗外而见证了其他人遭遇的底层互害:邻家女孩安卡的母亲因为两性关系混乱而导致了安卡被性侵,而母女俩也招致了严重的暴力。马特乌斯设计让施虐者被警察拘留,心惊胆战的安卡母亲决定搬家躲避,马特乌斯在解救了安卡的同时,也彻底失去了这位朋友。在《我是杀人犯》中,沃尔克的妻子儿女无疑也是底层人物,然而在一百万的诱惑之下,沃尔克妻子指控自己的丈夫就是杀人凶手,一对不谙世事的孩子也为了摆脱学校师生的霸凌而做出对父亲不利的证词。佩普日察将这种绝望摆在观众面前:来自亲密关系的互害进一步巩固着底层个体的困境,而是否成为受害者实际上与性别、残疾或健全,成年或未成年无关,要想避免成为受害者,有赖于每一个人心怀善意,最终构建起合情合理的守望相助模式与阶层突破机制。
三、佩普日察于当代中国电影的启示意义
在当下的中国影坛,佩普日察的创作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毫无疑问地,佩普日察再一次宣告了在电影中倾注人文关怀的必要性。佩普日察等人的作品再一次说明了,对人的关注与同情是电影人永恒的话题,它并不因电影类型的变化,电影制作流程的改变或权力、导演与观众之间关系的错位而过时。在佩普日察等电影人的积极努力下,现实主义继续大放异彩,成为波兰电影在转型之后继续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电影文化进行交流,获取国际声誉的关键。佩普日察电影在横扫波兰各大电影节奖项的同时,又得到了蒙特利尔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的肯定便是明证。在中国,同样不断以电影来展现自己人文观察与思考的电影人亦不在少数,如贾樟柯就曾表示:“在我们的视野中,每一个行走着的生命个体都能给我们一份真挚的感动,甚至一缕疏散的阳光,或者几声沉重的呼吸。我们关注着身边的世界,体会着别人的痛苦,我们用对他们的关注表达关怀。”其所创作的如《小山回家》,“故乡”三部曲等影片也正因此而价值粲然。尽管波兰与我国国情并不相同,但都经历着社会的巨大变革与飞速发展,观众对同类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对他们在时代冲撞下的尴尬,被时代抛弃的疼痛是有了解欲望和共情可能的,这呼唤着中国电影人继续注视自己的国家,体悟与演绎经历时代变化,遭受震荡的无名之辈的遭遇。
其次,佩普日察电影又彰显着现实性与艺术性并不矛盾。电影在拥有社会文化意涵的同时,还应给予观众隽永的美学享受,电影的具体叙事手法、镜头语言等始终是值得电影人精研推敲的,如小津安二郎就力主以电影来完成静物画,追求“秩序与自由的有机统一。……忠实恪守繁文缛节、束缚极多的程式”,如固定机位,几何学构图等。在佩普日察的电影中,不无静美温情的镜头设计,如在《生命如此美好》中,电影结束于马特乌斯在夜里独自一人通过望远镜看向天空,此时他身披一束浅淡的月光,仿佛置身于温柔的梦境中,而旁白则是:“今天是八月十一日,现在是晚上十点半。天上没有云,一轮新月高悬空中。我正看着水星和金星,明天的天气一定很好。”这一画面在本身就极为美好的同时,又重申着整部电影的主题,即马特乌斯父亲教他的“一切都会变好的”,而在窗边看星星这一场景,又呼应着马特乌斯少年时与父亲为数不多,却照亮了他一生的温情时光,是父亲教会马特乌斯观察星星,“人们以为星星是静止的,其实不是。星星一直在动。只有我们,地球上的人们,以为它们是静止的”。而父亲的死也是因为酒后他爬到窗边提醒儿子看他的“人造星星”,即烟花。
最后,佩普日察证明了,现实性与娱乐性、大众化之间存在协同并存的可能。毋庸置疑,目前现实主义影片处于一个商业语境勃兴,要谋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语境中,“大众以热情的关注(收视率、点击率、谈论与玩味的深广度)和货币式投票(通过各种方式购买相关“产品”)使自己成为文化或趣味市场的主体,成为一切资源的集体操作者与构成者。与之相比,官方趣味、精英趣味却在现实的社会文化生活中逐渐失宠、失语而相对退隐”。在这样的情况下,波兰电影已做出了相应调整,以佩普日察来看,他善于在成熟的类型范式下进行创作,其《新郎二选一》《我是杀人犯》《盲琴师》分别是典型的、有的放矢的喜剧片,悬疑片与传记片,在讲述精彩故事与观照社会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佩普日察还善于在电影中加入幽默的桥段。如在《生命如此美好》中,马特乌斯的旁白介绍了“我”在幼年时就因为母亲的裁缝职业而上了“生理课”,即通过女性的胸部来给她打分,在成年后,他一直以此来给女护工们打分,自己的姐姐因为讨厌他所以是零分,而那位让他惊艳的女护工玛格达让他“这一次我决定忽略胸部”。这让观众忍俊不禁。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电影亦已取得了客观的探索成就,如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饶晓志的《无名之辈》等,都可以视为其中的佼佼者,观众获得一种笑中带泪,悲中含喜的观影快感。另外,从《盲琴师》《我是杀人犯》中不难看出,对音乐的巧妙运用也是佩普日察增强电影娱乐性的方式之一,在《我是杀人犯》中,音乐实际上起到了讥讽主人公颟顸无能的作用,在此不赘。
正如安德烈·巴赞指出的:“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人道主义,其次才是导演风格。”波兰导演马切伊·佩普日察的创作正印证了这一点。可以说,在现实主义依然是我国电影创作主流的当下,佩普日察电影所具有的启发与鼓舞意义是不应被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