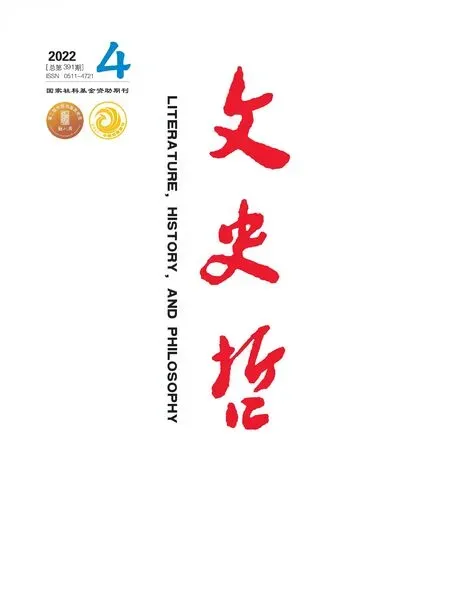“前后七子”并称与“前七子”塑造之完成
——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为重点
孙学堂
我们所了解的文学史往往并非历史发展的原貌,而是由世代累积而形成的一系列文学史知识,明代的文学史也不例外。关于“前后七子”尤其是“前七子”的认知,便存在这样一个累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嘉靖前期的王九思、李开先等人和明清之际的钱谦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王九思等人对“前七子”的初步塑造,笔者有另文专门论述。本文拟探讨明清之际随着“前后七子”并称,钱谦益等人在“前七子”重塑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前后七子”并称始于明末
自清代以来大量文献把“前后七子”并称,随之也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后七子”是“前七子”的追慕者、继承者。这在当今可以说是文学史常识,常有研究者采用“后七子举起前七子的复古旗帜”之类的表述。但此类表述是有问题的,因为并没有一个“前七子”文学集团先于“后七子”而存在。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徐中行、吴国伦等人在京师有过结社活动,不久后便被世人称为“嘉隆七子”(或称“嘉靖七子”“隆万七子”),可他们并不知道之前有个以李、何为首的“七子”社团。他们普遍推崇李梦阳、何景明,对徐祯卿、边贡甚至是王廷相诗的评价也比较高,而对康海、王九思却并无多少好评。他们从未把后人所说的“前七子”(或称“弘治七子”“弘正七子”“弘德七子”)视为一个文学集团。在他们的论著中,我们看不到任何表明他们追慕“前七子”的迹象。直到万历时期,大多数诗人或批评家谈论弘治、正德诗坛,所推崇的主要诗人还是李、何,有复古倾向的人也普遍推崇徐祯卿和边贡,或者把李、何、徐、边合称“四杰”,而所言之“七子”则是指“嘉隆七子”。
嘉靖时期的确有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等人,把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等弘、正复古思潮中的重要人物描述为反对李东阳萎弱文风的文学社团。王九思本就是这一复古思潮的亲历者,嘉靖十年(1531)他自撰《渼陂集序》说:“予始为翰林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焉。献吉改正予诗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然亦非独予也,惟仲默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发之。”即已把康海和李梦阳视为诗文复古集团的领袖;康海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嘉靖十一年所撰《渼陂先生集序》,列举弘治时“所以反古俗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并说他自己“幸窃附于诸公之间”,这便是后来人们认定的“前七子”的全体成员。张治道、李开先亲炙于王九思和康海,把康海落职解释为因其文学活动、文章成就和文坛影响而遭到李东阳嫉妒、嫉恨。在他们笔下,一个有文学活动和文学主张的诗文复古社团被描画得愈发清晰。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说康海“与鄠杜王敬夫、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吴下徐昌谷为文社,讨论文艺,诵说先王。西涯闻之,益大衔之”;李开先《渼陂王检讨传》说:
是时西涯当国,倡为清新流丽之诗,软靡腐烂之文,士林罔不宗习其体……及李崆峒、康对山相继上京,厌一时诗文之弊,相与讲订考正,文非秦、汉不以入于目,诗非汉、魏不以出诸口,而唐诗间亦仿效之,唐文以下无取焉,故其(引者按:指王九思)自叙曰:“崆峒为予改诗稿今尚在,而文由对山改者尤多,然亦不止于予,虽何大复、王浚川、徐昌谷、边华泉诸词客,亦二子有以成之。”
这里引述王九思《渼陂集序》的说法,且“补充”列出了七人的全员名单。

提出“前七子”这一名号并将其与“嘉隆七子”并称,是到明末才出现的现象。刊于崇祯十六年(1643)的《皇明诗选》卷首李雯(1608-1647)序云:
至于弘、正之间,北地、信阳起而扫荒芜、追正始,其于风人之旨,以为有大禹决百川、周公驱猛兽之功。一时并兴之彦,蜚声腾实,或咢或歌,此前七子之所以扬丕基也。……又三四十年,然后济南、娄东出,而通两家之邮,息异同之论,运材博而构会精,譬荆棘之既除,又益之以涂茨,此后七子之所以扬盛烈也。
可见李雯对“前七子”“后七子”是十分推崇的。观《皇明诗选》的编选次序,也可知陈子龙、李雯、宋徵舆已经有意识地把“前七子”“后七子”分别编在一起,只是由于分体编排,这一意图呈现得不很清晰。因为诸子所擅诗体不同,“前七子”中除李梦阳、徐祯卿外没有其他人八种诗体全部入选;就单一诗体而言,惟于五言古诗中有六人入选,其他各体入选者多少不一,而康海只选得七绝一首,在作者名下有宋徵舆的评语说:“对山工于文而拙于诗。”此一评语既可以代表人们的普遍认识,也可以视为《皇明诗选》虽接受“前七子”之说却不重康海诗的原因。钱谦益《列朝诗集》边贡小传说:“弘治时,朝士有所谓七子者:北郡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吴郡徐祯卿、仪封王廷相、济南边贡也。”宗臣小传说:
于鳞既殁,元美为政,援引同类,咸称五子,而七子之名独著。先是,弘正中,李、何、徐、边诸人,亦称七子。于是辁材讽说之徒,盱衡相告,一则曰先七子,一则曰后七子,用以铺张昭代,追配建安。……岂不亦发千古之笑端,遗圣朝之国耻乎!
其批评嘲讽之态度,与李雯之推崇意见完全不同。钱氏《列朝诗集》完成于入清之后,其所谓“辁材讽说之徒”,很可能暗刺云间三子。《列朝诗集》选诗,把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选在一起,而把何景明、薛蕙、李濂等人放在一起,以示“李、何”分庭抗礼之意;至于徐祯卿,则别置于吴中四子之列,以突出其“江左风流”之特点。
笔者所见明清之际谈到“前后七子”的其他文献(包括学界同仁所引用者),还有费经虞《雅伦》、计东《改亭文集》、毛先舒《诗辩坻》、宋荦《漫堂说诗》等。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一在陈子龙名下引龚翔麟之言,说艾南英讥诮陈子龙“学前后七子之诗,而并学其文”,龚氏自己则赞美陈子龙诗“力返于正”,认为“讵可藉口七子流派,并攒讥及焉”。尽管《静志居诗话》中所称“七子”大都是指“嘉隆七子”,而朱彝尊所辑《明诗综》把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七人编在一起,则说明他也接受了“前后七子”之说。
上举诸人对诗文复古的态度不同,都较早使用了“前(先)后七子”之说。他们的说法,毫无疑问是接续了康海、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等人关于弘、正复古文学“集团”的记述,从而使李开先用过的“弘德七子”说在“尘封”七八十年后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上文已经谈到,即使在王九思、李开先等人的书写中,本有“三才”“五子”“七子”“九子”等许多说法,其中并不甚特殊的“七子”说之所以能够被人拣选出来与“嘉隆七子”并称,后者的七人数目显然起到了较为重要的“选择”作用。对于近百年前的当事人康海、王九思,和年辈稍晚的记述人张治道、李开先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偶然的“历史选择”。而作为被选择的对象,康海的《渼陂集序》和李开先《渼陂王检讨传》所列出的七人名单对于“弘德七子”的具体构成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定型”作用。
一个在当时未产生广泛影响的说法在数十年后开始流传,固然有偶然性的因素,比如一定有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人阅读了康海、王九思、张治道等关中文人及与他们有过密切交往的李开先等人的相关文献,并且接受了他们的说法,而且“弘德七子”人数恰好与“嘉隆七子”相配;而必然性的因素更不可忽视:明末党社运动十分活跃,标榜风气严重,人们回看弘治、正德间的文坛状况,最容易接受具有党社或集团色彩的描述,而王九思、李开先和张治道的记载最符合人们的期待视野。而且,无论是复古思潮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在回顾明代文学发展时,都注意到李梦阳、何景明所代表的弘、正复古与李攀龙、王世贞所代表的嘉、隆复古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将二者并称,也可以视为云间三子、钱谦益等人回顾和描绘明代文学发展史的客观需要。
“弘德七子”的说法在明末如何被发现、如何与“嘉隆七子”并称为“前(先)后七子”,通过何种方式流传开来,这些历史的细节现在已很难求得其详。可以肯定的是,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表述为先有“前七子”(所谓“弘正中,李、何、徐、边诸人,亦称七子”)、世人遂将“后七子”与之并称(所谓“辁材讽说之徒,盱衡相告……用以铺张昭代,追配建安”),是与事实不符的。相比之下,李雯的表述“此前七子之所以扬丕基……此后七子之所以扬盛烈”,虽然也是把“前七子”的存在视为事实,但其表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后叙语态,更像是文学史总结者提出的论断。
在把“前七子”和“后七子”并称的这些人中,成名最早、影响最大的是钱谦益。他比李雯、陈子龙年长二十七八岁。他们彼此相识,用了相同的说法,是不约而同,还是谁受了谁的影响,尚难遽然得出结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虽然完成较晚,刊刻于清初,但其着手编纂的时间却早在天启初年,比陈子龙等人编纂《皇明诗选》还早了十几年。从种种迹象看,钱谦益在“前后七子”并称的流传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编纂《列朝诗集》,所撰诗人小传的资料来源很广,其中叙论弘、正诸子,大量采纳了李开先撰写的系列传记。他关于“弘治七子”的说法,可以肯定是来自康海、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诸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自己的加工改造。
虽然《列朝诗集》在编排顺序上并未全按“前七子”“后七子”整齐划一地进行,甚至也并未采用“前七子”这一“标准”表述(他用的是“先七子”),但就对后来文学史关于“前后七子”书写的影响而言,钱谦益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云间三子”和其他诸家。换言之,钱谦益对“前后七子”说的流行,对弘治、正德间文学史的塑造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前后七子”之说虽然未必是由钱氏率先提出,但作为一个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其所包含的知识、概念,却主要是由钱氏来塑造完成的。
二、重塑“前七子”的派系关系
弘治时期,文坛上本无清晰的流派或阵营分野,而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的相关记载都把康海和李东阳的矛盾上推到弘治年间,且推及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人,从而塑造了一个反对李东阳萎弱文风的文人集团,也描绘了一个有观念冲突、有阵营分野的弘、正文坛格局。按照他们的描述,李、何、康、王等七人为主的文学集团早在弘治间便开始了复古的文学活动,因而遭到李东阳的嫉妒和嫉恨。康海、王九思的落职,就是这一斗争的当然结局。他们的记述为后来文学史家关于“前七子”的书写奠定了基础。明末许多人在回顾复古论的发展时,采纳了他们的说法,开始把“前后七子”并称。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云间三子”在内的多数人只是接受了“弘德七子”的名号,把前、后两“七子”相提并论,并未充分关注“前七子”与李东阳矛盾斗争的话题。而钱谦益却大不一样。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王九思等人关于文学派系斗争的记述。可是他转换了叙事立场,改变了叙事声音,完全站到李东阳的一边,从而使王九思、张治道等人初步勾勒(建构)出来的复古派和李东阳相对立的阵营分野愈加清晰,而以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呈现出来。
钱氏对弘、正文坛格局和“前七子”文学倾向的进一步塑造,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把历史上本不清晰的“复古派”与“茶陵派”分野勾勒得轮廓鲜明;二是批评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反对李东阳为代表的台阁体,斫削“太和元气”。
(一)建构“前七子”与“茶陵派”之分野
我们认定钱谦益关于“弘治七子”的提法来源于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等人,除根据他们列出的七人名单一致外,还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钱氏特别强调“七子”与李东阳的对立关系。在嘉靖后期至明末的其他文献中,很难见到把李东阳与复古论对立起来的说法,一般都认为李东阳汲引后进,对复古思潮有先导之功,如王世贞谓:“长沙之于何、李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顾起纶《国雅品》赞同王世贞此说,并认为李东阳“尤能推毂后进,而李、何、徐诸公作矣”。钱谦益将二者对立起来,明显承袭了王九思等人之说。但不同的是,他完全站到了李东阳的立场上,把李、何等“七子”视作一个“诋諆先正”的文人群体。《列朝诗集》李东阳小传云:
国家休明之运,萃于成、弘,公以金钟玉衡之质,振朱弦清庙之音,含咀宫商,吐纳和雅,沨沨乎,洋洋乎,长离之和鸣,共命之交响也。北地李梦阳,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窜窃剽贼之学,诋諆先正,以劫持一世;关陇之士,坎壈失职者,群起附和,以击排长沙为能事。王、李代兴,祧少陵而祢北地,目论耳食,靡然从风。
“关陇之士,坎壈失职者”主要指康海和王九思。事实是,康海和王九思才是与李东阳发生矛盾的主角,他们把自己塑造为反对萎弱文风的一个阵营,目的就是要把自己与李东阳的个别矛盾说成是文坛新旧势力斗争的普遍矛盾。钱谦益接受了他们的说法,并且顺理成章地把七人中影响最大的李梦阳视为“诋諆先正”的代表,反而认为康海和王九思只是李梦阳的“附和”者。他还说:“德涵于诗文持论甚高,与李献吉兴起古学,排抑长沙,一时奉为标的。”则是把李梦阳、康海视为“七子”一派之魁首,与王九思的说法更为相近。
钱谦益还提出了“西涯一派”的概念,说:“吾友程孟阳读怀麓之诗,为之擿发其指意,洗刷其眉宇,百五十年之后,西涯一派焕然复开生面,而空同之云雾,渐次解驳。”这里所谓“西涯一派”主要是就诗体诗风而言。钱氏还通过《列朝诗集》的编纂,塑造了一个以李东阳为宗主、以石珤、罗玘、邵宝、顾清、鲁铎、何孟春“六公”为骨干,以陆深、杨慎、乔宇、林俊、张邦奇、孙承恩、吴俨、靳贵等“长沙之门人”为主力的“西涯一派”。他盛赞出西涯之门者“号有家法”,且赞美这些人“直道劲节,抗议论而犯权倖,砥柱永陵之朝”。他以这样的方式,全面反驳了王九思所宣称的“西涯为相,诗文取絮烂者,人材取软滑者”之说。
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等人谓李东阳嫉妒和排斥复古派,却从未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李东阳的门人群体,也没有指出或暗示李东阳周围有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钱谦益之所以要勾勒(建构)出“西涯一派”,针对的就是王九思、李开先等人批评李东阳的言论,或者说是对于王九思、李开先等人抨击李东阳的一系列言论的跨时空“回击”。从这一意图来看,“西涯一派”的建构与王九思等人建构“弘德七子”的意图是相似的。钱谦益评杨慎时说:“及北地哆言复古,力排茶陵,海内为之风靡。用修乃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不与角胜口舌间也。”认为杨慎也有为李东阳“复仇”的意图,这同样属于想当然之论。钱氏的这些评论以记述的方式呈现,很具有迷惑性,却愈发远离了弘治、正德间文坛的本来面目。
钱谦益从历史文献中择取“弘治七子”说,并且建构了“茶陵派”,把弘治、正德时期本来模糊的派系分野描绘得轮廓鲜明,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先是被万斯同《明史》所采用,该书李梦阳传谓:
初,弘治时,李东阳以宰臣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复古学,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其党王九思、康海、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和之,于是有“七才子”之目。……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祖述之,天下奉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而诗文正派实自梦阳而亡。迄于崇祯,其风始息,而国运亦终矣。
这段话中,无论是对李东阳“天下翕然宗之”的巨大的文学声势与影响的描述,还是把李梦阳视为李东阳的主要反对者,都明显采用了钱谦益的说法,只不过叙事立场稍显中立而已。这些说法后来被张廷玉主持的官修《明史》所沿袭,又被《四库全书总目》所采纳,成为更加权威的官方言论而广为流传。
把个体冲突向群体方向解释,把政治衍生的冲突解释为文学观念的冲突,是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等人建构“弘德七子”的基本策略,由此给后来的文学史书写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原发性问题”;钱谦益非但没有识破这些问题、力求还原文学史的原貌,反而将其继承和发扬,在推动“弘德七子”之说广泛传播的同时,也使这些原发性问题变得愈发严重。近年来有一些探讨复古派与李东阳(或茶陵派)“交恶”的论著,看似把文学群体和流派研究推向了深入,但实际是陷入了由康海、王九思、李开先、张治道首发,再由钱谦益转手重塑的历史迷雾中。
(二)认定“前七子”反对台阁体
上引万斯同《明史》把李东阳诗文视为“正派”,把李、何、王、李与“国运”之衰联系起来,也明显受到钱谦益影响。钱谦益认为李东阳代表的是“馆阁之体”,为“太和元气”之所系。其《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云:
国初之文,以金华、乌伤为宗,诗以青丘、青田为宗。永乐以还,少衰靡矣,至西涯而一振。西涯之文,有伦有脊,不失台阁之体。诗则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李空同后起,力排西涯,以劫持当世,而争黄池之长。中原少俊,交口訾謷。百有余年,空同之云雾,渐次解驳,后生乃稍知西涯。呜呼唏矣!……卷中之诗,虽非其至者,人或狎而易之。不知以端揆大臣,衔君命祀阙里,纪行之篇什,和平尔雅,冠裳珮玉,其体要故当如此。狎而易之者,只见其不知类而已矣。

认为“前七子”反对台阁体,也是现当代人的文学史“常识”。如宋佩韦《明代文学》说:“三杨台阁之体,平正纡余……后来李梦阳等复古派崛起,对于台阁体诗文,攻击不遗余力,而三杨遂为众矢之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说:“打起复古派旗帜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遂起来反对,打垮了‘台阁体’对明代文坛的统治。”这一“常识”可以追溯到钱谦益的相关论述。其实在弘、正复古诸子的文集中,并无从文体文风角度批评台阁体的意见。李梦阳还有诗云:“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说“前七子”在主观倾向上反对台阁体是不客观的,熊礼汇先生在《明清散文流派论》中对此做过有力的辨析。但可惜熊先生还是相信了王九思、康海、李开先、张治道等人的说法,认为“前七子”反对的“是李东阳代表的现行台阁文风之弊”,他还强调说:“不能把秦汉派反对李东阳代表的台阁文风之弊,说成是反对三杨台阁之体。”这也就基本认同了钱谦益就李东阳和“前七子”的对立关系所提出的“前七子”“訾謷馆阁之体”的看法。
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引康海之言说:“本朝诗文,自成化以来,在馆阁者倡为浮靡流丽之作,海内翕然宗之,文气大坏,不知其不可也。”针对李东阳而发,代表了“关中一派的私议”,不可推及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等其他人,更不可推及弘治、正德间更为广泛的复古思潮。钱谦益义愤填膺地批评李梦阳“力排西涯,以劫持当世”,从而带动“中原少俊,交口訾謷”台阁体的说法,是沿着王九思等人夸大事实的记述更向前一步,从而走得更远,因而也就非常值得怀疑。
钱谦益的说法,除了充分注意到康海和王九思对李东阳的不满,及李梦阳《凌溪先生墓志铭》对李东阳确有微词这些事实之外,还可能受到了后七子言论的“干扰”。王世贞《艺苑卮言》说:
其后成弘之际,颇有俊民,稍见一斑,号为巨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随就,即事分题,一唯拙速。和章累押,无患才多。北地矫之,信阳嗣起,昌谷上翼,庭实下毗,敦古昉自建安,掞华止于三谢,长歌取裁李、杜,近体定轨开元,一扫叔季之风,遂窥正始之途。天地再辟,日月为朗,讵不媺哉!
此所谓成弘之际的“俊民”,指的就是李东阳。王世贞认为李、何、徐、边“矫之”,遂有“天地再辟”之功。王世贞这段话,是真正不满于李东阳的诗文。由此可以说,如果把“前后七子”一体化看待,笼统地说他们反对李东阳和台阁体的诗风文风、改变了台阁体统治文坛的局面,会更客观一些。四库馆臣说:“明代文章自前后七子而大变,前七子以李梦阳为冠,何景明附翼之,后七子以攀龙为冠,王世贞应和之。……尊北地、排长沙,续前七子之焰者,攀龙实首倡也。”“尊北地、排长沙”,实际说的是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而并没有说李梦阳与“前七子”也“排长沙”。但前后文连在一起,读者自然会觉得“前七子”也是“排长沙”的。钱谦益却主要把反对台阁体、訾謷李东阳这笔账算在了“前七子”尤其是李梦阳的头上,就远离事实了。即使从创作角度看,李梦阳的确在转变台阁体诗风文风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不能就此认为他和何景明等人反对台阁体。
从钱谦益提出李梦阳等人“訾謷”李东阳为代表的台阁体,到今人所说的前七子反对和“战胜”台阁体,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过渡,那就是《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说。宋佩韦《明代文学》便引用了馆臣所撰《明诗综》提要:
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春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
这段话在整个明代文风丕变的视域下讨论台阁体与复古派之兴替,大概是为了叙述线条的清晰明快,遂省略了“如衰周弱鲁,力不足御强横,而典章文物尚有先王之遗风”的李东阳这一过渡环节,把前后七子直接与明初的台阁体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战胜了前者。四库馆臣对台阁体并不像钱谦益那样推崇,尤其不满于台阁体影响之下形成的巨大流弊,因此对“前后七子”带来的“文体一新”评价颇高。《空同集》提要云:“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制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细究这些表述,说的是李、何、王、李崛起、改变了台阁体带来的肤廓之风,并未说他们(尤其是“前七子”)反对或“攻击”台阁体,但其表述却很容易引起这样的理解。
三、重塑“前七子”的派系特征
由上引四库馆臣之言可见,在长时段、大跨度的历史叙述中,把“前后七子”并称,最突出的效应是把相隔半个世纪的两次复古高潮等同看待,甚至等量齐观。因为“前七子”集团本不存在,不但其派系关系是“层累”建构起来的,其派系特征也是随着与“嘉隆七子”并称才愈加“清晰”起来:接受这一并称的人,大部分是拿“后七子”的派系特点来看待和评价“前七子”,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弘正复古思潮的本来面目,也遮蔽了相隔半个世纪之久的两次复古思潮的巨大差别。
钱谦益讽刺那些把“前后七子”并称的人是“辁材讽说之徒”,似认为云间派用这种标榜方式推动了复古主义的传播。其实,云间三子作为“前后七子”的追慕者,很注重不同个体的特点和成就高下的衡估,如《皇明诗选》中称李梦阳为“国朝诗人之冠”,称何景明“与李梦阳齐名”而“稍有伯仲之分”;称徐祯卿“乃与二雄鼎足”;称边贡“声价在昌谷之下,君采之上”,等等。对于他们而言,把并不擅长诗歌的康海、王九思一并视为“七子”集团的重要成员,反而会为学诗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扰。与他们不同,钱谦益则是以俯视的态度批评“前后七子”。他并未细心探究弘、正与嘉、隆两次复古思潮的巨大差别,而是相当粗率地把“前后七子”等同看待,认为他们等无差别。他的近乎粗暴的批评,更容易被“辁材讽说之徒”所接受。
而在明清之际,钱谦益又是最重要的明代文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者,也是影响最大的明代文学史撰写人。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他是以时代距离较近、他更熟悉的“后七子”的特点描述和批评“前七子”,对于史料的组织和评论出现了较大偏颇,但他的说法影响极大,为同时代其他人所莫及。《明史》和《四库全书总目》中不少把“前后七子”等同看待的论评,比如认为“前后七子”皆“摹拟剽贼”、缺乏个人面目,皆相互标榜、猎取当世声名等,也都是采纳或接受了钱谦益的说法,并推波助澜,使其产生了更为深广的影响。
(一)“前后七子”皆“摹拟剽贼”、缺乏个人面目
弘治时期兴复“古学”的原初意图,是以朝廷“右文”为机遇,倡导质朴浑厚的诗文风格,为再创盛世的社会政治理想服务。观李梦阳《与徐氏论文书》、徐祯卿《与朱君升之叙别》等文可知其详。但正德以后政局骤变,士大夫原初的复古理想在现实中无奈地失落了。所以到正德后期发生的李、何论争,所争之事已与再创盛世、政治教化无关,而主要集中在诗文体貌和如何师法古人等问题上,表现为“铸形塑镆”“独守尺寸”与“领会神情”“舍筏达岸”的分歧。三四十年之后,“嘉隆七子”仕宦于严嵩当国之时,其所提倡的复古,出发点本就在如何师法古人,颇有以钻研诗文逃避黑暗政治的意味,与李、何等人积极干预现实的人生态度迥然不同。后七子推崇李、何,也主要着眼于诗文体貌和法度层面。李攀龙《送王元美序》评李梦阳“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这是肯定之;又说“超乘而上是为难尔!故能为献吉辈者,乃能不为献吉辈者乎”,则是对其“修辞”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仍感不满。徐中行《重刻李沧溟先生集序》发挥了李攀龙的这一说法,谓:
李献吉辈幸际其盛,亡虑十数家,轶挽近而力修古词。然其旁引经术,尚称说宋人,若功令亦有力救其偏者,而于修词靡遑焉。习流日波,余不敢知。乃有不与献吉辈者,知其异于宋人者寡矣。……(李攀龙)乃辄以古人自许。比讲业阙下,王元美与余辈推之坛坫之上,听其执言惟谨,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宝以下不齿,同盟视若金匮罔渝。
不满于李梦阳等人“旁引经术,尚称说宋人”,认为他们“于修词靡遑焉”,于是进一步强化了“文必西汉以上、诗必天宝之前”的复古理念。且其复古的诉求主要不在社会政治、复兴古盛世之政教风俗,而是在诗文体貌上复古。徐中行坦率地说他和王世贞等人把李攀龙“推之坛坫之上,听其执言惟谨”,毫不讳言以诗文猎取当世声名的意图。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
钱谦益把诗文风气与“国运”联系起来,本不应忽视弘治间李、何等人在社会理想和政教风俗方面的复古诉求。但他先入为主,在主观上早已认定李、何与王、李并无差别,都是摹拟古人陈言而已,于是大力批评前后七子在诗文创作上模拟剽窃,缺乏个人性情。他对李、何的此种批评也多为《四库全书总目》所继承,从而产生了更大影响。其《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云:
弘、正之间,有李献吉者,倡为汉文杜诗,以叫号于世,举世皆靡然而从之矣。然其所谓汉文者,献吉之所谓汉而非迁、固之汉也;其所谓杜诗者,献吉之所谓杜,而非少陵之杜也。彼不知夫汉有所以为汉,唐有所以为唐,而规规焉就汉、唐而求之,以为迁、固、少陵尽在于是,虽欲不与之背驰,岂可得哉!献吉之才,固足以颠顿驰骋,惟其不深惟古人著作之指归,而徒欲高其门墙,以压服一世,矫俗学之弊,而不自知其流入于缪,斯所谓同浴而讥裸裎者也。嘉靖之季,王、李间作,决献吉之末流而飏其波,其势益昌,其缪滋甚。……其规摹《左》《史》,不出字句,而字句之讹缪者,累累盈帙。
文中尖锐批评李梦阳、王世贞等人从形式、体貌甚至字面上学习汉文、杜诗,认为他们完全没有继承汉文、杜诗的内在精神。
这样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呢?结合李梦阳的诗歌创作及《与徐氏论文书》强调诗“宣志而道和”“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等主张来看,钱氏的批评是片面的。李梦阳诗歌学杜甫,的确有形貌逼肖之处,且在与何景明的论争中过于强调“严守尺寸”,故在中晚明时期被一些人讥为“效颦”,但似乎没有人对其诗文所表现出的精神面目和他的语言能力提出怀疑。极力反对复古、对钱谦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汤显祖也曾说:“李献吉、何仲默二公,轩然世所谓传者也。大致李气刚而色不能无晦,何色明而气不能无柔。神明之际,未有能兼者。要其于文也,瑰如曲如,亦可谓有其貌矣。世宜有传者焉。”而钱谦益则说:
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
又《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说:
试取空同之集,汰去其吞剥寻撦,吽牙龃齿者,而空同之面目,犹有存焉者乎?西涯之诗,有少陵,有随州,有香山,有眉山、道园,要其自为西涯者,宛然在也。
又《曾房仲诗序》说:
夫献吉之学杜,所以自误误人者,以其生吞活剥,本不知杜,而曰必如是乃为杜也。……献吉辈之言诗,木偶之衣冠也,土菑之文绣也。烂然满目,终为象物而已。
可见钱氏处处抨击李梦阳的诗文是生吞活剥的假古董,没有价值。
至于何景明,因其与李梦阳论争有“舍筏达岸”之说,故后来得到的推崇较多,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谓“信阳之舍筏,不免良箴”,堪称公允;《明史·文苑传》更进一步有所轩轾,认为“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影响到今天的许多研究者。而钱谦益则基本无视何景明的“舍筏”之说。他重点批驳何景明的“古诗之法亡于谢”及“古文之法亡于韩”之论,谓“今必欲希风枚马,方驾曹刘,割时代为鸿沟,画晋宋为鬼国,徒抱刻舟之愚,自违舍筏之论”,认为何氏不但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而且影响极大,后果严重,“弘正以后,讹谬之学,流为种智,后生面目偭背。不知向方,皆仲默谬论为之质的也”。这就基本把李、何针锋相对的意见等同看待了。他又论王廷相,谓:“子衡五七言古诗,才情可观,而摹拟失真,与其论诗颇相反,今体诗殊无解会,七言尤为笨浊,于以骖乘何、李,为之后劲,斯无愧矣。”
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固然并非“前七子”之全体,但自古至今人们论“前后七子”,大都是就代表人物而言的。甚至可以说,在世人眼中,“李何王李”四大家基本可以代表“前后七子”。把李梦阳说成“摹拟剽窃”、缺乏个性精神和个人面貌的“赝古”,与钱谦益的极端立场有关,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有意把“前后七子”或“李何王李”不加区分,等同看待。
晚明以来,人们对复古派“赝古”“摹拟剽窃”的批评更多指向后七子中的李攀龙。钱谦益对李攀龙批评的“火力”也同样最为猛烈。李攀龙小传中除了批评其“狂易成风,叫呶日甚”、高自标置和相互标榜外,对其诗歌创作的批评尤其尖刻,一是不满其由“拟议”而走向“影响剽贼”,“今也句摭字捃,行数墨寻,兴会索然,神明不属,被断菑以衣绣,刻凡铜为追蠡”,这些话可与对李梦阳的批评参看;二是不满其“唐无五言古诗”等说法,谓其“论古则判唐、选为鸿沟,言今则别中、盛为河汉,谬种流传,俗学沉锢”,这些话则可与对何景明的批评参看。这些批评虽然尖刻,就李攀龙的古乐府和《古诗后十九首》等仿作来说,还是比较公允的。但把同样的意思来批评李梦阳和何景明,尤其是作为全局性、结论性的主要判断,就有失公允。沈德潜、周准论李梦阳,谓其五古“过于雕刻,未极自然”,七言古近体“追逐少陵,实有面目太肖处”,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则谓“准之杜陵,几于具体,故当雄视一代,邈焉寡俦”,从而对钱谦益的论断提出质疑说:“钱受之诋其模拟剽贼,等于婴儿之学语,至谓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吾不知其何心也。”
在钱谦益的影响下,后来有不少评论认为李梦阳和何景明的诗文也都是字摹句拟的假古董,四库馆臣甚至也说李梦阳“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明人与其诗并重,未免怵于盛名”,又说:“李、何未出已前,东阳实以台阁耆宿主持文柄。其论诗,主于法度音调,而极论剽窃摹拟之非,当时奉以为宗。至李、何既出,始变其体。然赝古之病,适中其所诋诃,故后人多抑彼而伸此。”这里说的“后人”主要就是指钱谦益。四库馆臣在李东阳和“前七子”之间基本没有偏向,这固然与钱谦益不同;但把“前七子”和李东阳对立起来,认为后者为矫正前者而起,很快夺取前者之坛坫,这一说法则明显受到了钱氏影响;尤其是认为李、何的诗文恰好犯了李东阳所诋诃的“剽窃模拟”“赝古”之弊病,显然是接受了钱谦益的说法。
(二)“前后七子”皆相互标榜以取当世名
钱谦益批评李、何、王、李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说他们相互标榜以猎取声名。如说:“献吉……谓汉后无文,唐后无诗,以复古为己任。信阳何仲默起而应之。自时厥后,齐吴代兴,江楚特起,北地之坛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谓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历以迄成化,上下千载,无余子焉。”这是说李梦阳提出复古主张,何景明积极响应,此后建立坛坫,高自标置,相互标榜。王廷相小传谓:
子衡盛称何、李,以谓侵谟匹雅,欱骚俪选,遐追周汉,俯视六朝。近代词人,尊今卑古,大言不惭,未有甚于子衡者!嘉靖七子,此风弥煽,微吾长夜鞭弭中原,令有识者掩口失笑,实子衡导其前路也。
则又是把前后七子一体化看待,谓前者已然,后者更甚。此类论述还有不少,如张凤翔小传说:“献吉作传,以为子安再生,文考复出;关中人党护曲论,不惜人嗢噱,皆此类也。”张治道小传说:“关陇之士,附北地而排长沙,党同伐异,不惜公是,未有如孟独之力者也。”宗臣小传说:“升堂入室,比肩殆圣之才;叹陆轻华,接迹廊庑之下。聚聋导瞽,言之不惭;问影循声,承而滋缪。”等等。
实际情况是,李、何虽然都十分自信、自负,却并未明显以声名相互标榜;而王、李等“后七子”相互标榜的风气相对更盛。后者具有明确的结盟意识,在嘉靖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之间群体性的文学活动较为频繁,甚至与诗社之外的文坛和士林形成了较为紧张的关系。他们的结社本就带有较强的追求当世声名的意图,因此也容易产生意气倾轧,李攀龙和谢榛、吴国伦和宗臣,乃至吴国伦和李攀龙之间都有过或大或小的摩擦。后来人们认为李、何先“结盟”而后反目,其实是拿“后七子”的特点来解释“前七子”的行为。弘治时期李、何交往属于意气相投,二人以人品、诗歌获得了较高声誉,并称于士林、文苑,既无强烈的结盟意识,与后来人们所说的“四杰”“七子”中的其他人也并无结盟性质的文学活动。钱谦益说:“仲默初与献吉创复古学,成名之后,互相诋諆,两家坚垒,屹不相下。”此说同样经万斯同《明史》引用,影响到官修《明史》。后者谓:“两人为诗文,初相得甚欢,名成之后,互相诋諆。……各树坚垒不相下,两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李何论争确实导致了交游者的“左右袒”,但把二人的论争解释为“成名之后,相互诋諆”,则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二人当初相互结交,本有携手在文坛扬名的意图。就“并有国士风”的李、何而言,这恐怕是不确切的。李梦阳与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等人的交往主要是观念相近、意气相投,而并未像王世贞和李攀龙那样以携手“策名艺苑”为目标。到嘉靖前期,康海和王九思长期乡居,“弘德七子”之说处于酝酿之中,王廷相为李、何诗文集作序,才在回顾往昔时表现出对文坛声名的重视,同时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相互标榜的风气。
“四杰”“七子”等称号,其意义主要在于声名之标榜。如果是由其人自己提出,便是自我标榜、相互标榜。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作“五子诗”,便是如此。而弘治、正德时期“四杰”“七子”的称号大都是后来出现、别人赋予的,说李梦阳、何景明等人藉此相互标榜,便于事实不符。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三二《诸臣传逸》谈到何景明因刘健之议不能入翰林,谓“东阳代健为首揆,亦颇抗疏救拔景明,于是四杰七子继起树帜,互标榜”,又在何景明传后评论说:“仲默文章与献吉齐名。……尝时称景明与边贡、徐祯卿、李梦阳为四杰,然亦互相标榜云,率非寿世之作也。顾乃窒邪植谊,至性必白,事君告友,无少回佚,盖不以词泽为工者。”显然以为“四杰”“七子”都是李梦阳等人自持其说,故谓其“互相标榜”。这实在是冤枉了他们。但值得注意的是,查继佐并未把“前七子”全部视为“文章士”,而是将何景明、李梦阳(附王九思)列于“谏议诸臣”,将康海列于“讽谕诸臣”,王廷相列于“武略诸臣”,只把徐祯卿、边贡列于“文史诸臣”。在李梦阳传中,查继佐说他“居燕中,社集四方名士,兴复古文词,与信阳何景明互旗鼓,时人称李何。然两人各自成家。”在边贡传中称其“与李北地、何信阳皆以诗文为国士交。”这些说法都是比较客观的。查继佐评何景明所说的“不以词泽为工”,正是弘、正复古的共同特点。而该书谈及嘉隆七子,在徐中行传后论曰:“此风雅之归也。王、李始之,中原称七子。其诸附以见者,犹或鄙簿书为尘裹,颇尚晋麈。”所谓“颇尚晋麈”,是批评李攀龙等人以诗文复古为“避世桃源”,不务职守,仅靠诗文以猎取声华、追求不朽,这比较符合“后七子”为人处世的特征。“前七子”则大都积极入世、特重现实关怀。该书所录宗臣与李攀龙书云:“忆昔五子结盟,义掩白日。风波中起,羽翼相乖。谢榛以白发负心,梁生以青鬓长往……吴生亡赖,耳目纵横,意常驾仆。”所录王世贞谩骂谢榛之言:“老眇奴辱我五子,遇虬髯生,当更剜去左目。”可见其时相互结盟、标榜以取当世之名,成名后又彼此倾轧之丑态。而遍观弘治、正德时期所谓“四杰”“七子”之诗文,则找不到这样的材料。
四、把“不读唐以后书”归于李梦阳
清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复古派的代表性言论“不读唐以后书”是李梦阳提出的。如叶燮《原诗》说:“如明李梦阳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谓唐无古诗,又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自若辈之论出,天下从而和之,推为诗家正宗,家弦而户习。”又说:“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四库馆臣说:“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云:“不读唐以后书,固李北地欺人语。然近代人诗,似专读唐以后书矣。又或舍九经而征佛经,舍正史而搜稗史、小说;且但求新异,不顾理乖。”等等。
但“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并未见于李梦阳文集,也未见同时代人征引。在笔者所见文献中,谓李梦阳提出相似说法的记载最早见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于笔端搅扰,驱斥为难。”按照笔者的理解,“文”主要指范文,与“勿读唐以后书”意思不尽相同。而在其他地方,王世贞倒是以不读“唐以后书”盛赞李攀龙和俞允文,《答陆汝陈》说:“仆不恨足下称归文,恨足下不见李于鳞文耳。于鳞生平胸中无唐以后书,停蓄古始,无往不造,至于叙致宛转,穷极苦心。”又《俞仲蔚集序》称:“仲蔚又稍厌唐以后书,虽不能尽屏,搜猎一二计以共扫除之役,非素所仿慕也。”由此看来,“不读唐以后书”主要还是“后七子”一辈人的主张。马世奇《王凝明状》说:“凝明独矜贵,不轻下只字……盖子美所谓‘性僻耽佳句’,于鳞所谓‘勿读唐以后书’,于凝明见之。”也是把此语与李攀龙相联系。而梅守箕《凤皇山藏稿小序》说:
李北地欲振南宋之衰而主杜陵,何、徐以后诸公俱出入唐人,李于鳞乐府、古诗抑又进而之周秦汉魏间矣。……顾其为汉魏役者汰晋、六朝与唐,为唐役者汰宋,并其旨与音而废之,其为径捷而取材也狭,其因词也近而所志则浅,丰于规制而啬于风韵,得其筌蹄而失于神解,故拟议有之,而变化未也。……而奈何持唐以后书不足读之论耶?
把“唐以后书不足读”作为复古主义视野狭隘的代表性言论,但并未指明这是谁的话。
把“不读唐以后书”之说明确归于李梦阳名下,据笔者所见文献来看,也是在明末,且与“前后七子”并称这一现象有密切关系。艾南英《重刻罗文肃公集序》云:“弘治之世,邪说始兴,至劝天下士无读唐以后书,又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骄心盛气,不复考韩、欧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狭,中无实学,相率取马迁、班固之言,摘其句字,分门纂类,因仍附和。太仓、历下两生持北地之说而又过之,持之愈坚,流弊愈广。后生相习为腐剿,至于今而未已。”先把“不读唐以后书”称作弘治时期之“邪说”,后又说“太仓、历下两生持北地之说”,也是把“李何王李”等同看待,已基本把这一“邪说”归到李梦阳头上了。值得玩味的是,他所引“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恰是他所推崇的韩愈在《答李翊书》中的说法。吴应箕《陈百史古文序》说:“本朝李北地不读唐以后书,予狭之,及遍观国初诸集,然后知北地所为不读唐以后者,犹之韩、欧扫除六朝五代之意,故文不同,而其志在复古则一也。”这是与上举王世贞《艺苑卮言》相似的肯定意见,但把王世贞的“唐以后文”改为了“唐以后书”。钱谦益《读宋玉叔文集题辞》说:“献吉之戒不读唐后书也,仲默之谓文法亡于韩愈也,于鳞之谓唐无五言古诗也,灭裂经术,偭背古学。”又《列朝诗集》李梦阳小传云:“献吉曰:‘不读唐以后书。’献吉之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缪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说也。”都把这种说法实实在在地归于李梦阳名下了。艾南英、吴应箕与钱谦益年齿相仿,都熟悉王世贞《艺苑卮言》关于“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的记载,至于一字之差的“偏离”,则是受到其他近似说法的“干扰”。
另一相近的说法见于顾璘所著《国宝新编》,谓李梦阳“朗畅玉立,傲睨当世。初,读书断自汉魏以上,闻人论古昔有不解事,即曰:‘岂六代以还书邪?盖不之读。’故其诗文卓尔不群。晚始泛览诸家,益济弘博,或失则粗抑。矫枉之偏,不得不然耳”。顾璘是李梦阳的友人,他的记载可信度较高,但只是说李梦阳在最初的读书阶段崇尚六朝之前,且尤其强调其后来读书的“泛览”和“弘博”。方弘静《千一录》说:“李献吉闻有不解事,辄曰:‘是六代以还书耶?盖不之读。’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显然是引述顾璘之言,但已经大为走样,有了“不读唐以后书”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所推崇的李东阳门人邵宝曾称赞胡缵宗说:“君天资高明,前知师古,而后不屑于今之人者。书自六籍之外,非两汉以上无读也。极其所见,有独抱遗经之志。”可见书“非两汉以上无读”或“读六代以上书”,很可能是在弘治正德时期复古风气下较为普遍的带有夸张色彩的言论,即使李梦阳有是说,无论是功是罪,都不能把“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归于他一个人的影响。
钱谦益对明代复古派持否定态度,因此当今学界多注重探讨他对“前后七子”的批评意见,以及这些批评背后的主观意图,而尚未充分关注他对明代文学史尤其是复古派书写所起到的重塑作用。在钱氏之后,很多人看到他的评论有失公允,却又于不自觉中受到他的巨大影响。虽然文学史关于“前七子”的层累书写还在继续,但就大的方面而言已经不再有多少变动。可以说,以“前后七子”并称为契机,文学史家对于“前七子”的塑造至钱谦益而基本完成了。即使是现当代学者也大都深受钱氏影响,如郭绍虞先生提出的著名论断:“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便是引钱谦益《赠别胡静夫序》对此种风气的严厉批评为证。其实,《列朝诗集小传》对明诗史的书写正是凸显了各种类型的门户标榜和宗派纷争。郭先生提出这一论断,也正是深受钱氏明诗史书写之影响。就所谓“弘正四杰”或“前七子”的主力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而言,在弘治、正德间既未攻击李东阳和台阁体,也不知有什么“茶陵派”,并无“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事实,恰恰是钱谦益的记述和评论建构起他们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特点。这远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说这些述评还是沿着王九思、李开先等人初步塑造“弘德七子”集团的话题“接着说”,那么,他以李梦阳、李攀龙为核心,批评“前后七子”皆模拟剽窃、相互标榜,则是以距他时代较近、他更熟悉的“后七子”的特征来描述和评论弘治正德时期的“前七子”。经过这样的加工处理,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在当时文坛上本不清晰的派系关系和派系特征被勾勒得轮廓鲜明,相应地,这段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埋没了。我们的研究应该拨开这些影响极大的文学史家所制造的“迷雾”,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这当然十分困难。要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出弘治正德间的文坛状貌和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