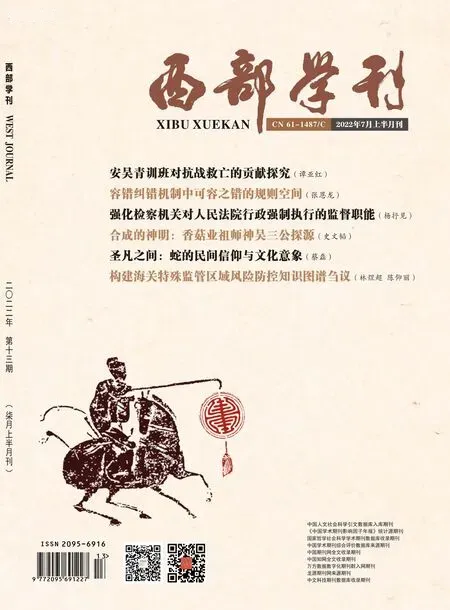圣凡之间:蛇的民间信仰与文化意象
蔡 磊
蛇是中国民间信仰中重要的动物崇拜对象,相对于龙文化意涵的类型性和影响的广泛性,蛇文化显示出更为复杂的意涵和区域性特质。上古时代,龙图腾和蛇图腾在某种意义上相互浑融,蛇的文化形象具有一定神圣性。至古代乃至近世,在宗教世俗化的大背景下,蛇图腾逐渐脱离龙文化,成为满足世俗社会生活需要,同时具有实用功能的民间信仰,蛇文化的意涵逐渐脱离龙形象的正义和正统,甚至走向邪恶和反叛,呈现出正邪交织、亦圣亦凡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典籍和传说中的蛇图腾
上古时期,我国形成了诸多氏族集团,东夷集团便是其中之一。东夷集团由太昊族、少昊族、皋陶族等氏族部落组成。太昊族也称伏羲氏,也有人称之为庖牺氏。太昊族的图腾中有凤鸟、太阳、火和虫蛇,根据《列子》中的记载,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和夏后氏皆是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汉画像中展现的伏羲形象也是人首蛇身[1]。传说中的伏羲是“蛇首人身,有圣德”,并擅长画八卦、结渔网、制乐器。伏羲有一个妹妹叫女娲,也是人头蛇身,他们为创造人类结为夫妇,成为人类始祖。
少昊族姓己,己字是蛇字的象形文字,说明蛇是其图腾中的一员,而这个己姓就是崇拜蛇的结果。皋陶是东夷集团的一个分支,他是淮夷的始祖,出生于山东曲阜,姓偃。皋陶氏主要活动在今安徽境内的江淮地区,这一带发现过许多带有“巳”字的陶器和青铜器。巢湖市北边的大城墩遗址出土过刻有“巳夷”的商代陶片,“巳夷”即是指崇拜蛇的夷人。
苗蛮集团在上古时代主要活动在今湖北、湖南和江西一带。《说文解字》中提及:“蛮,南蛮,蛇种。”从字形上看,古代南方地区的人与虫、蛇关系极为密切。欢兜是三苗中的一支,相传是以修蛇为图腾。《山海经·海内经》曾载:“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餐食之,伯天下。”[2]由此可以看出,苗族是崇蛇民族,他们崇拜的蛇神名叫延维,人头蛇身,如车辕般长,且有两个头,穿紫色衣,戴旃帽。延维还能辅佐国君,国君能得到他的神威相助,便可以称霸天下。如今重庆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敬蛇如神,不打蛇,不吃蛇,也不直呼蛇的名字,并尊称其为“金串子”“钱串子”等。在重庆秀山石提悬棺中曾发现两千多年前古代巴人遗存的蛇形文字和图腾,人们称之为“天书”。
福建闽族的图腾相传也为蛇。古代的闽族已发展成为今天的畲族和高山族,“畲”与“蛇”近音,由此可以看出畲族与蛇的渊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3]这里的“蛇种”就是“蛇族”,即信仰蛇神的氏族,“闽”字的“虫”通“蛇”解,意谓家里供奉蛇的氏族。
黎族也有关于蛇图腾的传说。相传在远古时期,海南岛荒无人烟,到处都是高山密林,密林之间的一座高峰里住着一条大蟒蛇。蟒蛇产下一个大卵,卵破后,一个女孩从里面跳出来,成为蛇女。蛇女长大后与一个采沉香的年轻小伙子结为夫妻,生下了一个男孩儿,没过多久她的丈夫去世了,蛇女便和儿子相依为命。儿子长大后,没有女子与其婚配,为了延续后代,蛇女决定让儿子往东边走,并嘱咐他若遇到女子便娶她为妻,她则打算西行。蛇女用“勾花”的办法在脸上刺上了花纹,以免被儿子认出。结果两人相遇时,儿子没有认出母亲,于是和母亲婚配,繁衍了后代,也就是后来的黎族人,因而蛇被认为是黎族人的祖先,黎族纹蛇纹的习俗也由此而来。
相传侗族也是蛇的后代。很久以前,有一对父女从山上挑柴回家,走到半山腰时,突然遇到一条大花蛇。父女俩见状,正打算逃走,不料大花蛇竟鼓起脖子大声说:“你们不要害怕,只要你家姑娘答应做我的妻子,我就让你们回去,若不答应,就把你们一口吞掉。”两人没有办法,只好同意。第二天,父女俩正在堂屋吃饭,忽然飞来了一只大蜜蜂,绕着两人唱道:“嗡嗡嗡!花蛇请我来做迎亲翁,姑娘嫁给花蛇郎,吃饱穿暖不愁穷。”姑娘会意点头唱道:“迎亲翁!迎亲翁!姑娘愿嫁花蛇郎,开山种地居山洞。”于是姑娘便随着大蜂去山洞与花蛇成亲,成亲后他们开始繁衍后代,于是便有了侗族人。在今天的侗族一些地区,蛇来到家里,人们会认为是祖先回家了,要焚香烧纸祈祷;如果久旱不雨,土地干裂,人们会祈求“蛇神”显灵,兴云降雨,免除干旱。
我国台湾高山族排湾人相传也是蛇图腾部落,他们视百步蛇为其祖先。在排湾族人中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远古时代,太阳来到世间,产下两颗红白色的蛋,并指定百步蛇来保护他们。这两颗蛋孵出了一男一女两个神,他们的后代就是排湾人的祖先。排湾人用百步蛇的图纹来装饰房子、器皿和衣物,以龙蛇纹身来象征威猛与力量。如果蛇来到了排湾人家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好预兆,蛇入家门是老祖宗驾临,会举行恭敬的迎送仪式来表达他们对蛇的尊敬。
二、民间信仰中的蛇崇拜
远古的蛇图腾经历世俗化的变迁,逐渐转化为民间信仰中的重要崇拜对象,许多地方建造有蛇的神像和庙宇,并举办祭祀活动,同时伴有多种禁忌和习俗。
(一)作为司雨之神
民间称蛇为小龙,龙为行雨之神,因而人们认为蛇也具有像龙一样的行雨能力。宋代文献《燕翼诒谋录》中记载:“八月中,有青蛇长数丈,出郡治,十六日风雨,林木、城门、营垒尽坏,压死千人,夜三鼓方止。”[4]在此则故事中,蛇能兴风作雨,具有神力。一些地方志和文人笔记中也记载有祭祀蛇神以求雨的习俗。如《南中纪闻》里记载了明代绥宁苗族通过供奉蛇神来祈雨的习俗。每遇天旱,巫师会入深山寻蛇,将其请回供奉,求得雨后,会给蛇戴上银项圈,然后敲锣打鼓将其送回山中[5]。
(二)作为水神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流行祭祀水神“蛇王施相公”,许多地方建有施相公庙,祭祀施相公成为江南地区的岁时风俗,时间一般从腊月廿五到除夕为止,祭品为用面粉制作的大馒头,还在上面捏一条蛇,称“施相公馒头”。清代中期以后,人们对龙崇拜由加便改捏蛇为龙,称“盘龙馒头”。据《华亭县志》记载:“市中卖巨馒为过年祀神之品,以面粉博为龙形,蜿蜒于上,循加瓶胜,方戟明珠宝绽之状,皆取美名,以谶吉利,俗呼盘龙馒头。”[6]之后,人们为了方便就做小馒头,在上面捏出小褶子,以象征蛇的身子,纪念神蛇。
(三)作为地方保护神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的樟湖镇每年农历七月七日为“蛇王节”。当地人称蛇王为连公菩萨,希望其保佑风调雨顺,船只无难,人员平安。当地蛇王庙临江而建,气势恢宏,古色古香,最有特点的地方就在于檐角处的仰头雕成蛇头的模样,形态逼真。
每年的农历六月份,当地的人们开始出乡捕蛇,然后将其放在蛇王庙的一个大瓮里,由专人饲养。据说谁捕获得多,谁就对蛇王菩萨最有诚意,受到的福佑也就最多。到了农历七月七日这天,人们来到蛇王庙对蛇王进行祭拜,仪式结束后由当地的捕蛇能手向村民分发蛇。之后人们抬着蛇王的神像,肩扛旌旗,鸣锣开道,进行游行。
此外,樟湖人每年都要举行“赛蛇神”和“游蛇灯”活动。游蛇灯是在每年正月初六至廿一元宵前后举行,按姓氏轮流,每姓负责一晚,每户带着自家所备的木制灯板参加游蛇灯。蛇首模型一般由集体统一制作,外糊绿纸做蛇头,双眼圆睁,造型夸张。蛇身由各家用竹木做的一块块灯板组成,每块灯板装有三盏内部插着蜡烛的灯,灯上裱糊白纸,还写着许多寓意吉祥的话语。蛇灯队伍蜿蜒前行,人们在家门口燃放鞭炮以迎接蛇灯的到来,场面非常热闹,这一祭蛇民俗一直延续到现在。2005年,樟湖崇蛇作为闽越文化的传统习俗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作为“四仙”之一的蛇仙
在我国北方地区流传着四仙的故事,四仙是民间信仰中四种动物神的合称,分别是红大仙儿狐狸、黄大仙儿黄鼠狼、白大仙儿刺猬和青大仙儿蛇。其中蛇因为其形貌像柳枝也被称为“柳仙”,在一些地方蛇被称为守家仙或是看家蛇,不仅不会被捕杀,还会被供奉。北京一带的“四仙”被称为“四大门”,在北京妙峰山与丫髻山的神灵体系里,四大门是重要的配祀神。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妙峰山“瓜打石玉仙台尊义堂茶棚”的正殿奉碧霞元君,山门内正奉灵官,配祀神中则有江蟒爷,江蟒爷是柳门,也就是蛇仙。民国时期北京德胜门外西侧有一座“大仙爷庙”,供奉的是蛇仙,传说当时香火很旺,很多人远道而来给蛇仙烧香。在此类民间信仰中,蛇更多地以家神或者地仙身份而存在,它们以自身的法力帮助人们消灾免难和发财致富,同时借此修炼功德,以提升在神灵体系中的地位和灵力。
(五)民间传说中的蛇精
秦汉以来盛行物老成精的观念,人们认为一些动植物吸天地之灵气,年深日久可以修炼成精。在民间传说中有许多关于蛇修炼成精,幻化成人的故事。这些蛇精多为女性,且相貌美丽,她们有的邪恶狠毒,专以美色迷惑男性,然后吸取其精气,以提高法力;有的善良忠贞,与人相恋,演绎出动人的爱情故事。
关于蛇精幻化成女子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唐谷神子《博物志》中的《李黄》《李琯》,其后还有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这三个故事讲的都是一男子被白蛇所变的美貌女子所迷惑,与之相处后死于非命。如《李黄》中故事主人公李黄和一个白蛇变成的寡妇同居了几日,回到家后便感到头晕目眩,随后卧床不起,家人揭开被子一看,发现他的身子都化成了水,只剩下头。《李琯》讲的是富家公子李琯被一白蛇妖女所迷惑,与她同住一晚后,第二天脑袋就裂开死掉了[7]。《西湖三塔记》说的是男主人公奚宣赞被白衣妇人缠住,再三想要掏取其心肝食用,最后由于道士相助才免遭毒手[8]。至明清后,蛇精形象开始更多地展现人性的色彩,最典型的是白蛇传说中塑造的白素贞形象,她善良勇敢,对待爱情坚贞不屈,为了捍卫自己的而幸福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
三、蛇的文化意象
远古形成的蛇图腾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蛇信仰赋予蛇以特别的文化内涵,蛇不仅是自然界的一种动物,也成为民间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重要动物类文化意象。这些意象的生成不完全是文化想象和建构,而是生发于人们对蛇本身习性的认识。
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冬眠的蛇开始慢慢苏醒,蜕掉旧皮换上新皮,古人据此认为蛇具有再生能力,是长寿永生之物。又因蛇的交配能力很强,人们往往用蛇来象征男女结合、子孙绵延。在江苏宜兴,每年农历九月初九被认为是蛇的生日,家家户户都会用米粉做“米粉蛇”。米粉蜿蜒曲折就像蛇身盘绕一样,米粉周围还要放很多表示蛇蛋的米粉团,寓意多子多福。民间剪纸艺术中还经常见到“蛇盘兔”的图案,或蛇首兔头相对,或蛇躯环绕兔身。这里“蛇盘兔”剪纸是雌雄交配、生殖繁衍的标志,表达了希望子孙绵延的愿望。关于蛇盘兔还有一个传说:在原始社会,相传以蛇为图腾的部落与以兔为图腾的部落产生了矛盾相互厮打,幸亏两位明智的酋长怜惜生灵,通过谈判和解,并为一个部落,从此兴旺发达,传为佳话,从而“蛇盘兔”也就象征夫妻和谐,生活美满。
蛇的吉祥寓意不止于此,民间还认为蛇象征财富。传说蛇有一个秘密的地下王国,里面有无数宝藏,想要发财致富的人都会到蛇庙里去祈祷。在民间还有“蛇盘兔,一定富”的俗语,类似的谚语还有“喜蛛石榴蛇盘兔,荣华富贵必定富”“蛇盘兔,家家富”。人们认为蛇机智灵活,善于招财,兔子柔顺温和善于守财,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说法。蛇盘兔不仅是一句流传广泛的谚语,也是一种小吃。在清明时节,山西、陕西以及甘肃一带的人们为了纪念忠诚孝义的介子推,就用面粉捏成“蛇”盘“兔子”的形状,“蛇”代表介子推的母亲,“兔子”代表介子推自己,“蛇”和“兔”缠绕在一起,用来表达孝道之心。蛇的动作犹如行云流水,迅捷而有力,这一美学特征常常被用来形容书法的流畅、活泼、雄健等。如“笔走龙蛇”,也常作“笔底龙蛇”,意指笔下的字犹如龙蛇舞动,形容书法雄健活泼、气势如虹。
蛇的文化意象具有多义性,不仅包含祥瑞与正义,也在很多层面代表危险、恶毒和狡诈,这与人类被蛇咬伤的经历有关。所以俗语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蛇为人类带来的恐惧,就连看到长相和蛇差不多的提井水用的绳子,也会感到害怕。成语“杯弓蛇影”,也体现了蛇意象中的恐惧和危险。此外,人类还将动物的天性人格化,蛇因毒液伤人而被赋予冷酷无情、心肠狠毒的个性,所以“蛇蝎心肠”“佛口蛇心”等成语被用来比喻心肠狠毒、口蜜腹剑之人。“嘴里念弥陀,心赛毒蛇窝”“毒蛇口中吐莲花”“八哥嘴巴毒蛇心”等谚语也体现了人类赋予蛇的恶毒个性。蛇因无足而行,行走悄无声息,因为被赋予变幻莫测、出没无常的阴险人格特质,与光明正大的正人君子形象形成对比,因而常用来比喻小人。如“龙屈蛇伸”,其中“龙”代指君子,“蛇”代指小人,比喻君子受屈而小人得志。
不过蛇的毒性也可为人所用。民间将蛇与蜈蚣、蝎子、壁虎、蟾蜍合称为“五毒”,苏州一带有端午前后给小孩穿五毒衣的习俗。端午乃五月初五,也是“恶月恶日”,此时天气湿热人容易生病,各种毒蛇毒虫也非常活跃,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被咬伤。为驱赶瘟疫,辟邪消灾,人们让孩子们穿上绣有这五种动物图案的衣服,取其以毒攻毒之意。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盛行一种叫“巫蛊”的神秘巫术,以蛇等毒物为原料,由巫师注入法力,毒物就有了灵气可以吃掉人的精魂。民间有许多相应的“送蛊”“躲蛊”“治蛊”“防蛊”的习俗。
相比于龙形象的正统、神圣和稳定,蛇的文化意象经历了由圣入凡的变迁,在由图腾转为民间信仰的过程中和世俗生活联系愈来愈紧,既保留了圣、神和仙的品质,又杂糅了妖、精的特点,呈现出正邪交织、圣凡结合的多元文化意象。
伴随现代化变迁,多数地方关于蛇的民间信仰已日渐衰落,但关于蛇的故事、传说、俗语依然在流传,蛇意象依然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蛇文化更多地与生肖文化相关联,具有现代吉庆文化内涵,一些地方的蛇习俗也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地方历史和文化的活态载体,宇宙久远的历史中人和自然、人和动物相处的智慧也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