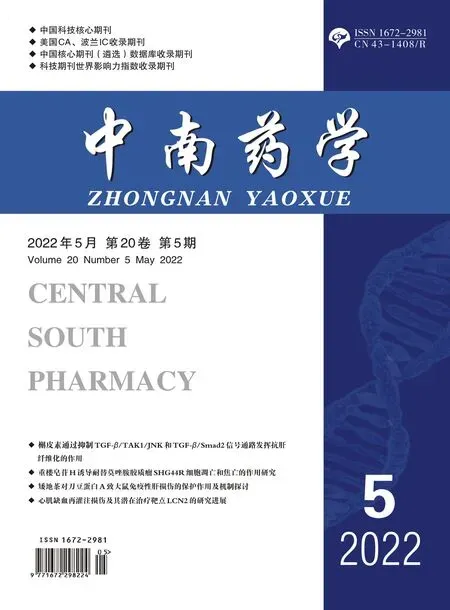峻下逐水药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
秦贝贝,贾泽菲,王佳莉,马琳,胡静(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1617)
肠道微生物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微生态系统,包含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肠道菌群,它们主要由细菌组成,其中专性厌氧菌占70%~90%。人类肠道中已经发现超过50 个细菌门,大多属于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肠道菌群与宿主之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正常情况下,机体与肠道菌群之间是处于动态平衡的,这种平衡对宿主的健康、消化吸收、代谢及免疫功能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环境、毒素、药物等因素破坏了肠道微生态结构,会造成肠道菌群失调,进而影响人体健康。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与肿瘤、代谢及免疫性疾病等都有密切关系[1-2]。
近年来,肠道菌群在中药药效和毒性方面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3-4]。肠道菌群位于胃肠,中医认为胃肠是六腑通降的枢纽,腑以通为用,胃肠以降为顺,胃肠通降则脏安,胃肠不通则脏病,因此,“通降法”是脏腑疾病的重要治则。研究表明,泻下药由于具有泻下通便、荡涤肠胃的作用,能够通过调节肠蠕动,促进消化等功能,调理肠道微生态平衡[5-6]。峻下逐水药泻下作用猛烈,归脾、胃、大肠经,苦能泄降,有毒而力强,善通利二便、排除肠胃积滞而泻水逐饮,并能攻毒、消肿、散结,用以治疗邪在肠胃,实热内结,大便不通或寒积、水结、停痰留饮等[7-8]。峻下逐水药药用历史悠久,具有重要的临床药用价值和较大的开发前景,虽然对其化学成分、药效、毒性作用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揭示其与肠道菌群相关性的研究相对较少[9-13]。本文结合近年文献从毒性、炮制减毒、药效、配伍禁忌等方面对峻下逐水药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该类药物临床安全合理使用和开展多方向研究提供思路。
1 肠道菌群与峻下逐水药毒性的相关性
1.1 与甘遂毒性的相关性
甘遂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为大戟科植物甘遂Euphorbia kansui的干燥块根,其性寒、味苦,具有泻水逐饮、消肿散结的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水肿、腹水、哮喘等。《本草纲目》将甘遂归入毒草类,其对胃肠道黏膜有刺激作用,能引起炎症、充血、腹泻、腹痛等。药理研究显示,甘遂能引起肝肾组织病理损伤和生化指标的改变[14]。Jiang 等[15]研究表明甘遂的毒性与大鼠肠道微生物Alpha 多样化的升高有关。在门水平上,甘遂组大鼠粪便以Firmicutes和Bacteroidetes为优势菌群,两者的相对丰度分别为56.37%和38.88%。进一步研究发现,甘遂给药后大鼠粪便乳酸菌属Lactobacillus相对丰度降低,蓝藻属Blautia相对丰度增加,且两者均为属水平上的高表达菌。此外,甘遂组瘤胃球菌Ruminococcus和异普雷沃菌Alloprevotella的相对丰度也降低。Lactobacillus可通过产生乳酸、过氧化氢、细菌素等抗菌物质保护肠道、抑制病原菌、增强肠屏障功能[16]。Blautia是肠道产酸菌,能将气体转化成乙酸,临床研究显示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体内的Blautia水平明显升高[17]。因此,甘遂可影响肠道菌群多样性,使益生菌的水平降低,有害菌的水平升高。
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是通过微生物-微生物和宿主-微生物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它们不仅是维持机体免疫稳态所必需的,而且影响宿主对许多免疫介导疾病的敏感性,是潜在的重要生理调节剂[18]。作为结肠细菌发酵的主要底物,复合碳水化合物的主要代谢终产物是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研究显示甘遂给药后,大鼠粪便中乙酸、丙酸、丁酸等SCFAs 的含量均显著降低[19]。SCFAs 不仅是肠道微生物本身的重要能量来源,也是肠道上皮细胞的重要能量来源,具有多种机体调节功能[20-21]。此外,甘遂给药后肝脏合成胆汁酸的能力下降,胆道发生部分阻塞,排泌的胆汁酸也相应减少[22]。
Tang 等[23]研究发现甘遂除了引起大鼠肠道菌群失调,还使大鼠尿液中牛磺酸、马尿酸、氧化三甲胺(trimethylamineN-oxide,TMAO)的含量显著升高。三甲胺(trimethylamine,TMA)是由肠道微生物从营养物质中合成而来,通过肝脏宿主酶进一步转化为TMAO。肠道微生物介导的磷脂酰胆碱、胆碱或左肉碱代谢最终均会产生TMAO。TMAO 水平的升高与慢性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密切相关,常被认为是肾功能损伤和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生物标志物[24-25]。马尿酸是尿液中常见的代谢物,其浓度和肠道微生物结构组成相关,被认为是有毒溶剂环境暴露的常用指标[26]。微生物代谢产物分析表明,氨基酸代谢是依赖于肠道微生物群功能代谢中最大的一类[20]。甘遂给药后能引起机体氨基酸代谢、三羧酸循环紊乱,使大鼠肾脏中异亮氨酸、亮氨酸、缬氨酸等支链氨基酸,苯丙氨酸等芳香族氨基酸,以及丙氨酸、赖氨酸的含量显著增加[27]。
1.2 与京大戟毒性的相关性
京大戟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为大戟科植物大戟Euphorbia pekinensisRupr.的干燥根,其性寒、味苦,具有泻水逐饮、消肿散结的功效,临床用于治疗水肿、腹水、痰饮积聚、咳喘、二便不利等。京大戟有毒,使用不当可引起肝脏和肠道毒性等[28-29]。
二萜类是京大戟的主要化学成分,可引起严重的肠道毒性,小鼠肠黏膜损伤和肠黏膜屏障功能减弱[30]。研究发现,京大戟二萜给药后,小鼠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发生显著变化,其中Bacteroidetes、Firmicutes、Actinobacteria、Patescibacteria为优势菌群,且Bacteroidetes、Actinobacteria的相对丰度均显著降低。此外,京大戟二萜组小鼠粪便中乙酸、丙酸、丁酸等SCFAs 的含量和结肠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显著降低,白介素-1β(IL-1β)、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炎症因子及内毒素血清磷酸脂多糖(LPS)水平显著升高。在肠道菌群与代谢物相关性分析中鉴定了京大戟二萜致结肠损伤的9 种关键细菌,其中Barnesiella、Candidatus Arthromitus、Alistipes、Enterorhabdus、Muribaculaceae、Alloprevotella对结肠起保护作用,它们与炎症因子成负相关,与紧密连接蛋白和SCFAs 成正相关,且相对丰度均显著降低;而Bilophila、Mucispirillum、Ruminiclostridium相对丰度均显著增加。此外,京大戟二萜引起的肠道微生物群紊乱还会进一步加重肠黏膜损伤[31]。京大戟肾毒性生物标志物主要包括次黄嘌呤、溶血磷脂酰胆碱、烟酰胺、苯丙氨酸、N,N-二甲基甘氨酸、C16-二氢鞘氨醇以及C18-植鞘糖苷[32];肝毒性生物标志物主要包括磷脂酰胆碱、溶血磷脂酰胆碱、脂肪酸、神经酰胺[33],有关这些内源性毒性代谢物与肠道菌的相关性还需进一步研究。
1.3 与千金子毒性的相关性
千金子为大戟科植物续随子Euphorbia lathyrisL.的干燥成熟种子,性温、味辛,具有泻下逐水、破血消癥的功效,为利水要药,临床用于二便不通、水肿、痰饮、积滞胀满、血瘀经闭、顽癣等。千金子有毒,使用不当可引起胃痛、腹泻等肠道系统和头痛、头晕、烦躁等神经系统毒性[34]。
研究表明,千金子造成肠道损伤的特征性差异菌属主要包括梭形杆菌属Lysinibacillus、嗜胆菌属Bilophila等[35]。千金子可使肠黏膜损伤,肠屏障功能标志物血清二胺氧化酶(diamine oxidase,DAO)、LPS 水平明显升高,使益生菌Lactobacillus、Bifidobacterium等水平显著降低[36-37]。Lactobacillus、Bifidobacterium在肠黏膜表面发挥抗炎作用,益生菌水平的增加可消除病原体,减少肠黏膜炎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38]。Lysinibacillus、Bilophila与氨基酸代谢、糖类分解[39]有关,可使结肠炎发病率增加[40]。因此,千金子的毒性作用表现为其通过影响肠道菌群多样性,改变正常肠道菌群的结构,使益生菌Lactobacillus、Bifidobacterium水平降低,致病菌Lysinibacillus、Bilophila水平升高,进而造成肠黏膜损伤、肠屏障功能减弱。
1.4 与芫花毒性的相关性
芫花为瑞香科植物芫花Daphne genkwaSieb.Et Zucc.的干燥花蕾,性辛、温,味苦,有毒,具有泻水逐饮的功效,临床用于水肿胀满、胸腹积水、二便不利等。药理研究表明,芫花可对大鼠造成明显的肝脏和肠道损伤,使血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胆酸、鼠胆酸、熊去氧胆酸水平均显著升高[41-42],改变肠顶端结构域、微绒毛和肠顶端连接发育所需基因的表达模式[43]。芫花平是芫花中的主要活性成分,同时也是毒性成分。研究表明,芫花平引起的肠道和肝脏毒性可造成肠道菌群紊乱和体内氨基酸代谢、脂类代谢、碳水化合物代谢的异常,同时使大鼠尿液中的14 种内源性生物标志物也发生了显著变化[44]。其中,苯乙酰甘氨酸是苯丙氨酸在肠道菌群作用下的代谢产物,3-甲基二氧吲哚是色氨酸代谢产物3-甲基吲哚在结肠细菌作用下产生的体内氧化产物。马尿酸是苯甲酸和甘氨酸在肠道内由微生物代谢合成,其变化反映了肠道微生物的代谢能力和组成,具有重要的毒理学意义[45]。芫花平给药后,大鼠尿液中苯乙酰甘氨酸水平的降低和马尿酸、3-甲基二氧吲哚水平的升高均与芫花平造成的肠道微生物群紊乱有关,这说明肠道菌群在芫花平对宿主的内源性代谢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峻下逐水类中药甘遂、京大戟、千金子等多有毒、作用猛烈,使用不当容易引起中毒。以上研究表明,这类药物的刺激性和毒性能够造成肠道菌群紊乱,影响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引起肠道菌群失衡,特征性差异菌属Lactobacillus、bifidobacterium、Barnesiella、Candidatus_Arthromitus、Alistipes、Enterorhabdus、Muribaculaceae、Alloprevotella等益生菌比例的降低及Blautia、Lysinibacillus、Bilophila、Mucispirillum、Ruminiclostridium等条件致病菌比例的增加等。肠道菌群的结构稳态是机体代谢功能稳态的基础,肠道菌群结构失调、微生态紊乱会诱发机体产生各种疾病。因此,峻下逐水药能够影响肠道菌群多样化,改变其结构数量,进而造成肠黏膜损伤、肠道屏障功能减弱、肝肾组织损伤等。此外,峻下逐水药使SCFAs 等代谢产物也发生了改变。代谢物是肠道微生物(有益的、致病的)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要驱动力,发挥着各种调节机体的功能。微生物代谢物既可以被宿主直接感知,也可以通过肠道转运被肠外细胞和组织感知,从而触发宿主的生理和病理变化[2]。甘遂、京大戟等引起了肠道微生物代谢物SCFAs 的改变、宿主氨基酸代谢紊乱以及TMAO、马尿酸、3-甲基二氧吲哚等内源性代谢产物含量升高等,这些代谢物的异常变化会进一步影响宿主与微生物之间的平衡关系,改变机体生理功能,从而产生毒性作用。
2 肠道菌群与峻下逐水药炮制减毒的相关性
峻下逐水药作用猛烈、有毒,易伤正气,使用时应注意中病即止、不宜久服,确保用药安全。传统中医药理论认为,炮制能降低该类药物的毒烈之性,缓和其刺激性和峻下作用。临床上,甘遂、京大戟、芫花需醋炙,千金子、巴豆需制霜后使用。
毒性研究表明,醋炙后的甘遂给药组小鼠的肠组织病理学、炎性损伤及黏膜渗透性等损伤指标均明显减轻[46-47]。与生品相比,醋炙甘遂给药组肠道微生物Alpha 多样化降低,潜在致病菌Blautia比例明显降低,益生菌Lactobacillus比例明显升高。醋甘遂大鼠粪便中乙酸、丙酸盐、丁酸盐、戊酸盐等SCFAs 水平也明显升高[15,48-49],SCFAs 能够通过降低趋化因子的产生或支持分子表达等降低肠道炎症。同时,醋甘遂给药组大鼠肝肾组织损伤较生品明显减轻,代谢产物马尿酸、TMAO、甜菜碱、氨基酸、赖氨酸、尸胺、牛磺酸、谷氨酰胺、肌酸、肌酐等的变化幅度也比生品缓和[50]。此外,千金子制霜后对大鼠中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大肠埃希菌、肠球菌等肠道菌群的作用减弱,引起的肠道菌群紊乱程度较生品降低,与千金子制霜后较生品泻下作用缓和一致[37]。
以上说明,甘遂、千金子经过炮制后缓和了生品对肠道微生物多样化的影响,使益生菌Lactobacillus、Bifidobacterium水平升高,潜在致病菌Blautia水平降低。同时,炮制缓解了生品对肠道微生物代谢物SCFAs、内源性代谢产物TMAO、马尿酸以及机体氨基酸代谢,蛋白质合成、糖酵解、三羧酸循环等的影响。甘遂、千金子炮制前后对肠道菌群结构、组成及代谢物影响的差异与传统炮制理论认为甘遂醋炙、千金子制霜能够缓解生品对机体的刺激性和毒性作用一致。目前,巴豆、芫花等炮制前后对肠道菌群及代谢产物影响差异的相关文献还很少,尚需进一步探索。
3 肠道菌群与峻下逐水药药效作用的相关性
甘遂、京大戟、芫花等对治疗重症胰腺炎、肝硬化、乳腺癌、肝癌、肠梗阻等重症恶性疾病有显著疗效[11,13]。肠道菌群与便秘、腹泻、肠易激综合征、肿瘤等多种疾病密切相关,被认为是治疗肝癌、结肠癌、直肠癌等的潜在作用靶点。
3.1 与泻水逐饮作用的相关性
甘遂被历代医家称为“泄水圣药”,是治疗水肿、腹水的良药。研究发现,醋甘遂能够明显改善癌性腹水(malignant ascites,MA)大鼠的腹水病理状态,促进排尿、排泄、水通道蛋白及其mRNA 的表达,抑制腹水生成,促进腹水排泄,且甘遂醋炙后发生腹泻、胃肠道损伤等不良反应的程度也明显降低。醋甘遂给药后,MA 大鼠的肠道损伤明显减轻,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结构也趋于正常,益生菌Lactobacillus等比例明显增加,潜在病原菌Blautia、Anaeroplasm、Lachnospiraceae等比例明显降低。同时,Lactobacillus的干预能增强醋甘遂的逐水作用和对肠道菌群的影响[51]。此外,醋甘遂的泻水逐饮作用还与苯丙氨酸、酪氨酸、色氨酸生物合成,苯丙氨酸代谢、色氨酸代谢、精氨酸代谢、甘油磷脂代谢等代谢通路相关。醋甘遂通过这些代谢通路和内源性代谢产物纠正MA 大鼠的肠道菌群紊乱和肠上皮细胞的通透性,增强肠道防御的能力,维持肠道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等。内源性代谢产物与肠道菌群相关性的研究表明,Lachnospiraceae与γ-亚油酸、9-羟基十八碳二烯酸、4-氧-视黄酸、磷脂酰乙醇胺水平成负相关;Alistipes与苯丙酮酸水平成负相关;Ruminiclostridium9 与γ-亚油酸、4-氧-视黄酸、磷脂酰乙醇胺水平成负相关;Ruminiclostridium与4-氧-视黄醇、磷脂酰乙醇胺水平成负相关[52]。
巨大戟烷型和假白榄烷型二萜是甘遂的主要有效成分,醋甘遂二萜可增加MA 大鼠的尿量、排便量,降低Na+、K+、Cl-的水平,从而显著减少腹水形成。甘遂二萜减轻肠黏膜损伤作用的关键肠道菌群为Prevotellaceae和Bacteroidetes[53]。肠道菌群Beta 多样性研究表明,二萜类成分通过增加有益菌Lactobacillus相对丰度,降低有害菌Lachnospiraceae和Anaeroplasma相对丰度,调节腹水大鼠肠道菌,发挥泻水逐饮作用[53]。甘遂大戟萜酯C(kansuiphorin C,KPC), 甘逐萜酯A(kansuinin A,KA)是甘遂中含量较高的二萜类成分,可使Lactobacillus相对丰度增加,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相对丰度降低,并通过调节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代谢等改善大鼠的腹水症状。当剂量为10 mg·kg-1时,KPC 对MA 大鼠腹水的抑制效果明显优于KA,且对肝、胃、肠的损伤更小。KPC 对Helicobacter 水平降低的效果是KA 的3.5 倍,说明其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更强。在体内微生物作用下,KPC、KA 通过氧化、水解、脱水和甲基化转化成小极性代谢物,其中KPC 在体内的转化率更高[54-55]。
3.2 抑菌作用
研究表明,商陆皂苷对产气荚膜梭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普通变形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56-57]。巴豆果壳和种子提取物均具有一定的抑菌活性[58]。此外,芫花对大肠埃希菌抑杀作用较强,而肛管性疾病的感染以大肠埃希菌为主,提示了其对大肠埃希菌的抑制和杀灭作用是治疗肛管性疾病(如痔瘘)的作用机制之一[59-60]。
由此可见,峻下逐水药不仅对生理性肠道菌群有影响,对病理性肠道菌群也有调节作用。当肠道菌群失调时,体内的微生态平衡被打破、机体免疫功能下降,正常菌的定植力下降,致病菌大量繁殖,导致“邪气”入侵和疾病发生。峻下逐水药能够直接作用于病理性肠道菌群,调节其多样性,使益生菌的比例增加、致病菌的比例降低,从而纠正紊乱的肠道菌群。峻下逐水药对机体正常菌群“扶正”和对致病菌“祛邪”的过程,体现了中医“扶正祛邪”“整体观”的理论基础[61]。此外,峻下逐水药还能调节宿主的代谢功能和内源性代谢产物的水平,改善机体生物学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4 肠道菌群与峻下逐水药配伍禁忌的相关性
我国历代医者在不断研究和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以 “十八反”为代表的中药配伍禁忌理论,药物配伍禁忌的实质是药物与机体的相互作用。
研究表明甘遂、甘草合用可造成肠道菌群失调,使条件致病菌Mycoplasma、Desulfovibrio、Enterorhabdus的水平显著增加、Prevotellaceae的水平显著降低,肠道菌群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发现Desulfovibrio、Mycoplasma、Enterorhabdus主要与Prevotellaceae竞争。甘遂、甘草合用还引起了肠道菌群宏基因组的变化,且该变化与Mycoplasma密切相关[62]。芫花、甘草合用可引起明显的肝肾损伤和生殖毒性,造成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生物合成及酪氨酸代谢、甘油磷脂代谢中断。其中,甘油磷脂代谢途径与肝损伤有关,苯丙氨酸、酪氨酸、色氨酸生物合成和酪氨酸代谢途径与肾损伤有关[63]。芫花、甘草合用导致Desulfovibrio水平显著增加,结肠硫化氢(H2S)代谢紊乱,并影响了肠道微生物宏基因组的1172 个基因。巴豆霜、甘草合用不仅削弱了巴豆霜的快速利尿作用,还使小鼠小肠组织的损伤加重,同时肠道菌群结构和数量均发生显著变化,有害菌属Streptococcus、Rikenellaceaeukn、Desulfovibrio、Streptococcaceaeukn水平显著升高,且差异肠道菌属的种类与给药剂量相关[64]。以上研究证实,甘遂、芫花、巴豆霜与甘草合用均会造成Desulfovibrio水平显著升高,Desulfovibrio参与H2S 生成,可引起肠道菌群失调,造成机体氨基酸、胆固醇代谢功能紊乱和代谢产物H2S 的异常变化[65]。
京大戟、甘草合用不仅抵消了甘草增加Lactobacillus比例的作用,而且使Akkermansia和Butyricimonas的比例显著降低,链球菌Streptococcus和Prevotellaceae的比例显著升高。此外,京大戟、甘草合用还能使大鼠粪便中丁酸等SCFAs 的含量显著减少,且甘草所占比例越大,SCFAs 含量下降越明显[66]。千金子、甘草合用导致肠道菌群宏基因组结构发生异常变化,其中98%显著调节的基因功能是两药合用后产生的。特征性差异菌属分析表明,千金子、甘草合用使Enterococcus、S24_7_ukn、Candidatus arthromitus等7 个肠道菌属的种类和含量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Enterococcus为肠道致病菌,S24_7_ukn、Candidatus Arthromitus与内毒素合成及肠道免疫相关,这些菌属含量的增加会导致肠道内毒素增加、肠黏膜损伤、肠道免疫功能被破坏。此外,两药合用后芳香氨基酸代谢、黏液降解功能紊乱,入血LPS、DAO 水平显著升高,肠源尿毒素硫酸吲哚、硫酸等毒性物质的含量显著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肠道损伤[35]。
由此可见,甘草与甘遂、京大戟、芫花、巴豆霜配伍不仅影响了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使益生菌Lactobacillus等减少,致病菌Enterococcus、S24_7_ukn、Candidatus Arthromitus、Desulfovibrio、Streptococcus,Rikenellaceaeukn、Desulfovibrio、Streptococcaceaeukn等增加,而且还改变了肠道微生物宏基因组。相反配伍的增毒作用还会引起氨基酸、胆固醇、H2S 等代谢功能紊乱,菌群代谢产物SCFAs 含量降低和内源毒性代谢产物含量增加等,而这些代谢的失衡与结肠炎症、肿瘤等多种疾病都密切相关。
5 展望
综上,肠道菌群在峻下逐水药的毒性、药效、炮制和配伍中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峻下逐水药对正常肠道菌群平衡的影响和对病理性肠道菌群紊乱的纠正体现了其对肿瘤等恶性疾病以毒攻毒、扶正祛邪的治疗作用。峻下逐水药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见图1)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峻下逐水药能够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多样性,肠道有益菌/条件致病菌的比例和细菌代谢产物等产生毒性或药效作用;另一方面,肠道微生态环境的改变会影响宿主相关代谢功能的稳态和代谢产物的水平,也能发挥药物本身及药物配伍之后的毒效作用。峻下逐水药-肠道菌群-特征差异菌属-细菌代谢产物-机体代谢为中药及其配伍作用的研究提供了新模式,其中特征性差异菌属、代谢产物的鉴别及其相关性的揭示是研究的关键。目前,峻下逐水药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的研究仍处于积累阶段,肠道微生物既可以作为调节靶点,也可以作为中药与机体相互作用的媒介,其结构平衡和代谢功能同时受到药物和肠道微生态的影响。中药-肠道菌群-代谢产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中药毒效、炮制和配伍机制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此外,剂量大小是有毒中药对机体产生疗效还是毒性的关键,不同剂量的峻下逐水药与肠道菌群关系的研究对于其临床药效的发挥及不良反应的降低也具有重要意义。

图1 峻下逐水药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Fig 1 Interactions between drastic purgatives and intestinal microf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