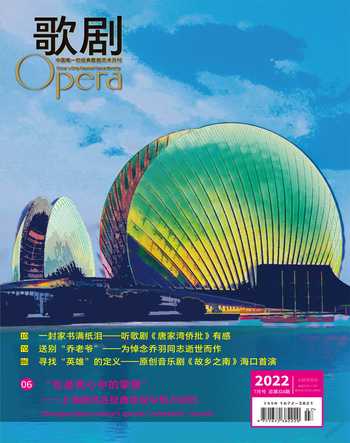难舍七十年友情
杜高

6月20日,是一个流泪的日子。早晨传来噩耗:乔羽逝世。我惊呆了,像是忽然受到了猛烈的打击。
一周前我还同他通过电话,约定秋凉后聚会。自从他的夫人去世后,他就在女儿的陪伴和精心呵护下生活。女儿为了使他高兴,每年至少要安排我们俩聚会一两次,畅快地喝两杯酒,无拘无束地回忆往事。这三年,疫情阻挡了我们的会面,我只能通过电话向他问候。他的女儿总是希望我们多聊聊,可是我发现他的话一次比一次少。我感到他老了,思维也大不如以前了。他每次对着话筒经常重复两句话:“我没病,我很好。”一周前的通话时,我问他还每天喝酒吗,他说“喝!”便放下了话筒。这次,女儿接过话筒低声对我说,他最近停杯了,怎么劝也不喝一口。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脑子里闪过杜甫离世前不久写的那句伤感的诗“潦倒新停浊酒杯”。这种预感不幸应验了。我止不住地流泪,我失去了最后一位维系了整整70年友谊的亲爱的朋友。
70年前的1952年,为了促进戏剧创作的繁荣,中央决定把几个主要艺术单位的创作骨干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剧本创作室,隶属文化部艺术局领导。乔羽和我都调了进来,我们走到了一起。这个创作室在第二年召开的二次文代会后就归属到中国戏剧家协会辖下。在当时,这个创作室可说是人才济济,老中青结合。主任是老剧作家陈白尘,成员中年龄最大的是田汉先生的夫人、前辈作家安娥,还有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诗人贺敬之,小说家和剧作家路翎,北京市民最早看到的一出解放区的秧歌剧《一场虚惊》的作者李建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表现工人生活的话剧《红旗歌》的作者刘沧浪和鲁煤等,一共20多人。乔羽和我是当时创作室里最年轻的两个人,我那年22岁,他也不满25岁。他写歌剧,我写话剧。
乔羽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我们相识后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待人热诚谦和,为人善良风趣。他读书多,很有学问,同他聊天既愉快又多有所获。
我们那时都沉醉在对艺术的追求里,我们交谈最多的是读书的心得,也交流创作经验。那时我们都是很单纯的青年人。高兴了就上小馆子喝一盅二锅头。乔羽很用功,成天埋头写作。他那时写了一部儿童歌剧《果园姐妹》,作曲家刘炽为他谱曲,广播电台播放了,反响不错。乔羽很受鼓舞,他请刘炽喝酒,把我也叫上了。
我举杯向他俩祝贺。刘炽是一位很优秀的作曲家,我记得他写的那首歌曲《新疆是个好地方》,旋律明快活泼,又富有新疆民歌的情趣,在当时是最受群众欢迎的歌曲之一。刘炽是最早发现乔羽歌词创作才华的作曲家。他说,读着乔羽写的歌词,就会唤起他的灵感,脑子里就会回荡起旋律。
乔羽那几年埋头写作歌剧,在《剧本》月刊上又发表了歌剧《杏林记》。当时他快27岁了,还是孤单一人,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创作室的副主任田兵,是个好心肠的老干部。他认识艺术局的一位叫佟琦的女青年,身材高挑,长得秀美,就当红娘给他俩牵线。果然,聪慧的佟琦一眼就看上了这个貌不驚人的才子,认定这是一个可以依托的好男人。不久他们就举行婚礼,乔羽要我帮他做招待员。
那晚,创作室的小院红灯照耀,喜气洋洋,桌子上摆着一盘盘喜糖、香烟和新鲜水果。记得那晚,田汉、欧阳予倩、曹禺,这些戏剧界的领导和前辈们都高高兴兴地来祝贺这一对新人。人们开始起哄了,要新郎坦白交代恋爱秘密。乔羽平时讲起笑话来口若悬河,妙语连珠,这回轮到要讲自己了,却变得狼狈不堪。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的那种既滑稽又无奈的表情,是怎样逗得人们捧腹大笑的。
转眼就到了第二年。
夏初的一天上午,乔羽神情紧张地闯进我的小屋,连声说:今天下午你得陪我。我急忙问他出了什么事,他结结巴巴说,佟琦要生孩子了,你得陪我到医院去。我答应了。
为了消除他的紧张情绪,我们先到了北海公园。
那时白塔旁有个小茶馆,客人少,我们两人就在那里喝茶聊天。我记得那天聊的是小说《红与黑》,乔羽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它的许多细节。我听得津津有味,也很受启发。我们吃完一笼包子后就下山直奔妇产医院。
佟琦躺在床上,旁边是襁褓包裹着的是一个小男孩。我们走进病房后,佟琦从被子里向乔羽伸出了手,乔羽冲上前握住了她的手。心情激动的乔羽,既惊喜、感激,还有点羞涩。现在回忆起来,那是一个多么甜蜜和温馨的时刻啊!我那时还是一个单身青年,更没有做父亲的体验,但我确实感到乔羽做了父亲后变得成熟了,他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的情感也升华到了一个新境界,他的诗情和现实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恰好刘炽又接受了两部电影的音乐创作任务。一部是严恭导演的儿童片《祖国的花朵》,另一部是沙蒙导演的战争片《上甘岭》。
刘炽向导演提出,主题歌一定要请乔羽写歌词。于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两首歌诞生了!它们激起了广大群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歌声响彻中华大地,从孩子们到城乡大众都广泛地传唱着。这两首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词坛升起了一颗闪亮的新星!
我们为乔羽庆幸,为他高兴。
乔羽是一个幸运者,他遇到了刘炽这样一位难得的艺术知音和亲密的合作者。乔羽又是一个清醒的艺术家,他深知打动人心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作者的真情实感,是浪漫优美的意境。他的歌词通俗朴实,但正是这些朴素无华的句子里蕴含着充满时代气息的深挚诗意。青年乔羽的文学修养和政治信念使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能自觉地把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我认为这是他超越同时代许多作家的了不起的成功。
1955年,那位爱护青年的田兵,竟然把上级分配给创作室的两张“五一”劳动节游行的观礼券,没有按资历送给老干部,而是给了乔羽和我两个年轻人。这在当年可是一种很高的奖励。“五一”劳动节一早,我和乔羽一同高高兴兴登上了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
也就是在这一年,文艺界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胡风集团”的政治运动,我们平静的创作生活被打碎了。创作室的成员路翎作为“胡风集团”
的骨干分子,被公安部逮捕。剧本创作室很快也就解散了。这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席卷全国,一个比一个更加猛烈地冲击着人们,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命运。乔羽和我从此天各一方,朋友们各自在不同的境遇中度过了动荡不安的20多年,直到“文革”终结。
年轻的人们今后只能从历史记载中了解这些运动给社会造成的伤害,再也无法体验我们所经受的磨难和精神痛苦了。田兵被贬到了偏远的贵州,我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刘炽受到了致命的沉重打击。
相比之下,在朋友们当中,乔羽算是平安的。他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谨慎地和人相处。在严酷的“批斗”中,他虽然无力解救他人之危,但他是非分明,严格恪守了道德底线,绝不为保护自己而伤害他人。
“四人帮”垮台后,乔羽随舞台剧《杨开慧》剧组到长沙演出,受到湖南文化部门的盛情接待。当时我在长沙街道工厂做工,乔羽请求接待干部帮忙找到我,希望能和我见面,但被接待的干部拒绝。
虽然我没能见到他,但他对落难老友的这份情谊,让我至今难忘。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掀开了历史新篇章,为中国的发展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党中央拨乱反正,纠正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案,1979年的春天,我重回戏剧工作岗位,和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相聚,乔羽和我紧紧拥抱了。
我脱离戏剧工作20多年,现在遇见的都是陌生的新人。没有想到,许多年轻人亲切地对我说,我们对你并不陌生,“乔老爷”经常向我们讲起你呢。我听了很受感动。恰巧那年田兵老人也从贵州来到了北京,乔羽夫妇是那般欣喜,他们始终感激这位红娘,惦念着他,有了他,才有乔羽的美满家庭。乔羽夫妇为田兵举办了一个丰盛的晚宴,请来了许多文艺界的新旧朋友。刘炽也来了,这是我劫后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最后一次。朋友们举起酒杯,个个含着眼泪畅快地痛饮。那晚的情景,我记忆犹新。我被人间真情深深感动了,也对乔羽夫妇的感恩情怀产生了敬意。不久后听到刘炽先生去世的消息,田兵先生也于2002年在贵州病逝。我感到悲伤。
挣脱了长期的思想禁锢以后,乔羽的创作焕发了青春。他的艺术才情闪耀出新的光彩,艺术生命盛开出美丽的花朵。他的新作接连不断地带给人们喜悦,唤起人们对新生活的热爱,激发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牡丹之歌》《夕阳红》《难忘今宵》,每一首歌都伴随着人们度过美好的时刻,那一句句优雅动情含义深刻的歌词,深深地打动着人们,把人们的精神世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人们喜爱的“乔老爷”真不愧是新时代最受人民尊敬的艺术家。
1987年的春晚,毛阿敏演唱乔羽的《思念》,轰动全国,好评如潮。一次我和乔羽聚会时,他问我对《思念》的看法。我想了想说,我想不出能有第二首歌,在短短的几行歌词里,塑造出一个有文学意味的形象,像一只蝴蝶唤起人们无尽的联想。他却说写歌词是很苦的,由不得你,还得看你是否碰得上一位好作曲家和一位好歌手。他说,人们喜欢《思念》,是谷建芬的曲子写得动听,毛阿敏又唱得好。我提议,为《思念》的完美的“三结合”干一杯。我们把酒斟满,一饮而盡!一杯之后,我沉吟片刻,补充说,更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改革开放带来宽松的创作环境,让艺术家们得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才华。乔羽默默地、深情地点着头表示赞同,我们再一次举起了酒杯。
如今,乔羽走了,人们隆重地悼念他。我读到许多篇年轻朋友哀悼他的文章,每一篇都使我深受感动。人们不仅高度地评价了他的歌词艺术成就,而且深刻地赞颂了他崇高的人格。我坚定地相信,人民艺术家是永远属于人民的。乔羽没有死去,他永远活在人民高唱着的他的歌声里,他在人民的心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