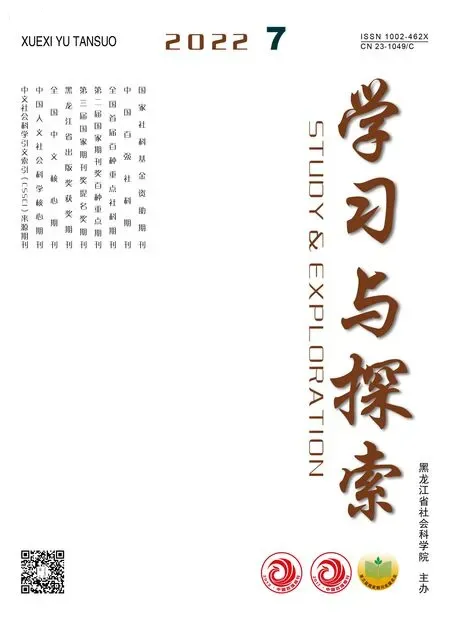如幻:德藏闵刻“西厢版画”之于文本关系再探
乔光辉,张岭南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南京 211189)
现藏于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闵齐伋(1580—1661)刊《西厢记》版画(下简称“西厢版画”),共有图像21幅。近年学界争论不断,笔者就其属于“彩绘”还是“套印”、插画还是独立画、闵刻“西厢版画”之独特性等三个关键问题予以再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彩绘”与“套印”辨
国内较早关注德国科隆藏“西厢版画”者是蒋星煜先生(1920—2015)。他在20世纪90年代即撰文述评。综观其观点,大致认为闵齐伋“西厢版画”是彩绘,“绝非出于同一人之手”,除了有署名的第一幅与第十五幅是闵齐伋手笔外,其他并非闵氏作品。他说:
那些彩色原作的画面是画,还是木刻?国内的学者专家也有不同看法。我认为第一第十五两幅是木刻,其他的则是画,因为明末时代,朱墨两色或朱墨蓝三色套印书籍已经是最考究的印刷了。那些五光十色的山水或仕女,木刻能在线条上符合要求,如此复杂的套色印刷当时没有条件,要么只有临摹。珂锣版、铜版等制版技术都是后来的事情[1]577-578。
蒋先生注意到科隆博物馆所撰写的长篇评介文字,也谈及该文之不足,如“他们在技法上用以对比的一部画册是《十竹斋笺谱》,其他作品几乎没有接触”,“过于局限在绘画的天地里”等。由于识见所限,蒋先生没有关注到明末以《十竹斋书画谱》等为代表的印刷技术的进步。
众所周知,《十竹斋书画谱》始刻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成于崇祯六年(1633);《十竹斋笺谱》初刊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德藏“西厢版画”第十五图署“庚辰秋日”即1640年秋天,则版画创作时间应在此时。与胡正言(1584—1674)所刊刻《十竹斋笺谱》时间大致相同。
学者蒋炜、李烨指出德藏“西厢版画”与《十竹斋笺谱》之间关系,称:“闵刻《西厢记》第三图中的一双蝴蝶与《十竹斋笺谱》第二卷《凤子》的第八图,闵刻本第十图的屏风和家具与《十竹斋笺谱》第二卷《闺则》第四图和《高标》第二图,造型十分相似,很难让人不产生二者之间关系的联想,尤其是在彩色套印本还很稀缺的那一时期。”[2]蒋、李判断极为准确。
需要补充的是,《十竹斋笺谱》第二卷共设有“龙种、胜览、入林、无华、凤子、折赠、墨友、雅玩、如兰”等九个门类,其中《凤子》一类即为蝴蝶。该门类下共有8幅蝴蝶画;另外,第四卷《杂稿》中也有一幅“梦蝶”图。它们或一只独立、或两只共舞、或三只嬉戏。也就是说,《十竹斋笺谱》特设专科,以9幅图展示了17只蝴蝶之形态[3]。正是《十竹斋笺谱》设“凤子”类专攻蝴蝶绘制,才有闵本“西厢版画”第三图之细腻呈现。
对于闵刻“西厢版画”中频繁出现的器皿、案桌、动物意象等,《十竹斋笺谱》对应题材绘画作品也极多,如笺谱所绘鸟、雁等禽类动物9幅、鱼类2幅、案桌类5幅、屏风类2幅、各类器皿类26幅,凡此,均为闵刻“西厢版画”提供了技术借鉴。其中,《十竹斋笺谱》第四卷中《寿徵》之“海屋”、《杂稿》之“沧海月明珠有润”两图,与闵刻“西厢版画”第十六图之间继承关系极为明显(如图1与图2所示)。可以看出,闵本第十六图“草桥惊梦”以蚌蜃构图,营造海市蜃楼之幻境,在《十竹斋笺谱》中已然存在。
参见胡正言辑《十竹斋笺谱》,第242、285页。
《何璧校本北西厢记》附闵齐伋绘刻《西厢记》
彩图,第224页。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江宁人吴发祥(1578—?)天启六年(1626)刊刻颜继祖辑《萝轩变古笺谱》,早于胡正言之《十竹斋书画谱》7年,蒋、李文称:“《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却难以回答的问题。由于有关吴发祥的史料极为稀少,吴发祥制作笺谱的情况便成为一团迷雾。”[2]但对比《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笺谱》的目录,可知两者在类目上继承痕迹明显。前者上册有“画诗、筠蓝、飞白、博物、折赠、琱玉、斗草、杂稿”八目,下册“选石、遗赠、仙灵、代步、搜奇、龙种、择栖、杂稿”八目,其中如“画诗、龙种”等类目直接为后者所继承,有些则略作变化,如“博物”变“博古”,“遗赠”变“折赠”,而为后者目类吸收;有些则并入新的分类。
关于“西厢版画”的刊刻地,王重民判断:“考三山一在福建,一在江宁,则又知是书(指《六幻西厢记》)刻于寓五客南京时也。”[4]所言甚是。即闵齐伋所刊刻《六幻西厢记》是于崇祯庚辰(1640)秋其客居南京时,闵刻“西厢版画”也在南京刊刻。由于同处南京,绘工、刻工等技术人员可互聘。以吴发祥刊刻《萝轩变古笺》(1626)、胡正言刊刻《十竹斋书画谱》(1619—1633)、《十竹斋笺谱》(1644)为代表,在南京聚集了一大批刻工与绘工,推动了饾版彩色套印技术的进步。闵刻“西厢版画”与之形成系列精品,共同见证了南京版画的繁荣[5]。
在金陵版画兴起之前,徽州墨商程大约(1541—1610)刊刻的《程氏墨苑》于1594—1605年间梓行[6]。该书也大规模采用套印技术,所绘蝴蝶2幅、禽鸟15幅、桌案1幅、各类器皿9幅、鱼类3幅;也为后来彩色套印技术之兴起提供了技术积累。其中卷三“舆图”之“龙门图”与闵本“西厢版画”之第九图也可比较(见图3)。在《萝轩变古笺谱》与《十竹斋笺谱》中,“鱼”均列入“龙种”门类,结合《程氏墨苑》后“龙门歌”云“有时鼓鬣奋天池,无限灵光辟水犀”[7],及《十竹斋笺谱》之“鳌鱼”图,都令人想起“鲤鱼跳龙门”之典故。因此“西厢版画”之第九图除去鱼雁传书典故外,尚有以鱼喻生,暗示张生高中榜首之义。
第193页。中图为《十竹斋笺谱》第二卷《龙种》之“鳌鱼”图,参见胡正言辑《十竹斋笺谱》,第84页。
右图为闵刻“西厢版画”第九图,参见《何璧校本北西厢记》附闵齐伋绘刻《西厢记》彩图,第211页。
至于以多色套印画作为小说戏曲插图,明末清初也不乏其例。以笔者曾校注之《西湖佳话》为例,该书以金陵王衙康熙十二年(1673)《精绘设色全图西湖佳话》为底本,其插图采用五色套印而成,极为精美。只不过闵刻“西厢版画”敢为天下先,率先将饾版套印技术由画谱引入戏曲插图。因此,蒋星煜先生“如此复杂的套色印刷当时没有条件”实属于误判。
其次是署名、流传问题。蒋星煜先生以为第一与第十五图有闵齐伋“寓五笔授”“庚辰秋日寓五”的署名,便断定这两幅是闵齐伋的手笔,而其他图作者则另有其人。熟悉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绘刻的人都知道,首幅插图署名后,后面连续的插图皆可视为第一幅署名者所作。如凌濛初评《西厢记》五卷的插图,首幅插图署名“新安黄一斌刻”,则后面插图虽未署名,但均为黄一斌所刻;另外,该插图仅在最后一幅署名“吴门王文衡写”且有“青城”印章一枚,则该插图从头至尾均为王文衡所绘。闵齐伋刊刻了“西厢版画”,虽不意味他就是绘工与刻工,然既署名“寓五笔授”,笔授即用笔记述口授的话。很明显,整套版画是按照闵齐伋的思想进行整体设计。换而言之,他是该版画的总设计师。
至于该版画的流传,德藏“西厢版画”系斯巴瑟(蒋文前后不一,又作维也纳·随巴塞)教授于1962年从柏林A.Breuer的珍贵藏品中收购。“再没有追索到1962年以前的流传、收藏的经过。”[1]579对此,有学者提出,A.Breuer是二战期间在中国行医的德籍眼科医生,于北京购得此版画[8]4。高级藏品的辗转流传的确鲜为人所知,但与该版画有密切关系的闵齐伋所刊《六幻西厢记》也许提供了某些线索。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影印致和堂刊《六幻西厢记》本,卷首留有齐林玉藏书印:“齐林玉世世子孙永宝用。”(图4)齐林玉(1614—1685)为颜元(1635—1704)、李塨(1659—1733)弟子,也是著名藏书家。
“子孙永宝用”常用于钟鼎铭文,而用于私人藏书印,则唯齐林玉一人。线索就在于齐氏独有之藏书印“齐林玉世世子孙永宝用”与闵刻“西厢版画”第六图青铜觯之“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如出一辙(见下页图5)。闵齐伋编撰《六幻西厢记》为齐林玉所收藏时,他应当于其中见过“西厢版画”。
据日人小林宏光提供的线索:“塩谷温在昭和二年(1926)北京图书馆中见过和科隆相同的附有插图的闵齐伋本……六十年前确为北京图书馆之藏书的闵齐伋本西厢记与其插图版画,竟在何处?”[9]我们无法确定德籍眼科医生A.Breuer二战期间在北京所购的版画就是塩谷温于1926年在北京图书馆所见版画。但“齐林玉世世子孙永宝用”之独特藏书印,将原本属于青铜器皿之铭文转用到藏书领域,极有可能受到闵刻“西厢版画”第六图的铭文影响。然考齐林玉后人齐如山之回忆录,并未言及此书及插画[10]。当年齐林玉所见《六幻西厢记》之版画插图流落何处?齐氏藏书之流传或可为闵刻“西厢版画”缺失的流传历程提供新的线索。
二、“插画”与“独立画”再辨
关于闵齐伋所刊刻《六幻西厢》与其所刊“西厢版画”之间关系,学界意见有二。一是闵刻西厢版画即《六幻西厢记》致插图,以周芜为代表。他说:“过去学者以为闵氏《六幻西厢》,其版画共用凌氏《西厢五本》,据此当属臆断。”[11]即该版画就是《六幻西厢》之插图。继有学者沿此深入,王宇认为:“科隆大学所藏的这套西厢记版画是脱离原本,以单页托裱的形式流传于世的,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末年闵齐伋出版的《会真六幻》,恰好缺失其序言中所列《幻因》部分的图……科隆所藏的西厢记版画,正是《会真六幻》第一部分《幻因》的图。”[12]小林宏光则认为“科隆版画被认为是装饰第三套四卷西厢记的版画”[9],即匹配的是《六幻西厢记》第三部分“剧幻”的插图。
二是闵西厢版画并非其刊刻《六幻西厢记》之插图。例如,张国标认为:“本册图文第十五图‘伤别’扇面上题款‘庚辰秋日’,天启年间没有庚辰干支,这是崇祯十三年,也就是说这本册页刊刻年代最早也只能是这个时候,显然与《六幻西厢》刻本是天启年间不合。”[13]范景中所坚持的“独立、并列”说提出:“德藏本图可能属于闵齐伋的《会真六幻》,但却根本不是配合王、关《西厢记》的附图。它应是《六幻》中的独立一种,与他书并列,或者说,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14]实际认为此版画不是插图,而是《六幻西厢》丛书中的“独立”一种。
解决上述不同意见可从德藏“西厢版画”第一图的图题入手(见下页图6)。该图右上角有篆书图题。对此图题的辨认,范景中、董捷诸位均将第二字释为“玄”[14][15],即图题为“如玄第一图”。但是,检索“玄”与“幻”二字篆书的字形演变,即可见两字的明显区别。篆书“幻”字与“玄”字区别在于上面是否有一横,下面两圆是否有交叉。闵刻版画中第二字上面没有一横,下面两圆有交叉,当为“幻”字,版画只是稍作艺术美化而已。而“玄”字篆书,上面应多一横,且未见两圆交叉写法。因此,笔者判断是“如幻第一图”而非“如玄第一图”(参见图6和下页图7)。
“如幻”而非“如玄”的重要发现,解决了德藏闵刻“西厢版画”与闵刻《六幻西厢》之关系问题。作为总设计师的闵齐伋,其版画设计也是遵循《六幻西厢记》之编撰原则的。众所周知,闵齐伋编撰《六幻西厢记》之宗旨,在于以佛释西厢,“董、王、关、李、陆,穷描极写,攧翻簸弄,洵幻矣”[16]1-2。而德藏“西厢版画”以“如幻第一图”为图题,其他诸图则依次为“如幻第二图、第三图……第二十图”,“如幻”即是此套版画之总纲。换而言之,“西厢版画”以“如幻”之设计理念,回应了《六幻西厢》之编撰宗旨,即“洵幻矣”。因此,无论西厢版画是否具有独立画之特点,它都是闵齐伋所编撰《六幻西厢记》之插图。
明乎“如幻”而非“如玄”,则诸家争论可迎刃而解。上文已经阐释了“如幻”之设计理念与《六幻西厢记》“洵幻”主题相呼应,此处再考察下德藏“西厢版画”与《六幻西厢记》文本内容之对应关系。
闵齐伋编撰《六幻西厢记》共包括“幻因”(元才子《会真记》、图、诗、赋、说、梦)、“搊幻”(董解元西厢记》)、“剧幻”(《王实父西厢记》)、“赓幻”(《关汉卿续西厢记》,附《围棋闯局》《笺疑》)、“更幻”(《李日华南西厢记》)、“幻住”(《陆天池南西厢记》,附《园林午梦》)六个部分。德藏“西厢版画”除去托名盛懋写的崔莺莺肖像外,其余20幅插图所绘内容与《六幻西厢记》之“剧幻”“赓幻”部分所载《西厢记》也一一对应。《六幻西厢记》“剧幻”“赓幻”之“出目”如下:佛殿奇逢、僧寮假馆、花阴倡和、清醮目成、白马解围、东阁邀宾、杯酒违盟、琴心挑引、锦字传情、妆台窥简、乘夜踰墙、倩红问病、月下佳期、堂前巧辩、长亭送别、草桥惊梦、泥金报捷、尺素缄愁、诡谋求配、衣锦还乡。德藏闵齐伋“西厢版画”与《六幻西厢记》“剧幻”“赓幻”之出目一一对应。
德藏闵刻“西厢版画”直接以“如幻第ⅹ图”命名,但这只是插图排序。考虑到德藏闵刻“西厢版画”第十九图(如图8)采用傀儡戏形式构图,而傀儡戏台柱上以马灯形式标出了演出内容是“诡谋求配”,这一标注直接取自《六幻西厢记》“赓幻”部分之出目标题“诡谋求配”。其余19幅虽然没有题名,但依照版画内容题名模式,一幅既已标注,则其他诸幅标注与之同,即19幅插画图题可直接视为19个出目标题。闵刻“西厢版画”与《六幻西厢记》之剧幻、赓幻部分文本回目一一对应,每本内容也均以四幅插画来表现。这与凌刻《西厢记》插图之对应模式相同。
德藏闵刻“西厢版画”不但与戏曲出目对应,既署“寓五笔授”,插图也自然打上了闵齐伋对文本理解的印痕。仅以第十五图“长亭送别”为例(隔页图9)。闵刊《六幻西厢》“赓幻”附《五剧笺疑》之“四之三”即“长亭送别”评云:
【二煞】、【收尾】二曲。……如饯行祖道,行者登程,居者旋返,古今通礼。所以此词“再有谁似小姐”之后,生即上马而去,徘徊目送,不忍归。“青山隔送行”言生转过上坡也。“疎林不做美”,言生出疎林之外也。“淡烟暮相遮蔽”,在烟霭中也。“夕阳古道无人语”,悲己独立也。“禾黍秋风听马嘶”,不见所欢,但闻马嘶也。“为甚么懒上车儿内”,言己宜归而不归也。“一鞭残照里”生已过前山,适因残照而见其扬鞭也。宾白、填词,的的无爽,而诸本俱作生、莺同在之词,岂复成文理耶?且俟曲终,莺红并下,而后生方上马,何其悖也!王实父断不如此不通。徐本于礼则合,于文则顺。耳食者竞吹其疵,独不于此原之乎[17]。
闵齐伋认为并非“俟曲终,莺红并下,而后生方上马”,在“长亭送别”剧终之前,崔、张早已分开,相望而不忍离;“西厢版画”第十五图(隔页图9左)的右侧可见崔老夫人与方丈已经远去,车夫在等莺、红;而图的左侧,琴童已挑行李远去,唯见张生骑马不忍去,崔、张隔水遥遥相望。此图中人物层次感强,正是闵齐伋解读之图像再现。他本如金台岳刻本、凌濛初评本(隔页图9右)等以崔张二人执手构图,可见闵齐伋对文本的理解决定了插图之创作。这正是第一图“寓五笔授”之寓意。
至于王宇视此版画“正是《会真六幻》第一部分《幻因》的图”,则没有对20幅“如幻”图与文本关系作深入探讨。闵刻《六幻西厢记》之“幻因”部分包括“元才子《会真记》、图、诗、赋、说、梦”,如德藏闵刻“西厢版画”直接对应“幻因”部分而不是整部《六幻西厢记》,则其第一幅标注就应为“幻因第一图”而不是“如幻第一图”。至于小林宏光认为是匹配《六幻西厢》第三部分插图,则是因所见版本差异所致。其所见《会真六幻西厢》第三部分相当于致和堂本《六幻西厢记》之“剧幻”“赓幻”部分。由于“赓幻、幻住”部分是李、陆对王、关《西厢记》的改编,二作分别为三十八出、三十六折,且与王、关西厢之部分出目相同,闵刻“西厢版画”与其虽未一一对应,视作其部分插图也未尝不可。
综上所述,考虑到插图的依附性与独立性,德藏闵刻“西厢版画”以“如幻”21图形式回应《六幻西厢记》“洵幻”的编撰思想,其可视作整套《六幻西厢记》之插图。但在具体内容上,闵刻“西厢版画”对应“剧幻”“赓幻”部分,直接镶嵌于其王、关《西厢记》五本二十折之文本出目中,属于“六幻”之主体即“剧幻”“赓幻”部分插图。
三、从“洵幻”到“如幻”:闵刻“西厢版画”之美术呈现
众所周知,文学插图从属于文学文本。德藏闵刻“西厢版画”不仅是王、关《西厢记》插图,其具体图解了杂剧《西厢记》的五本二十折内容,但又绝非剧本内容的简单美术再现。其区别于一般文学插图在于,闵齐伋带着强烈的主观意志改造了插图,使得闵刊“西厢版画”打上了“如幻”色彩。这也是其编撰《六幻西厢记》思想在图像中的延伸。
闵齐伋《六幻西厢》之编撰思想集中体现在卷首《会真六幻》序中。闵氏借助禅法,阐发其对《西厢记》的看法:
云何是一切世出世法,曰真曰幻。云何是一切非法非非法,曰即真即幻、非真非幻。元才子记得千真万真,可可会在幻境。董、王、关、李、陆,穷描极写,攧翻簸弄,洵幻矣!那知箇中倒有真在耶!曰微之记真得幻即不问,且道箇中落在甚地。
昔有老禅,笃爱斯剧,人问佳境安在?曰: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此老可谓善入戏场者矣。第犹是句中玄,尚隔玄中玄也。我则曰:及至相逢一句也无,举似“西来意”,有无差别?古德有言:“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不数德山歌,压倒云门曲”。会得此意,逢场作戏可也,褏手旁观可也。黄童白叟朝夕把玩,都无不可也。不然,莺莺老去矣,诗人安在哉?耽耽热眼,呆矣!与汝说“会真六幻”竟。
幻因:元才子《会真记》、图、诗、赋、说、梦;搊(chou)幻:《董解元西厢记》;“剧幻”:《王实父西厢记》;“赓幻”:《关汉卿续西厢记》,附《围棋闯局》《笺疑》;“更幻”:《李日华南西厢记》;“幻住”:《陆天池南西厢记》,附《园林午梦》[16]卷首。
闵齐伋谈编撰《六幻西厢》之原因。一是如何观世界?他借助《金刚经》“非法非非法”言说方式,提出真与幻本为一体。“非法非非法”是《金刚经》的常用言说方式,即一件事物既是非某又是非非某,诸如“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其意是概念与事实有联系但又不同,又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等。闵齐伋以此论证世间万物“即真即幻、非真非幻”,此为闵齐伋批评《西厢记》之逻辑起点。此美学思想用于西厢解读,闵认为元稹《会真记》(即《莺莺传》)有史实依据,属“千真万真”,但崔张相恋恰似一“幻”;至于后来董、王、关、李、陆诸作“洵幻矣”,其中“倒有真在”,“幻中有真”。如此,其世界观与作品分析便完美统一了。
二是关于“句中玄”与“玄中玄”之辩。闵齐伋认为“及至相逢一句也无”比“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更能体现《西厢记》之微妙。前者出自第一本第一折末尾【赚煞】唱词,诸家评点皆认为此句是“一部西厢关窍”[18]21,即崔张生情只于四目相对的瞬间,以致引发二人一见钟情,引发剧本诸多情节。但闵齐伋却认为“及至相逢一句也无”才是《西厢记》之关键,该句出自第五本第四折【沈醉东风】:“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将腹中愁恰待申诉,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只道个先生万福。”千言万语却无法用语言表达,极平淡而极深情。徐渭评此句云:“欲言不言,若疏若亲。的的真情,亦的的至情。”[18]382闵齐伋认为这就是“佛祖西来意”。换言之,前者强调一见钟情,其实为情所牵,属于闵氏所称"句中玄";后者则情极浓而极淡。纵有千种风情,待及相见,一归平淡。属于“玄中玄”。阅读西厢,不仅要看到崔张二人情感之生发,更应体悟崔张二人情感之“平淡”。能入能出,方为情感解脱之道。
三是视《西厢记》为文字禅,借西厢以禅悟。闵齐伋推崇佛果禅师,其序言中“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不数德山歌,压倒云门曲”句,即是说圆悟克勤佛果禅师(1063—1135)的巨大影响力。据耿延禧(?—1136)作《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序称:“佛以一音,而演说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至圆悟大禅师,此音益震。师因频呼小玉之音与檀郎认得之音,然后大唱此音。不数德山歌,压倒云门曲。……若知此音,则圆悟老师功不浪施。若不知此音,而以语言文字求会解者,是人行邪道,不能见老师云。”[19]耿延禧明显为圆悟开解。须知圆悟克勤是临济宗五祖法演法嗣,因推行文字禅而知名于禅林,其《碧岩录》被誉为(临济)“宗门第一书”,恰是“以语言文字求会解者”的禅师典范。以致其弟子大慧宗杲禅师(1089—1163)以有违慧能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宗旨,一度烧毁《碧岩录》之刻板。
闵齐伋推崇圆悟克勤之文字禅,便是主张借助文字以悟禅法。他认为阅读《西厢记》自当依据文本,但“即真即幻、非真非幻”,更应与文本保持距离。“会得此意”即不拘于文本,视文本为解脱之载体,即《心经》所言“色即是空,色空不二”。其对立面是“耽耽热眼”,如《易经》云:“虎视眈眈,其欲逐逐。”即贪婪注视,己心为剧情所牵,情不能自控。“会得此意,逢场作戏可也,褏手旁观可也。黄童白叟朝夕把玩,都无不可也。”如果将西厢故事视作文字禅或禅宗公案,则作戏、旁观、把玩,都无不可。借西厢以解脱烦恼,便是闵齐伋编撰《六幻西厢》之宗旨。
德藏闵刻“西厢版画”虽为配合王、关《西厢记》五本二十折之插画,但首图即注明是“寓五笔授”之“如幻第一图”,可见闵齐伋“借图悟幻”之用意极为明显,其插图之构思方式也呼应“西厢洵幻”之宗旨。为论述方便,笔者依插图之于文本呈现方式之或明或隐,将21幅插图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画面直接呈现文本情节,如第一、第七、第八、第十八、第二十图等。此类插图的构图,闵齐伋多以扇面、卷轴、画框等为外形设计,旨在使读者与文本之间保持审美距离,使读者由沉浸式阅读转为把玩式阅读。插图反映剧本内容,本属自然。如第十五图展现的是“长亭送别”内容,但与其他版本直接呈现剧情的“长亭送别”图不同的是,德藏“西厢版画”采用了扇面形式构图,将情节图以扇面形式展示。这正反映了闵齐伋设计此套插画之思想,他视《西厢记》文本为文字禅,“以语言文字求会解者”,借助于西厢故事以体悟解脱之道,“即真即幻、非真非幻”,避免使读者沉溺于文本故事中不能自拔。如果直接呈现剧情插图,则容易使读者、观众“入戏”,成为“耽耽热眼”的“呆汉”。扇面构图则有意识地拉开了读者与文学故事的距离,插图功能由沉浸式“带入”转为有距离的“把玩”。闵齐伋提醒读者,我们只是在观赏一幅扇面画而已(如下页图9左)。再如,第一图“佛殿奇逢”采用横轴画面构图,第十八图“泥金报捷”采用纵轴画面构图;至于首图“莺莺小像”、第八图“琴心挑引”、第十一图“乘夜逾墙”则采用条纹画框构图;凡此卷轴、画框之使用,均在令读者与画面保持距离,闵齐伋在提醒读者,我们是在读剧本、在看戏。尽管插图明显直接呈现剧情,但闵齐伋有意识采用扇面、卷轴、画框镶饰等构图,其意在引导读者超脱文本,避免沉入其中,与文本保持距离。
第二类是不直接画剧情内容,而是将剧情内容与某类器皿相结合,即画面整体呈现是器物,西厢剧情作为器物之装涂纹饰呈现,由把玩器物而体味剧情。如此,将剧情的把玩与器物古玩之欣赏完美融合。闵齐伋用来构思的器物有钵(第二图)、青铜觯(第六图)、屏风(第十、十三、第十七图)、灯具(第五、十四图)、玉佩(第十二图)等。
先看钵(第二图)、青铜觯(第六图)的图像展示(如图10)。从画面看,闵齐伋展示的是器物图,但在器物表面则分别绘以第一本之第二折“僧竂假馆”、第二本之第二折“东阁邀宾”内容。由于剧情画成为器物之装饰,那读者自然要问,我们是把玩器物还是欣赏剧情?这正是闵齐伋插图设计所要达到的效果。其视文本为文字禅,“以语言文字求会解者”,将《西厢记》作为开悟之工具,若紧随文本反成烦恼,成为“耽耽热眼”之“呆汉”。闵齐伋的高明之处是他意识到把玩器物也容易执着。其第六图“青铜觯”篆书“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文字并非雕刻在瓶口内壁或镶嵌于瓶口外侧,而是排列整齐,漂在瓶口中间。如是设计,其潜台词是诸如“眉寿万年、子孙永宝用”等铭文,不过是一个浮幻的心愿,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与无常哪一个先来到,遑论什么永垂不朽?此正典型体现了闵齐伋的“即真即幻”之设计意图。
次看屏风。第十七图“泥金报捷”(如下页图11)画面本身采用巨幅屏风构图,屏风之上所绘的莺莺后面亦有一架屏风,从而形成“屏中屏”的“重屏”模式。大屏风正面绘以剧情画,背面书写东坡之《赤壁赋》;屏中之“屏”,正面饰以山水画,背面可以辨认出是“百寿图”。如此,此图将百寿图、《赤壁赋》、剧情画三者并列,然剧情时间在中唐、东坡则生在北宋;作为文学插图,闵齐伋岂不知东坡在元稹后?如此颠倒,即真即幻,正是其编撰《六幻西厢记》之宗旨。第十三图“月下佳期”,巨大的屏风内,崔张二人正在亲热,但只绘床被不绘人;屏风之外,红娘在偷窥;红娘之后,又有欢郎在偷窥;那读者自然会想:谁在演戏?谁又在看戏?
巫鸿在分析第十图之后说:“画面的稳定构图所引起的是一种分离的目光,不再迫使观者参与到图画所表现的情节中。”[20]所言极是。正是采用屏风构图,使画面空间划分增多,闵齐伋得以从容将多个画面并置,剧情画也并非唯一内容,观者目光由剧情而分离,关注到更多信息,从而将读者引向闵序所言之“亦真亦幻”之心理体验。
再看灯具与玉佩。德藏“西厢版画”第五、第十四图采用灯笼构图。其中第五图“白马解围”采用了跑马灯形式(如图12)。跑马灯是传统灯笼之一种,灯内点烛,烛产生热力造成气流,令轮轴转动。轮轴上有剪纸,烛光将剪纸的影投射在屏上,图象便不断走动。本图灯面分别绘制了孙飞虎、杜确、惠明等武将骑马图画,转动时似在追逐一样,极富动感。与“白马解围”剧情的激烈场面相吻合。画面呈现了跑马灯完美构造,中间剪纸分为上中下三个空间:天上有飞鸟在飞,中有孙、白、惠三将在追逐,下有鱼蟹在水中嬉游。西厢故事已成为过去,由元稹《莺莺传》而改编的戏文故事,恍若走马灯一般穿梭不停。昔人已逝,后人还在不断评说。或许我们自己的人生,终究没机会成为跑马灯上的剪纸,是否一样真情演出?第十二图“倩红问病”以连环玉佩构图,两环似是两只眼睛,分别透视张生与莺莺所在空间,一时两地两场景于两环中并列;而两环相叠又组成一篆书幻( )字,两地“互动”“时空相叠”构成“即真即幻”之寓意。
第三类不直接呈现剧情故事,而是调动动物意象的隐喻象征来含蓄反映剧情,并传达出闵齐伋的看法。如第三图“花阴唱和”、第九图之“锦字传情”、第十六图的“草桥惊梦”等。第三图采用蝴蝶构图,画面绘两只翩跹起舞的蝴蝶,另有两片荷叶,上面分别写着崔张二人月下联诗:“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正是出自文本的两首诗歌表明了插图与文本的关系。月下联诗是崔张二人爱情之见证。但闵齐伋推崇的是“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即真即幻”,情至深而至淡。《庄子》载:“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21]庄周梦蝶,清醒之后与梦境孰真孰幻?闵齐伋以蝴蝶构图,引出庄子之问。也正面回应了其编撰《六幻西厢》之宗旨:“洵幻矣。”蝴蝶蹁跹,崔张之恋也不过是蝴蝶一梦。再如第九图“锦字传情”,图左以鱼、鸟构图,令人想起古之“鱼雁传书”典故,鱼雁、鸿鳞也被称为信使。前文已述及,鱼喻张生“独占鳌头”;青鸟为传说中的西王母之信使,此处喻红娘。图右则以横轴书卷形式书写张生写给崔莺莺的情诗,照应了本折“锦字传情”的剧情内容。整图全用隐喻,剧中人物并没有出现,极隐晦曲折地传达出西厢“如幻”之设计理念。
第十六图“草桥惊梦”(图2)写张生于草桥旅店,梦见崔莺莺追随自己,而为兵卒所追。诸如刊刻于崇祯十二年(1639)冬陈洪绶为《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所绘插图,均绘以张生在做梦;而1640年秋,闵刻插图则以“蚌蜃”为中心构图。陈研曾在检索“蚌”与“蜃”关系后,指出:“蜃最初的含义‘蚌’并没有消失……蛟属与蚌属的蜃其实是同名异物。”[8]117如前已述,闵本构思受《十竹斋笺谱》之“沧海月明珠有润”等图启发明显。陈洪绶绘张生做梦图与文本所述文字吻合;闵本则以海中大蜃吐气以致张生之梦,即张生做梦不过是蚌蜃之“梦中之梦”。如此,以“玄中玄”形式将“草桥惊梦”解构。它促使读者反思:我们究竟是谁的梦境?西厢岂不“如幻”?
综上所述,笔者由辨析“彩绘”“套印”入手,提出了晚明南京饾版套印技术成熟是该版画出现之语境,而晚明齐林玉之藏书印也为本书之流传提供了某些信息。经过辨认,该版画第一图图题应为“如幻第一图”而非“如玄第一图”,其内容直接对应王、关《西厢记》之五本二十折之出目,是插图而非独立画,其中涉透着闵齐伋对《西厢记》的独特理解。闵齐伋以文字禅解释《西厢记》,视文本为禅悟之载体,“如幻”之设计理念也呼应着《六幻西厢记》“洵幻”之编撰思想。正是在“如幻”的设计理念下,闵刻版画对《西厢记》文本进行了美术再现。插图体现文本而又超脱文本,使读者始终保持与文本的审美距离。因此,在众多的西厢插图中,闵刻“西厢版画”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插图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