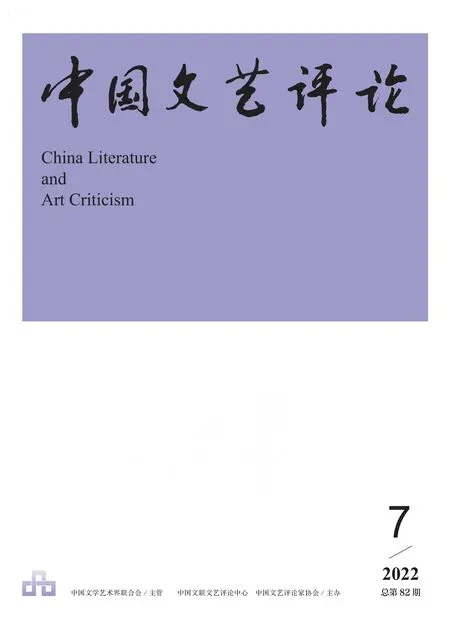论福柯读《宫娥》
■ 陆 扬
一、《宫娥》
福柯于196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词与物》,扉页上收入了17世纪西班牙著名画家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的著名油画《宫娥》(),并以之作为第一章的标题,就此展开不厌其详的迷宫式解读。福柯读《宫娥》的开场白是:

图1 [西班牙]委拉斯开兹 《宫娥》 油画 318cm×276cm 1656年
这个开场白就叫人迷糊。画家是委拉斯开兹本人自不待言,可是他明明看着前方,那是我们看画的人、也就是画作观者的位置,他如何在他面前的这块巨大画板上,表现顺着他捧着调色板的左手,一字儿排开的八个人物?又如何再加上后墙一块长方形镜子里国王和王后的隐隐约约的影像?是不是画家面前有一块巨大的镜子,委拉斯开兹在对着镜子画画?我们发现福柯甚至不能断定将这11个历史人物的神情惟妙惟肖固定下来的瞬间,是在这幅名作的收官阶段,还是画家尚在颇费猜测地构思画面阶段,甚至未及落下他的第一笔油彩时。惟其如此,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宫娥》这幅17世纪西班牙古典油画中的巅峰之作。
委拉斯开兹于1599年出生在西班牙萨维利亚(Sevilla),1660年在马德里谢世,是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IV)宫中的首席画家,也是西班牙文学艺术“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画家和巴洛克时期的领军人物。他尤以描绘宫廷人物与贵族生活称雄画界,其代表作便是这幅扑朔迷离、后来被W.J.T.米歇尔(W.J.T.Mitchell)称为“元图像”的《宫娥》。19世纪初叶,委拉斯开兹成为写实主义与印象主义画家的楷模,马奈(Édouard Manet)说他是“画家中的画家”。20世纪,毕加索(Pablo Picasso)不计其数变形摹写过《宫娥》,达利(Salvador Dalí)也画过委拉斯开兹的《宫娥》,以探究绘画中的“真理”。这幅让历代画家、哲学家与艺术史家欲罢不能的《宫娥》,是委拉斯开兹1656年所绘,彼时他在宫中作画已达三十余年。作品尺幅巨大,高318厘米、宽276厘米,现收藏于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Museo del Prado),这也是西班牙最大的博物馆。
《宫娥》画面的左侧是巨大的画架背面一侧,画家本人握笔站立,凝视着前方,那是画面之外模特儿的位置,也就是我们观者的站位。作为观者,我们看不到委拉斯开兹在画什么,以至于福柯都无从知晓画家是画完了呢,还是刚要启笔。画面中心是腓力四世年方五岁的女儿、金发披肩的小公主玛格丽特·特里莎(Margarita Theresa),腓力四世与其第二任妻子玛利亚娜(Mariana of Austria)的独生女,彼时王室唯一的后裔。小姑娘身着束腰紧身上衣、巨大的裙摆,那是典型的皇家服饰,虽然一脸稚气,却已然有了君临天下的气势。公主两边即是此画后来得以易名的两位小宫娥:左手边是伊莎贝尔(Isabel),正欲向小主人致礼;右手边是玛利亚·奥古斯蒂娜(Maria Agustina),跪在地上,手拿饮料点心托盘,在请小主人用点什么。画面右侧边上是一条狗和两个小矮人,小矮人都是小公主的玩偶,其中德国人巴伯拉(Bárbola)注视着前方隐身模特方位,意大利人佩图萨多(Pertusato)一只脚搭在狗身上,像要驱走黄狗的睡意。伊莎贝尔身后是小公主的监护人马塞拉(Marcela de Ulloa),身着丧服,正在跟一名保镖模样的男子说话。景深处后墙门口的台阶上站着一名黑衣男子,那是委拉斯开兹的亲戚——宫里主管挂毯事务的涅托(José Nieto),正注视着屋中场景,右手似推开门帘,让更多自然光进入画室。后墙中央偏左位置,与门楣平行的一面镜子里,映照出腓力四世与王后影影绰绰的肖像。
国王夫妇应是画家表现的模特儿,站位是在画面之外,绘画鉴赏者所在的方位。画像总体有九位人物,加上后墙镜中的两个影子,这正是文艺复兴以降古典人文主义题材绘画的标准人数构思。16世纪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者阿尔伯蒂在其《论绘画》中,解释他鼎力推崇的“历史画”(istoria)时,即强调“历史画”贵在丰富性,而丰富性不仅仅是好在多变,而且要庄严冷静、高贵节制,所以人数要有限定:
在阿尔伯蒂看来,“历史画”的丰富性最终落实在人物身体的互相协调上面。在这方面,委拉斯开兹的《宫娥》可谓在画家的这个微妙且神秘的王室私人空间里,将平衡协调做到了极致。腓力四世跟两个妻子一共生过12个孩子,只有两个成年。画中的玛格丽特公主后来嫁给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后。这是后来的故事,画家当时自然不会知情。可是冥冥之中天意使然,右侧过来的光线,高光聚焦在画面中央的小公主身上,以至于衣着亮得近乎发白。小姑娘完全不理会她边上两个侍女,头偏着,目光却笔直射向画架背后的正前方。那还是模特的位置,也是我们看画的人的方位。是以新的问题出来了:抑或小公主原本就是画像主角,被突然造访的父母亲吓了一跳?
画面左侧的委拉斯开兹神情严肃,他给小公主画像也好,给国王夫妇画像也好,怎么把自己也画了进来?这样来看,镜子的假设当是情理之中。《宫娥》的作者对镜子肯定不会陌生,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Jan van Eyck)望远镜和显微镜式的北欧文艺复兴的镜像杰作《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就挂在腓力四世宫中。
二、福柯读《宫娥》
反观福柯对《宫娥》的空间阐释,又有一种后结构主义的深意。虽然1966年正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高光时代,后结构主义尚还不知为何物。画面左边是委拉斯开兹站在画架面前,巨大的画架几乎顶天立地,虽然只有背面一条给切进了画面。福柯的评价是,观众只能看到画架背后的边缘,正面画布上画着什么,却一无所见。观众能看到画家全身,他刚从目不可及的画布面前冒出来,恰恰处在左右摇摆的一瞬间,黑暗的身躯与明亮的脸面,介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画家正在凝视一个看不见的点,这个点应是他正在表现的对象,可是这个对象所在,正是我们观众的站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脸、我们的眼睛。是以委拉斯开兹正在观察的那个景象就有了双重的不可见性:这个方位并没有见于油画空间,然而这个盲点恰恰是我们作为观者自己所在之地。我们看不见画面,只能看到它的背面:高大的画架。画架上的画布重构了画面上缺场的我们所在的空间。表面上看,似乎情景简单,不过是一种互动:我们在凝视油画,画家反过来也在画中凝视我们,相看两不厌。但是: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福柯认为它们意味着这里所有的视觉都是不稳定的,主体与客体、观众与模特持续不断地颠倒位置。而且因为画面不可见,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视线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同样也在迷茫:我们究竟是在看呢?还是在被看?甚至,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概言之,主体消失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一切都只是这个看似确定,实际上飘忽游移、极不确定的秩序网络之中的一个元素罢了。
福柯进而谈到镜子。福柯指出,这面后墙上位居画面透视焦点处、映出国王夫妇影像的矩形小镜,它压根儿没有照出屋中人物,既没有照出背对镜子的画家,也没有照出画室里的其他人物。镜子入画是荷兰画家的传统,在这个传统里,镜子只是在一个非真实的、修正、缩小而且弯曲的空间里,重复画面里的东西。但是委拉斯开兹的这面镜子,展现的并不是画中景观,它直接穿过被再现的整个图景,照出画面中几乎所有人物都在凝神观看的国王和王后,那也正是观画者所在的方位。那么,是不是国王与王后以目不可及的画外视角,开启了这个你看他、又看我,我也看你、又看他的相互凝视景象呢?福柯认为这是一目了然的。国王与王后位居视线交叉的中心地位,这从画面中人物的尊敬目光,以及小公主与小矮人的一脸惊诧中,便可见端倪。但这个中心点又是无中心的中心,在所有衣着华丽的画面人物中,镜中的国王夫妇是最朴素、最苍白的,而且最不真实、最为脆弱。画中人物稍许移动一下,光线稍许变幻一下,他们就消失了。
福柯分析了委拉斯开兹《宫娥》这幅画中的三组视线。以国王夫妇站位为中心,福柯认为在这里是交叠了三组视线:一是国王及王后作为模特的视线;二是观画者看画时候的视线;三是画家构思画面时候的视线。这三种“凝视”功能在画面之外的一个点上交合:它是被再现的对象,也是再现的出发点。在再现的画面上它并不存在,然而它又确确实实在画面中得到了投射。画家的视线中看到模特,画面上的画家在将模特复制到面前的画布上面。国王的视线中是自己的肖像,但是肖像在画布上,画布面对画家、背对国王,国王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不到画布。在观画者的视线中,站位在国王中心方位,看到全部真实画面。但是,福柯强调说,镜子所表现出来的慷慨是虚假的;也许镜子隐藏的同它揭示的一般多,甚至更多。他最终以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他的著名的《宫娥》解读:
这里的关键词是“表象”(representation),这个词在法文和英文中同形同义。在中文语境中,哲学界习惯译作“表象”,如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此书原名是,英译名为。在文学和艺术批评界,它的传统译名是“再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渐成燎原之势的文化研究领域,它更通行的译法是“表征”。表象也好,再现也好,表征也好,它们都同时可以作为动词和名词使用,也同时指涉过程和结果,学界因此有过关于representation的中译名论争。如任教杜克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刘康就坚持这个词的“再现”本义。但是《宫娥》里的再现纵是殚精竭虑,似也难有确定的所指。在福柯看来,在三种视线错综复杂的交织网络中,主体和客体的那一层相似性不复可见,反之,一种后结构主义的秩序浮出水面,仿佛这个秩序就是主体,然而主体已然不见。再现一旦从相似性中脱颖而出,便成为再现的再现、纯粹的再现,或者说,表象的表象、纯粹的表象,表征的表征、纯粹的表征。哪怕多年以后,它更变身为什么也不反映、什么也不再现的纯粹“拟像”(simulation)也罢。
《宫娥》这幅油画岂止只有后墙一面镜子。画家面前的画布也是一面镜子,映出他工作室里的整个场景。画布上的镜中影像,来源则似是国王与王后站位处的镜子,假如没有这面画面之外的镜子,委拉斯开兹再现他本人的自画像其实不好想象。这两面镜子相互映照,最终成就了《宫娥》这个17世纪最为神秘的视觉哲学再现映像。谁在看,谁在表征,谁在被看,谁在被再现,实际上成为一个互相映照、互相循环的怪圈,终究没有一个原始的视觉起点。主体消失了,作者不过是话语的体系使然,话语就是结构。而福柯的结构,一如他的《宫娥》解读,展示的却是解中心、多元化的典型的后结构主义范式。或者毋宁说,福柯的上述分析,可视为他在次年的著名讲演《他种空间》中所提出的“异托邦”思想的一个预演。
三、米歇尔读福柯读《宫娥》
美国艺术史家W.J.T.米歇尔读福柯的《宫娥》解读,在呼应福柯读《宫娥》谓主体消失、话语结构取而代之的同时,更围绕“元图像”主题展开。元图像即图像的图像,或者说,指向自身或其他图像的图像、用来表明什么是图像的图像。以图像自身来说明什么是元图像,米歇尔同时举证的例子有美国漫画家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1964年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的漫画《螺旋》(发表时名为《新世界》),画中画家以自己为中心画螺旋形圆圈,高高在上地主导了底下的山丘树木炊烟景观,仿佛画家就是上帝,创造了螺旋边线上的风景。同时还有阿兰(Alain)1955年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后来被贡布里希称为“风格之谜”(riddle of style)的《埃及写生课》,画中11位埃及的美术系学生正在给一个正面侧脸的裸体女模特画像。米歇尔不同意贡布里希将此画解读为一叶障目而“以不同的方式感知自然”,而是认为今天西方艺术系的学生也一样用拇指来比量模特以确定比例,即是说,我们与其嘲笑埃及人,不如嘲笑我们自己。此外还有美国心理学家约瑟夫·加斯特罗(Joseph Jastrow)的《鸭—兔》:一个图像朝左看是鸭子、朝右看是兔子,以及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的《奈克尔立方体》()、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双十字》和英国漫画家威廉·希尔(William Ely Hill)改写1888年发行的德国明信片、发表在1915年11月美国《泼克》()杂志上后广为流传的《我的妻子与岳母》等。米歇尔认为上述这些图像都是自我指涉的元图像。分别来看,《鸭—兔》《奈克尔立方体》和《我的妻子与岳母》当属于感觉和知觉关系错乱的幻觉图。所谓感觉,我们通常是指外部景观的输入;所谓知觉,则多指大脑对感觉积累的选择、组织和阐释过程。而当这一过程更进一步有语言文字强行介入的时候,那便有了让福柯和米歇尔同样欲罢不能的比利时画家勒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这不是一只烟斗》。
在米歇尔看来,委拉斯开兹的《宫娥》是上面所有这些漫画元图像各个不同特征的集大成者。首先从形式上看,它就模糊了斯坦伯格《新世界》一目了然式的自我指涉与阿兰《埃及写生课》漫画式自我指涉之间的边界。《宫娥》再现了委拉斯开兹画画的场景,可是对于画家究竟在画什么,我们其实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只能看到画布的背面。所以:
这是说,《宫娥》如福柯所言,是再现了古典主义的艺术再现或者说艺术生产场景。但米歇尔认为福柯的说法还不够确切,因为《宫娥》再现复再现的方式,也还是古典主义的,是以福柯的“对古典再现的再现”,不妨更改为“对古典再现的古典再现”。米歇尔指出,比较来看,其他两幅自我指涉的元图像作品中,阿兰的《埃及写生课》是古典再现的框架中的古代再现,斯坦伯格的《新世界》则是后现代框架中的现代主义再现。
但是即便都被名之以“元图像”,米歇尔也承认《宫娥》与《鸭—兔》一类的幻觉游戏完全不同:《宫娥》是西方绘画史上的辉煌经典,《鸭—兔》不过是刊登在幽默杂志上的一幅无名漫画,后来成为了心理学文献中的插图;《宫娥》是反映绘画、画家、模特、观众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迷宫,百解不厌,《鸭—兔》不过是被用来确证一种零度阐释,显示视觉错觉如何发生,一般并不认为它具有深刻寓意或者悖论意义。前者是黄钟大吕,后者是雕虫小技,若非维特根斯坦讨论过“鸭—兔”问题,几乎没有人会记得它,它也肯定不会跻身元图像之列。而问题是,假若福柯没有讨论过《宫娥》,它固然仍旧不失为伟大经典,但是同样不会成为元图像。
米歇尔认为,有如维特根斯坦用《鸭—兔》举例来谈视觉错觉,福柯大谈《宫娥》,也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让刻板僵化的学院派元图像话语进入了特定的语言游戏,换言之,进入了两人各自的“哲学”语境。维特根斯坦敦促我们不要去解释《鸭—兔》,而来聆听我们所说的东西,思考它与我们的视觉经验之间的关系。福柯则提出,我们必须假装不知道《宫娥》里的人物是谁,他们都在做什么,我们应当放弃导致我们不足以充分“可见事实”的那种语言,而求诸一种“灰色的无名的”语言媒介,惟其如此,它才可以成就《宫娥》从艺术史上的一件杰作到元图像的历程。简言之,跟上述其他元图像一样,它也用再现的自我认识,通过追问观者的身份来激活观者的自我认识。
由是观之,《宫娥》中的这一追问跟权力与再现密切相关,包括绘画与画家的权力,也包括作为隐含观者的国王与王后的权力。这主要表现在委拉斯开兹把自己画成宫廷仆人,然而通过安置在不起眼方位的那一面镜子,机智且谨慎地表达了自己主宰和控制再现的一种主权,从而使反仆为主成为可能。不仅如此:
米歇尔与福柯英雄所见略同,都是重申画面中观众缺场又在场的神秘视角。他表示欣赏福柯的说法:《宫娥》是给我们呈现了再现的整个循环景观。这个循环圈里有三个支点:一是画家在画板上工作时占据的位置;二是画中模特占据的位置,他们很可能就是镜中的影像;三是观者占据的位置。而这三个方位投射出来的“没影点”分别是:一、门口画家的亲戚挂毯主管;二、后墙镜子里的虚假影像,他们应是观看这个场景的国王与王后;三、画面中心的小公主,她也是父母以及我们观众的凝视对象。
在以上纵横交错的视线与视觉的交换网络中,米歇尔再度确认了观者的主体性就建构在无法再现的隐蔽空间里。他重申福柯《词与物》中的著名描述:一切凝视都是不稳定的,在中间视线穿透画板的地方,主体与客体、观者与模特,颠倒了他们的角色。我们只能看到画布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在被看呢,还是在观看?米歇尔认为,《宫娥》的视觉颠覆能力也重构了我们对君主主体性的想象:我们将空间、光和设计的主宰归于画家,将民众的主宰归于历史上的君主,将自己的视觉/想象领域以及外观和意义的主宰归于自我。所以,我们是现代的观者,是我们私人空间“精神王国”的统治者。
所谓福柯是用他“灰色的无名的语言”在谈《宫娥》,而由此将《宫娥》从艺术史的阐释客体变身成了一幅元图像,米歇尔指的是《词与物》第一章第二节开头的一段话。彼时福柯说,我们看画时会纠结在一些不稳定的抽象名称里不能自拔,诸如画家、人物、模特、观者、形象等,这是说不清楚的。我们只需要说,委拉斯开兹创作了一幅画,在这幅画中,画家在画室里或者君主的房间里,把自己也跟画中人物一起再现了出来。小公主玛格丽特端坐在中央,看他作画。米歇尔注意到,福柯逐一交代了画面上各个人物的名字,包括看不到的模特原身,只能在镜子里见到模糊影像的国王夫妇。之所以逐一点名,福柯的说法是这些专有名字会避免含混,告诉我们谁是谁。但是,词与物的关系远不是这样清楚明白的。米歇尔引用了福柯《宫娥》论中画龙点睛的一段著名话语:
这是说肉眼所见不足道,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很难用言词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即便求诸形象的比喻也是枉然,绘画的意义最终将由话语的结构来作解释。米歇尔对福柯的这一立场,表示无条件的认同。
那么,福柯上面交代的人名又当何论?正是给人物安上名字,我们才知道了画面上的人是什么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第四章中谈摹仿,说摹仿的好处之一便是当主体不在场的时候,可以用再现的画像来替代他的在场,从而达成认知功能,让人一见便认出画中人原是何许人也。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的第五幕第一场中说,诗人可以给子虚乌有的东西加上一个居所和一个名字。有了名字,语词与事物、与图像的关系就变得清晰起来。如福柯本人所言,名字对于绘画意义的传达有点石成金之妙,我们可以指着图像说,这是谁谁谁。换言之,悄悄地将说话的空间指示到注视的空间。不过米歇尔同样发现,如此凭借相似性来寻找终极的解释,固然是艺术史的使命,也许同样也是再现理论的正当使命,然而它却不是福柯的目标。福柯的目标是保持语言与视觉对象的开放性关系,将两者之间的不相容性作为言语的起点,而不是障碍。所以,如若我们想要最大可能地接近语言与视觉对象,就必须清除名字,以保持词与物的无穷的开放性。惟其如此,一如福柯所言,通过这一灰色的、无名的、因为宽泛无边而总是过于精细和重复的语言,图像可望一点一点地照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