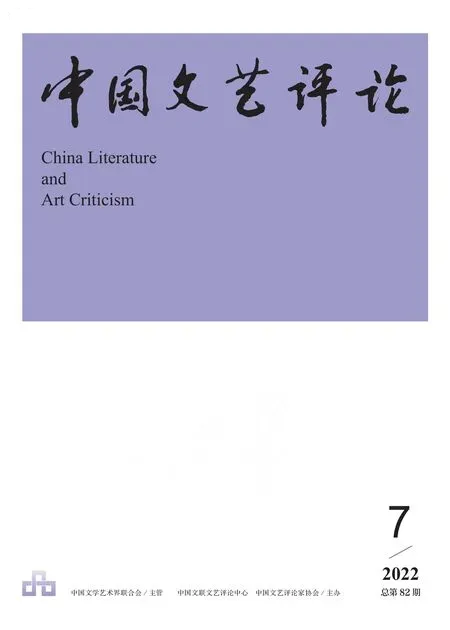书法的主体自觉与路径创新
——以徐渭、董其昌为例
■ 李帅文
一、徐渭与董其昌的书学背景
二、徐渭之“真我”

图1 徐渭《行草应制咏墨轴》352cm×102.6cm 苏州博物馆藏
三、董其昌之“仿书”
刻板临摹古代法帖的方式在“独抒灵性”的解放思潮下面临危机,但不参古法地一味“独抒灵性”又消解了书法之法的传统。董其昌在这一背景下将“仿”这一概念广泛地运用到实践中,既继承先贤仿画、仿书之法,又加以己意形成独特的风格面貌,这是避免时代书风趋同与流俗的关键之举。

图2 董其昌《录旧作四首》93cm×38cm 北京保利 2011年春季拍卖会
四、顿渐之间:笔墨中的禅学意趣
徐渭“露己笔意”与董其昌“不合之合”的书法创作观彰显了二者共通的主体自觉,而之所以形成动静相异的书风则需要进一步探究其形而上的认识观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在晚明儒佛互阐、佛教复兴的背景下,徐、董二人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如徐渭在狂禅影响下的顿悟修行以及董其昌在游戏禅悦中的顿渐体悟。

图3 徐渭《提鱼观音图》116cm×25.8cm上海博物馆藏
五、似与不似:书法的主体自觉与路径创新
相对于徐渭对顿悟的审美感知,董其昌则更倾向于在禅悦之风中渐修书中气韵,如其所说“胸中脱去尘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董氏认为存在“尘浊”是渐修的前提,正如神秀诗偈中所写的“莫使有尘埃”,因心有尘埃作为前提,所以需要“时时勤拂拭”才能明心见性。显然在董其昌看来,经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渐修过程才可去除胸中尘埃、悟得书中三昧,这区别于徐渭“一棍打破”的顿悟方式。同时,董其昌书画集诸法于一身,借助“仿书”的渐修方式从合其法度规范的基础上离形去知,超越所仿对象之形。这同样指向了“教外别传”的禅宗教义,不滞于物亦不囿于形,而是“以心传心”,不依赖文字语言等形式达到悟道的境界。同理,董氏有意挣脱传统法度的桎梏,拆其外在的骨肉之形从而见得自身的本来面目,这对书法临池中由临摹到创作转换的阶段具有方法论意义。所以从徐渭的“真我”和董其昌的“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顿悟或渐修,均可实现由法度到超越法度的路径创新。
徐渭与董其昌分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今书坛的现代性与学院派特征。董其昌的“仿书”主题基于传统形式不断锤炼技法,以追求不重复古代先贤的“不似之似”,在渐修气韵、顿悟淡雅的过程中明心见性;徐渭之“真我”观是超越形式、打破理性所形成的自然书写,并不执着于形、色的法度,在“不求似而有余”的书法创作中直抒胸臆、诗意地栖居。徐渭与董其昌在“似与不似”的美学命题上从顿悟与渐修的不同角度呈现了书法中的主体自觉与路径创新。再观当代艺术创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守正创新是艺术技法提升的必要条件,而创作主体的审美自觉更是由技入道的必由之路。从书法角度而言,守正创新既需要传统书学理论与实践的渐修,更需要在“集大成”的基础上超越古今主客二分的临摹范式,达到传统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实现物我合一的自然通感。在这个意义上,董其昌的“仿书”为形式与技法的书学渐修阶段提供了临创转换的新路径,而徐渭的“真我”观则一定程度上为理性临习传统的书家提供了主体自觉的新思想,二者在顿渐之间为当代书法的守正创新开拓了思路并指引了笔墨中的心灵归宿,同时亦启发了当代书法创作对审美理想的塑造以及对精神境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