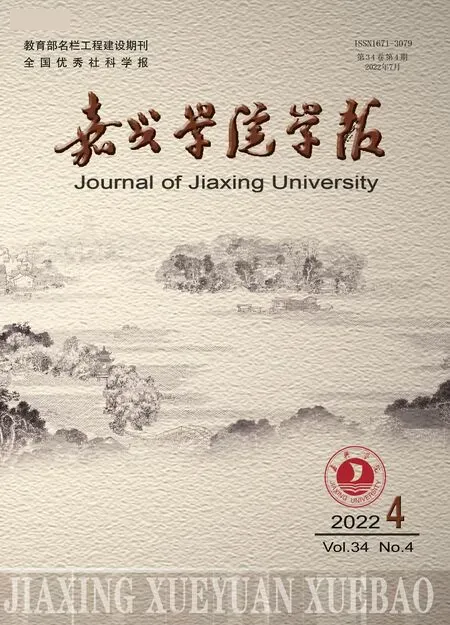王国维论《蒹葭》考辨
王 飞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通识教育中心,江苏徐州221004)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二十四则云:“《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1]70这是王国维对《蒹葭》的高度赞赏之词,“最得风人深致”的表述颇不寻常,表明王国维在阅读《蒹葭》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审美体验,于是生发出这样深刻的感叹之语。我们通过对这一评论的考察,可以发现王国维的个性化解读不仅别出心裁,而且所来有自,内涵丰富,体现了王国维对《蒹葭》的文学风格、审美表现、哲学思考等诸多方面的认知,甚至包含着王国维对人生理想追求的感叹。
一、主旨辩说
要探究王国维对《蒹葭》评论的含义,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蒹葭》一诗所表达的主旨是什么。目前,学界对《蒹葭》主旨的理解一般分为三种:一是“美刺说”。《毛诗注疏》之“小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2]郑玄笺曰:“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小序”和郑笺的意思相同,都认为《蒹葭》是批评秦襄公不以“周之礼法”治国,故而秦国的政治道路充满坎坷,即所谓“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其出发点在于现实政治问题。这里以“伊人”喻“周礼”,属于一种礼法制度。二是“思贤说”。宋代王质的《诗总闻》卷六云:“秦兴,其贤有二人焉:百里奚、蹇叔是也。秦穆初闻虞人百里奚之贤,自晋赂楚以五羖羊皮赎之。因百里奚而知蹇叔,曰蹇叔之贤而世莫知,使人厚币迎之。所谓伊人,岂此流耶?”[3]534这就是“思贤说”,以“伊人”喻贤人,百里奚、蹇叔是其代表,表达的是明君对贤人的追慕之情。“思贤说”中的“伊人”不再是指抽象的“周礼”,而是明确指向一类人,即贤人。近代兴起的第三种观点即“爱情说”。傅斯年1927年所作《诗经讲义稿》云《蒹葭》“此亦相爱者之词”[4]。这里,“伊人”所指既非“周礼”,亦非“贤人”,而是“恋人”,表达是的一种爱慕之情,是爱情诗。以上三说中,“伊人”形象发生了三次变化,从富有政治意味的“周礼”到表达士人情怀的“贤人”,再到表达世俗爱情的“恋人”,抒情色彩越来越浓厚,政治意味越来越淡薄,也更加贴近世俗生活。“爱情说”虽然是后起之说,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成为目前广泛流传的一种观点。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伊人”所指代的对象有所不同,因此考察“伊人”的所指是理解《蒹葭》主旨的关键。
“伊人”何谓?我们首先来看当代研究者对“伊人”的看法以及对《蒹葭》主旨的判断。《诗经鉴赏辞典》云:“这是一首情歌,是男方对意中人的热烈追求,还是女方对所爱者的倾心爱慕很难确定,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对这一首情诗的理解和欣赏。”[5]金启华《国风今译》:“男女相思的情歌。”[6]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纯粹为民间恋歌无疑。”[7]高亨《诗经今注》:“这篇似是爱情诗。诗的主人公是男是女,看不出来。叙写他(或她)在大河边追寻恋人,但未得会面。”[8]余冠英《诗经选译》也认为:“这篇似是情诗,男或女词。”[9]以上诸例几乎都倾向于认定追求者与“伊人”是“恋人”关系,《蒹葭》是一首爱情诗。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研究者在认定《蒹葭》为爱情诗的同时,还是留下了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这主要表现为两个“不明确”:一是“伊人”的性别不明确,既好像是男子,又好像是女子,如上文所举《诗经鉴赏词典》《诗经今注》《诗经选译》即是。也有的研究者则认定“伊人”是女子。如褚斌杰《诗经全注》:“这诗写一个男子想追寻所爱的人。”文中注释称“伊人”为“那人,指男子所爱着的人”[10]。向熹《诗经译注》在《蒹葭》的题解中说这首诗是“诗人追求他的意中人”[11],译文中的表述使用的是“仿佛她在水中央”“仿佛她在小河滩”“仿佛她在小洲里”,则“伊人”是女子。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伊人”是男子,说《蒹葭》是“一首待字闺中的女子求偶情诗,‘伊人’是想象中的男性形象”[12]。凡此种种,表明对“伊人”的性别问题存在争议。二是在是不是爱情诗的问题上留有余地。如高亨“似是爱情诗”与余冠英“似是情诗”的推测之词,则对此一问题仍然存疑。
这些不确定的地方恰恰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如果仅从“伊”字作为人称代词的词性上,我们确实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有研究者从语言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伊”字意义的源流,来解决“伊人”的所指问题。研究认为,在上古汉语中,“伊”只是作为指示代词和语气词使用;汉以后,始用作人称代词,可以是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且无性别差异和褒贬色彩;金元以后,“伊”作为第三人称代词开始具有亲切、喜爱的意味,渐渐用来指代美好形象;而在近代汉语中,“伊”多用于指女性。[13]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研究者会把“伊人”解释为女子。实际上,由于《蒹葭》一诗中“伊人”“在水一方”的形象缥缈朦胧,给人以风姿绰约之感,直观上确实容易被判为女子,而且女子的形象似乎与诗歌的意境更为协调,这或许就是一些读者往往不去深究“伊人”是男是女,而径直把“伊人”视为女子的原因。但是从研究者对“伊”字的语源流变的分析看,《蒹葭》中的“伊人”最初并不确定性别,那么,把《蒹葭》理解为爱情诗恐非古人本义。
这一点从《诗经》的古代注解本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古人的注解本几乎都没有把“伊人”解释为女子,也没有把《蒹葭》理解为爱情诗。《毛诗正义》郑笺云:“伊,当作繄,繄犹是也。”[14]“是”即“这”,是个近指代词。朱熹《诗集传》:“伊人,犹言彼人也。”“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15]97“伊”是远指代词“那”,且明言“伊人”“不知其何所指”。清姚际恒《诗经通论》:“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16]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惜招隐难致也。”[17]在这些笺注中,都没有将《蒹葭》解读为爱情诗,也没有涉及性别问题。回过头来再看“爱情说”,疑点就非常明显了,只能说,那是后人的新解了。在徐中玉等主编的《大学语文》提供了一种比较折中的说法,认为《蒹葭》是一首“抒情诗”,“‘伊人’不坐实”[18],“只要把‘在水一方’视作一种象征,它就涵容了世间各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生境遇。”这里采用了比较宽泛的“抒情诗”的说法,不去认定“伊人”的身份,而是理解为一种象征手法。这正是《诗经》“赋比兴”中“比”的具体运用,《蒹葭》实质上具有“比体诗”的性质,整首诗都以“比”的手法,写对“伊人”的追慕,这个缥缈而美好的“伊人”乃是作者的虚构之词,未必是真实的存在。作者创造这个形象,最初恐怕并没有对其性别或身份作出某种预设。陈子展评《蒹葭》云:“诗境颇似象征主义,而含有神秘意味。”[19]这种“神秘意味”正是由诗境的“象征主义”引起的。诗境中包含两个人,一是追求者,一是被追求者“伊人”。如果“伊人”象征意蕴的指代对象发生了变化,诗歌的主旨也就会随之发生改变,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伊人”形象的象征性导致了《蒹葭》主旨解读的多义性。如果以“伊人”象征“周礼”,它就是一首政治讽喻诗;以“伊人”为“贤人”,它就是一首“思贤诗”;以“伊人”为“恋人”,它就是一首“爱情诗”。甚至我们可以把“伊人”的象征意蕴推而广之,用来指代可望而不可及的任何目标,甚至是抽象的情感、人生的理想、未来的目标等。
二、“风人深致”考源
由“伊人”的象征性引发了主旨的多义性,使得《蒹葭》的解读呈现多元化倾向,不同的读者结合个人体验,对《蒹葭》的主旨进行了个性化解读。王国维认为《蒹葭》“最得风人深致”,亦是如此。但王国维的评论又有其独特的内涵,在此需要首先就“风人深致”一语的源流进行一番深入的考察。
“风”在《诗经》中有十五“国风”,“风”字一般解释为“音乐曲调”[20],宋人郑樵云“风土之音曰风”[21],十五“国风”即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22],“风人”则是地方民歌的“歌者”。朱熹《诗集传》中对“风”诗的内容及艺术特点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述。朱熹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15]1“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15]2这里有几个值得注意之点,朱熹认为“风”诗在体裁上属于民俗歌谣,作者是“出于里巷”的民间歌者,内容上反映的是世俗民众的情感,表达方式上则是以言情为主。
再进一步探究,古代尚有“风人体”“风人诗”之说。“风人体”最早起于唐代。清人翟灏《通俗编·识余》云:“六朝乐府《子夜》《读曲》等歌,语多双关借意,唐人谓之风人体,以本风俗之言也。”[23]这段材料对“风人体”的体裁特点及艺术特征都有所揭示,非常值得重视。我们首先从概念上看其体裁特征。《子夜》《读曲》皆为六朝乐府中的吴声歌曲,《旧唐书》卷三十三云:“《子夜》,晋曲也。晋有女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晋日常有鬼歌之。”[24]那么“风人体”所指的就是像《子夜》《读曲》这样的民间歌谣。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风人”之体云“论杂体则有风人”[25],其中也包含了《子夜》等民间歌谣。因此,所谓“风人体”实质上是民间歌谣的一种。其次,我们来看这种民间歌谣的艺术特点。《通俗编·识余》告诉我们,多用“双关借意”,所谓“借意”是指借同音字表示双关之意,“双关借意”亦即字面上指的是一个意思,文字之内又隐含着另一个意思。这种“双关”的艺术手法在宋人曾慥所编《类说》卷五一乐府解题类“风人诗”条中表述成为一种固定的格式:“梁简文帝《风人诗》,上句一语,用下句释之成文。”[26]这里把“双关借意”的表现手法具体概括成“上句一语,用下句释之成文”。从具体例证来看,曾慥《类说》所引用的“围棋烧败袄,著子知然衣”,翟灏《通俗编·识余》所引用的“攡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反映的内容都是民间社会生活和民间风情,语言通俗而且别有旨趣。据钱南扬的分析,前者的意思是:“上句围棋,即著子;然,同燃;袄,即衣。下句的实在意义,著,犹云使;衣,谐音作矣;言使你知其所以然了。”[27]153后者的意思则是:“匹本为缎匹,而借作匹偶;关本为关门,而借作关心。”[27]154都含有“双关借意”,即所谓“有意不把意思说明白”“本义隐藏在字面义之内”[28],这表明“风人诗”存在着这样一种结构形式,此形式应为此类诗歌的一种体制,具有鲜明的民间歌谣特色。从表达效果看,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云:“《乐府解题》以此格为‘风人诗’,取陈诗以观民风,示不显言之意。”[29]所谓“不显言”,即是由字面意义推知隐含的意义。此种表达方式,一方面表现出一种语言的机趣,另一方面又具有语意朦胧之感,需要通过想象的思维方式由已知推测出未知,这就是“不显言”的“双关借事”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从以上分析可知,作为一种民歌体裁的“风人体”,多用“双关借意”的表现手法,具有“隐含其事”的艺术效果,亦即具有象征性,所要表达的意思隐含在字面义之内,这是此类文体最突出的特点。但是“象征性”并非民间歌谣所独有。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二云:“唯李商隐云:‘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水,薛王沉醉寿王醒。’其词微而显,得风人之体。”[30]认为李商隐的咏史诗《龙池》也是“风人体”的表现,它的选材不过是唐玄宗宴饮之事,事属微末,但主旨却隐含着对历史事件的讽刺意味。李商隐的这首诗并非民间歌谣,但因“词微而显”,遂被誉为“得风人之体”。就《蒹葭》一诗而言,也是这样。从表面上看写的是追求者对“伊人”的思慕之情,但从其文字之内却可以对其意旨有更多的想象。王国维赞许《蒹葭》“最得风人深致”,也同《鹤林玉露》赞许李商隐《龙池》一样,侧重的是文字之内所隐含的意旨,言在此而意在彼,言近而旨远。

三、“洒落”意蕴探究
王国维评《蒹葭》“最得风人深致”,参以晏殊《蝶恋花》,揭示两者之间的异同,认为两者“意颇近”,《蒹葭》“洒落”而《蝶恋花》“悲壮”。“洒落”一语突出地表现了王国维独特的审美感受、人生情怀。
与《蒹葭》进行比较的《蝶恋花》在《人间词话》中出现了三次,都有所寄托。除第二十四则外,还有第二十五则:“‘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34]第二十六则:“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从王国维的这二则评论看,他赋诗言志的用意是明显的,所论的绝不仅仅是诗歌的字面意义,而是寄寓着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蒹葭》也是如此。
但《蒹葭》与《蝶恋花》又有诸多异同之处。其相同之处在于,两者描写的都是秋天的景象,内容都是表达对人的追求或思念,而且都是求之而不得。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抒情主人公的追求行为有所不同。《蝶恋花》是登楼远眺,《蒹葭》则是付诸行动,上下求索。其次,抒情主人公的审美特征不同。《蝶恋花》中的追求者登楼远眺的只身孤影是茕茕孑立、苦心孤诣,《蒹葭》中则是义无反顾、孜孜以求。再次,两者在表达的情感体验上也有所不同。《蝶恋花》是愁苦之中蕴含着无尽的凄凉,《蒹葭》则是缥缈迷朦之中的怅然若失。从以上三点差异来看王国维评《蒹葭》的“洒落”一词,表现了追求者洒脱自然、无拘无束的追求姿态,是他对《蒹葭》解读的个性化精神体验。王照圆曾评论说“《蒹葭》一篇夷犹潇洒”[35],诚如斯言。相比《蒹葭》中的“洒落”,则《蝶恋花》无疑是“悲壮”的。王国维所说两者“意颇近”而非“全同”,言语之间,融入了他对两者的玩味和解读。清人牛运震《诗志》中的观点亦可与王国维的观点相互辅证。他说《蒹葭》是“《国风》第一篇缥缈文字。极缠绵,极惝恍,纯是情,不是景;纯是窈远,不是悲壮。感慨情深,在悲秋怀人之外,可思不可言。萧疏旷远,情趣绝佳”。此说与王国维“最得风人深致”之语相得益彰。
那么,王国维在《蒹葭》解读中寄寓的人生感慨是什么?王国维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杰出学者,学识渊博,清末民初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对他的读书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常常陷入一种悲观主义情怀。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总结王国维的性格特点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知与情兼胜的禀赋”,二是“忧郁悲观的天性”,三是“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36]3-18。也就是说:他不仅富有学识,而且具有敏锐的感悟能力;对人生的思考往往充满悲观主义的情怀;对理想的追求又有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执著精神。《蒹葭》中的追求者形象成为他人生理想的写照。
对此,王国维也有直接而切近的表述。在《〈红楼梦〉评论》中,他说:“理想者可近而不可即,亦终古不过一理想而已矣。”[37]“可近而不可即”,这与“在水一方”的“伊人”何其相似;而“终古不过一理想而已矣”,《蒹葭》中,诗人追慕到最后的结果,也如同理想一样“可近而不可即”。王国维几乎是亲口说出了《蒹葭》与其追求人生理想之间的象征关系,所谓“伊人”就是他预期的人生理想,追求者即是他的精神化身。由此可见,王国维“最得风人深致”与“洒落”的赞许之词,实质上揭示了他对《蒹葭》主旨的理解,寄寓着他对人生理想深深的感叹。
王国维以《蒹葭》表达对人生理想的看法与其早期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1903-1907年这五年间,王国维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了西方哲学的研究之中,热爱叔本华、康德、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学术著作,形成悲剧主义的文学观照方式。他对《蒹葭》的论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悲观主义哲学观,应当视为哲学观念在诗歌研究中的映射。佛雏说:“王氏的‘理想’始终浸透了浓厚的悲观主义。”[37]403这种悲观主义“本于西方某种悲观哲学”[33]340,俞晓红对此言之甚明:“王国维关于生活本质为欲的观点,与叔本华对于生活之欲之痛苦的论述有明显的承继关系”。[38]12王国维本人也认可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相通性质:“特如文学中之诗歌一门,尤与哲学有同一之性质。”[37]39因此,王国维借助西方哲学观念探究文学作品的内涵,实质上是他解读古典文学的独特视角,在其中融入了个人的哲学思考和人生体验。
四、结语
对《蒹葭》的个性化解读体现了王国维“以我观物,则万物皆着我之颜色”[1]11的文学观照方式,王国维正是在对《蒹葭》的解读中,赋予它以“我之颜色”,借此寄托其精神追求。作为民间歌谣,《蒹葭》意境的象征性,为王国维的解读提供了足以支撑其思想内涵的文本基础,更兼具独特的个性品格,为他的个性化解读提供了必要条件。王国维虽然并未直接表述《蒹葭》所寄寓的主观情感是什么,但多方考察,我们仍然可以从这样一个微观视角清楚地感受到王国维精神世界中对理想的追求、期待与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