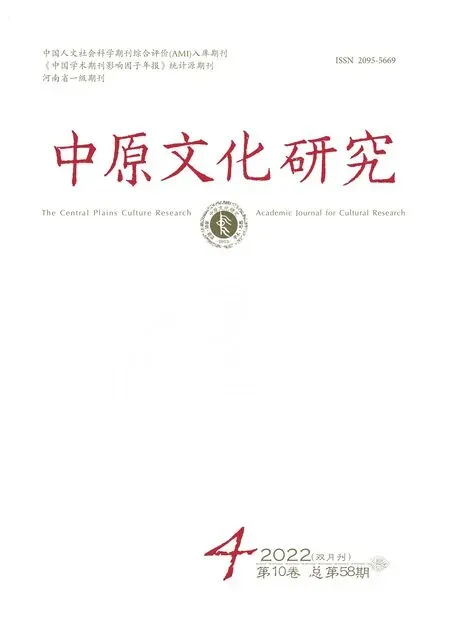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多京体系中的两京主体制
丁海斌
中国古代的都城制度,总体上以多京制为主,形成了多元化的都城体系。但在实行多京制的过程中,大多又以两京(首都与某一重要陪都)为主体,其他陪都则居于次要地位,这样就形成了多京制都城体系中的两京主体制。这种体制在唐、宋、元、明、清各朝已经极为普遍,并渗透到古人的观念中。多京体系中的两京主体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关于中国古代的两京制问题,学界已有所涉及,研究的重点在明代的两京制,如郑天挺《明清的“两京”》、刘中平《明代两京制度下的南京》、林旭《从两京一都制到两京制——明朝曲折的定都之路》等①,文章对明代的两京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意义和作用进行阐释。但现有研究成果对两京制的整体性、脉络性的研究还很匮乏。本文试图结合中国古代的多京体系和陪都问题,对中国古代多京体系和陪都体制下的两京主体制问题进行整体性阐述。
一、两京制发展之两个历史阶段——东西与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
在古代社会管理能力较低的背景下,出于管理国家的需要,特别是管理一个大国的需要,国家常常在首都之外设立另外的辅助性都城——陪都,来提高管理国家的能力或满足某种特殊需要(军事、政治、经济需要等)。而如果某一陪都地位比较突出,就与首都一起形成了都城体系中的两京主体制。
唐以前(包括唐朝),在国家管理中东西方关系的矛盾(指黄河流域的东方和西方)比较突出,所以在两京设置上以东西平衡型两京制为主;此后,政治、经济、军事的格局发生了转变,南北矛盾日益突出,所以在两京设置上以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为主。以上两种两京制格局是中国古代都城体系的主要格局。其中又以东西两京主体制在中国古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反映了中国古代早中期的主要政治格局。
(一)最早的两京制——商朝的两京制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陪都出现于商朝②。商朝开始形成了中国古代最初的陪都制度,是中国古代陪都制度的起源时期。
商朝最初在夏遗址上建都偃师商城(也有人认为是别都),这是震慑夏人、巩固统治的需要。在夏人的居住地建都,固然有其建国初期的合理性,但也有不安定因素和心理上的排斥。此为他乡非故乡,作为新政权的主人,商人当然希望建都在自己的老家。于是,在营建了初期的都城——偃师商城之后不久,商王朝又营建了一座形制和规模都较偃师商城更为庞大的新都城——郑州商城。迁都郑州商城后,在商朝的早中期就形成了两座都城(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并存于世的特殊格局,即后世所称的两京制格局。在这个两京制的设置中,偃师商城作为陪都,既可以辖摄伊洛平原,同时也是商王室向关中平原、晋南平原进行军事扩张的前哨重镇[1]233。
由于商朝的统治区域还比较狭小,这两座都城之间的距离很近,与后世的两京制相比,其实际意义相对较小。偃师商城在商迁都郑州商城之后,仍作为陪都存在,主要是出于监视夏人的需要,军事意义较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现有资料(主要是考古资料)来看,商朝早中期实行两京制是较为明确的,但它是否是多京制体系中的两京制,还存有很大的疑问。因为,在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两京并存于世的商代早中期,似乎未见其他具有陪都地位的城市,因而也就未形成多京制。也就是说,这时是单纯的两京制,而非多京制体系下的两京主体制。至于商朝中后期的情况,因为文献记载不足,较深入的问题就难以说清了。
(二)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
两京主体制的基本走向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大趋势。中国古代的早中期,黄河流域是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区域,黄河中游沿河东西走向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大动脉,这个大动脉的两端矗立着东西两京,即渭河平原的长安和伊洛平原的洛阳,并由此形成了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是中国古代多京制体系下两京主体制的主要形式。自西周初起,迄唐末止,除三国时期吴都建业(今南京)、蜀都成都(今成都),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都建康(今南京)外,雄踞伊洛平原的洛阳和渭河平原的长安,常常是互为首都和陪都。东西两京,相辅相成,大约占据了中国古代约4000年都城史的一半时间,从而成为这段时间里中国都城发展变化的轴心。
在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中,洛阳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点。优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文明史以及繁荣的经济,使得洛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次被设为都城或陪都。洛阳号称“天下之中”,《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2]1371洛阳因占据黄河中游的特殊位置,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早中期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成为了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的东京,是历代王朝控制中原及中国东部、南部的统治据点。
(三)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向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的过渡
从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向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的过渡,最早始于唐代。唐代总体上实行多京制,其中首都长安与先后设立的东京洛阳、北京(北都)太原、南都江陵这东西南北四京构成了一个“┿”字形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东西走向的两京重于南北走向的两京,所以仍然是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但南北走向的两京已开始显现。
南北走向的两京在唐代初露端倪后,北宋则进入从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向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转换的时期,其都城体系的特点是:在黄河中游并不广阔的地区(今河南、河北),设东南西北四京,形成了兼具东西与南北走向的多京体制。即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与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形成的东西走向,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形成的南北走向,共同形成了“┫”形多京体系,呈现出明显的从东西两京主体制向南北两京主体制过渡的特征。
但这一时期的东西两京主体制与此前之东西两京主体制有所不同:长安-洛阳的两京制,从全国看意义重大,两京相连形成千里王畿,其辐射面包括了整个中原地区,东西平衡的主体作用明显;而开封-洛阳的东西两京主体制中,洛阳已由东京变为西京。开封、洛阳两京相距不远,局促在同一地区,其在全国的辐射控制作用并不明显,东西平衡的主体作用不大。当然,这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大势所致:宋代,中国政治经济大势日趋向东、向南,长安已失去都城意义,被抛弃也是历史之必然。
(四)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
元、明、清三代实行了较明显的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且两京中的陪都皆为留都。但它们有明显的区别:明代实行的是较典型的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元、清两代则是在北方地区实行的南北两京主体制,重心明显偏北;元朝实行的是两都(大都与上都)巡幸制;清朝虽然也号称两京(北京与盛京),但盛京在全国来说,地位并不重要,难以与北京形成真正的两元。
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在汉族统治下、大运河串联下的基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两大政治经济核心区的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另一种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下基于中原统治中心和本民族肇兴区、根据地的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在这两种类型的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中,北京成为首都的最佳选择和平衡轴心。当汉族统治时,主要在江南经济力量的作用下,陪都设于江南,如明朝的南京;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主要在北方政治意义的作用下,陪都设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正如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形胜》引《图书编》曰:“高皇帝定鼎金陵,文皇帝迁都金台,则跨江、河南北而各为一大都会。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用东南之财赋,会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3]455总的看来,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陪都的特点是:汉族政权向南设陪都,少数民族政权向北设陪都,这是他们的政治重心不同、发祥地不同等造成的。
二、两京主体制下的政治体制双套制
在两京主体制的都城体制中,首都的体制设置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已阐述得较为清楚了,所以本文重点是谈谈两京主体制中陪都的体制建设。
我们之所以称两京主体制,之所以将首都、陪都称为双主体,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双套制。两京主体制下的政治体制双套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行政体制的双套制与皇家机构的双套制。当然,由于资料的局限和历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我们对这些两京主体制中陪都机构设置的了解也有所不同。总体来说,早期各朝代机构设置不够完善、我们了解得也相对较少,晚期各朝代机构设置渐趋完善、我们了解得也相对较详细。以下因篇幅所限,择两例简要介绍之[4]。
(一)隋、唐东都洛阳的机构设置
隋朝时,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书中就写道:“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5]61可见,在营建东都洛阳的同时,隋炀帝就着手在陪都设置一套中央行政体系。《隋书》中对东都洛阳行政机构的变更也有记载:“有汉已来旧都。后魏置司州,东魏改曰洛州。后周置东京六府、洛州总管。开皇元年改六府,置东京尚书省。其年废东京尚书省。二年废总管,置河南道行台省。三年废行台,以洛州刺史领总监。十四年于金墉城别置总监。炀帝即位,废省。”[5]834
唐代,东都洛阳同京师长安一样,亦设置了一套中央衙署。皇帝离开洛阳时,委派官吏担任“东都留守”,统领这套衙署,保障其正常运作,并视情况的缓急,定期或飞速向皇帝汇报工作。东都留守例加某部尚书或检校某部尚书判东都尚书省事,如《太平广记》载:“唐崔珙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6]570所以“留守”实际为东都分司百官之长,负责东都百司的行政事务。唐玄宗之后,皇帝不再巡幸洛阳,东都留守成为常设职务,代表中央在洛阳主持日常工作。因东都几次更名,故东都留守又曾称洛阳宫留守、神都留守和东京留守等。东都留守的地位在唐代前期和后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后期相比,前期东都留守的地位甚高。东都留守统领的中央衙署,有尚书省及所属六部、御史台、国子监等。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东都的御史台负责监察东都留守官(京官)和洛阳地方官(外官)。开元七年(719年),监察御史分为左右巡,纠察违失,左巡主管两京以内,右巡主管两京以外,包括两京所在的地方雍州、洛阳全境。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以监察御史察看两京的馆驿。大历十四年(779年),两京以御史一人主管驿馆,称为管驿使。龙朔二年(662年),又在东都设置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成“两监”。后来,又设置了国子馆、太学、四门馆、广文馆、律馆、书馆、算馆和崇玄学等学校,由官员管理,教师授课,培养人才。
唐代洛阳作为陪都之外,还有其他两个行政级别,也设有相应的行政机构。即唐代陪都洛阳共有三个行政级别:一为都城,即洛阳宫、东都、神都、东京;二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即府、州;三为介于都与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之间的总管、行台、都督府。其中,洛阳作为府、州的行政级别最为稳定。这点我们大致可以从《唐会要》及《新唐书》中得以了解。《唐会要》卷六八“河南尹”条载:
武德四年,平王世充,废东都,置总管府,以淮阳王道元为之。其年十一月十一日,置洛州大行台,改为东都。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改东都为洛州。九年六月十三日,废行台,置都督府,以屈突通为之。贞观十一年三月十日,改为洛阳宫。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废都督府,复为洛阳州,以裴怀节为长史。
显庆二年六月五日敕,洛阳州及河南洛阳二县官,同京官,以段宝元为长史。其年十二月十三日敕,宜改洛阳州官为东都州县官员,阶品并准雍州。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神州都。神龙元年二月五日复为都。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河南府,以李杰为尹。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改为东京。上元元年九月二十日,停东京之号。元年建卯月,改为中都。[7]1189
《新唐书》对此也有相关记载,但不若《唐会要》详细:
东都,隋置,武德四年废。贞观六年号洛阳宫,显庆二年曰东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龙元年复曰东都,天宝元年曰东京,上元二年罢京,肃宗元年复为东都。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开元元年为府。[8]981-982
(二)清朝盛京的机构设置
清朝统治者为了突出盛京地位,隆重陪都体制,并模仿明制,设立了盛京礼、工、户、刑、兵五部。盛京五部直接对中央负责。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盛京设礼部,次年又设户部、工部。康熙元年(1662年)设刑部,康熙三十年(1691年)设兵部,并设侍郎以下各官。至此,始成盛京五部之制[9]935。
同时,由于盛京有强烈的留都性质,所以为管理皇家事务,特设立盛京总管内务府。它是清廷在其陪都盛京设立的皇家服务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掌管盛京三旗包衣与宫禁等有关事务,隶属北京总管内务府。清廷迁都北京时,内务府也随迁北京。但盛京仍保留并扩建有皇宫、皇陵,并经常准备接待皇帝东巡祭祖活动等,有相当数量的包衣在粮庄、果园、采捕山场等为皇室服务,所以需设立相关管理部门。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铸发关防,设“盛京上三旗掌关防佐领”,由三佐领中选一人掌印理事,实际是盛京内务府的前身。乾隆十三年(1748年)仿照北京总管内务府对其机构进行了改组,形成了盛京总管内务府。清朝灭亡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盛京地区的宫殿、庄园、产业等仍由盛京内务府管理。
三、两京主体制的形成原因与历史作用
辅助首都进行国家管理是两京制陪都得以形成的基本原因和发挥的基本作用。即所谓“邦畿连体,各有采任”[10]4128。在这些方面,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陪都的作用比较明显,它也是洛阳作为著名古都存在的重要意义所在。总体而言,两京主体制的都城体系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唐太宗《入潼关》诗云:“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两京使东西或南北连通,建立统一的王畿。《汉书》载:“初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10]1650《资治通鉴》中唐代名臣褚遂良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这一点:“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11]6207
具体来说,我们又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来谈谈两京主体制形成的原因与作用:
(一)政治方面
本文主要是指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并且,这种政治关系与国家的经济、军事、文化等皆有所关联,它以政治集团为主要表现形式,以经济、军事为主要支撑。
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欠发达的时期,政治集团的数量少、独立性强。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地域、不同部族、不同共同体的政治集团日益形成,这些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斗也就开始了。两京主体制的本质,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为加强对已有的或潜在的敌对政治集团的控制与防御设立的。两京之间的平衡首先是政治的平衡。
具体地看:商朝的偃师商城主要是为了防止夏人的反抗保留的;周朝的东都洛阳首先是为了囚禁殷贵族和接受东方诸侯朝拜而设立的;秦汉至唐,两京主体制都城是东西方政治集团平衡的产物,统治集团多居于黄河中游的西部,他们为了控制东部政治势力,多在黄河中游的东部设陪都;两宋以后,西部政治集团日益衰弱,中国成为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北方政治集团和以经济、文化为基础的南方政治集团的角逐之地,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体制建立。
(二)经济方面
两京之制,事关重大,与经济必然密切相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12]173经济是基础,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固的上层建筑。
1.长安之经济意义
在中国古代早期文明中,西北地区比较发达,尤其是西北的关中平原是黄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曾是我国古代早期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地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正因为如此,先秦、秦汉、隋唐等多个朝代定都城于长安。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土地肥沃,适于人类生存发展。从上古到两汉,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关中地区,一直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先秦时,周人崛起于陕西渭河流域,建立了西周王朝,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在此建立了秦国并发展壮大,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西部地区举世闻名的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就是在此前后建立的,对当地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长安位于黄河流域中部的关中盆地,平原辽阔,土地肥沃,河流密集,泾、渭、灞、浐、潏、沣、滈、涝等水流经境内,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沃野千里,十分宜于农耕,能为人口众多的首都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这也成为在此定都的重要因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道: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3261-3262
比较而言,此时的南方还很落后,生产力低下,关中的优势则较突出。特别是西汉时期西域地区比较繁荣,开辟了贯通中西的大动脉——丝绸之路。这条商路东起长安,向西可达地中海沿岸,促进了东西方经贸往来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唐朝定都长安,以关陇地区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朝的西部疆域超过了汉朝,在西域地区设置了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统辖西域。当时的长安城是著名的国际大都会、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长安虽处关中平原,但关中平原面积有限,当人口尚未膨胀之时,粮食供应尚可。而隋唐之际,人口急剧膨胀,长安的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甚至出现了“逐粮天子”,经济问题反成长安继续承担首都角色的重大障碍之一。
2.洛阳之经济意义
千年东都洛阳之建制,与其经济地位息息相关。一个王朝自始至终都需要解决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粮食问题。都城建立后,由于城内人口众多,仅靠附近地区的粮食生产常常是难以充足供应的,因此就需要将粮食从其他生产地转运至首都。在东西两京中,长安虽位于关中平原,土地肥沃,但仍不足以自给;而洛阳不但不需要通过外运粮食解决自身问题,反而它是全国粮食转运的中心。
西周时,成周成为全国征收贡赋的中心。据《兮甲盘》铭文,周宣王命令兮甲(即尹吉甫)“政(征)司成周四方责(积)”[13],所谓“四方积”是指诸侯上缴的贡赋。成周不仅是对周围“郊甸”征发人力物力的中心,而且是对四方诸侯征收贡赋的中心,更是对四方被征服的夷戎部族征发人力物力的中心。自西周至隋唐,洛阳一直扮演着长安经济主要支撑者的角色。
东汉时期,洛阳逐步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东起点。而隋唐之际,号称盛世,长安靡费极甚,对洛阳的经济依赖更为强烈。《通典·食货十·漕运》载:“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14]118
虽然两京之间有发达的水陆交通,但一旦关中地区闹饥荒,就难以负担,连皇帝都要携宫廷百僚到洛阳“就食”。在开皇十四年(594年)的一次灾荒中,隋文帝就被迫到洛阳就食,所以他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逐粮天子”。而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也因粮食问题多次到洛阳“就食”。景龙三年(709年)关中饥荒,“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11]6639。由此可以看出隋唐时期,粮食的供给问题已成为朝廷最大的困扰和难题。
3.经济大势的转变与两京主体制的转换
漕运在古代中国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转漕问题就是运东方的粮食以充实长安(宋以前),运南方的粮食以充实开封(北宋)、北京(元明清),漕运的格局与两京主体制的格局是一致的。从全局来看,最重要的转运中心在中原的洛阳等地,从秦朝开始,这一带就建有大型粮仓。所以,在洛阳设立两京制陪都与漕运关系颇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屡经战乱,南方相对安定,在生产开发方面有着明显的进展。但北方毕竟有雄厚的经济文化基础,只要局势稍有稳定,各方面就又能比较迅速地恢复起来,仍然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隋唐时期,长安和洛阳虽然是政治中心,但已称不上经济中心了,西北地区经济逐渐衰落,长江流域的加速发展使得经济中心逐渐转移至此,尤其是当时的扬州和益州,其经济上的繁荣富庶应该是超过了长安和洛阳,故而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后来,经过五代和北宋约220年的持续增长,到南宋时,全国的经济重心终于转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种经济大势的转变,成为长期存在的东西走向的两京主体制转换为南北走向的两京主体制的重要因素。
(三)军事与自然条件方面
古代设都,军事控制力常常是首先考虑的因素。两京主体制陪都作为都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军事意义毋庸置疑。我们仍以东西两都为例:古代中国地域广大,一个都城难以统御全国。特别是都城偏居边地(如长安)时,不利于统治者管辖全境,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设置陪都,平衡设都,两都分别控制东西方。两京各具天险,并且东西连片,形成对全国的控制。就中国古代历史上两京主体制的主角——长安和洛阳来说,特殊的地理条件是长安、洛阳得以为都的自然原因。
长安四面环山,有“四塞之固”之称,“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2]2716。隋唐以后,中原政权的军事威胁主要不再来自西北,而是逐渐转移到北方和东北。长安的军事意义逐渐削弱,不再成为首都或陪都也就理所当然。
洛阳地处河南省西部黄河中下游以南的伊洛平原。它北临黄河、南据嵩岳、西接崤函、东临虎牢。函谷、伊阙、广成、大谷、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环卫于外,伊河、洛河、瀍河、涧河四河纵横于内。邙山、秦山、龙门山、万安山雄踞四方,所以洛阳素有“四险之国”之誉。洛阳凭险足以固守,又因交通便利,广蓄物资可持久。清人顾祖禹认为洛阳“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15]2034,正是洛阳地理优势的真实写照。隋炀帝在营建洛阳陪都的诏书中说:“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5]61
从整体上看,长安位于与西北少数民族征战的前线,凭险以拒西北;而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凭险以控中原。
(四)文化方面
就两京主体制都城体系而言,该体系中的两京由于其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也就成为应有之义了。“故西京有六学之美,东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纷纶掩蔼,响流无已。逮自魏晋,拨乱相因,兵革之中,学校不绝,遗文灿然,方轨前代。”[16]1471我们以洛阳为例说明两京主体制都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洛阳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古代关于伏羲、女娲、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的神话传说,多传于此。1959年以来,陆续在古洛阳范围内的偃师、登封、巩义、渑池、孟津一带,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遗址计200 多处,可知洛阳所处的河洛地区早期文明之绚烂,是中华民族率先迈进文明历史的重要地区,河洛文化也常常被被奉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我国古代科技、教育、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许多重大成就,都曾滥觞于此。东周礼乐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道学、佛学、理学都与此地大有渊源;地动仪、浑天仪、候风仪发明于此;《汉书》在此修成,魏晋文学在此兴盛;而隋代洛阳宏丽至极,史载:“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5]1588
四、古人对两京的认知——两京观念和制度渐成传统
自周朝以降,经秦汉,至隋唐,两京的观念日益成熟。并且,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结束。
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从文献中“两京”一词的使用情况来考察一下古人两京观念的发展情况:笔者检索大量古籍,发现“两京”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从南北朝时开始出现的(见图1)。如谢灵运《会吟行》诗云:“两京愧佳丽,三都岂能似。”唐代是“两京”一词第一个暴发式出现的时期,是唐代两京主体制意义显著的标志。“两京”一词暴发式出现还包括宋、明、清等朝。但这些朝代的文献中所说的“两京”一词,除指代本朝的两京外,有许多指代此前各朝的两京。而且,越是时间靠后的朝代,文献中反映此前朝代内容越多,如清朝文献中绝大多数的“两京”一词指代的此前各朝,尤其是唐、明两朝的两京。

图1 中国古代各时期文献中出现“两京”一词的数量图
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中国古代各时期人们对“两京”的认知情况:
在西周,虽然两京业已形成,但西周文献中未见“两京”一词,盖因其遗留文献数量少、两京形成时间短之故也。
秦汉之际,虽然两京主体制已出现多时,东京、西京、东都、西都等名称已出现,但“两京”并称还很少见,在所检索的秦汉文献中未检索到“两京”一词。汉代有著名的《两京赋》(张衡撰)和《两都赋》(班固撰),《两京赋》实为《西京赋》《东京赋》,《两都赋》实为《西都赋》《东都赋》,《两京赋》《两都赋》只是后人赋予的合称。尽管目前我们尚未在汉代文献中检索到“两京”并称的情况,但其观念已渐趋成熟。
汉晋以后,经过西周至两汉历时一千多年两京制的不断发展,使得“两京”逐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两京”一词。如南朝谢灵运《撰征赋》有云:“窃强秦之三辅,陷隆周之两京。”
南北朝后,“两京”的观念在唐朝人的意识中已经十分清晰,检索到的唐代文献中的“两京”一词达471 处之多(见图1)。在唐朝帝王和大臣的意识中,“两京”的存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唐高祖言:“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11]6004唐太宗言:“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17]3唐高宗言:“两京朕之东西二宅,来去不恒。”[18]760唐玄宗言:“则知帝业初起,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洛为会同之府。”[19]261“三秦九洛,咸曰帝京,五载一巡,时惟邦典。”[19]295这些都说明在唐朝皇帝的头脑中,有着清晰的东西两京的意识。
宋代文献遗存较多,文献中“两京”一词检索到的数量也较多,达527 处(见图1),所指代的主要是西周、汉、唐及本朝的两京。如明人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一载:“太祖以金陵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当动深长思矣。欲联属两京以制天下。”[20]22-23
元代虽也实行两京主体制,但元代的汉语文献中所说的两京多指唐宋两京,而非本朝两京。如《文献通考》《宋史》中分别出现64 处、47处“两京”字样,所指主要是唐宋两京。
辽、金的多京制中往往没有起主体作用的两京,除首都外,其他四京或五京常常没有地位突出的一京与首都并称两京。所以,辽、金文献中的两京,非两京主体制之两京,而是辽、金多京中的某两京。如《金史》中有“中、西两京”[21]1808之句,这里的中、西两京显然不是我们所说的两京主体制的两京。
明代人士亦有清晰的本朝“两京”的观念。明代文献中检索到349 处“两京”字样(见图1),除指代此前各朝之“两京”外,亦有大量是指代本朝的“两京”,并有明确的“南北两京”的说法。如明代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略例中写道:“周二京,汉两都,非其盛也。我朝两京峙建,方初方盛,猗欤胜矣。《帝京》编成,适与刘子薄游白下,朝游夕述,不揆固陋,将续著《南京景物略》,已属草矣。博物吾友,尚其助予。”[22]26
清之两京是仿明制形成的,但盛京实则留都,实际功能有所不足,难以形成真正的两京主体制。因此,虽清代文献中出现的“两京”字样最多,但多指代周、唐、明等前代之两京。当然,清承汉制,对自己的龙兴之地颇为重视,所以,文献中谈及本朝两京也是有的。如乾隆《帝都篇》中有“幅员本朝大无外,丕基式廓连两京”[23]1之句。
总之,通过考察“两京”一词在古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关于“两京”的观念,经历了西周、两汉等朝的酝酿,唐宋两朝之渐趋成熟,以及明清之际的继承延续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大部分时间,是中国古人关于都城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郑天挺:《明清的“两京”》,详见《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中平:《明代两京制度下的南京》,《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3 期;林旭:《从两京一都制到两京制——明朝曲折的定都之路》,《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6 期。②也有学者认为炎黄时期和夏朝已有陪都,笔者未采信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