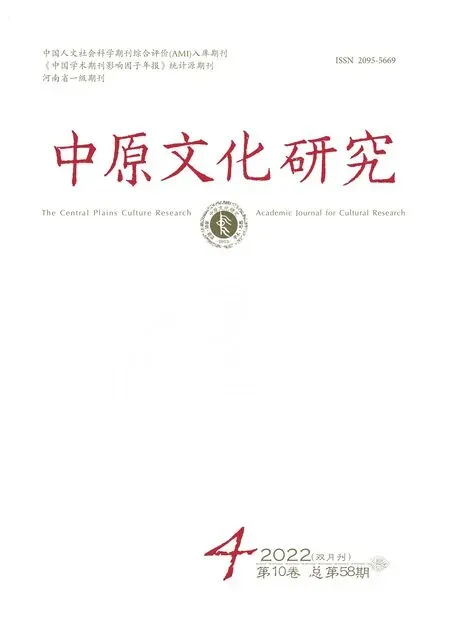“拆洗王介甫”:王安石形象传播与刻板化略论
冯 伟
在文学视域下,王安石形象有一个独立嬗变的过程。以往学界主要关注其在文本中的静态特点,而忽视其嬗变的动态过程。相关考察已体现出鲜明的坐标意义,并形成一条清晰的“墨线”:两宋文人笔记—元代史传文学与俗文学—明代白话小说。就整体演变轨迹而言,这条“墨线”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足以反映出该形象跨文体、跨语境的宏观走向。然而,如以之为基准线,进行动态考察,短板又是显而易见的:坐标点的特征过于清晰,会在相当程度上消解我们对坐标间隔的关注,而留有较多讨论空白。简言之,王安石形象的演变以这条“墨线”为参照系,却不以之为根本线索,这归根结底是一个考察人物形象转变内因,而非呈现面貌的问题。本文拟从文本传播和创作语境的视角对宋、元、明三代文人“拆洗王介甫”①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两宋:王安石形象的两极化
两宋时期的王安石书写绝大多数集中于文人笔记中,周勋初先生编《宋人轶事汇编》共收录王安石相关条目近240 条,涵盖近90 种书目②。需要补充的是:第一,笔记作者捃摭、转引前人旧说者大有其在,严格来说,王安石的出场频率实际上远高于此。但我们所关注的是王安石形象的整体呈现特点,因此重复内容暂不纳入统计。第二,除去作者捃摭、转引的情况,宋代以降新出的笔记仅10 条左右,可见该形象并未得到更为纵深和广泛的建构,两宋精英文人已经完成了王安石形象在自身语境内的基本定型。颇为有趣的是,两宋文人笔记中的王安石形象特点驳杂,其内部明显存在一个渐趋稳定的转变过程。
实际上,这个过程并不复杂,却颇为有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王安石变法后不久,相关文人笔记显著增多,且呈现出褒贬鲜明的两极化趋势。对王安石文学形象的负面塑造主要集中于其妖魔化的出身,以及在政治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专横倨傲、投机媚上、奸邪诡诈等负面性格。如:
昔与小王先生者言:“王舒公介甫何至于无后?”小王先生曰:“介甫,上天之野狐也。又安得有后?”[1]1191
介甫请并京师行陕西所铸折二钱,既而宗室及诸军不乐,有怨言,上闻之,以问介甫,欲罢之,介甫怒曰:“朝廷每举一事,定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为?”退,遂移疾,卧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乃起。[1]1205
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1]1201
王介甫诡诈不通外除。[1]1195
相比之下,对王安石形象进行正面刻画的笔记内容不再聚焦于其政治行迹,而是延展至日常生活轶事,涵盖其思想、文才、性格、教养等诸多方面,对其才能的记述尤多。如:
王荆公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1]1214
王荆公退居金陵,结茅钟山下,策杖入村落。有老氓张姓,最稔熟。公每步至其门,即呼“张公”,张应声呼“相公”。一日,公忽大咍曰:“我作宰相许时,止与汝一字不同耳!”[1]1215
(王安石)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贽及程试文有美者,读一周辄成诵在口,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见者皆伏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日辄尽为诸弟所费用,家道屡空,不一问。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诎。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1]1229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话语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并不存在明显的“错时”区间,在几乎共时演进的过程中,享有相对独立的叙述语境,此中缘由颇耐人寻味。笔者以为,问题的答案最终还是要回到对笔记书写者的观照上。
经考察,以鲜明褒贬动机建构王安石形象的内容多集中于以下三部作品中:司马光《涑水记闻》(褒0 贬9 中1)、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褒4 贬22 中3)、陆游《老学庵笔记》(褒7 贬0 中0)。前二者呈现出相当强烈的“贬王”倾向,在此后20 余种作品的74 条不相重复的负面叙述中,仅此二书所录就已近半数,且绝大部分内容剑指王安石的政治行迹,极具针对性。陆游《老学庵笔记》则以纯粹的正面立场为王安石作翻案文章,但又有意规避了与王安石相关的政治内容,多以品学、轶事为常。
这本质上是书写者的有意为之。一方面,司马光与邵伯温基于政治立场对王安石的文学形象展开负面建构,主要原因是熙宁变法背景下的党派争逐。正如范立舟所言:“攻之者亦难以对王安石的人格与事业进行全面否定,盖因其品行之洁,文辞之高,经术通透,思想精深,皆是客观的事实而难以以敌对立场全部加以抹灭,因而就发生针对其个人形象的抹黑与诋毁声浪,试图以此来降低王安石对宋神宗与朝廷的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以及有效地削减王安石的政治地位。”[2]72上述二人对王安石形象的有意诋毁,与其说是一种文学阐释,毋宁视之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产物。另一方面,陆游对王安石形象的建构,亦非依循客观立场,而是缘于家族私交的影响,有意为其翻案③。这本质上都是囿于自身立场的片面书写。可见,两宋文人笔记中王安石形象的两极化呈现,实际上是不同立场下,不同书写者合力建构的结果。
其二,南宋后期,王安石形象的两极化趋势迅速式微,诸多精英文人已经基本脱离对其过度褒贬的偏仄语境,转而以一种颇具意趣的笔触,多以欣赏的态度记录王安石的各类轶事。如:
田承君云:“顷为金陵酒官,有王荆公处老兵,时来沽酒,必问公之动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书院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人莫测其意。[1]1217
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1]1232
这两则材料都隐约流露出颇为积极的叙写态度,后者甚至将前人用以妖魔化王安石的说辞加以调侃,可见此时的文人群体对王安石形象的接受态度已渐趋平和。一个关键的原因或许在于:熙宁变法的影响式微,王安石的政治标签逐渐淡出文人视野,变法之前“品行之高洁,文辞之高妙,思想之精深”的王安石形象得以重新占据话语上风。换言之,绝大部分书写者在本质上是精英文人士大夫,其创作在学养、文化、审美上都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根本性的文人特质。基于这种立场,司马光、邵伯温对王安石集中、片面甚至失真的书写便很难在主流文人话语中持续发酵,而陆游笔下的“文人”王安石则更符合他们的审美品格。
以上,不难看出两宋时期精英文人语境内王安石形象的两极化呈现。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其拥有完全独立的传播系统,若我们尝试沿着那条“墨线”进入元代史传文学与俗文学语境,则会发现更多腾挪的空间。
二、元代:王安石形象的世俗化
史传文学与俗文学语境中的王安石形象更像是精英文人话语上行和下移的结果。或者说,由宋入元,以文人笔记为中心,该形象完成了向上至史传文学、向下至民间俗文学的双向分流。
先来看史传文学中的王安石形象,这里以《宋史·王安石传》为典型。被学者普遍诟病的是,元修《宋史》过程中大量引用、套用前朝已有的文献资料……并没有在广泛涉猎宋朝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3]101。当然,就史的层面而言,其成书固然相当不严谨,但我们恰恰可以基于这种“不严谨”,反向考察《宋史·王安石传》在引用已有文献资料时,对王安石形象做出的接受与转变。
《宋史·王安石传》的内容可以简单归纳为:王安石才学俱佳、淡泊名利、心怀抱负、崇尚法治、变法举措及后世评价六个部分④。以熙宁变法为节点,对王安石形象做出了由褒到贬的处理。《宋史·王安石传》用相当长的篇幅详论八处变法内容,皆以贬斥态度展开,而此前都是对王安石的褒扬,此后更引苏洵作《辨奸论》之事与朱熹的论断予以评论性叙述干预。当然,从史家传统而言,《宋史·王安石传》表面上不讳褒贬的记录风格看似符合一贯的史传书写传统,但若具体到细节(如篇幅比例、论述详略等),则不难发现其对王安石的书写态度偏于消极。此外,有学者指出,《宋史·王安石传》是元朝的撰修官们以宋人洪迈等人编撰的《四朝国史》为底本撰写而成的……《四朝国史》对于王安石变法内容的选取及态度大部分都源于南宋初重修的《神宗实录》。《神宗实录》是在高宗的授意下编撰的,而高宗本人倾向于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党人,并将北宋灭亡的罪因归结于王安石变法[3]101。李心传亦称:“先臣修《神宗实录》,首尾在院,用功颇多。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4]1487我们同样不能忽视,除去朱熹对王安石的评价,《宋史·王安石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能在两宋笔记中找到“本事”,这本身即证明了该书与两宋文人笔记之间的因袭痕迹。综上,不难想见《宋史·王安石传》对王安石形象书写的随意、片面与污名化倾向。
相较于文人笔记,史传显然更具有普遍而严肃的说服力,当王安石的负面形象由笔记进入史传语境后,其性质也会从“街头巷语”变为“史家实录”。正如清人蔡上翔所言:“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5]586可以说,王安石形象由宋入元、由笔记入正史的过程,也是其进一步刻板化的过程。
再来看俗文学中的王安石形象,这里以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拗相公》,元杂剧《花间四友东坡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为例。《大宋宣和遗事》简述王安石怒贬韩琦、实行变法,并分别受到同僚、弟安国、子王雱斥责变法误国事,并穿插其性格执拗、任人唯亲等性格特点,由于篇幅散碎,在此不多作赘述。相比之下,其余三者对王安石形象的刻画颇为规整。如:
王安石执拗,民间称为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贬;说便,便加升擢。凡说新法便民者,都是谄佞辈所为。其实害民非浅。[6]63
今有王安石在朝,当权乱政,特举青苗一事。我想这青苗一出,万民不胜其苦,为害无穷。小官屡次移书谏阻,因此王安石与俺为仇。[7]卷三,349
我有一策,要行青苗助役于民间。在朝诸官,多言不便;独翰林学士苏轼,十分与我不合。昨日上疏,说我奸邪,蠹政害民。我欲报复。况主上素重其才,难以轻去;且本官志大言浮,离经叛道,见新法之行,往往行诺吟咏。我已着御史李定等劾他赋诗讪谤,必致主上震怒。置之死地,亦何难哉![7]卷三,212
不难发现,类似内容在两宋笔记中屡见不鲜。然而,笔记中王安石形象的褒贬弹性与建构张力,在由文人话语向民间语境渗透的过程中,已经被过滤成了相当纯粹的负面表述,从而进一步推动其负面形象的刻板化。另外,《拗相公》已经初步体现出了王安石形象跳出民间语境向精英文人语境回流的尝试,后文详述。
当然,《宋史·王安石传》对俗文学的创作是否产生关键影响我们无从得知,但无论从时间线索,还是从书写内容来看,民间俗文学对两宋笔记的接受更为明显。《宋史·王安石传》聚焦于变法本身,而元代俗文学则以变法为中心,延展至对王安石负面形象的全方位展示。如果说《宋史·王安石传》是基于史家立场,更倾向于“政治叙事”,那么民间俗文学如此书写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缘于受众审美品格,民间叙事有选择地接纳了上层语境中符合自身话语特点与审美倾向的部分,略去了市井群众认知中晦涩枯燥的符合文人审美品位的部分。话本、元杂剧的主要叙事目的,是凭借搬演符合大众群体审美趣味的故事,提高表现效果,不断扩大受众群体,这种叙事诉求使王安石故事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王安石是上层统治阶级与精英文人的代表,与一般大众的文化地位存在巨大差距,如赵毓龙先生所言:“正是文化地位的巨大差距,留下了大片想象腾挪的空间……尽管很难在故事中寻见自身的文学投影,市民们却依旧乐道皇帝与各色文臣武将之间的故事,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本朝的,不管是悲剧性的,还是充满喜剧意味的,都能引起受众的极大兴趣。”[8]20大众在接受此类故事时,很难具备客观的道德评判态度。换言之,民间叙述道德认知的根本特点在于更具强烈的主观性、浓烈的情感性及通俗的文学性。市井群众很难也无心掌握全面的材料,冷静、辩证、客观地审视所述事件,只得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以及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仅从被抽象、简化的事件中,习惯性地按照“二元对立”的道德标准来认知历史人物。这种叙述逻辑,本身就容易使王安石形象道德化、刻板化。
其二,从社会心理层面看,王安石形象在民间叙述语境中的污名化和刻板化,亦有其必然原因。且不论荆公改革之得失,改革这一行为本身,就会为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这难免会给民众造成诸多心理活动,而一旦事情未向好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些心理活动就会不可避免地滋生负面色彩,如焦虑、恐慌、愤怒等。为消解这些负面情绪,市井群众会在潜意识里启动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代替或转移自己内心的不安。这种心理模式被当下研究者称为“替罪”⑤。以此反观该形象在民间叙述中的污名化与刻板化,便可做出合理推测:社会群众正是将王安石充当了负面心理活动的“替罪羊”,通过满足对其丑化、鞭挞的幻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内心负面情绪的消解。
可以说,两宋精英文人话语在上行至史传文学,下移至民间俗文学语境的过程中,形成了符号学意义上的分流路径。尽管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丑化王安石形象的刻板化趋势,但由于叙事立场与审美品格的不同,二者书写风格与叙事倾向差异明显。更为有趣的是,随着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兴起,宋元俗文学语境中已经基本定型的王安石形象,又体现出由民间话语体系向精英文人语境的回流。
三、明代:王安石形象的文人化
需要指出,这种附着于拟话本的回流是很不彻底的。一方面,拟话本的创作主体已经由服务于“场上”表演的书会才人,转变为学养深厚的下层文人,其难以恪守民间话语的创作标准,而有意无意地将自身思想、立场、观点携带进编创活动中。同时,在重新加工宋元旧本的同时,他们也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旧本的故事底色,那么旧本及其相关的民间思维特征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另一方面,考虑到拟话本的文体特质,即使是那些文人创作的作品,文人编创时也势必固守宋元话本的传统接受程式,将市井大众作为理想读者,其中的文人意趣也难免受到世俗性的制约、浸染和消解。严格来说,明代拟话本中的王安石形象更像是文人个体意识与市民集体意识的合流。
这里,我们且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下简称“三言”)和《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二拍”)中王安石形象的相关部分,整理如下(见表1):
如上,改编旧本而来的上述作品与宋元俗文学一脉相承,皆明显保留了对王安石形象的负面书写态度,而文人创作作品对此则显得兴趣寥寥。另外,我们还能发现更多有趣的现象:第一,《警世通言》中的两篇都以王安石为主要人物铺叙故事,二者一褒一贬,能够较为直观地体现出文人个体与市民群体的话语差异;第二,“三言”收录相关篇目四则,仅一则为略写,尽管“二拍”中只有一则是以铺垫式话语带过的篇目,但仍是以民间“变法害民”的既有印象为基础的。那么结合二书的成书性质和编创本位,不难发现,王安石形象确实存在由民间语境回流至精英文人话语的过程,并被进一步解构、稳定为以“害民”为内核的单薄的形象符号。
当然,从“二拍”对王安石形象的处理,大可预见王安石形象发展的刻板化,同时不能忽略,在该形象的发展由元代俗文学到明代拟话本演变的过程中,“三言”处在关键位置。在这种视域下,“三言”比“二拍”显然更具考察意义。这里,我们以《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为典型个案,略作申论。
严格来说,该篇对王安石“劣迹”的刻画与旧本《拗相公》并无根本差异,皆沿袭“变法害民”的基本底色,阐述王安石的种种“罪状”,拟话本主要在叙述语言、场景和情节的细节处加以修改,使故事更为饱满和生动。就性格特征而言,这里的“王安石”被有意放大了“性格执拗”的标签,但“执拗”的否定程度并不高。相比之下,全书类似于心胸狭窄、任用奸佞等更具贬斥性的评价则很少出现,其本身即代表创作主体在批评态度上的转变。
不唯如此,一个看似有意思的悖论在于:全文主要以民间对王安石变法的怨言为线索展开叙事,却有不少为王安石翻案的痕迹,颇令人疑惑。如:
恁般一个好人,未能大用,不尽其才,却到也留名于后世。[9]20
(安石)吩咐:“我虽宰相,今已挂冠而归……恐惊动所在官府,前来迎送……骚扰居民不便。若是泄露风声,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诈害民财。若吾知之,必皆重责。”[9]22
该文将叙事重点放在民间对变法和王安石其人的申斥上,而每每被责骂时,文中一贯位高权重、养尊处优的王安石却无丝毫气愤,反而是羞愧和自责。也就是说,在叙事者的言说语境里,王安石顶多算是无心做错事,且真心知错的人。这不仅不“拗”,还通过明显的愧疚、懊悔和补过心理,创造了“洗白”的空间和可能。
笔者以为,“隐含作者”理论或可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可行的答案。简言之,在叙事文本中,“叙事者”掌握架构文本的绝对权力,会在某种叙事目的或道德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对故事进行取舍与构造,具有不可靠性;而“隐含作者”是读者根据文本推演出来的能体现真实叙事态度的道德与价值体系⑥。具体到该故事,虽有相当篇幅对王安石的负面形象大书特书,却也有多处表现王安石淡泊、清俭、爱民的言行。毋宁说这是“叙事者”与“隐含作者”角逐下的结果,“叙事者”热衷于塑造王安石的负面形象,而“隐含作者”却为读者模塑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好官”。基于此,便可作出进一步推论:文人在改编该故事时,为了迎合受众的审美趋向与接受习惯,创造了一个“贬王”形象,却无法完全跳出自身语境,多次在有意无意中就“隐含作者”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反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等文人创作作品,创作者彻底摆脱旧本桎梏,可以全方位介入叙事,王安石形象便自然而然地“高大”起来了。由此,“三言”的重要转关位置已不言而喻,其不仅是王安石形象演进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更是市民集体意识与文人个体意识合流的关键所在。
综上,王安石形象自两宋笔记生成后,又在有元一代产生了上至史传文学,下至民间俗文学的分流,后通过拟话本实现由民间话语向精英文人语境的回流,最终在市民集体意识与文人个体意识的“合谋”下,成为一个刻板化的形象符号。当然,这并不代表王安石形象演化进程的停滞,如晚清、近代乃至现代、当代亦不乏对王安石做出新解读者。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形象的建构与阐释,限于篇幅,笔者拟以他文另述。另外,还需要注意到,王安石形象的发展过程只是众多历史人物由现实进入文学,继而在跨文本、跨语境的过程中不断演进、发展的一例,仍有较多同类情况亟待考察。这里,可以将“王安石形象”作为一个经典个案来看。
注释
①据《石林燕语》记载:“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折洗’。”后注曰:“番下当有脱字。号折洗,王介甫云作一句读。”参见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4 页。《宋人轶事汇编》转引《石林燕语》记作:“号‘拆洗王介甫’云。”参见周勋初主编:《宋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7 页。这里,笔者借用“拆洗王介甫”语为题,意在更为形象地阐明本文论述目的,与原文无关。②参见周勋初主编:《宋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③参见邢蕊杰:《王安石形象“翻案”与士人历史意识书写——以陆游〈老学庵笔记〉为中心》,《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 期。④参见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90-2693 页。⑤参见勒内·吉拉尔著,冯寿农译:《替罪羊》,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⑥参见杰拉德·普林斯著,乔国强、李孝弟译:《叙事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