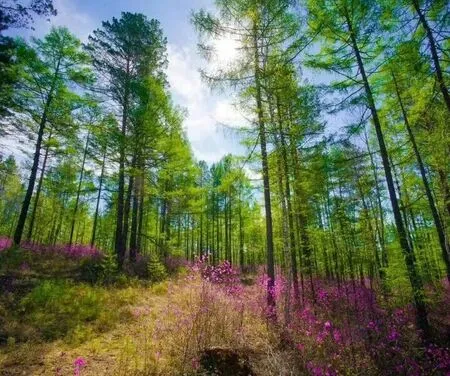关于朝阳地区森林生态系统脆弱不稳定原因刍议
黄冬梅
(辽宁努鲁儿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辽阳 朝阳 122000)
朝阳地区位于辽宁省西部,辖7个市(县级)、县、区,林业用地面积107.52万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78.01万公顷,占林业用地面积的72.55%,森林覆盖率35.6%。虽然从有林地面积和森林覆盖率上,相对于省内其他地区及全省平均水平并不是很低,但朝阳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并不是以地带性树种为主体所构成的多世代、多树种、多层次、多种类、多效益、多功能的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因此仍是十分脆弱、不稳定。抗干扰自我护卫保持原有状态的能力较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自然环境能力、调节气候等生态贡献能力较低。笔者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和工作实际认为森林生态系统脆弱不稳定的产生原因有以下几种。
1 森林生态系统脆弱不稳定产生原因
1.1 历史性严重破坏
大量的考古资料、历史档案资料证实,朝阳地区是从森林遍野、山清水秀、荫蔽千里、风调雨顺的生态环境系统平衡之地,逐步走向生态环境恶化的。
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古代的辽西朝阳地区,植被茂密,各类蕨类植物、裸子植物种类丰富。曹正尧、吴舜卿等学者在1997年的《科学通报》中提到:“辽西出土了大量的植物化石,其中以银杏类和松柏类为主,以及少量的真蕨类和苏铁类植物,进而证明了辽西地区为各类生物提供了是以生存的空间。”
据《朝阳县志》记载,在秦代,朝阳地区畜牧、农业等多种经济相结合,自然资源利用合理,林业树种以刺槐、柳树、松柏类为主;隋唐时期,朝阳地区土地肥沃,山林中野兽成群,生态环境良好。
辽金元时期,契丹、女贞、蒙古族等各族人民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农则农,生态环境保持了相对稳定。
明朝时,草原和森林植被总体良好,但朝阳南部地区,因人口剧增和战争破坏,森林资源出现匮乏,木贵如玉。
明末清初年间,辽西地区爆发了改变中国历史的几场战事,对朝阳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重的影响。在《燕行日记》中描述,辽西朝阳地区“不见一石一木,野天相间,禽鸟亦断,而目极黄沙”。森林资源遭到了大肆砍伐、毁林开荒等严重破坏,原始植被屡遭摧残,基本枯竭。新中国成立前夕,建平县有林面积仅0.9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不足2%。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有林地面积仅为0.48万公顷,凌源市林木资源所剩无几。解放初期调查,朝阳地区森林覆盖率只有3.4%。森林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导致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森林损毁退化为灌丛、灌草丛、草丛,使温带大陆性气候的朝阳地区演变成了干旱半干旱区,岩石裸露、丘陵荒秃、土壤干旱贫瘠、肥力弱差,十年九旱,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自我培育和更新调整困难。
1.2 人工设计造林毁林
新中国成立后,朝阳人民齐心协力“植树造林,绿化朝阳”,尤其是1981年胡耀邦总书记视察朝阳以来,林业建设步伐加快,坚持辽宁省政府提出的“以水土保持为中心,造林种草为重点,实行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方针,先后实施了“2732”“西辽河防护林”“世行项目”“德援”“三北防护林”“两退一围”“大禹杯竞赛”等国际、国家、辽宁省、朝阳市大型生态建设工程。使有林地面积由解放初不足7万公顷发展到近8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增加了9.47倍。
但由于当时造林追求成活率,快速成林,使得山地绿化工程产生造林中毁林弊端。山地造林前整地是造林环节中最为重要的工程,要求横山定点、株行距准确,栽植坑横平竖直、整齐划一、长宽深一致。整地坑基本分为穴状坑、鱼鳞坑、竹节壕和水平沟4种。以竹节壕和鱼鳞坑为例,阐述造林毁林之严重性。竹节壕整地:横山定点,株行距1米×2米,规格为坑长150厘米、宽70厘米、深40厘米、拦水埂高30厘米、拦水埂宽约20厘米,1公顷设计2505个竹节壕(每个竹节壕栽2株)。按此计算,平均每个竹节壕破坏面1.35平方米,每公顷破坏面达到3381.75平方米,占每公顷的33.82%。鱼鳞坑整地:横山定点,株行距1米×2米,规格为坑长80厘米、宽60厘米、深40厘米、埂高30厘米,1公顷设计5000个鱼鳞坑。同理计算,每坑破坏面0.48平方米,每公顷破坏面2400平方米,占每公顷的24.00%。竹节壕整地和鱼鳞坑整地平均1公顷破坏面0.29公顷。以朝阳市几大工程造林面积和假设使用竹节壕整地、鱼鳞坑整地各1/2面积计算,造林整地产生的破坏面达97916.76 公顷,近10万公顷。
森林是由乔木植物、灌木植物、草本植物、活地被植物、层间植物、野生动物、微生物等所构成,它是一个生态系统,各成分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只有相辅相成,才会系统稳定不脆弱,发挥最大效能。为栽造乔木而毁幼树、灌木和草本,不仅对正在恢复原生植被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产生较大影响,对造林后形成稳定森林生态系统也十分困难。
1.3 纯林设计不尽合理
据部分县市区林业和草原局、林场、各乡镇林业站林业档案资料,朝阳地区85%以上的森林面积为人工林,基本设计格局为阴坡油松、阳坡刺槐或沙棘。以朝阳县朝阳林场2011年森林二类调查数据为例:森林总面积由1968年的108公顷增加到现在的16188.5公顷,其中人工林面积由零面积增加到14879.4公顷,占91.91%;在人工林面积中,油松纯林9430.7公顷,占人工林面积的63.38%;刺槐纯林5199公顷,占34.94%,两树种面积合计占98.32%;其他纯林和混交林面积为249.7公顷,占1.68%。营造人工纯林只是绿化上的暂时达标,不能顺其自然形成森林生态系统和带来较大的生态效益,并会造成日后经营管理上的众多“麻烦”和经济投入。
营造纯林有违森林价值理念:森林的价值不仅限于木材本身,还有多重的经济价值、生物学—生态学价值和社会—精神价值。对于朝阳地区来说森林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改善环境及气候等生态效益价值更为重要。有研究表明,保护土壤不受侵蚀不能单靠树木本身,而应该更多地依赖于林下的枯枝落叶层、腐殖质层以及低矮的下木灌草或苔藓层的立体庇护。在坡地上,单纯的林木不足以有效防止表土的流失。再者,依据以前和目前朝阳气候条件和山地丘陵的立地条件,想要长成“参天大树”只是美好的梦想。20世纪60年代所营造的油松林,树高1.5~4.5米,很大一部分已成为低产林、小老树,朝阳县朝阳林场油松人工林每亩平均蓄积量只有1.05立方米。
营造纯林有害生物发生猖獗:朝阳地区平均每年发生松毛虫灾害5130公顷,发生杨干象灾害4261公顷,杨树肿茎溃疡病等病害发生面积2879公顷,本世纪初以前,建平县有700公顷世界面积最大的沙棘人工连片林,但由于沙棘木蠹蛾的危害而大面积死亡。造成有害生物发生猖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面积的连片纯林,这正是在造林植树中忽视的一个生态学原理——“单一性导致脆弱性”所起的作用。
1.4 封育措施实施较晚和不全面
封山育林措施提出的较早,但实施的较晚,进入80年代,国有林地封育较严格,集体林地乱砍盗伐、毁林开荒、刨根割柴、牛羊啃食等现象屡见不鲜。还有的乡村将山林分包到户,不但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反而造成“自家山随便砍柴开荒”无人管现象,如此等对森林的破坏非常严重。同时还有“只封林不封荒”现象,严重影响所谓“荒山”的森林植被恢复。
2 建议
2.1 小坑整地雨季造林
依据朝阳地区丘陵山地的立地条件,造林前需要整地挖坑,可根据实际立地情况区别坑的大小,尽量小坑整地,同时建议采取雨季造林根部覆膜的方式进行造林,如此可减少原植被破坏和提高成活保存率。
2.2 引入本土天然植物种类
据史料记载,朝阳地区原始林是由油松、蒙古栎、辽东栎、山杨、侧柏等为主体的构成的森林,所以可营造原始多树种混交林,同时引入其他森林生物品种,如早花忍冬、锦带花、三裂绣线菊、玉竹、沙参等。注入自然原始成分,去除以往人工林的一些弊病,发挥出天然林的一些优势,形成一种人工—天然复合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