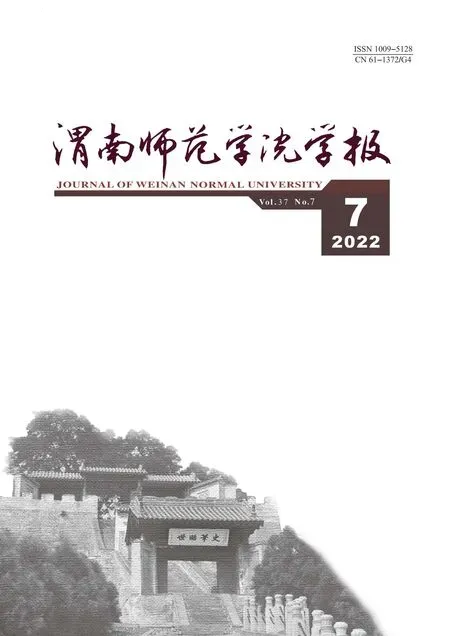《说文统释序》探赜
陶 生 魁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714099)
钱大昭(1744—1813),清代学术大师钱大昕之弟,字晦之,号竹庐,又号可庐,嘉定(今上海嘉定)人。大昭博贯经史,著书满架,在经学、史学、金石学、小学、目录学等学术领域均有创建。
《说文统释》是其未刊之作,手稿至今未见,所幸有《说文统释序》传世,凡三万余言,遂成为了解《说文统释》内容、体例与著述宗旨的重要文献。王欣夫先生因此推测:“一序已洋洋三四万言,全书可与同时段、桂两家鼎足焉。”[1]158事实亦当如此。
面谢启昆(1737—1802)是钱大昭同时代的人,其《小学考》卷十云:“《说文解字》之学,今日为盛,就所知者有三人焉:一为金坛段玉裁若膺,著《说文解字读》三十卷;一为嘉定钱大昭晦之,著《说文统释》六十卷……皆积数十年精力为之。”[2]166但对此序,笔者心中有疑,古人撰序虽有长短,但三四万言的长序实不多见,而且此序几乎通篇都在讨论文字演变和使用中的失误,只在结尾处说明《说文统释》撰作的“十条”宗旨,不大像是《说文统释》的序。查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发现钱大昭名下尚有《说文分类榷失》《说文叙义考释》等著作,心向往焉。所幸《说文分类榷失》已经收在李运富先生主编的《清代〈说文解字〉研究稿抄本丛刊》第一册中[3]153-422,与前序比照,略见端倪。因不揣谫陋,求教于方家。
一、《说文分类榷失》与《说文统释自序》
《说文分类榷失》,凡六卷,正文前有钱氏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亲撰的《〈说文分类榷失〉序》,序下钤有“北京图书馆”“刘之泗”两方印。序前有藏书小记,字体为行草书,云:“余家藏《说文叙义考释》二册,郭氏刻《说文统释叙》一卷,并与是书略同,此殆摘其注文而分类者,疑初稿也。公鲁识。甲子十二月初五夜。”记文中的“公鲁”为清末著名藏书家刘世珩(1875—1926)之子刘之泗(1902—1937)的字,甲子年即1924年。“郭氏”系指郭传璞,清代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刻有《金峨山馆丛书》十二种,其中有《说文统释序》一卷,小记所言郭氏刻本即是此本。
郭氏刻本锓于光绪壬午(1882),前有郭传璞《重刊〈说文统释序〉序》,正文部分称《说文统释序》为《说文统释自序》。云“重刊”者,因《说文统释序》尚有乾隆年间亳州何天衢校刊本,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有著录,今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三册中。比较何、郭氏刊本,可见其内容尽同,而郭氏刊本错误较少。
刘之泗小记所言《说文叙义考释》,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有著录,今藏国家图书馆,笔者未见。小记怀疑《说文分类榷失》是《说文统释序》的初稿,有待进一步核证。今就何校本《说文统释序》与写本《说文分类榷失》从形式、内容、行文、结构等方面作进一步比照、考察,以见二者之关系。
(一)形式比较
《说文分类榷失》包含序、目录、正文三个部分,而《说文统释序》不分卷次,是一个整体。为了便于后文比照,兹录《〈说文分类榷失〉序》全文如下:
上古结绳,文明之耑未启,中古早字,书契之象聿宣。虫鸟书鸟迹,茫昧难知,岣嵝琱戈,纷纭莫辨。迨八体既分,而六书益盛,视犬画狗而形举,见禾中人而自成。王居门为闰,一贯三为王,重夕为多,重日为叠,古人制作,具有精微,后学迂疏,渐滋谬误。洎乎隶、楷日兴,以致篆、籀失讲。沿及陈、隋,迄夫唐、宋,六经家自为说,三史人自为书,讨论愈疏,乖戾益甚。总而计之,其失盖三十有四焉,特分类举之,成为六卷,命名“榷失”,以纠谬也。夫读书以通经为本,通经以识字为先,经学必资于小学,故郑司农深通六经而先明训诂,小学必资于经学,故许祭酒专精六书而并研经义,学者以此为指归,则通儒无难于及矣。乾隆五十有五年十月可庐居士钱大昭晦之甫序于得自怡斋。
由此序可以了解作者撰作《说文分类榷失》,目的在于总结历代文字之失,是正谬误,从而识字通经。序言之后是目录,见表1。
此目录之后就是《说文分类榷失》的正文。可见《说文分类榷失》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而《说文统释序》只是《说文统释》的序文,所以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

表1 说文分类榷失目录
(二)内容比较
如果以《榷失》为参照,《统释序》在内容方面有三个特点:
其一,内容较《榷失》大幅增加。《统释序》几乎涵盖了《榷失》序言与正文的所有内容,且有大幅增加。《榷失》将古今文字失误分为34类,《统释序》与之相同,但每类之下内容的多寡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增加了举证内容。比如“穿凿之失”类,《榷失》的举证有57例,而《统释序》有67例;“借用之失”类,《榷失》的举证74例,《统释序》则有75例;“方音之失”类,《榷失》的举证有15例,而《统释序》中举证则有130余例,内容大幅扩充。
二是增加了注释文字。如“穿凿之失”类的“天为二人连”条,《榷失》注释作:
唐冯翊《桂苑丛谈》云:太保令狐相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睹前壁题云:“一人堂堂,两曜重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双勾两日全。”众莫能辨,独班支使云:一人“大”字;二曜日月,“明”字也;尺一者寸土,“寺”字也;点去冰旁,“水”字也;二人相连,“天”字也;不欠一边,“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燃,“无(無)”字也;添却双勾两日全,“比”字也。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無)比”乎,众人皆悦服。
《统释序》引《桂苑丛谈》至“比字也”即止,但接着云:又,宋欧阳修《归田录》:“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于文为‘二人’以为‘二人圣’者,悦太后尔。”又如“声急之失”类“不敢言敢”条,《榷失》注:庄公二十二年《左传》“敢辱高位以速官谤”杜注“敢,不敢也”。《统释序》注:庄公二十二年《左传》“敢辱高位”、昭公二年“敢辱大馆”并注云“敢,不敢也”;《仪礼·聘礼》辞曰“非礼也敢”,注“敢言不敢也”。可见,《统释序》增补了新的内容,因此它的内容要比《榷失》多出许多。
另外,《榷失》在第六卷“声缓之失”举证后就结束全书,而《统释序》则接着阐述了自己对“六书”的观点,仅在结尾处阐发了《说文统释》的著述体例。为了后文比较,亦照录如下:
求制作之大意,五百四十部已得其全,考经典之微言,九千三百文必穷其奥。大昭识惭梼昧,学愧豹窥,积二纪之勤劬,殚一生精力,覃思研精,欣然有得,探赜索引,卓尔未由。撰集斯编,聊附述者,定名《统释》,以示来兹。盖卷有六十,例成二五焉:一曰疏证以佐古义(1)每例之下原有小字注释,文繁,故删之。,二曰音切以复古音,三曰考异以复古本,四曰辨俗以正讹字,五曰通义以明互借,六曰从母以明孳乳,七曰别体以广异义,八曰正讹以订刊误,九曰崇古以知古字,十曰补字以免漏落。今于许氏本注升为大字,而仍用楷书,许氏本皆以大字作篆文,而本注则用楷书,学者便之,今仍其例。于自撰《统释》附于分行而比诸经疏。大抵读书以通经为本,通经以识字为先,经学必资于小学。故郑司农深通六经而先明训诂,小学必资于经学,故许祭酒专精六书而并研经义。苟学者以此为指归,则通儒无难于及矣。乾隆五十有五年十月可庐居士钱大昭书于得自怡斋。
其二,《统释序》在内容先后上作了一些调整。如在“方音之失”中,《榷失》第五例为“同一语而有东齐、中齐、杂齐、右齐、南楚、西楚、关东西、山东西、赵、魏、周、晋、秦、陇、宋郑、韩、燕、代、鲁、卫、陈、邠、陶、越、蜀汉、东瓯、西瓯、毒屋黄石、野、朝鲜之不同”,“本是一音而有青、徐、兖、冀、扬、衡、幽、凉、荆、雍、梁、益、豫州,嵩岳、海岱、大野、平原、徐土邳圻、东海、河济、河阴、河汾、河北(2)按,“河北”当作“河内”。、江淮、江湘、江沔、江湖、淮汭、淮汝、汝颍、沅湘、周洛、冽水、泲水攸异”(注云:以上二条并见扬雄《别国方言》),《统释序》将以上内容调整为“方音之失”的第一条,用意很明显,就是让它“总领下文”。还有一个细节很重要,在扬雄《方言》中没有“右齐”这个名称,抄本有误,《统释序》作“齐右”,显然是纠正了《榷失》的错误。
其三,在文字上作了加工润色。如“隐谜之失”类中的“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条,《榷失》注云:
《会稽典录》云:蔡邕题《曹娥碑》后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黄绢,色丝也,“色丝”为“绝”:幼妇,少女也,“少女”为妙;外孙,女之子也,“女子”为“好”,“齑臼”受辛是“辞(辤)”。大昭按,此乃好事者托名蔡邕为之,伯喈不如是之不识字也。
而《统释序》作:
《后汉书·曹娥传》注引晋虞豫《会稽典录》:曹娥碑成,蔡邕题八字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世说新语》:杨修见八字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之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辤)”。
比较可见,二注有三点不同。首先,东晋虞豫的《会稽典录》在《隋书·经籍志》有著录,但亡佚已久,《榷失》直接引用佚书会引起误解,《统释序》指出《会稽典录》的内容出自李贤的《后汉书注》,这样就严谨多了;其次,“黄绢,色丝也”等语非出《会稽典录》,若据《榷失》,可能误解文句出处,进而可能导致误解文意。《统释序》在“黄绢,色丝也”上增补书名、人名就消除了歧义,避免了误解;第三,《榷失》有“大昭按”,《统释序》则无,揣摩抄本大昭按语可知,钱氏正是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与“黄绢,色丝也”等语连读而误解了文意。试想,就算是“好事者托名蔡邕”,“蔡邕”岂能不知自己所题何意。大昭按语于理不通,所以《统释序》删掉了。
(三)行文比较
《榷失》与《统释序》在行文方面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对34类文字之失的表述里。《榷失》的表述方式是“类”下“举例—注释”,而《统释序》是“举例—注释”再归类,以“此某某之失也”作结。行文的差异体现了《榷失》与《统释序》性质的不同,《榷失》是完整的专著,而《统释序》是序文。《统释序》改变《榷失》的表述方式,便于行文。
(四)结构比较
前文已述,《榷失》包括序言、目录、正文三个部分,《统释序》则是一个整体,以《榷失》作参照比较,可见《统释序》是把《榷失》原序(3)《说文统释序》采录了《说文分类榷失序》的内容,文字稍有出入。分成了两个部分与《榷失》正文重新作了整合。具体说就是将“盖三十有四焉”之前的内容(见前文)改为《统释序》的开头,“夫读书以通经为本”之后的内容改成《统释序》的结尾,《榷失》正文部分则经补充润色后作为《统释序》的主体部分,补充的内容即前文所述“六书”的内容和《说文统释》“十例”;另外,为了与上文意气相连,还把“夫”改成了“大抵”。原序中“特分类举之,成为六卷,名为《榷失》,以纠缪也”的话则删掉了,因为它与《说文统释》的著作旨意不同。
经过重新整合,《说文分类榷失》就成了《说文统释序》。不过,从文脉言,原序浑然一体,《统释序》则不免有割裂之感;而且将《榷失》的正文作为《说文统释》序的一部分与《统释序》所述《说文统释》的“十例”也不尽相符。谢启昆的《小学考》初稿成书于清嘉庆三年夏(1798),其中盛赞《说文统释》的学术成就,还节录了《说文统释自序》,这也可能是《说文统释自序》最早的引文,可惜只有“十例”(见前文)。谢氏应当见过《说文统释自序》,却对“文字之失”的内容只字未提,是有意不提还是他所见到的序与今传《说文统释序》本来就有不同,现在就不得而知了。
通过以上比照,可以认定《统释序》是《榷失》的增改本。不过,也许有人会问,如果以《统释序》为参照,会不会得出《榷失》是《统释序》简编本的结论呢?当然不会。文献的生成总是后出转精,《榷失》虽然是完整的著作,但在内容上比《统释序》粗疏,因此对《榷失》有误的地方《统释序》作了修正,语焉不详的地方《统释序》作了加工润色。试再举二例,“袭谬之失”类下《榷失》举证有57例,末了云“此类概见郭仲恕说”,《统释序》则作“以上经典多误,自蛇虫至此,并见《佩觿》”,郭仲恕的著作不止一种,前者语焉不详,指明《佩觿》就明确了。再如“贪多之失”类下的“颜元孙未知符融之符”条,《榷失》注:“符融其先,鲁顷公孙,仕秦为符玺郎,以符为氏。苻坚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谶文改为苻。《干禄字书》云‘从艸者为姓,从竹者为印’,盖未知符融之姓符也。”《统释序》注:“《通志·氏族略》:‘符氏,姬姓,鲁顷公之孙公雅为秦符节令,因以为氏。后汉有符融。’又《晋书·前秦载记》:‘苻洪初姓蒲,其孙坚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干禄字书》谓‘从艸者为姓,从竹者为印’,盖未知符融之姓从竹也。”
不言而喻,《统释序》注释更加规范明确,简编本当不致把原本正确的改错,原本明朗的改含糊。因此认为《榷失》是《统释序》的简编本是不合常理的。至此可以明确,《榷失》是《统释序》的增改本。
赘述一句,《〈说文分类榷失〉序》的落款为“乾隆五十有五年十月,可庐居士钱大昭晦之甫序于得自怡斋”,《统释序》落款作“乾隆五十有五年十月,可庐居士钱大昭书于得自怡斋”,时间相同,不能以此确定先后。但《榷失》较《统释序》多一个“甫”字,耐人寻味,也似乎透露出一点信息。
二、《说文统释序》的价值
既然《统释序》是《榷失》的增改本,便可以当作专书来研究。根据前文分析,《统释序》的内容上可以分成三部分,即“历代文字之失”“钱氏六书解”“《说文统释》十例”。从分量而言,“历代文字之失”是其主体,下面讨论《统释序》的价值就以此为基础。《统释序》是从“失”的视角归纳问题、解决问题的,反映出作者的学术思想与见解。站在今人的视角反观,可以揭示《统释序》的价值。为了叙述方便,这里姑且从文字学、训诂学、文献学三个角度作以论述。
(一)文字学价值
《统释序》中涉及文字学的内容很多,以“隶变之失”与“借用之失”最为典型,从中可见其“隶变”观和“借用”观。
1.“隶变”观
“隶变是对汉字书写性能的改革”[4]72,汉字由篆文变为隶书,改变了缓慢徐舒的书写节奏,汉字形体与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笃信《说文》者没有看到它的历史必然与功绩,而认为隶变破坏了汉字的形体,造成了汉字书写的混乱,因而对隶变十分排斥,钱大昭专门列出“隶变之失”一类,也反映了他对隶变的态度。为了纠正隶变的失误,他考察了四十余种的汉碑和两种魏碑,还对一些“俗字”形体作了归纳总结。这些考察是以“纠谬”为目的的,但客观上对于我们认识汉字形体演变,识别文献讹误是很有帮助的。从“隶变之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钱氏关于隶书改变篆文形体方式的归纳总结。(4)参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88页。
(1)改曲线、弧线为直线、折线
(2)偏旁混同、省并

(3)偏旁变形
(4)简化
2.“借用”观
文字借用是很复杂的汉字使用现象,李运富先生说:“所谓借用是将汉字形体当做语音符号去记录与该字形体无关但音同音近的语词。”[5]201钱大昭归纳的“借用之失”即属于这种情况。他在“借用之失”下列举了74组音同音近的字,并根据《说文解字》一一辨证,这对于认识本字、本义是很有价值的。但钱氏奉《说文》为圭臬,指出“借用之失”的目的是恢复“本字”,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比如“次叙为序”条作者根据《说文》指出“叙”的本义为“次第”,“序”的本义为“东西墙”,因此认为把“次叙”的“叙”用作“序”是失误。今天看来钱氏的认识有些局限,因为词义是不断发展的,《说文》的解释可以作为区别本义的依据,但文献用字不一定都用本义。事实上,“序”亦有“次序”的意思,《广雅·释诂》:“序,次也。”《仪礼·乡饮酒》:“众宾序升,即席。”郑玄注:“序,次也。”
又如“童仆为僮”条作者认为把“奴仆”的“童”用作“未冠”的“僮”也是失误,以《说文》为据当然没有错,但文献中这两个字的职能有混乱的情形,《干禄字书》“童僮”条说:“上幼童,下僮仆。古则反是,今则不同。”所说与《说文》训解正好相反。段玉裁“童”下注云:“今人童仆字作僮,以此为僮子字,盖经典皆汉以后所改。”
钱大昭把“隶变”“借用”归纳为文字之失,客观上对于我们认识隶变与文字借用是有价值的。钱氏在认识上有偏颇,在思想上有崇古倾向,代表了当时一批学者的认识和思想,因而也具有文字学史价值。
(二)训诂学价值
在训诂学方面,《统释序》质疑前人训释与音读,推陈出新,富有新意。下面从“质疑前人训释”“是正前人音读”两个方面分别举例。
1.质疑前人训释
(1)训坛为除地封土(歧义之失)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舍不为坛”《释文》“服虔本作禅”,《正义》“王肃云:除地坦坦者;服虔云:除地为禅”。大昭按:《祭法》注“封土曰坛,除地曰禅”,《土部》“坛,祭坛场也;禅,野土也”,二字义本各别,《左传》义应作“禅”而字作“坛”。杜氏不得其解而云“封土为坛”。言“封土”则合于坛字之义,言“除地”则不悖先儒之解,巧为弥逢,适形其谬耳。
按:钱大昭认为杜预将“坛”训为“封土”是错误的,指出《左传》“舍不为坛”中“坛”字服虔本作“禅”训作“除地”,王肃本作“坛”解作“除地坦坦”,而《说文》中两字训解不同,认为字当作“坛”而义当按“禅”解释。按钱氏所说,即是把“禅”视作本字,把“坛”视作借字。考《周礼·夏官·大司马》“暴内陵外则坛之”郑玄注:“读如同禅之禅。郑司农云:读从惮之以威之惮。书亦或为禅。”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坛,音禅”,《集韵》“坛,或作禅”,则两个字确可通用。
(2)训貳为貳心则疑(歧义之失)
《释诂》“貳,疑也”,大昭按:“貳”当作“忒”。《诗·曹风·鸤鸠》“其仪不忒”传“忒,疑也”,疏以为《释诂》文,然则“貳”字乃“”字也。,他得切,《易·豫卦》“四时不忒”《释文》“京作”。《管子》“如四时之不”,《礼·月令》“宿难不贷”“毋有差贷”“无或差貨”皆“”字之误也。《释文》于《月令篇》并存忒、二两音,非是。《贝部》“貳,副益也;贷,施也;,从人求物也”,《心部》“忒,更也;,失常也”,忒之讹为以音同,又讹为贷以形似贷,又讹为貳亦以形似古貳字。如《诗》“无貳尔心”、《书》“任贤无貳”、《孟子》“妖寿不貳”古训皆不云“疑”,则“貳”当为“忒”明矣。
按:这条训诂,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士貳其行”“其仪不忒”条下有详细考证,结论云:“盖忒,本字也;,借字也;貳,讹字也。”《经义述闻》初刊于嘉庆二年(1797),后于钱氏考证数年,比较两家考释,《统释序》虽草创而不失精审,《述闻》则后出而转精,可谓异曲同工。
2.是正前人音读
(1)舍人不知旭、勗同声(音释之失)
《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旭日始旦”《释文》:“旭,许玉切。《说文》读若好,《字林》呼老反。”《释训》“旭旭、跻跻,憍也”《释文》“旭旭,谢峤许玉切,郭璞呼老切”,疏引《诗经·小雅·伯巷》“骄人好好”为证。《日部》“旭,从日九声,读若勗”,《广雅》“旭,明也”,曹宪音勗,又忽老反。大昭按:旭字从九得声,故读若好,陆氏所见《说文》是唐初善本,古者九、好同声,故萧、肴、豪、尤古每通用,或读若勗、,莫候切,与懋勉之“懋”同字,仍与九声相近,曹宪、吕忱、郭璞俱不误读。自谢峤、陆德明、徐铉之徒,但知旭、勗之为许玉切,而许老之音,几无视之者,赖有《说文》《字林》《广雅》之音可以正其误。
按:旭字古音在晓纽觉部,好字晓纽幽部,晓纽双声,幽觉对转。钱氏认为“旭”字旧音读若好,当可信。《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旭日始旦”《释文》云:“旭,《说文》读若好。”
(2)陶甄之甄为之人切(音释之失)
《鸡肋编》:“甄彻大观中登进士第,时林摅为同知枢密院,当唱名,读甄为‘坚’音,上以为‘真’音。摅辨不孙,呼彻问之,则从帝所呼,摅遂以不识字见黜。”按《吴志》,孙坚屯军甄官井得传国玺,坚以甄与己名音协,以为受命之符,是三国以前未有音之人切者。孙权继位,尊坚为武烈皇帝,诸儒为吴讳,转而音真,其苻秦世祖坚、隋高祖坚皆因吴音,暂避其讳。
按:钱氏推测“甄”字在三国以前不读“之人切”,当是。《史记·孟尝君列传》“复与梁惠王会甄”《集解》“甄,音绢”,“绢”古音在见纽元部,“坚”在见纽真部,读音十分接近,所以孙坚认为与自己的名字“音协”。《左传·庄公十四年》“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释文》云:“鄄,音绢。甄,音绢,又音真;或音旃,又举然切;或作鄄。”可见到唐代“甄”又有“真”音。又,《左传·文公十年》“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杜预注“将猎,故置二左司马”,《释文》云:“甄,吉然切。”《慧琳音义》卷十二“甄叔迦”注:“甄,音坚。”仍读“坚”音,则林摅呼为“坚”亦为有据。
《统释序》不是训诂学的专门之作,词义考释、音读考证的内容在其中分量不大,但从以上几例也可见钱氏考释功力。
(三)文献学价值
《统释序》的文献学价值体现在两个方向,一是文献资料价值,一是文献校勘价值。在资料方面,《统释序》辑录的语言文字资料很丰富,比如,在“方音之失”里,作者从《方言》、《尔雅注》、《周礼疏》、《淮南子》注、《尔雅注》、《汉书注》、《公羊传》注、《战国策》、《史记集解》、《史记索隐》等文献中辑录了130余条方言资料,可以作为汉语方言词汇、语音、词义研究的语料。而“穿凿之失”“隐谜之失”“避嫌之失”“妄改之失”的内容可以直接作为汉字文化学研究的资料。
《统释序》的文献校勘价值首先在于其中大量的举证本身就是校勘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同时又可作为其他文献校勘的佐证资料。如在“传写之失”“颠倒之失”“坏字之失”“俗别之失”中指出的文字之误,都有较高的校勘参考价值。举例以见之。
1.《尚书》以荥为荧(传写之失)
《禹贡》“入于河溢为荥”,大昭按:“荥”当从“火”。《周礼·职方氏》:“荥洛。”《春秋》中《闵公十二年》《宣公十二年》和《左传》及后序诸文“荥泽”《释文》皆作“荧”;隐公元年《释文》且云:“荧阳或作荥,非。”梁顾野王《玉篇》荧字下亦云:“荧阳县。”《汉韩勅修孔庙后碑》:“河南荧阳。”《太尉刘宽碑》阴:“河南荧阳。”《晋右将军郑烈碑》:“荧阳将封人。”唐卢藏用撰书《纪信碑》:“困高祖于荧阳。”字皆从“火”,此其证也。又按,《左传·闵公二年》“荧泽”,唐《开成石经》及宋岳珂《刊正三传》并从“火”。
按:此例属于形近而讹,钱大昭以传世文献与碑刻文献为据证明了《尚书·禹贡》“入于河溢为荥”之“荥”字为“荧”字形讹,可为通例。
2.三十本世(离析之失)
元申屠駉重摹秦《会稽刻石跋》:“《史记》‘攸长’作‘修长’,‘世’字作‘三十’,今俱依石刻。”大昭按:秦《泰山》《会稽》《峄山》刻石诸种,其文皆以四字为句,《会稽刻石》“世有七年”正与上下句法相合,《史记》作“三十有七年”,是以五字为句矣,此传写者误析为二字。
按:此例属于一字讹为两字之误,钱氏进一步从字数、句法上作出判断,很有参考价值。相同的例子还有“孙心本(逊)(离析之失)”等。
3.讋乃龍言(合并之失)
《史记·赵世家》“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战国策》作“触讋”,盖误合“龙(龍)言”为一字。
按:此例属于两字讹为一字,钱氏指出“讋”为“龙(龍)言”误合,虽没有做进一步考证,然亦见其敏锐。王念孙《读书杂志》对此有详细辨证,学界多有引述,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书》证明“龙(龍)言”是对的。王氏《战国策杂志》后序作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冬,晚于《统释序》二十余年。
清末学者朱一新曾盛赞钱氏兄弟的校雠学,云:“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而国朝诸儒,则于此独有偏胜,其风盛于乾嘉以后。其最精者,若高邮王氏父子之于经,嘉定钱氏兄弟之于史,皆淩跨前人。”[6]75大昭的校雠之学于此可见一斑。
三、《说文统释序》的不足之处
前文我们肯定了《统释序》的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块完璧。《统释序》作为《榷失》的增改本,其不足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复古倾向
《统释序》把历代文字之失归纳为三十四类,目的在于“纠谬”,而“失”是以《说文解字》为尺度衡量的。汉字规范是必要的,然而“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7]10,要求后人遵守1600年前的规范,必然违背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而走向复古。“隶变”是汉字形体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次伟大改革,钱氏归纳为“隶变之失”,欲使它回到“隶变”之前的状态,反映出他认识的局限性,在现实中也难以行得通。另外,文字借用是解决汉语与汉字矛盾的权宜之计,汉字一经借用又具有一定的约定俗成性。在“借用之失”中钱氏指出了“借用”中的很多本字,这是很有价值的,但把“借用”视为失误且一律用本字则大可不必。
(二)排斥俗体
“俗体”是就“正体”而言的,笃信《说文》的人以《说文》为“正体”,而常把《说文》以外的字视为俗体加以排斥。在《统释序》中径以“俗”字分类的有“随俗之失”“俗别之失”,其他涉及“俗体”的分类还有“委巷之失”“新附之失”等。裘锡圭先生说:“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中,俗体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候,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8]49可见,钱大昭排斥俗体字,也反映出他认识的局限性。
四、结语
综上,《说文统释序》是对《说文分类榷失》的增订与改编。它勾稽文献,辑录文字之失,分门别类,注释考证,客观上展现了汉字在演变和使用过程中的各种现象,为我们认识汉字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由于受正俗观念的影响,作者排斥俗体,在文字观上也带有明显的复古倾向。指出《统释序》的不足不是为了苛责古人,而是为了正确认识它、更好地利用它。《统释序》辑录的各类资料及其考证的成果在文字学、训诂学、文献学等方面的价值终是瑕不掩瑜。
-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基于OBE理念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