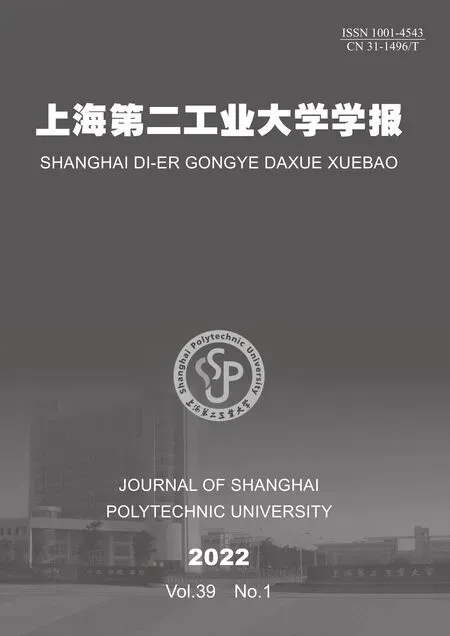从中国楹联的译介看概念翻译中的图式影响
王世钰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209)
0 引言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下学界讨论的焦点。而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译介活动密不可分。无论精神文化产品是否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呈现,为了异域接受的顺利,往往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译介。中国精神文化产品的外译开始得较早。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已经开始了有史记载的外译活动。这一时期的北天竺僧人曾将中国僧人所著之《大乘章义》译成梵文, 此后至隋文帝时期,又有其余佛教典籍的外译,及至唐朝贞观年间请玄奘翻译《老子》,标志着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典籍开始了外译活动[1]。中国精神文化产品的外译范围也较广,比如,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是我国首次系统全面地进行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工作,其中涵盖了诸多中华精神文明产品的精华,囊括了诗词曲赋、小说散文、戏剧、古代文论、兵法脉学等。
楹联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介绍给异域文化。“楹联” 亦称 “楹贴” “对子”, 是 “悬挂或粘贴在壁间柱上的联语”, 要求“对偶工整, 平仄协调”,也即“对联”[2]。楹联虽然具有较强的中国文化特色,但却具有普适性意义,其缘起与人类对世界的基本认知一致。楹联源于人们对最古老的宇宙状态的感性认知。从盘古将混沌世界一分为二以及古老的阴阳概念可以看出,从一生成二,这是人们对世界最原初的秩序的看法。康福尔德指出,一分为二是一种生殖状态, 实际上是最古老的秩序, 混沌(chaos)这个词一开始并非指无秩序状态,而是指一种裂开的大缝隙[3]。因此, 楹联是世界最基本的秩序的体现,代表了普适的思想。此外,楹联也与现代多种媒介形式结合,在新时代重焕生机。20 世纪90年代,楹联与影视形式结合,产生了不少与楹联相关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在影视作品中也时常可见楹联踪迹。在近几年兴起的一些年轻人高度聚集的文化社区和视频网站中,围绕楹联展开的传作,获得广泛欢迎。有代表性的如B 站的《课堂请勿对对子》系列情景剧,完全围绕楹联展开,每一集几乎没有与楹联无关的镜头或元素,部分剧集已获千万次点播,点赞、转发者亦不计其数。因此,楹联在当代社会与通俗娱乐形式结合,自身焕发新的生机,更应成为文化传播的对象。
但是,中国楹联的概念在被英译到西方时,译者在图式的影响下将楹联的英译与西方国家中已有的概念混淆。楹联概念和内容从被译入英文开始, 就受到了西方以自身文化为模型的削足适履式翻译的文化过滤、重塑与驯服,致使其后的概念误传。那么,这类概念误传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该如何对待这类翻译中的概念误传?本文将以楹联这一概念的译介为切入点,探讨翻译中的图式影响及应对策略。
1 图式理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
“图式(schema)”是“指个人用来组织知识并指导认知过程和行为的心理结构。人们根据共同的元素和特征,使用图式对物体和事件进行分类,从而解释和预测世界”。在具体实践中, 简而言之, 它可以使有机体“在部分信息结构的基础上感知一个事件或对象的全貌” (见Britannica Encyclopedia 官方网站中对词条“schema(cognitive)”的解释)。比如对于“树”这样的对象,人们根据过往自己看到过的树,在头脑里组构树的属性,可以推断出树有根、树枝、叶子等。简言之,“图式”就是有机体过往的相关经验和认知。
康德首先将“图式”(学界有时译为“图型”) 用来讨论系统性结构以及如何在其影响下阐释世界[4]。康德将“把知性概念在其运用中限制于其上的感性的这种形式的和纯粹的条件称为这个知性概念的图型,而把知性对这些图型的处理方式称之为纯粹知性的图型法[5-6]。”McVee 等[7]认为康德所说的图式“介于外部世界和内部心理结构之间; 图式是一个透镜,它既塑造了经验,也被经验所塑造。”Heidegger 等[8]则认为图式学说意义重大,“仅仅提到关于图式学说的章节在推理阶段的顺序中的系统地位,就可以看出《纯粹理性批判》的这11 页必须构成整个庞大作品的核心。”
此后,图式理论在认知心理领域的研究被运用到了实践中。Bartlett 等[9]提出“记忆图式理论”,认为过去的感应或经验会对人施加影响,在这些影响方式中, 图式界定是最根本的方式。Reed[10]认为,巴特莱特的图式研究推动了认知心理学的发展,经由 Minsky (1975) 和 Rumelhart (1980) 的倡导, 图式开始被认为是认知心理学的“基石”,“图式”的概念趋于清晰化,图式被定义为“阐释感官数据、从记忆中检索信息、组织行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此外,图式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构”,再用具体情境中的细节属性来填充这个框架结构。
图式理论的应用较为广泛,20 世纪末期开始被运用至翻译研究中。Bell[11]认为, 图式“以自上而下的方向运作,帮助我们解释来自世界的自下而上的信息流”。Hatim 等[12]则指出, 译者自己的社会认知系统(如译者的文化和价值观、信仰等系统)在为翻译决策提供信息方面起重要作用。实际上这里的译者的社会认知系统就包含译者头脑中的图式。Gutt[13]提到影响译者的“社会惯例”实际上也是译者所受的图式影响。Kafipour 等[14]则调查了图式理论在翻译中的作用。也有学者从知识图式的角度来探讨其在翻译方面所起的作用[15]。
总体而言,图式理论在翻译研究逐渐得到重视,但对译者在进行跨文化、跨语言翻译时受到的图式影响的研究则较少。而中国的楹联在译介过程中被强制纳入西方的“对句(couplet)”概念,使其概念在翻译后被消解,这背后的图式影响值得深思。
2 楹联概念译介中的图式影响
“楹联” 在英语中常常被翻译成 couplet,或Chinese couplet, antithetical couplet, contrapuntal couplet, 其他译法也偶见于论文或著作中,如doorway couplet[16], matched couplet[17], parallel couplet[18],poetic couplet[19],rhymed couplet[20-21],red paper couplet[22], auspicious couplet[23]等, 楹联中的常用的一类“春联” 则被译为spring couplet。虽然译文中的couplet 前有明确的限定语,以表明其与英语世界中的couplet 的区别,但这些译文的中心词大多是couplet, 目标语的读者见到用couplet 来翻译的“楹联” 的概念时, 往往将couplet 代入来辅助理解楹联。但这样的译法却是译者受到图式影响的结果:译者直接用已知的couplet 的概念来替代了汉语中与之形式差别较大的楹联。译者在将楹联译为couplet 之前, 对couplet 定义及用法的掌握及其所有的知识图式,当其遇到楹联这样表面与couplet 都具有双行特征的异域概念时,便不假思索套用现成的couplet 的概念来替代了楹联,而罔顾两者的显著差别。
couplet 和“楹联”差别较大。Britannica 对couplet 的解释揭示出couplet 的两个主要特征:其一,通常尾词押韵(偶有例外); 其二, 连续两行, 或于两行末皆有停顿(每行末皆有标点), 或于首行末无停顿(首行末无标点,首句意思延续到第2 行)。couplet 有两种: 封闭的和开放的。开放式couplet 虽形式为两行, 但却是连续的句子; 封闭式couplet 的两行句子是完整独立的句子,假如封闭式对句使用了五步抑扬格,则可进一步细化为heroic couplet(英雄对句)。比如以下法语写就的对句, 尾词分别押œur(liqueur,cœur 虽拼写有异,但 eur,œur 读音相同), `ere 韵:

此处从上往下每两行为一则对句, 故有两则对句。楹联与此则完全不同。如前所述,楹联的两个要素分别为:对偶工整, 平仄协调。因此,虽然couplet和楹联用现代方式书写看似均为双行,但除此之外截然不同,couplet 通常尾词押韵, 而楹联则不需要;首行末无停顿的couplet,首行意思延续到第2 行,可以跨行接续,而楹联则并非如此,楹联讲究上下联对应字词的词性相同、字词对偶、平仄协调、语法结构相同,而couplet 则不必考虑这些因素。此外,楹联还有横批, 尽管在一些情境中经常被省略。更重要的区别是, 楹联常常在实际生活中用于祝愿、祈福等,而couplet 则无此功能。通常楹联的上下联同样位置处不可以重复用字,但couplet 中的两行文字相同位置经常出现重复的词句, 比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8 首中的名句: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and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and this give life to thee.
因此,couplet 和楹联二者除了“双行”这一书写特征外, 全然不同,但在翻译“楹联”这一客观对象时,却使用了couplet 的概念图式来限定。阐释的偏差导致理解的偏差, 概念的误传也由此产生。维基百科在antithetical couplet 的词条下则直接用couplet来指涉“楹联”: “在中国诗歌中,楹联(couplet,简体字: 楹联;繁体字: 對聯;拼音:du`ıli´an)是一对遵守一定规则的诗歌(poetry)。”虽然在下文中, 维基百科一一列举了楹联的组成要素,且特别提到“第1 行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仄调,这就迫使第2 行的最后一个字必须是平调”,但接下来所举的例句却仍旧违反了这条规律,列举的8 个楹联例句中,有两则将上下联颠倒。可以看出,楹联这一外来文体,其特殊之处并未触发译者认知的敏感性,其形式的独特性消解于译者所认知的couplet 之中。
在实际使用中, 人们为方便起见, 又直接用couplet 来替代以couplet 为中心词的词组(如Chinese couplet 或 antithetical couplet 等) 来指涉楹联。Bischoff 就用couplet 来指涉《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句式[24]。霍克斯直接用couplet 来指涉文中的楹联[25]。沙伯理同样也用couplet来指代楹联[26]。这类在翻译时用本土文化中的现象强行替代异域中的概念的行为,显然模糊了目标语群体对楹联的理解。
3 概念译介中图式影响的表现
楹联的概念被翻译成与其迥异的couplet,且在西方被普遍当作是与楹联内容形式迥异的couplet,是译者受到过往经验和知识的图式影响的典型表现,这一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对楹联这一概念的译介中, 也存在于对异域概念的译介中。译者或异域概念的接受者也常常借助已知图式来了解这些对其而言是新事物的异域概念,并将这些新概念削足适履,而他们所借助的图式往往是自身的经验,或本土看似与外来概念有相似特征的客观对象。这种图式的改造常常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根据已知概念为其他文化中的新事物翻译或命名;其二,根据已知事实来理解、臆测或改造新事物。
根据已知概念为其他文化中的新事物翻译或命名是人们对异文化中新概念的理解缘起,往往使后来者也根据图式影响下的翻译或命名来理解新事物,与真实的异域概念产生一定的偏离。比如,古代阿拉伯和波斯作家西将中国古代的皇帝译为“巴格布尔(Baghbugh 或Baghb´ugh、Baghb´ur、Faghf´ur)”,意为“神之子”;《地理志》作者埃德里西笔下的中国皇帝也沿用此名[27], 这就是根据彼时阿拉伯地区的文化图式影响来给异域的新事物命名,与楹联的译介方法相同。对物品的命名亦如此, 比如提及中国产丝绸等商货时, 其中一种名为“哈扎尔秦尼(Ghaz´arsini)” 的物品远近闻名, 裕尔坦言在阿拉伯字典中未查到此字, 猜测可能和gauze (薄纱) 一词有关[28]。埃德里西对中国事物的命名显然受到其本国语言和文化的图式影响,而裕尔对埃德里西所造词语的猜测也受到裕尔本国(英国)语言的图式影响。与此相似,“菠萝(pineapple,字面意思为松树苹果)”一词源于“松果 (pine cones)”,因为第 1 批发现“菠萝” 的欧洲人觉得这种水果长得像他们自己国家生长的松果,且属于一种水果,因此用“pine”和众所周知的水果“apple”来命名这种他们眼中的新事物[28]。
人们也时常根据已知事实来理解、想象甚至改造异域中的新概念。中国的丝绸传入西方伊始, 西方人对这种昂贵的进口物品感到陌生,诗人维吉尔则讲述了赛里斯国(古代中国的别称)如何从森林的树叶中提取出绒毛织就丝绸的,诗人们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认识,尽管在此期间,商人们已经获得比较确切的信息,知道丝绸是该国农人饲养的某种昆虫生产的原料,但理性客观的学者如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等,仍沿用了维吉尔等诗人的臆测[29]。诗人维吉尔对丝绸来历的判断是基于自身的经验,树叶上的绒毛是他在自己已知的客观经验中能够提取出来、与精致而脆弱的丝织品联系起来的客观对象,因此用来解释他不曾了解的丝绸,这就是用旧有的内容图式来框定新的内容。已知事实也会被作为参照来理解新事物。再如,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时, 常常用自己文化中的认知图式来阐释、理解中国的文化,他在提及中国一条道路的来历时说,据传2000 年前,有个山西男子刘韩信力大无穷,曾被猛虎吞食,活着出来了,作者认为这一经历“跟尤纳斯/Jonas/遭遇相似”, 之后因为战胜了水龙, 所以他“成为赫克力斯一类的人物”[30]。李希霍芬对中国的神话传说非常陌生,因此在获悉了他的传说故事后,用他熟悉的希腊神话中的相似情节来辅助理解。参照物是客观的,但是使用参照物进行理解的施动者则具有主观倾向。阿列克谢耶夫这样描写1907年北京城外的道路: “一头模样丑陋但很强壮的毛驴驮着我出了北京城。宽阔的大路变成了羊肠小道,与我们俄罗斯的道路相差无几[31]。”对本国道路的了解成为了理解彼时北京城的道路的参照,同样也是固有的已知图式在认识异域的客观对象时施加的影响。
4 概念翻译中图式影响的本质及应对之策
图式影响下的阐释和翻译往往与异域概念原本的“真” 有误差。对不同文化中的不同概念用自己文化中的概念来阐释,实则是在不知不觉中对异文化中概念的斩头去尾式处理。而当人们将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运用到理解和翻译其他文化中的新事物时,译文的所指与源语中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产生偏差,一如楹联和couplet 的概念则相去甚远。译文形成后,后之译者和接收者也会受到具有优先权的译文影响, 即便认识到此前译文的谬误, 也常常不愿意对其进行修正[32]。如同“楹联就是couplet”的概念流传一样,谬误随着不实的概念开始新一轮传播。意大利天文学家西亚帕瑞利于1877 年绘制火星地图时,将该星球表面的明暗区域分别描述为“海洋(seas)”和“大陆(continents)”。由于望远镜产生的错觉(当时不为人知),他还标出了他认为是“海峡(channels)”的东西,并以意大利语“canali”标注。他的同行则将其误译为“运河(canals)”,美国天文学家珀西瓦尔-洛厄尔据此深信火星上运河存在, 甚至绘制了火星上数以百计的运河地图,而且还撰写了3 本著作,皆与这一主题相关[33]。西亚帕瑞利对火星上明暗区域的命名就是根据自己的已知经验来对其进行猜测、(与地球上的事物)比对和命名的,但即便是望远镜产生的错觉在当时还不为人知,天文学家将未知的明暗区域命名为“海洋(seas)”和“大陆(continents)” 也有不妥, 因为缺少足够清晰的证据,加之地球上海洋和大陆的概念带给天文学家的认知图式,使得天文学家在见到其他星球上某种程度与海洋和大陆有相似性的客观对象时,忽略了更多的相异性和新的可能性,摒弃了科学的理性,服从于不可靠的经验,使命名与事实产生了第1 次偏差;而其同行也在潜意识中用自己语言(英语)中的图式来理解意大利语:看到意大利语中的canali 时直接将其与英语中的canals 对应,这就又与事实产生了第2 次偏差;其后的同行则一错再错,使得后来者对火星上的物质构成以及对火星在望远镜下明暗物体的理解谬误更深。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尼采所谓的“认识”的过程,“把某种陌生的东西归结为某种已知的、熟悉的东西”[34]。
因此在概念的翻译中应当力避图式影响带来的概念翻译偏差。如何尽可能减少图式影响对概念翻译带来的消极遮蔽?以楹联的翻译为例, 如若译者初次接触这一概念,应尽量避免将其与本土文化中的概念杂糅, 甚至等同, 而应多给予其独立的地位,比如将楹联或可直接音译为“duilian”或“yinglian”,以彰显其与本土文体、概念的区别。再如前文所提及的意大利语“canali”,如若直接将其迁移至目标语中, 必然不会产生概念的误传。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一客观事实,要彻底避免概念翻译中的图式影响暂时还有难度,因为图式认知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世界的本能之一。对外来概念没有充分了解之时,根据自身所处的文化对其进行框定、臆测, 这是人们在对待未知事物时常用的处理方式, “在我们的思想中, 基本特征是将新材料嵌入旧模式(相当于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强使新材料与旧材料如出一辙[35]。”对一切新事物的了解都是借助已知经验进行的。即便是被认为是神圣不可擅改的异域形象,流传至本土也会被本土人士根据自己的认知图式来改造。比如释迦牟尼的佛像流传至中国,中国的云冈石窟将其塑造为与南北朝鲜卑族帝王相似的头像,将其打造成双耳垂肩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并不符合释迦摩尼佛像的原型; 犍陀罗的佛头造像则具有希腊的波浪卷发,嘴唇较薄,佛身衣褶和希腊雕像中的褶皱一样,因为亚历山大东征至今天的巴基斯坦附近,这一带的人们根据希腊人的特征来塑造了对他们而言是新事物的释迦牟尼像;而笈多佛像头上则是右旋螺发,嘴唇宽厚,这都是不同地方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已有认知图式将异域的释迦牟尼庄严宝象改造的结果。因此, 如何客观地看待图式对翻译带来的影响,如何尽力稀释其消极影响,也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5 结 语
译者在翻译楹联等概念时受到已有的经验图式影响,导致概念的误传和误译,这是图式对概念翻译产生消极影响的典型案例。在对其他异域概念的翻译中,译者亦常借助已知图式为其他文化中的新事物翻译或命名、理解、臆测甚或改造异域中对其而言新颖的概念。而这一图式影响下的阐释和翻译往往与异域概念原本的“真”存在误差。因此在概念的翻译中应当力避图式影响带来的概念翻译偏差,在无法找到对等概念时,不妨直接将原文迁移或使用目标语的形式改写后迁移至目标语中,以唤起目标语接受者对其特殊性的敏感性。当然, 图式认知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世界的惯习之一,要在概念翻译时完全避免这类影响不无困难,但是认识到这一点,并思考如何最大化地减少因为图式影响带给目标语受众对源语概念认知的却是值得翻译实践和理论工作者继续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