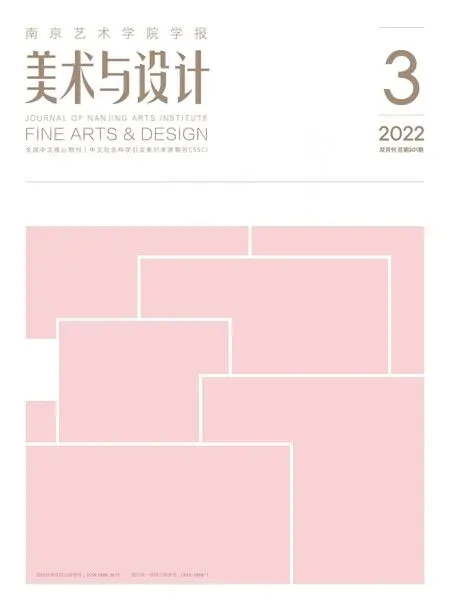从公开到神圣:20世纪之交的清宫“扮装像”
董丽慧(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扮装像(costume portrait)曾在18世纪中国宫廷出现过一次制作高峰,以雍正、乾隆二位帝王的此类肖像为最。有学者认为,这一扮装像在清宫的“突然出现”,与当时中西文化交流、及国际外交活动影响有关;而以往研究也已对这些帝王扮装像或用于稳固多民族国家政权、或隐喻皇权合法传承、或对自我观看和形塑的制作意图进行了多方面的挖掘,其中亦论及18世纪西洋文化、外交及传教士美术对清宫视觉艺术创新的影响。到18世纪末,尚未即位的嘉庆皇帝也试图延续这一扮装像的制作传统,命人绘制了着汉服画像,置身竹林中效仿七贤隐逸。然而,嘉庆扮装像仅止于汉服装束,无论在形象的丰富程度,还是展示方式的多样性上,都已远不如前。进入19世纪,更是再无男性统治者扮装像问世。
直至20世纪之交,这个一度中断的18世纪清宫传统,才在女性统治者慈禧手中再度出新,在制作媒材、传播展陈方式及神化形象的塑造上均开千年未有之先河,呈现出形态、服饰、布景多样,且涉及更多肖像制作媒介、面对更多观众、经由更多现代方式展示和传播、跨多种宗教和文化的新一代中国统治者形象。目前笔者已知现存慈禧扮装肖像绘画五种、照片两组,包括故宫藏《慈禧佛装像》和《慈禧观音像轴》传统行乐图立轴两种(以《慈禧观音像轴》为母本的另一件“双胞胎”作品曾现身2015年苏富比秋季拍卖),故宫藏《慈禧扮观音、李莲英扮韦陀》册页一卷,故宫藏心经手卷一册(扉页有慈禧扮观音画像),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艺术博物馆(Chazen Museum of Art)藏《慈禧扮观音》绢本设色画像立轴一幅(1909年彩色刊印于赫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清宫回忆录的扉页)。此外,还有戴五佛冠舞台布景照片一组(四种七张)、中海乘船照片一组(五种七张),这两组照片和底片藏于故宫博物院和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Sackler)。
本文即以20世纪之交这批清宫扮装像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传播方式、制作媒介、塑造的宗教形象三个角度入手,剖析光绪末年、尤其是清末新政中,清宫扮装像的一系列变化——它们不仅是对18世纪清帝王肖像这一制作传统的重新激活,更因慈禧本人作为女性摄政的身份,加之这些扮装像与宫内宫外、国内国际、宗教政治等诸种语境的共生、对抗和互渗,见证并参与着晚清末年的内政与外交,影响着此后中国统治者形象的制作、传播和相关宗教领域内圣像的塑造。
一、从宫廷走向公众
现存故宫博物院和近年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两幅相似的《慈禧观音像》“双胞胎”立轴,以寿石、寿桃、灵芝、蝴蝶等图像符号传达出庆贺耄耋之寿的含义,都将这组慈禧扮观音像的绘制年代指向1904年前后,慈禧筹备七十大寿之时。画中慈禧着蓝色竹叶纹样观音袍,置身竹石间,头戴五佛冠,五佛冠两侧垂下绘有寿桃和万字纹图案的饰带,肩披莲花状珍珠云肩,交脚坐于五彩莲花蒲团上,手抚寿字形山石,画面右侧立一手捧灵芝的善财童子。五佛冠、莲花云肩、背景竹林,这些元素在故宫博物院藏另一幅尺寸近似的绢本立轴《慈禧佛装像》中也出现了,因此这两幅立轴也常被比对研究。王正华教授认为,相比而言,《慈禧佛装像》仍着彰显宫廷身份等级的明黄色吉服,其场景也是对宫中日用之物的描绘,是“扮演”观音;而《慈禧扮观音像》则完全放弃对世俗身份和生活场景的描绘,俨然化身观音本尊,置身竹林山石中,更进一步的“成为”了观音。那么,“作为观音的慈禧”这一精心排布的表演,仅仅是自娱自乐的、自我欣赏式的奢华“消遣”,还是有其特殊功用、有预设的潜在观众?他们的展示、传播途径和用途是怎样的?
现藏故宫由慈禧“敬书”于1904年7月6日的《心经》扉页上,也绘有一帧扮观音像。清宫帝王手书《心经》的传统在乾隆朝尤甚,而慈禧不仅模仿了乾隆《心经》卷尾“得大自在”的印玺,还将这一印玺转至卷首扉页、其扮观音像的头部上方。画中慈禧化身观音坐于出水莲花座上,一手持杯,一手持杨柳枝,身侧分别放置经书和净瓶,头戴蓝色竹叶纹观音兜,身后有象征神性的圆形头光和火焰状背光。除观音袍、配饰等细节和颜色稍有不同外,这幅扮观音像与故宫藏另一《慈禧扮观音、李莲英扮韦陀》册页中的慈禧扮观音像类同。
关于这些画像的传播和用途,美国传教士赫德兰曾记载,清宫画师多有承担绘制慈禧扮观音像的任务,并将其扮观音画像与太后手抄观音经文装裱在一起“作为扉页,再用黄色丝绸或缎子整体包起来,把它们作为礼物赏赐给太后特别喜欢的官员”。在这里,慈禧不仅延续了乾隆皇帝抄经赏赐群臣的传统,还别出心裁地将其化身观音的形象放在经卷首页,在赏赐大臣的过程中,强化着其作为观音化身的视觉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慈禧扮装观音的经卷扉页和册页画像,潜在观众是宫中近臣,传播途径仍延续着宫廷赏赐的统治传统。与传统又有所不同,慈禧不再限于以往帝王赏赐手书墨迹,而直接赏赐其作为观音的化身形象,这与乾隆皇帝化身居于唐卡中心的文殊菩萨像有异曲同工之处:统治者不再与臣子一同膜拜神祇,统治者本人已经化身为供臣子膜拜的神祇。
为慈禧祝寿的庆典,不仅在宫廷内举办,海外华人群体也在国外多有组织,为慈禧祝寿的活动,直接促成了慈禧油画肖像的绘制及其在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的展出。而与上述慈禧扮观音手卷和立轴画像制作时间类似,慈禧全部扮观音照片也均拍摄于其七十大寿庆典前后(1903-1904年间)。与绘画相比,慈禧的照片因媒介的可复制性而流传更广,可以说,经由摄影这一媒介,慈禧扮装像不仅在宫廷内展示传播,还进一步走入更广阔的、遍及海内外的公众视野。故宫藏慈禧着色放大肖像照,即以画框镶嵌,配有覆帘和挂钩,“为其寿辰时悬于宫中或赏赐他人之用”;根据《圣容帐》记载,慈禧照片共有六幅分别悬挂在乐寿堂寝宫,以及会见外宾的海晏堂;而向外国友人赠送肖像照片,也是慈禧在收到国外统治者照片作为外交礼物中习得的国际礼仪。那桐日记记载,1904年,奥、美、德、俄、比公使为慈禧祝寿呈递“万寿国书”,作为回礼,慈禧赠予五国君主、五国公使“照相各一张”。民国时期亦有流传慈禧扮观音照曾“悬于寝殿宫中”,有的照片甚至还“晒印了好几页,随处悬挂,后来流传京外,各直省都仰慈容”。赫德兰曾在美国驻京领馆看到慈禧赠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大使康格的大尺寸照片,并认定慈禧赠送照片而非画像的原因是,画像不如照相像慈禧本人。此时,与慈禧画像在宫廷和近臣间的传播相比,其照片已流出宫廷、“流传京外”,并作为外交礼物流传至海外,甚至刊登在国外大众媒体上。
那么,就统治者肖像的传播范围和预设观众而言,20世纪之前,清宫统治者延续着以往近千年禁止帝后肖像流出宫廷的传统,作为行乐图的肖像只能在宫中小范围悬挂展示,慈禧肖像也遵循着这一展陈方式,与其真实相貌一样仅为内廷宫人得见。20世纪之后,随着宫廷外交的活跃,西方统治者肖像作为外交礼物越来越多地进入慈禧视野。经由庚子之变,慈禧于1901年西行回銮,途中即宣布新政改革。正是在其回銮紫禁城途中,慈禧真实容貌第一次公布于世,由西方摄影师抓拍并刊登在法国《画报》上。照片中的慈禧并未对拍照行为表示制止,反而向摄影者挥手示意。回宫后,慈禧频繁展开内廷女性外交,召见公使夫人等外国女眷进宫,不仅与她们合影留念,还分发其摄影照片作为纪念。这些照片迅速流出宫外,见诸国内外报端、印制成明信片,公开在市场上售卖,而并没有得到有效禁止:1904年6月到1905年12月,有正书局在《时报》上频繁刊登出售慈禧照片的广告,1907年7月30日也刊登出类似广告;上海耀华照相馆在1904年6月26日的《申报》上刊登出售慈禧照片的广告;1905年5月上海耀华照相馆再次登报出售“专赠各国公使夫人”的慈禧照片。在这个意义上,慈禧肖像的观众群体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中国的统治者肖像也首次承担了服务于外交、面向公众的政治和宣传功能,而慈禧作为女性统治者的主导身份,又难以避免地与传统视觉语言中女性作为欲望客体的被动地位发生重叠。
1904年10月13日,上海发行的《时报》即刊登广告出售慈禧扮观音照:“皇太后以次新照相五种:太后扮观音坐颐和园竹林中,李莲英扮韦陀合掌立左,妃嫔二人扮龙女右立。此相照得最清楚洁白,与前次者大不相同,八寸大片每张洋一元,太后扮观音乘栰在南海中,皇后妃嫔福晋等皆戏装,或扮龙女者,或划栰者,六寸片两张,合洋一元。”这两种尺寸的慈禧扮装照,在当时可谓售价不菲,广告中尤其强调了慈禧和宫中女眷的扮装形象,其中,“清楚洁白”的三维影像画面,既是这则广告的卖点,也是这则广告误导观众的信息所在。首先,结合现藏故宫博物院和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慈禧与众人乘平底船扮观音照看,扮龙女二人是庆亲王奕劻之女(人称四格格)和另一位不知名的宫女,并非广告中所说“妃嫔二人”,而对后宫妃嫔众多的想象,使观者自动将照片中除年迈慈禧以外的宫中女性均视为神秘的皇帝“妃嫔”,加之广告中提及的几种售卖照片,又都有宫中女眷形象,可推测带有宫中女性的照片比一般照片更易吸引顾客。其次,售卖的第二类照片“太后扮观音乘栰在南海中”,真实拍摄地应是西苑“中海”,而将慈禧一众乘船的地点自动匹配为“南海”,隐含着将慈禧与一众人的扮装组合直接与“南海观音”及其仆众画上等号。最后,结合现藏故宫博物院和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慈禧《带五佛冠圣容》扮装照看,所谓太后坐“竹林中”,并非真实的“颐和园竹林”,而完全是由照片布景结合背景幕布绘画制造出的视觉空间幻象,观者误将布景的紫竹林绘画描述为“颐和园竹林”,体现出观者更乐于以展示“颐和园”这一皇家私人园林作为吸引顾客的手段。这些有误导作用的信息,当然可能是由于广告发布人对照片内容不了解、直接读取了慈禧扮观音照所呈现的幻象而造成的,而通过这样的误读,也可返观当时公众对慈禧扮装像的直接解读,其中显著的,就是对这位女性统治者从居所到身份的神秘化、神祇化、神圣化想象。
二、制造幻境的新技术

图1 《带五佛冠圣容》,照片,故宫博物院藏
20世纪之交清宫扮装像的变化,还明显体现在制作媒材和技术手段上。慈禧扮装像使用了摄影这种从西洋舶来的技术,在摄影术诞生之前的帝王扮装像中是没有的。虽然传闻光绪皇帝和珍妃是最早参与摄影的清宫统治者和后妃,但并无充分资料和实物留存。一般认为,慈禧在1903-1904年间的摄影实践,开启了清宫统治者利用摄影这一西洋媒介大量制作肖像的先河。而慈禧的摄影实践,与《辛丑条约》(1901)签订后,官方将学习和发展摄影这一技术手段,提高到“实业救国”、体现一国“文明”之程度的政治策略基本同步。就清宫统治者肖像制作而言,西洋摄影术的引入,为慈禧扮装像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也因其可复制特性促成了这些图像更大范围的传播。其中,摄影与绘画之间的合作互补,在戴五佛冠舞台布景这组照片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现存五种戴五佛冠扮观音照片,均由两人或三人围绕或站或坐于中央的慈禧摆拍而成,是一组典型的舞台布景照片(tableaux photo),与1903年9月建档的《圣容帐》所记“带五佛冠圣容十件”相合。这组照片的基本模式是慈禧扮观音、李莲英扮韦陀、四格格扮龙女、或李莲英与崔玉贵扮高僧。有研究者认为故宫博物院藏《慈禧扮观音、李莲英扮韦陀》对开册页,就是参考内有“李莲英扮韦陀”的慈禧扮装照片绘制的。其中韦陀身着武将铠甲、护心镜,双手合十以手臂托金刚杵,均与上述照片大体一致,尤其是画中慈禧和李莲英的面部刻画晕染,与照片中的人物面容相似又有相当程度的美化,但与慈禧其他画像对比,仍能从美化后的面容看出此画应作于慈禧晚年。
而《慈禧扮观音、李莲英扮韦陀》绘画册页与照片的不同,则首先体现在人物服饰上:扮装照中韦陀着武将戏装冠服,册页中韦陀服饰冠冕则来自于民间木刻画谱。其中,照片与绘画虽可相互借鉴,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又面对不同的视觉范式:照片中人物的服饰需要实际可穿,那么一个便捷的方式就是取材自用于通俗戏曲表演的戏服;而绘画中的服饰无需模特实际穿着,对画师而言,更便捷的方式则是继续沿用流行的平面图像样式。这样不同的视觉范式,也影响了扮装摄影和绘画在对“仙人幻境”视觉建构方式上的不同:因对全方位“真实”服饰道具的使用,摄影更易制造三维视幻觉,也因戏装作为扮装服饰更方便取用,扮装摄影更具戏曲表演的舞台效果,即“剧场感”;而扮装绘画中,除人物面容参考照片以阴影凹凸法稍作晕染外,画师仍主要遵循民间二维平面视觉传统,可根据像主需要,按照传统视觉符号和观看习惯,对画中人物服饰道具删减添加,比如加入彩色头光、脚踏祥云、浩渺烟波、衣带飘飞等表现仙人的传统绘画元素。
与上述册页相比,在戴五佛冠扮观音的舞台场景照片中,既可看到三维舞台效果的呈现,也可看到背景绘画中,以二维平面描绘的想象空间和根据像主需要添加的视觉符号,真正实现了照片和绘画两种媒介在“制造幻境”上的合作:就这组扮装照前景而言,相对于绘画,照片经由对舞台布景实物的摆拍,更便于建构充满视幻觉的“真实”三维立体场景——根据林京先生记载,这组戴五佛冠扮观音舞台布景照片的拍摄地应当是在慈禧于颐和园的寝宫乐寿堂前,搭棚拍摄。与绢本设色《慈禧佛装像》中露出屏风边框的传统绘画手法不同,整组照片的前景和背景都刻意隐去所处的真实宫廷空间,而通过摄影镜头只截取边界之内的舞台场景,前景更是摆满真实的荷花,地面也以实物覆盖模仿水波。有研究者认为,这些真实存在的荷花增强了场景拟真的视觉说服力,通过虚化地平线,慈禧从荷花丛中显现这一幻象也显得更加“真实”。然而,由于前景遮挡视线的荷花,起到了将舞台和观众隔开的作用,慈禧仿佛置身于彼岸净土的荷花池中,于是,这一视觉幻象的“真实”,实际上仍专属于另一个理想中的世界,而非世俗民众所处的人间。
此外,就照片中荷花对身体的遮挡而言,在以往关于南海观音的图像中,多以一叶莲花和简洁的水波纹寓意海上波浪,鲜少以大片莲花遮挡观音的身体。中国肖像画传统强调对身体完整性的呈现,尽量避免对身体的裁切和遮挡,这样的观念和视觉传统也影响了中国人早期的肖像摄影。而在这组照片中,舞台前景的大朵荷花在镜头下被虚化,当人物站立时,荷花甚至遮挡了人物身体的三分之二,这样的构图方式,不仅在传统观音图像中甚少出现,在传统后妃赏花图中也鲜有。
于是,经由真实荷花场景的营造、以及以大片荷花隔开并遮挡身体的方式,照片营造出慈禧所处的彼岸,一个视错觉造成的“视幻空间”,这是与观众所处的“日常”世界隔开的、半遮半掩的、神秘的、另一个虚幻的、却在视觉上“真实”的世界。在中国传统视觉语言中,尤其在以绘画彰显精神道统的主流文人画坛,对透视法的使用和对“视幻空间”的表现长期不占主流,高居翰认为这不仅仅是中西方绘画风格不同的问题,对“视幻空间”的拒绝,实际上是对不合道统的“视觉吸引力”的避免,巫鸿也将透视法造成的“视觉可信度”与“视觉诱惑”联系起来,认为在中国人看来,西洋透视法强化的恰恰不是现实的“真实性”,而是“神秘感”和“虚幻空间中的距离感”。在这个意义上,舞台布景及照相机镜头制造出来的“视幻空间”,恰恰满足了慈禧扮观音所需的、超越日常真实性的“神秘感”和“距离感”。
而就这组照片的背景而言,幕布也并非真实场景,乃是由宫廷画家绘制而成,这一想象中仙山竹林幻境空间的绘制,既延续着传统绘画的视觉模式,又根据像主需求添加了具有隐喻意义的视觉符号。幕布描绘的是寓意南海观音住所的紫竹林和普陀山潮音洞,与慈禧头顶祥云上的文字“普陀山观音大士”、观音和龙女的人物组合以及净瓶绿柳、满海莲花等图像组合在一起,都暗示着慈禧在此间的身份实则是刚走出住所的南海观音——根据于君方教授的研究,完全汉化的女性“南海观音”形象,自明代以来十分流行,对其典型形象的文字记录见于18世纪问世的《香山宝卷》,但16世纪就应当已有题为《香山卷》的著作流传于世。而背景幕布绘制的观音住所,又与真实场景中慈禧身后的寝宫形成双关。在南海观音图像中,除男女胁侍外,白鹦鹉也是常见胁侍之一,其图像在16世纪以后随普陀山和南海观音信仰的传播而流行,其文献来源可溯及大乘佛教、中国民间文学和密教经典。在这组照片中,背景幕布上,一只白鹦鹉正从作为观音居所的潮音洞中飞向画外,学者李雨航注意到这只白鹦鹉口衔“宁寿宫之宝”授印,实际上指出“宁寿宫”这座不在场的宫殿所隐含的作为“退休的皇帝”的居所之意。由此结合慈禧传统肖像中对以往帝王行乐图范式的借鉴,尤其对乾隆的推崇,可推论:宁寿宫作为乾隆修建的“退休”住所,也为慈禧“还政”后所用,那么,其中隐含的权力传承再度强化,通过照片背景中绘制的白鹦鹉口衔“宁寿宫之宝”授印,从画中的观音住所飞向画外慈禧所处的空间。而观音形象在中国语境中的性别模糊性,亦可为跨性别权力传承的合法性背书。
另外值得提及的是,上述戴五佛冠扮观音舞台布景照片中,以前景大片荷花制造中景人物与现实世界距离感的手法,在慈禧呈站立状的照片中尤为明显,且屡次出现与祝寿相关的意象符号。有学者认为,其中体现出慈禧的身份认同及对自我神性的着意建构:尽管慈禧在这一场景中是“演员”,在扮演观音这个“角色”,但慈禧从未完全放弃自我而全身心投入和模仿角色,相反,慈禧意在创造一个“慈禧”和“观音”的合体,既保有“演员”本色,又以“角色”的样子呈现出来——慈禧不是要“变成观音”(become Guanyin),而是要让她自己“像观音一样”(as Guanyin)——换句话说,慈禧的扮观音,与民间流行的扮观音的宗教实践不同,慈禧并未放弃自我权威和对主体的建构,而是利用扮观音的方式,塑造其“作为观音的慈禧”这一至高无上的、强有力的、甚至是的独一无二的形象。在美国亚洲博物馆藏慈禧《带五佛冠圣容》的一张底片上,甚至可以看到经由暗房处理后、赋予像中人神性的“头光”。
三、化身全能的神:从观音、娘娘、佛爷到圣母

图2 《慈禧乘船圣容》,照片,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上述《时报》刊登广告出售的第二组乘船照片“太后扮观音乘栰在南海中,皇后妃嫔福晋等皆戏装,或扮龙女者,或划栰者”,与内务府档案中的两则记载类似:“七月十六日海里照相,乘平船,不要蓬。四格格扮善财,穿莲花衣,着下屋绷(另一份档案上后两句改为:穿《打樱桃》丫鬟衣服)。莲英扮韦陀,想着带韦陀盔、行头。三姑娘、五姑娘扮撑船仙女,带渔家罩,穿素白蛇衣服(另一档案后二句改为:穿《打樱桃》二丫鬟衣服),想着带行头,红绿亦可(另一份档案无后四句)。船上桨要两个,着花园预备带竹叶之竹杆十数根。着三顺预备,于初八日要齐,呈览。”
德龄回忆录提到1903年7月(农历闰五月)中,慈禧在西苑渡船,看到湖里荷花开得好,于是想到在船里拍几张照。1903年9月(农历七月)建档的《宫中档簿·圣容帐》中也有“乘船圣容三件”的记载。而从上述内务府两则档案可以看到,拍摄乘船照的服饰行头要提前数日准备齐全,其中人物扮装服饰主要来自戏装,需在拍摄之前将一应道具“呈览”,可见这组照片拍摄的具体安排之细致、涉及人力物力之庞杂、准备和审批程序之烦琐。
据笔者所知目前至少存在五种慈禧乘船照,均为慈禧坐船中央,其余人站立左右。其中三种乘船照中,船上共七人,除慈禧外,有持大葫芦着戏装女性一人(从照相面容对比看应为四格格),另有宫中女性一至两人(有着素白衣裳者,有着戏装撑船者,可能是三姑娘容龄、四姑娘德龄),还有着渔家罩太监三至四人(包括船尾撑船太监一人,船中慈禧身后撑华盖太监一人,船头持“带竹叶之竹杆”太监一至两人,当船头太监增至两人时,增加的太监站在更靠近船尾外侧处,从照相面容对比看增加的人应是李莲英)。另有两种乘船照为16人乘船(除慈禧外,有四名太监、宫中女眷十一人、女孩一人),可辨识出持“带竹叶之竹杆”的李莲英、慈禧身后的光绪皇后,以及瑾妃、四姑娘、元大奶奶、德龄、德龄母亲路易莎,包括慈禧在内均着常服,慈禧手持葫芦一枚,有学者推测可能是正式扮装照之前的彩排。船上均放置花瓶、几案、果盘、香炉、屏风,屏风上缀有卷轴形文字框,框内写有“普陀山观音大士”字样,船头花瓶和船中央几案上的香炉炉身有宁寿宫字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组乘船照片,经由暗房加工后,香炉上有形似“寿”字状炉烟,“寿”字上方还写有“广仁子”字样。“广仁子”是慈禧的道号,这一道号据称得自于作为道教祖庭之一的白云观。在民间信仰中,虽然“观音”这一形象来源于佛教,但观音信仰却并不限于佛教徒。观音形象及其故事在中国的传播,融合了道教、儒家以及传统民间文化,观音被纳入道教神阶体系的一员,常常要奉玉皇大帝之命行事,也是儒家孝道的奉行者和捍卫者。根据于君方的研究,明清时期许多新兴教派(如一贯道、在理教、先天道)也都信奉观音,从而“将观音提升至创世主及宇宙主宰的崇高无上地位”。尤其对居家女信徒而言,高彦颐使用“家内宗教”(domesticated religiosity)一词描述明清士族妇女的宗教信仰:膜拜观音的女性,不一定是佛教徒,同时可以接受道教信仰,甚至是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情教”。
慈禧对道教活动多有资助,与道士关系密切,这与顺治入关以来满清统治者对道教不甚尊崇的“强硬宗教路线”形成对比。明清以来,女性、太监等“边缘群体”成为宫中道教信仰的主要实践者,送子娘娘、催生娘娘、痘疹娘娘、眼光娘娘这些“娘娘”女神,不仅能够为女性提供祈求生育、子孙和家人健康的庇佑,道观也为太监提供了类似于家庭的庇护、以及实际的养老场所。据传同治皇帝死于天花痘疹之前,慈禧曾向痘疹娘娘进香祷告,白云观道人高仁峒与慈禧的贴身太监私交甚笃,民国时期仍有传言慈禧与高仁峒多有往来。
现藏北京白云观的一组22幅《娘娘分身图》于1890年道教女神“碧霞元君”生日庆典时,由高仁峒主持揭幕,一改以往传统道观和木刻图像中,这位女神作为家庭辅助地位的(送子、生产、维护家庭和睦)、年迈的主妇形象,而通过对女神生平事迹的描绘,侧重于表现这位道教“娘娘”自身的修行经历,以及与其长生不老并存的年轻、美貌与生命力。“娘娘”图像的这些转变,与晚清贵族道教女信徒的审美和修道需求有关,而晚清贵族妇女对道教的赞助和修道活动,又为最高统治者慈禧的喜好和导向所影响。
慈禧其他扮观音像中,也常常糅合多种宗教元素。比如,慈禧扮观音、化身“老佛爷”也受到藏传佛教转世思想的影响。比如,《慈禧佛装像》桌上放置的金刚杵和法铃,乃是藏传佛教法器,慈禧头戴的五佛冠至今也仍多见于藏传佛教图像中。清宫帝王一直有赞助与加持藏传佛教的传统,慈禧与藏传佛教有关的行乐图也见于布达拉宫壁画,记录着1908年慈禧于西苑接受达赖朝觐的情景。布达拉宫藏四幅描绘中原统治者与藏传佛教领袖会晤的壁画中,慈禧太后现身其中两幅,作为另外两幅壁画中前朝男性统治者明成祖永乐、和清世祖顺治的合法传承人。不同的是,虽然顺治帝端坐于画面中央,但顺治帝的肖像只有达赖尺寸的一半大小,而在关于慈禧的两幅壁画中,慈禧在人物尺寸上比达赖只大不小。此外,在《达赖十三世向慈禧太后献佛》这幅壁画中,慈禧端坐,而达赖伏地跪拜,向慈禧敬献一尊无量寿佛;在另一幅《达赖十三世朝见慈禧太后》壁画中,慈禧则接替以往的中原男性帝王与达赖并坐于中央,光绪皇帝站在慈禧身后。
从中原统治者的视角看布达拉宫这两幅壁画,慈禧以女性大家长的身份,确立了自身作为政权代言人的绝对权威,也彰显了中央和西藏的尊卑等级。而从藏传佛教僧侣的视角看,这幅画也有效宣示了中央对其信仰合法性的授予。在藏传佛教中,自14世纪,就将格鲁派首领视为观音化身,在这个意义上,《慈禧佛装像》中藏传佛教的图像符号也是对中原观音信仰所展现出的统治策略的补充,呼应了雍乾以来,清宫帝王对藏传佛教扮装像的图像传统。而慈禧在布达拉宫壁画中作为以往中央正统男性君主传承人的女性身份,也与观音这一源于大乘佛教的男性神祇传入中国后,在明清之后更偏向于女性身份的特质相呼应。
除这些媒材丰富的扮观音肖像外,参展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圣母皇太后》杉木桌屏,近年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架以慈禧肖像照片和慈禧油画像照片为底本、由上海土山湾孤儿院耶稣会士绘制并雕刻的圣母子桌屏,被认为由慈禧间接委托制作:委托者要求桌屏主题为“圣母皇太后”,且要将慈禧太后与西方的圣母子图像结合起来表现。土山湾画家范殷儒所绘《圣母皇太后》油画小稿中,保留了慈禧照片中的坐姿、服装样式和紫藤纹样,以更年轻的目光下垂的安格尔圣母面相,替代了照片中慈禧直视画外的面容,又在圣母怀中添上圣子立像,并将原照片中的背景屏风代之以寿字图案,延续着为慈禧祝寿的用意。这幅画稿完成后,交由委托人审批,之后,土山湾木工间按委托人要求,去掉画稿左右上角“皇后”二字,代之以桌屏左右下角的两个“喜”字,完成后又经金工间镀金,于1904年8月20日前顺利通过金陵海关申报,送至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展出,被授予金奖,涉及桌屏制作一事的所有经办人员也在此后得到奖赏。

图3 《圣母皇太后桌屏》,1904年,杉木,私人收藏
现藏美国旧金山圣依纳爵教堂的《中华圣母像》(Our Lady of China),署名范殷儒(Wan Yn Zu)绘制,是在《圣母皇太后》桌屏油画底稿的基础上创作的。画中去除了《圣母皇太后》中彰显满清皇室身份的龙纹地毯、及为慈禧祝寿而作的背景寿字图案,不过,这位“中华圣母”仍身着满清贵妇氅衣、项系围巾。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可见作为《圣母皇太后》桌屏底本的慈禧肖像为黑白照片,1908年6月20日刊登在法国《画报》封面时,慈禧的氅衣被手工着色为黄色,这既与女画家卡尔和男画家华士·胡博绘制的慈禧油画像服饰颜色一致,也与故宫藏慈禧着色照片多着黄色服饰一致,同时又符合了西方人对中国皇室喜好明黄色着装的想象。不过,以《圣母皇太后》为底本创作的这幅《中华圣母像》,虽未改变圣母氅衣的款式和纹样,却参照西方圣像传统修改了圣母服饰颜色,慈禧黑白照片中不知实际颜色的氅衣,被绘制为着金色花纹的大面积蓝色。
另一件由宫廷画师私自赠予美国监理会传教士赫德兰的《慈禧扮观音》传统绢本设色立轴,1909年彩印刊登于赫德兰出版的书籍扉页,即以深浅不同的蓝色,描绘了慈禧的观音冠服,这一配色可能与宫廷画家考虑到委托人的视觉习惯有关:宫廷画家从传教士处知晓西方蓝衣圣母像的视觉传统,又在就医等实际事物上有求于传教士夫妇,因此当传教士提出要一张慈禧扮观音画像后,宫廷画家特意绘制了这幅取悦于传教士的蓝衣观音像。考虑到慈禧以往的扮观音服饰和扮观音画像中,也多着蓝色观音袍,赫德兰收藏的这幅《慈禧扮观音》画像可谓“观音蓝”与“圣母蓝”二者的巧妙融合。
回到《圣母皇太后》桌屏,其所呈现的圣母子形象,在中国最早见于元朝扬州女性基督徒墓碑雕刻,明末经由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传播真正为中国人所知。有学者认为,送子观音形象在晚明的涌现,即是受到西洋传入的圣母子形象的影响。16世纪末的南京,中国人以为基督教的“天主”就是一个怀抱婴儿的妇人,有时还会将“圣母子”图像理解为“送子观音”,而虽然耶稣会士意识到了宣传圣母图像可能存在的“异教”风险,但他们仍然乐意使用美丽的圣母形象吸引中国信众。晚清之际,当慈禧太后多以扮装观音的形象示人时,“圣母皇太后怀抱圣子”这样的图像,也启发了传教士对基督教“圣母”的形象塑造。1904年范殷儒设计绘制的这幅《圣母皇太后》,在1908年被选为“东闾圣母”的范本,1924年又为天主教驻华代表刚恒毅主教(Celso Costantini)选中,最终成为“中华圣母像”的绘制蓝本。可以说,在《圣母皇太后》这样一个兼具“送子观音”和“圣母子”含义的形象中,正致力于改变国际形象的慈禧太后,与正积极寻找代表高贵美丽、至高无上中国圣母形象的传教士,达成了一致。时至今日,在北京北堂展示并出售的几种流行样式的圣像中,仍可看到延续着自1904年《圣母皇太后》桌屏开启的,着满清皇室服装的中国圣母子图像传统。

图4 《圣母子》,油画,北京西什库教堂藏
四、从“帝王”到“帝国”的形象转型
综上所述,以慈禧为代表,20世纪之交的清宫扮装像呈现三个突出特点:首先,就展示和传播途径而言,与以往清宫帝王扮装像只限于在宫廷以内展示不同,慈禧不仅将这些扮装像赏赐大臣,赠送外国友人,甚至默许它们的复制品在市场上售卖、在国内外出版市场上发售,在客观上,迈出了中国统治者形象走出宫廷、走向公众的现代化转型的第一步;其次,在制作媒材和技术上,首次运用西洋摄影术,并尝试与中国传统绘画相结合,共同制造幻真的图像空间,以建构虽虚拟却看似更为“真实”的视觉形象;最后,就宗教形象的塑造而言,与以往雍正、乾隆皇帝扮演文人雅士、外国武士、异域绅士等扮装题材不同,慈禧肖像涉及的扮装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扮装对象均为宗教神祇,一方面通过化身观音,成为跨越汉地佛教、道教、藏传佛教、及民间诸多信仰中的“全能”女神,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展示其作为“圣母皇太后”的“圣母”形象,与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尝试在地化的图像宣传策略达成一致,成为“中华圣母像”的图像样本,影响至今。
在论及“扮装像”的中西差异时,巫鸿教授认为,中西方帝王扮装像有着本质区别:清宫扮装像是“帝王式”(imperial)的,是传统中国帝王“天下一人”的自我想象,反映出对内稳固政权的诉求;欧洲同一时期展示各国异域服饰的扮装肖像,则是“帝国式”(imperialist)的、是向外的扩张,与欧洲文化世界性的征服进程与殖民想象同步。而通过本文研究可见,与18世纪清宫扮装像相比,在一个多世纪后的20世纪之交,在中西文化碰撞和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中,以慈禧为代表的清宫扮装像再度发生了变化:慈禧的扮装像制作,既延续着“帝王式”“天下一人”自我想象的清宫帝王扮装像传统,同时又不得不放眼世界,吸收西方肖像的公开展示方式、现代摄影技术、宗教人物形象,创造出新的、兼容对内对外双重诉求的“神化”主体。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之交清宫扮装像的制作及展陈方式的变化,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实则开启了20世纪中国统治者从固步自封的自我想象,向放眼世界的国家形象建构的艰难转型。
——战斗的圣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