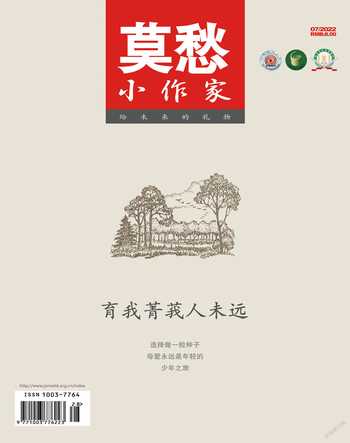大缸
将大白菜、莲花菜、胡萝卜、青笋洗净,撕成叶,切成块,焯水。往缸里铺上一层,撒些盐,淋上花椒、生姜、尖椒熬的汤汁,再铺一层。直到缸里快满了,搬来一块石头,压住菜,合上盖,母亲拍了拍手,舒了一口气。缸满了,似乎也舒了一口气,它已经很久没有满过了。放在阴凉处,隔几天,这缸麻菜就腌好了。吃时,捞出几片,切碎,拿热油一泼,香。
这样的冬菜,一定要腌在缸里,一定要用石头压住,鼓鼓囊囊,五味杂陈,才不会坏,才出味道。腌菜的这口缸,陶质,缸口直径20公分,上下一般大,通体暗黄,外壁有许多凸点,有些硌手。缸是泥土的华丽重生,既防鼠虫,又能隔潮,装水、腌菜、搁米、盛面,不可或缺。
在家乡,缸不管大小,都称为大缸。汪曾祺有句话,说家里缸多,光景就好。如此说来,以前我家的光景,堪说惨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母亲嫁过来时,家里有口缸。口小肚大,矮胖矮胖,蹲在地上,肚里盛了腌菜。没几个月,腌菜吃完,这口缸像长了腿,跑邻居家去了。这缸原是借来的。
借邻居的缸还回去了,又从三姑家借来一口,用了好久。后来父亲买回几口缸,腌菜的这口最值钱,花了两块多,我们叫它“精品缸”。其他都是五毛錢一口的残次品,灰头土脸,有裂纹。装不了水,就装米、装馍、装洋芋。其中一缸,口大肚大,个矮,缸壁有两只抓手,像两只耳朵,裂痕有些大,父亲用铁丝在缸口细细箍了一圈,我们叫它“耳朵缸”。装馍、装油饼的缸,口小,肚大,个矮,我们叫它“油饼缸”,听这名字,好像缸里总藏着油饼,承载了我们太多盼头。其实,只有腊月二十八以后,这缸才会装满油饼,其他日子,里面只蹲着三五块巴掌大的黑面馍。
我们返城后,母亲攒了钱,陆续购置了四五口缸,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多是瓷质,耐看耐用,放食物,久置不坏,成了家里值钱的家当。
在父亲心目中,缸被赋予了另外的寓意。多年来,他不止一次说,做人不可尖酸刻薄,不可落井下石,要像缸,沉稳大气,有肚量,啥事都能装。据旁人私下讲,有人曾给父亲使过绊,但父亲从未说过那人的坏话。母亲无意中透露,有哪些人从父亲手里借过钱,一些还了回来,一些没了音讯。但父亲闭口不谈。前几天就有位老友拿来三千元。父亲回忆,当初借出两千,已近二十年了。另外一千,老友非要算作利息。父亲拿这钱换了一部新手机,他说,也算是个纪念吧。
如今生活好了,缸显得笨重,占地方,已经越来越少见。大家更喜欢冰箱,比缸肚量大。还喜欢用塑料袋、塑料箱装蔬菜,装米面,看似方便了,但比起缸来,似乎有些潦草,总感觉少了些什么。更有趣的是,不知从哪里,总会传来一些消息,说某人在乡间发现了一口缸,是古物,捡了漏,好运气。传来传去,显得愈发神奇。不过,这样的缸,我听了无数次,却一次也没有真正看到。
张立新: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多家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