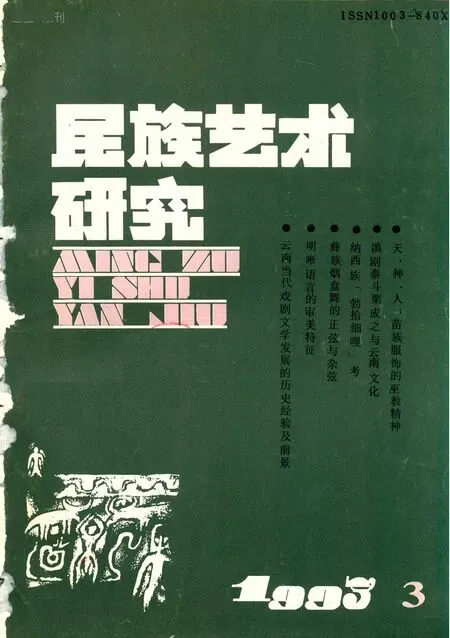“玩灯”:艺术感官体验与乡村社会治理
陈 曦,陈双美
昆明市呈贡区(原呈贡县)位于滇中高原滇池盆地东部,其气候属于北亚热带大陆性气候,冬暖夏凉,过去盛产粮食、花卉、蔬菜、鱼等农畜产品,汉族约占总人口97%以上,农业人口居多数。(1)参见呈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呈贡县志:1978—2005》,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003年后昆明城镇化建设大规模推进,呈贡区经济、社会结构经历剧变,在国际花卉交易市场、大学城、地铁带来繁华的同时,本地老百姓如何通过民间艺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重建社交网络、获得幸福感是本文研究的起点。
花灯戏是广泛流行于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中的一种民间戏曲,于明清时期在中原地区形成发展,流行于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并形成不同支系(2)参见顾峰《云南歌舞戏曲史料辑注》,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戏剧研究室编印,1986年版。。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投入到云南花灯戏的研究中,对其起源及历史、戏曲整体时代特征和具体文本进行了阐释(3)参见徐嘉瑞《云南农村戏曲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顾峰《云南歌舞戏曲史料辑注》,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戏剧研究室编印,1986年版。,对其舞蹈、音乐等观感模式进行了专业化表述(4)参见杨友明《云南花灯的地域性特征》,《民族艺术研究》1993年第3期;金重《云南花灯的美学特征及其发展趋势》《民族艺术研究》1988年第3期。。近年来研究者更注重花灯表演技巧、艺术审美、教学和传承等具体实践的研究(5)参见黄富《云南花灯的审美教育功能》,《民族艺术研究》2000年第6期;吴戈《生存还是毁灭?——从“文化自觉”谈云南花灯的发展》,《民族艺术研究》2013年第4期。,而对其主体及背后的社会文化阐释却涉及不多。花灯戏在呈贡流传百年,分布在每个村,民间历来有“呈贡60村,村村有花灯”之说。明嘉靖年间杨升庵“九枝灯下开华宴,百戏棚中夺彩绸”(6)杨慎:《晋宁观社将归留别诸君子》,载《杨慎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记录了该地区花灯的盛行景象。2008年呈贡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花灯)之乡”,2013年呈贡花灯被列入云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呈贡区文化旅游局:《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灯》,昆明市呈贡区文化和旅游局官方微博,http://blog.sina.com.cn/u/1267009335,发表时间2014年2月12日。。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参与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被逐渐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提出“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乡村“非遗”保护的原则,由此看出通过民间艺术促进乡村治理离不开对主体的重视。当下人类学界提出本体论转向的观点,提倡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主观意识表达作为其人类学研究的宗旨(8)参见朱炳祥、张佳梅《“本体论回归”与主体性诉求》,《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对参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民间艺术,有必要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些民间艺术生产的社会语境和艺人的身体感官、个人情感予以关注,注重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文化问题和生活问题。本文试图回应后现代思潮下的“身体的转向”和“感官的转向”(9)Howes D.,Sensual relations:Engaging the senses in culture and social theory,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12.理论,将“玩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放置到其完整的社会语境中,通过分析研究“玩灯”的艺术感官体验,探讨艺术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关系。
一、感官体验:理解社会文化和促进社会治理的工具
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在学界已被认可,马凌诺斯基认为“民俗是一种依传统力量而使社区分子遵守的标准化的行为方式——是能作用的或能发生功能的”(10)[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民俗包括信仰、表演仪式等,花灯戏也在该范畴中。民间戏曲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体现在以礼俗文化加强凝聚力、传达时代精神和提升人们的审美趣味等方面。昆明的城镇化进程给呈贡区带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其过去的乡土社会关系网断裂,人们在新的生活空间中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民,难免产生个体的无意义感。而“玩灯”恰好能再造集体生活,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的需求,并强化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弥合上述断裂,从而促进乡村治理,而其感官体验正是达成上述目标的媒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加拿大人类学学者戴维·豪斯(David Howes)与康斯坦茨·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带领下,一批学者分别针对嗅觉、视觉、味觉、触觉与听觉做了民族志调查,创立了感官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senses)。感官人类学主张感官研究不仅是生理的研究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更是构成社会意义的基础,其与社会结构、文化、消费、经济都有着密切的联结并与象征隐喻相关联。(11)Herzfeld M.,Anthropology:a practice of theory.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7,No.49,pp.301-318.因此,感官可以作为理解世界的工具,玩灯产生丰富的“知觉项(categories)”(12)参见余舜德《身体感:一个理论取向的探索》,载余舜德编《身体感的转向》,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版。不单指生理的快感,还涉及心理和文化层面的内容。它来自文化和历史的过程,呈现在知识、科技、物质与环境中,由文化成员长期于文化物质环境中生活成长而内化而成(13)参见余舜德《从田野经验到身体感的研究》,载余舜德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例如认同感、归属感正是“玩灯”感官体验中的内容,这种体验与乡村治理有密切的正向关系。
首先,特定的人群对感官刺激做出特有的反映,正如花灯爱好者将花灯所带来的审美体验称为“灯味”,这种感官体验被赋予了“地方感”(14)参见段义孚《地方感:人的意义何在?》,宋秀葵、陈金凤译,《鄱阳湖学刊》2017年第4期。的意义。“地方认同”的概念主要由段义孚提出,他认为空间是由经历建构的意义中心,该意义指向情感和关系,当我们对特殊的地理空间产生感情时,空间成为地方。(15)Tuan Yifu,Space and Place:Humanistic Perspective,in Stephen Gale,Gunnar Olsson,(eds),Philosophy in Geograph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9,pp.387-427.花灯戏在呈贡受众广泛,无论是在外务工的青壮年还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儿童都听过、看过或参与演出过,是当地文化的重要表征。虽然是“玩”,却不是玩耍,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也是对参与者全部花灯戏知识和经验的调动,折射着参与者的文化认同、价值观念、社会记忆和社会经济生活,其带有乡土社会的人伦色彩和乡村伦理精神。正如马凌诺斯基所认为的:“即使在欧洲国家,民族特色最后的堡垒也是它的娱乐方式;而没有闲暇和娱乐活动,文化种族都不能存在。”(16)[英]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这说明人们乐于玩灯不仅仅是生理的狂欢,更与社会文化和个人生命价值取向密切相关,这与现代广场舞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基于情感和社会关系产生的“地方感”强化了社会和文化认同,缓解了城镇化建设中因物理空间改变给当地人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疏离和情感不适,从而使人们获得归属感。
其次,人在感知美时往往渗透着其审美情感,情感是审美心理结构中的中介因素,其连接着审美认识和审美意志,具有驱动作用,是一种“隐含着功利的愉悦”(17)张玉能:《深层审美心理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3页。。身体感与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例如感动、神圣感、共鸣是身体感也是情感。情感对于社会凝聚力形成有一定的作用,斯宾诺莎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影响着身体实践和观念。(18)参见[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花灯戏往往以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内容为题材,容易带动观者产生审美情感的共鸣,甚至产生涂尔干提出的“集体欢腾”现象(19)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集体情感要通过集体来表达,并在协作中表达,在这个过程中促成群体的团结和凝聚。
二、感受“玩灯”:社区共享的情感纽带
“玩灯”产生的身体感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由艺术形式带来的感觉和审美知觉——“灯味”;二是审美活动中被调动的生活经验和情感。
(一)“灯味”与社区成员向往的亲密关系
在方法论上,感官人类学主张“身体不仅是肉体,感官可以用于观察体验身边的事件进而理解地方、他者和我者,并且身体经验影响到如何体验和解释周围的世界。”(20)C.Classen,Foundations for 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7.No.49,pp.153.“用身体了解”是感官人类学的认知方式,花灯爱好者在评价春台戏时使用最多的词是有“灯味”,部分老年观众认为专业剧团的花灯戏舞美华丽但是没有“灯味”。究竟何为“灯味”?大多数花灯爱好者无法用语言形容这种感觉,他们会亲自演唱或将“灯味足”的视频音频发给笔者。“味”在辞源解释中一为滋味,古时将酸、苦、甘、辛、咸称五味;二为意义、旨趣。(21)参见吴泽炎、黄秋耘、刘葉秋编《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灯味”是感官维度下具有冲击力的审美知觉,就如川菜的麻辣感让人一尝就知道是川菜;呈贡花灯戏特有的唱腔、道白、动作、表演共同带来的感官刺激构成了“灯味”。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灯味”并非纯艺术的特征表述,其带有浓厚的地方情感。
第一,从声腔旋律说,一场有“灯味”的大戏最基本的是要使用观众熟悉的传统曲调。云南花灯有百余支影响较大的优秀传统曲调,都分别对应相应的情感表达。例如:玉溪〔放羊调〕之四、〔光棍哭妻〕及云南省著名花灯艺人李永年演唱的〔苦道情〕等,都可以表达极悲痛的情感;〔前十字〕〔虞美情〕〔五里塘〕用于缓慢的抒情;各地较盛行的传统花灯曲调〔十杯酒〕〔一蓬藤〕等主要用于喜庆的情感。粗略统计,在百余首常用的传统曲调中,仅表达悲痛的就有十余首,可见花灯曲调的情感层次十分丰富。各地还有各具特色的唱法,例如呈贡曲调〔金纽丝〕 (背宫调)听起来很有特点和韵味。要做到有“味道”,必须关注到方言的吐字、装饰音的运用、节奏音型、真假嗓混合的比例等内容。虽然花灯曲调多且旋律转折起伏较大,但当地人尤其是中老年人都能熟练吟唱。花灯爱好者通常通过集体娱乐、音乐视频播放、一对一示范的方式进行学习,而且只有亲自参与学唱才能感受到花灯的“味道”,当地人把这种学习方式称为“灌耳音”。虽然大量花灯曲调已被记录,但是口传心授仍然是民间最重要的传承方式,这是一种渗透式的学习。
第二,方言的使用是“灯味”的重要特征。花灯戏的演唱语言为昆明方言,也被当地人称为“老本腔”。这里的昆明方言指圆心为昆明市区的滇中一带包括呈贡、晋宁、嵩明等地的方言,无明显界限。昆明话乃至整个云南省的汉语方言都属于汉语方言中官话方言区的“西南官话”一支。(22)参见张华文、毛玉玲编著《昆明方言词典》,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由于昆明及周边地区汉族来自不同时期的移民,明清之际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使用了保留历史时期的古语词,因此与普通话相比其语音、词汇上有自身特点,在普通话中难找到精准的替代词。例如:
本人村中王媒婆,就靠一张嘴来说,撮(撮合)的着么吃的着,大象说成是骆驼,背锅(驼背)说成花一朵。憨包说成有才学,麻子说成是酒窝。(23)据笔者对呈贡知名花灯老艺人王某某(已故)的访谈,此台词在“条纲戏”中的媒婆角色中广为使用。访谈时间:2018年7月。访谈地点:王某某家。
上述台词中的“着”“学”如果按普通话发音,其韵脚就会被破坏,失去了“味道”。方言的使用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强化了社会记忆,使社区人群达成特有的默契,呈现出当地社会特殊的血缘、地缘关系。行话、方言的使用及其渗透式的学习方式体现出“熟人社会”逻辑,呈现了当地人在玩灯过程中语言情感的融入。
第三,花灯肢体语言的运用也是其“灯味”的体现。花灯戏以扭动、跳跃为基本动作,用于烘托热闹的气氛,无论场上人多人少,无论唱还是讲,都伴有活跃的肢体表达,正如花灯戏的常用“崴步”所呈现出的热闹感觉。“民间的花灯团队平时不需要系统地练习基本功,很少有武打场面,因此排练中没有危险。花灯中最具有特色的肢体动作是挥舞折扇或手帕,扇子手帕‘耍得团’需要一定的技巧,手腕灵活才能让扇子和手帕流畅地挥舞。但是学习中不需要吃苦,人人可参与,学习过程中不会因难度过大而放弃。”(24)据笔者对小莲花花灯艺术团编剧,云南滇戏、花灯老艺人吴某某(78岁)的访谈。访谈时间:2021年7月6日。访谈地点:吴某某家。简单易学是花灯戏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在欢快舞动的过程中感受热闹的生活气息是花灯戏的重要追求。
总之,“灯味”由曲调、语言、肢体语言等方面组成,这种与地方感相关的文化符号体现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审美心理,体现了“熟人社会”中对欢闹气氛和乡亲间默契感的追求。首先,由“灌耳音”习得的花灯音乐旋律非常容易唤醒人们对故土的情感,特定的声音标识具有独特的情感和心理力量,唤醒人们共同的记忆和情感,成为人们交往的媒介。其次,学唱花灯有非常高的互动性,群体性的口传心授加深了人们的亲密感,产生了类似于涂尔干描述的“集体欢腾”现象,激发人们的共鸣。此外,花灯戏排演过程中,观众可以对剧情的发展提建议,甚至很多时候观众与演员的身份会进行自由切换,这种演员和观众之间良好的互动,回归到花灯戏作为自发的广场娱乐,追求热闹欢腾和“好玩”的初衷。
(二)花灯戏剧情与集体情感
花灯戏的创作素材多来源于乡村日常生活的嬉笑怒骂、悲欢离合,排戏多年的老艺人认为成功的戏要“好笑到观众笑得肚子疼,悲到观众淌眼泪”(25)据笔者对小莲花花灯艺术团编剧,云南滇戏、花灯老艺人吴某某(78岁)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2月6日。访谈地点:大洛羊社区客堂演出现场。。
搞笑是春台戏带给观众的重要体验,有多年编戏经验的老艺人告诉笔者“好笑的方法一是幽默,二是俗”。(26)据笔者对小莲花花灯艺术团团长杨某某(64岁)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8日。访谈地点:呈贡区文化馆花灯排练室。“歪打歪用”是花灯戏常用的幽默手法,例如弘扬孝道的《杀狗教子》中不孝儿子有段打趣台词,“孝子就是孝敬儿子”“婆娘(云南方言指媳妇)就是婆婆的娘,所以婆婆要伺候儿媳妇”,这种手法花灯戏中非常常见。所谓俗,指向通俗、接地气的表达。具体表现在,表演者非常善于抓住事物最典型的特征进行化虚为实的描述,以最简单易懂的词汇精准勾勒对象,例如把赌徒描述为“赌钱人赌钱人,腰间别(系)根绳,输了想吊死,又怕明天赢几文。”寥寥数字把赌徒的形象和心理呈现在观众面前,生动又有趣,这些描写完全出自对生活的细腻观察。正因为源于生活,所以更容易引发共鸣,让观众自然而然地将戏剧与生活经验进行对照从而反思。
“让观众淌眼泪”的悲伤体验也是“好玩”的一部分。《山伯访友》《孟姜女》《窦娥冤》是每年必演的剧目。在欢天喜地的过年氛围中本应喜庆,但是春台现场的观众认为,“糖吃多了想吃酸的刺激一下自己,平时好日子过习惯了想看悲戏。”(27)据笔者对花灯爱好者,观众李某(65岁)、蒋某(68岁)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2月6日。访谈地点:大洛羊社区客堂演出现场。笑和哭都产生强烈的情感刺激,悲剧容易让人对自身进行反观并通过痛苦的通感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拔脱出来,在悲痛中感受到日常关注的狭隘功利已是虚妄,因此悲伤往往带来更深的审美体验。再配合观众熟悉的〔烟花调〕 〔前十字〕 〔新十杯酒〕等感染力极强的曲调,更容易唤醒观众的共鸣情感。
“好笑”和“流泪”源于人们辛苦劳动后需要放松,也来源于人们在戏剧中看到人生的倒影,体现的是植根于乡土社会的人性与精气神。汉族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世俗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忠、孝、诚,这些观念在受观众喜爱的《杀狗教子》《卖妙郎》《白扇记》等剧中均有体现。花灯戏剧目内容表现的多是农民身边小事和他们所关心的事,剧中不仅蕴含着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百善孝为先、人穷志不短、重义轻利等处世哲学和朴素的乡民道德观念,还成为了地方集体情感的表征。
“玩灯”的感官体验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感,承载着人们共有的历史记忆,体现着人们对特定空间的情感。其内容深嵌于社会结构中为人们共享,增强了其社会认同感。同时,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说,审美知觉不是审美感觉相加的总和,而是他们的有机整合,具有恒常性、稳定性、持久性的特征。(28)参见邱明正《审美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因此,“玩灯”成为一条可共享的较稳定的情感纽带,人们通过“玩灯”恢复和激活乡村的伦理精神,调动了地缘亲缘等传统资源,成为社会治理的助推力之一。
三、“玩灯”:在城乡交叠地区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2003年5月,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一湖四环”“一湖四片”的现代新昆明建设战略构想,规划建设面积107平方千米,规划人口95万人,2008年呈贡区开始了第一批次城建建设用地征地任务。(29)参见呈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呈贡县志:1978—2005》,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大量的呈贡农民在失去土地后选择在近郊的晋宁、嵩明等地继续租地务农或就地打工,年轻人外出读书、就业,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依靠占地赔款和养老保险生活。基于农耕文化和建立在一定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传统社会的影响,住进小区的农民生活呈现出“城市中有乡村、乡村中有城市的交叠状态”(30)马翀炜、杨英:《生成好在的地方:左脚舞的城市化及其城乡影响》,《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145—155页。,人们在这一适应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
例如赌博现象,在农民刚获得补偿款的时候最明显。村民说:“留在呈贡的(不需要工作的村民)平时爱好是洗桑拿、玩手机游戏、喝酒,疫情前主要是打麻将,一晚上输赢可以到一两万。”(31)据笔者对斗南村民陈某(24岁)的访谈。访谈时间:2022年2月8日。访谈地点:斗南村陈某家。呈贡区老年大学校长原区人大主任说:“我之所以组建呈贡老年大学花灯艺术团是因为退休后看到一些村里的人拿到二三十万补偿款,没了土地没事干就每天打麻将,打到妻离子散。我想做的是通过大家喜欢和熟悉的花灯把人聚起来。”(32)据笔者对呈贡区老年大学校长张某某(73岁)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3月4日。访谈地点:呈贡区老干局。再有如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也在下发补偿款期间集中出现,让部分农民财产受到损失,这是现代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其根源首先是身份缺失。这些地方的农民在失去土地的空窗期虽然获得了大量资金,但是却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产生了生活的无意义感,人们需要强烈的感官刺激寻求个人的存在意义。因此富起来后做什么,如何确认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是人们面对的问题。再者,生活空间疏离使交往需求难以满足。这个群体年龄在55—80岁间,子女在外务工求学,他们习惯了过去熟人社会的社会网络,他们需要重组乡村社会关系排解孤独感。同时,文化水平较低、社会接触面比较单一,以至于容易沉迷于赌博或上当受骗。因此,城镇化中的中老年人需要在新的生活空间中寻找生活的意义,而“玩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这些城镇化过程中因与原来乡土生活断裂产生的问题。
韦伯提出“情感社群”理论,认为共同信仰、价值观、兴趣是情感社群形成的基础,“部落其实是情感共同体的隐喻,可以共享价值观并找回自身基本价值”(33)许轶冰、[法]波第·于贝尔:《对米歇尔·马费索利后现代部落理论的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21-27页。。“玩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具备实现个人价值的功能。老艺人回忆:“大约在1960年,那时我17岁不到就参加下乡演出了。那天我们演武打戏,演完后累得衣服都懒得脱就睡了。第二天中午我醒来吓了一跳,村委会杀了一只大羊!村干部没人吃一坨羊肉,他们只吃羊杂,当时是困难年代啊。我就觉得一定要好好演戏。”(34)据笔者对小莲花花灯艺术团编剧,云南滇戏、花灯知名老艺人吴某某(78岁)的电话访谈。访谈时间:2021年4月20日。演武松的演员回忆过去演出结束全场老少给武松行大礼,“头都要把地挖个洞”。他们认为演戏是一种享受,演好官观众说“官像这样就好了”,演个坏人“脸都会被梨核打肿”。访谈中,演员多次强调“掌声拍得不歇气,谢了四五次幕,这是百姓给你的光荣”(35)据笔者对小莲花花灯艺术团演员李某某(70岁)、郭某(65岁)、小张(62岁)关于演出感受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2月10日。访谈地点:呈贡区文化馆排练教室。,“伟大”“享受”等词汇被多位演员用来形容自己唱灯的感觉。笔者调研过的花灯戏班中有成员从16岁开始40多年没有在家中过年,但仍然乐此不疲,“玩灯”带给他们巨大的成就感,他们自身的价值在唱花灯的过程中得到实现。
“玩灯”现在已成为当地人获得身份认同的方式之一。呈贡区老年大学2018年被列为市级“非遗”传承基地,2019—2020年全区开设花灯班185个,招收学员4610人,聘请教师24名,(36)参见昆明市呈贡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呈贡年鉴》,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实现了全社区覆盖。教师中除了专业演员,大部分来自普通农民。社区老师说:“刚被占地的时候,我没有文化,只能帮人种地或到餐馆端盘子,我从来没有想过老校长能让我成为老师,获得收入和 ‘面子’,我接触的老师都是国家演员,社区的学生很尊重我,我特别珍惜这份工作。班上的学生打工的多,她们帮人收菜20元一工时,但是每次演出买衣服都很舍得,每次活动都很积极。”(37)据笔者对呈贡区老年大学教师邵老师(42岁)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4月8日。访谈地点:呈贡区老年大学排练室。从上述话语中可以看到,普通农民通过“玩灯”获得了新的社会角色——老年大学教师、学生、文艺工作者、抖音网红。通过“玩灯”人们获得了体面,这种“面子”体现的是身份的被确认。
除了弥补自我身份的迷失,“玩灯”还具更深层的社会交往意义。方李莉认为,要把乡村价值放在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共生的视野中,“修复乡村价值”就是修复乡村秩序、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8)参见方李莉《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民族艺术》2018年第1期。这主要体现在重建熟人社会方面。呈贡历来有“过年不唱灯,牛死马遭瘟”一说,这个风俗持续至今。“玩灯”作为乡村共同情感及传统信仰的载体,它将演员个体嵌入戏中,演员产生了唱好戏的责任和义务,唱一次春台戏村委会付报酬2000—3000元,平均到每一位演员每一场不超过20元,但人们仍积极参与。学习过程中以身体接触示范的方式学习,增进了演员间的亲密感情,加上排练活动中以共同交流、集体创作的方式形成完整的表演,音乐和肢体接触带来的刺激使得成员之间产生在这一社区生活中特有的情感,这种情感又渗透到生活中转变为信任,弥补了原有社区物理空间改变后的人际关系疏离。排戏过程中,花灯演员以“大哥、大姐、小妹”相称,团员在排练中倾吐自己的困难,团中遇到成员婚丧嫁娶都相互帮忙,各个社区花灯团队还自发组建了“呈贡花灯协会”,协会花灯爱好者之间形成了基于业缘的人际交往圈。“玩灯”这项集体性强、凝聚共同记忆的活动,如一股不可见之力交织在生活中,将原来的乡里乡亲联系起来,修复了曾经断裂的人际交往的网络。在传统的礼俗影响下,不演出的人也会围观唱灯活动,每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的唱灯更是被推上高潮。春节期间由呈贡区政府组织的花灯惠民演出超过30场,还不包括各个社区自行组织的50余场演出。(39)资料来源于笔者2018年1月对呈贡区老年大学花灯唱腔班统计数据。演出次数数据来源于昆明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公共文化处,2019年1月。每场春台戏少则百人多则五百人以上观看,有观众说“看电视不如看灯好玩”。“好玩”还源于春台戏演出现场的年味。鞭炮、锣鼓、音乐刺激听觉,舞台前点燃的清香刺激了嗅觉,舞台表演刺激了视觉,年货小贩随处可见,无不使人感到热闹欢腾,身体和情绪均融入了这充满春节仪式感的空间中,这唤醒了人们在原村庄中的共同情感,而社区的社会秩序反而在这热闹狂欢的气氛中得以建立。这正是民间艺术“艺”的功能——从情感、娱乐的维度弥合社会群体的离心力(40)参见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与此同时,群众的思想认识在这样的艺术体验中获得了提升。花灯戏的演出内容除了才子佳人的还包括妇女权利保障、赌博的危害性、抗击疫情等内容。“一声鼓儿孤,好女嫁不着好丈夫,自从嫁着你,没得着一尺鞋面布”形容了好赌家庭的悲苦,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唱词至今流传不衰;呈贡举办“讴歌生命·抗击疫情”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群众广泛参与,其中花灯歌曲《神州打响防疫战》用群众熟悉的走板调编写防疫知识、歌颂医务工作者,被花灯爱好者在微信圈中广泛转发。加上表演花灯戏的演员和观众通常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大家情感上很容易打成一片,每个人都成为正能量传播的参与者。大政方针被融合在大家喜闻乐见和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剧目中变得既通俗易懂,又带动了剧场中所有人审美情感的生发,人们的自主意识获得了调动。审美感官体验在民众和政策间搭建桥梁,把文化认同培育、社会秩序的重建融入了有“地方感”的戏剧中。
中国文化有温度,讲“人情”;中国人生活中崇尚自然融洽的游乐态度,追求有烟火气息的社会生活。“玩灯”之所以能够以礼俗文化培根筑魂,是因为呈贡有花灯的土壤,这也是前文分析到的特定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审美知觉和审美活动中的共同情感、社会关系所发挥的作用。“玩灯”的身体感唤醒了人们的身份认同,提升了人们的思想境界,增强了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促进社区凝聚力的形成。感官人类学主张立足于内在感知、关注身体经验,通过对身体、自我和世界的关照来理解社会文化在生活世界中的建构,以“好玩”的身体感作为一种研究社会治理的视角,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的回应。
结 语
在感官人类学的分析框架下,身体感成为人们理解社会文化的工具。花灯戏的艺术感官体验承载着社区人们的信仰、习俗、集体情感、价值追求,成为社区共享的情感纽带。城镇化进程中,“玩灯”唤醒共同记忆,加强了集体凝聚力,在营造热闹开心的氛围中恢复和激活了乡村伦理精神并达成修复乡村文化秩序的目的,从而助推乡村社会治理。
对感官的重视其实是对主体的强调,感官人类学所关注的身体体验、感官体验形成的过程、情感经验呈现出主体的自主能动意识,其在未来的乡村振兴中尤其重要,能充分发挥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乡村振兴和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相关政策中均有体现。透过对“玩灯”的艺术感官体验与社会治理关系的分析,我们看到艺术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当下提出的建设乡村文化“自我供给”系统正是需要从乡村文化的基本特色出发,满足村民的主体意愿,才能提升其文化建设的质量与服务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