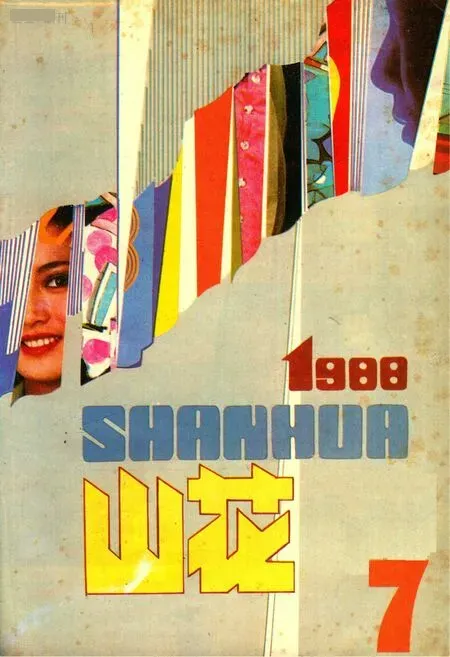文学机械论与美国浮世绘
黎幺
一
在文学世界当中,存在着一个普遍但未必合理的现象:那些声望最高、名头最响的作家,在他的时代过去之后,很容易被遗忘。即使他的生平仍旧是不错的谈资,他的作品却不再受到重视。文学作品的历史评价从来都与“公正”无关,而且也从来都不是恒定不变的。时间是某些作家的天使,对另外一些作家而言,则是喜新厌旧的妖魔。无论读者或是评论家,总像是一些任性的地质队员,在勘测一个时期的文学矿藏时,偏爱发掘“遗珠”的乐趣,宁愿不辞劳苦,向更幽深更隐秘之处钻探,对于陈列在历史表层的精妙与壮观却往往视而不见,甚至故作不屑。
作为一代短篇小说巨匠,欧·亨利也没能成为极少数免于蒙尘的旧时珠玉。但他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易用三言两语概括。事实上,自欧·亨利离世至今,已超过一百一十年,他的作品始终有庞大的读者基础,但似乎从来没有得到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他的不少小说被中学和大学的文科专业列为必读材料,但当代作家中很少有谁将他奉为自己的文学偶像,更罕有人承认与他的承袭关系。
欧·亨利曾被誉为“美国短篇小说之父”,这固然是一顶华丽的高帽子,但尊敬多于赞赏,而且还隐约暗示了文学的俄狄浦斯情结。他的同龄人契诃夫至今仍被认为是短篇小说艺术的巅峰,甚至可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若将两者进行对照,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荒谬的印象,似乎欧·亨利是一位古早时期的前辈,德高望重但老朽不堪,尽管他作品中的角色和背景往往现代得多,时髦得多。
“时代局限”当然是一个常见的托词。然而,一名作家真的可以“超越时代”吗?他有必要“超越时代”吗?“超越时代”算是文学的核心任务吗?这一系列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回答,也无法简单地以“是”或“否”作答。事实上,以所谓“超前”称许作家及其作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显得十分轻率,它以看待日常生活的线性时空观来看待文学,遮蔽了文学经典化逻辑的吊诡之处,遮蔽了解读和评论的主观性——它们常常并不是由作品驱动,而是由解读者的目的驱动的——从而也遮蔽了直接、鲜活的阅读经验。
几乎所有作家都梦想着进入经典的序列,然而,极少数得偿所愿的佼佼者并不能充分代表其所处时代的文学面貌。文学史的叙事容易给人造成两种典型的错觉:其一是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直在沿着某种轨迹发展前行,每个时代均有各自鲜明的文学风气;其二是文学的发展总以某种方式呼应了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变迁。
然而事实上,文学的各种类型早已相对固化,在此基础上,出版与阅读的习性也已逐步形成,新理论新潮流固然层出不穷,但对文学版图的冲击极小;文学史的线索也绝对谈不上清晰,如若它显得清晰,那也更多是依据事先确定的框架进行人为筛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本身就是对随波逐流的抵抗,它与时代的映射关系绝不体现在浅层和表象,而就精神的基底而论,人的变化其实极其缓慢,也极其有限。乔纳森·弗兰岑[1]或者丹尼斯·约翰逊[2] 等当代作家笔下的美国人和欧·亨利小说的主角其实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差异,只是被选择性地呈现了不同的面相。
有关欧·亨利文学成就的争议其实从他成名开始便一直存在,而且从未有任何能够解决的迹象。这些争议或许会被搁置,但不可能被遗忘,因为它们关涉到一个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问题。原本为阅读而生的文学自发展出专门的学科、专业的机构和人才之后,便出现了这个问题:普通读者(在经济原则下,这个词常常被置换为另一个词:市场)和专业研究者,究竟谁才是文学的主体?
大多数读者非但没有为极少数文学家加冕的权力,也没有这种意愿。文学价值的评定一直是大学教授与专业评论家的分内事。他们自认是万神殿里的大祭司,而读者则只能充当不问情由的虔诚信众。可出人意料的是,越来越多的读者不愿再承受庄严的重负,比起进殿瞻仰,更乐意在殿外徘徊观望。
欧·亨利曾经被抬到了神殿的台阶上,但终于还是被摆在殿外的广场,而如今,那里也许是人流最为密集之处。换句话说,如果将目光从专家学者们的权威意见上跳开,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欧·亨利式的小说至今仍旧是文学的主流。
二
对于欧·亨利的常见评价,无论褒贬,总会采取一种简单的二分法。《剑桥美国文学史》称欧·亨利的作品“妙趣横生”,叫人“眼花缭乱”,但只是“雕虫小技”而已;评论界巨擘哈罗德·布鲁姆则说欧·亨利“喜剧天赋突出”,“笔触细腻”,但算不上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主要创新者”。
两者其实如出一辙,只不过布鲁姆还补充道:“最重要的是,他留住了一个世纪的观众:众多读者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不是更真实或更离奇,而是正像他们自己的现在和过去。”
哈罗德·布鲁姆的评价大体是公允的。而所有针对欧·亨利的贬低和轻视也并非毫无来由,对于理解其人其作,亦具有一定的分析价值。但毫无疑问,欧·亨利对世纪之交的美国所作的全景式描绘,对不同年龄、阶层、职业、地域的数百个角色的精确刻画,体现了宏大的社会视野,丰富的人际观察和高超的写作才能,这很难和“雕虫小技”划上等号。
与“小技”之说异曲同工的是,许多评论家将欧·亨利的作品定义为一种“高级消遣”,显然有意在他和“严肃文学”的“正典”之间划出一道鸿沟,但在执行这一动作的时候,又显然不够坚决。那么,他们究竟在犹豫什么?
首先,哪怕言必称“纯文学”的原教旨主義者也不能完全否定文学的休闲用途,何况从亚里士多德到叔本华,无数思想家均肯定了“闲暇”的价值,可以说,人类的精神成长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消遣”中实现的;其次,专家们恐怕都得承认,哪怕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也颇有些“消遣”的成分。再者说,诸如查尔斯·兰姆的《伊利亚随笔》之类本就是“消遣文章”的作品,也早就登上了英语文学的大雅之堂。所以,“消遣”一词本不能构成一种指控,甚至都算不上一个指责。除非,给予欧·亨利以负面评定的学者们都意识到,他恰恰在“消遣”之外具有重大的价值,很可能还对他们一贯享有特权的文学领域产生了某些显著的影响。惟有如此,这一否定才有实效可言。
的确,欧·亨利很少在作品中讨论人性的复杂和伦理的困境等文学传统的重大母题,更不会用他那些篇幅短小的故事探索终极意义。此外,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缺乏深度,他笔下的罪犯不会像拉斯柯尔尼科夫[3] 那样进行痛苦的自省,他笔下的农家姑娘也不会像苔丝[4]或艾玛·包法利[5]那样具有人生的悲剧意识(仅就这一点而言,哈罗德·布鲁姆已经为欧·亨利作了辩护。其实,一代又一代文学名著中的主人公从本质来说,大抵都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一直在按照知识分子的想象和需要反映某种典型的精神处境;多数普通人的人生却始终懵懂而平静,虽说难免有些波澜,但终将会过去,也终将与他们自身一起被人遗忘。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钟摆》便是一个与此有关的寓言)。
这显然是他被诟病的主因,但前提是,他无法仅仅被当作一个供人“消遣”的通俗作家来对待。单从欧·亨利的作品被众多创意写作课程列为必读材料这点来看,这一前提无疑是成立的。可问题是,这导致了一种极其荒谬的矛盾和断裂:似乎欧·亨利必须被学习,但不值得被鉴赏;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将欧·亨利的小说比作一杯醇酒,那么人们所做的无异于把酒倒掉,只拿走华丽的酒杯——他们关心的是欧·亨利的方法,而不是欧·亨利的作品。这一买椟还珠的行为固然粗暴,但也揭示了真正的核心问题:问题恰恰在于欧·亨利的方法得到了太多的关注,受到太多人效仿,而过于强调所谓“欧·亨利式的结尾”或“欧·亨利式的幽默”有让文学创作公式化的风险,或者说,有让文学陷入机械论的危机。
因此,将之贬低为“雕虫小技”似乎确实有必要,以缪斯的尊严为名,也似乎确实是一个堂皇的理由。
我无意再为欧·亨利辩护,但事实上,在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众多范式,它们以或隐或显的形态影响着每一代的创作者。一种范式的出现,就像是为“文学之泉”筑坝导流,非但不意味着僵化的风险,反而恰恰是生命力的体现,结果只会使文学的流向更为灵活多样,因为,对个性与风格的追求永远是最重要的创作动机。
此外,一名艺术家最大的优点往往也是他最大的缺点,反之亦然。欧·亨利的小说也许并未推进对于人性的认识,但却给了平凡的人生以更多的共鸣;与哲人式的深邃相比,他的幽默和机智也更易收获普通读者的爱戴。至于文学艺术理应给予人的升华感,在《麦琪的礼物》的隐喻中或《警察与赞美诗》的转折中,也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当然,他过多地借助了巧合,而非人物的合理选择来推动故事情节,这使他的不少作品在贡献了阅读快感之余,鲜能引发进一步解读的欲望。可以说,他在文学的技术性与普适性上做到了极致,在超越性方面却存在欠缺。然而,欧·亨利一生的小说作品近三百篇,类型多样,风格多变,其中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和思想上均有突破,绝不能一概论之。例如《咖啡馆里的世界主义者》这样的讽刺作品,放在任何一位大师的小说集中都足够犀利新颖。
三
对待欧·亨利这样的作家,最合适的做法绝不是离弃,而是更充分地阅读其作品。对于读者来说,真正应当避免的是在理解层面的“文学机械论”。
事实上,任何人在细读之下,都很难忽视欧·亨利在文体上的努力,他的修辞丰富,描写精当,对简洁铺陈和繁复织构都得心应手,这使他的小说往往从头至尾都散发出极强的感染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几乎用短篇小说这种积木块般的“小体裁”搭成了像《人间喜剧》那样宏伟的文字建筑。如果说巴尔扎克创作了一系列庄严的古典油画,陈列在一间壮丽的画廊里;那么欧·亨利则以近三百幅形形色色的浮世绘展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两者至少在广度上不相上下。若单论这一成就,至今也没有其他短篇小说家可与欧·亨利相比。而他的一些天才式的发挥,也对之后许多重要的小说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比如只有短短几页的《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便预示了着力表现美国梦破灭的战后一代作家的风格和题材,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塞林格和雷蒙德·卡佛[6];而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以拉丁美洲为背景的《卷心菜与国王》则令人吃惊地成为“拉美文学爆炸”中一系列政治小说的先声(这部群像小说常被算作短篇小说集,其中一些独立性较强的篇章,例如《海军上将》,绝对是技艺高超的杰作)。
值得一提的是,欧·亨利的全部作品所呈现的最终图景,有可能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至少在他的文学生涯初期,不可能萌发这样浩大的动机。而这一幕罕见的文学奇观之所以能够形成,必定和欧·亨利虽然短暂,但丰富得出奇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在人世仅仅生活了四十八年,却从事过药剂师、会计、牧羊人、厨师、经纪人、出版商、歌手、戏剧演员等十几种天差地别的职业,甚至还遭过几年牢狱之灾;在美国南部的乡镇、西部的平原,以及最繁华的大都市,他都曾安过家,为了避祸,他还曾逃往中美洲的洪都拉斯;他与形形色色的人有过来往,其中包括社会名流、新闻记者、流浪汉、农场主、底层雇工、各地移民、印第安人等等。
这样的人生几乎不可能复现,对于欧·亨利的创作而言,自然是得天独厚的资源,加之他在几千字的空间里辗转腾挪的过人本领,使得对他作品的阅读如同观赏一场人类生活的博览会,能够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智识享受。而有志于文学创作的读者更需要多读、细读欧·亨利的作品,他的几本小说集题材、风格各异,但均体现了极强的叙事技巧,是天然的文学教科书。
总而言之,已经被称为“经典”的欧·亨利小说其实并未完成他的经典化进程,但这对于作者而言并非不幸,这意味着对他的阅读与争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也意味着,在文学的天空下,欧·亨利的時代不但远未结束,很可能还在来临之中。
注释:
[1] 乔纳森·弗兰岑,美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纠正》《自由》等。
[2] 丹尼斯·约翰逊,美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烟树》、短篇小说集《耶稣之子》等。
[3] 拉斯柯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4] 苔丝,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的主人公。
[5]艾玛·包法利,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
[6]塞林格与雷蒙德·卡佛均为以短篇小说知名的美国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