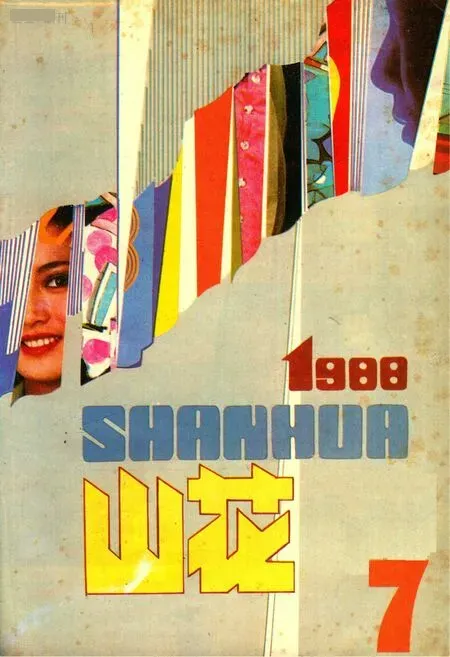摄影,重要的是情深而不是景深
杨安迪
今天的摄影已从传统影像时代全面跨入数字时代,但摄影胶片却从未完全消失,伴随着职业摄影师和艺术家对摄影的不断探求和思考,胶片这一材料越来越受到职业摄影师和艺术家的追捧。
银盐时代胶片作为记录影像的介质和载体,是保存影像的原始材料,新一代的摄影者对这一材料的认知越来越少,因而失去了对它的使用和表达。
尽管如此,在摄影史上,还是出现了许多利用这种感光材料进行大胆创作的摄影家,如曼·雷、哈尔斯曼等将传统影像用于超现实主义创作,但终究没有实质性地摆脱传统影像的观看与表达。
直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后,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英国艺术家吉尔伯特与乔治利用影像创作出的大量作品,彻底打破了摄影与其他艺术的界限。安迪·沃霍尔使用照片进行丝网印刷,利用宝丽来一次成像相机进行拍摄,原本只是用于旅游和家庭快照的一次性小尺寸照片相机,在艺术家的手上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展示形式。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用照片拼贴的艺术作品,改变了人们对摄影传统机械复制的看法,并开始重新审视摄影艺术创作与表现。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安塞尔姆·基弗在他的装置作品中,大量使用废墟照片,成为其作品重要的表现元素。
我一直使用传统底片拍摄时代变迁中的工业遗迹和废墟,其中也包括拍摄城市发展变化下各种文化的消失,如街道的改变和老建筑的拆除等等。
同时期我也在工作室创作了大量关于“花”的系列,力图通过“制造”表现“生命”在不同色彩、不同时间、不同情绪下的反应。在这些创作中,我尽量主观介入,大量施予观念表达,并强调个人情绪的释放和表达。批评家们认为这一类作品具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特征。
以花为媒进行创作,最早起源于 2014 年。那年初春,我突然得知远在异乡的友人患了绝症,不久将离世,心情万般失落。我惋惜她年轻的生命即将就此结束,而彼时正值人间最美四月天。也就是那一年的夏季,我和几位好友在贵阳举办了一场名为《五只机》的手机影像作品展。展览最重要的策划,便是邀请病危的友人参展。我至今也无法忘记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拍摄的每一张影像,那是她对生命和死亡最直接的诠释。
而我参展的那组《花》系列和那些我女儿快乐的生活照片,正是我最想表达的关于生命的一切。也就是从那这个时候开始,我正式开启了用花作为题材的系列创作。
坦白地说,在此之前,我从未以花为媒进行过创作,尽管我知道许多摄影大师都曾以花之名,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对我而言,面对任何不能触动我心灵的景与物,我是无法按下快门的。我一直认为,激情是一切艺术创作最原始的动力。
红色系列是我创作中最疯狂的一次摄影行为。白色的玫瑰被我一束束染成红色,摔打在白色的工作台底板上。红色的黏液溅在我的脸上和白色的衬衫上,也刺向我的眼睛。我一边拍摄一边拍打着底板,让花瓣在空中飞舞。我甚至用手捧着它们拼命地大喊着:“坠落,再次坠落。我要在空中起舞,我要在光中歌唱。”手上的相机在不断地颤抖,取景框里沾满了泪水,我不停地按动快门,闪光灯像白色的闪电;而视网膜前,却是一片混沌的红色。
在这个系列中,我还时常在荒野和废墟中寻来各种旧物和奇花野草,精心安排它们,直到接近我要表达的情景出现。我从不相信所谓理想的场景会自然出现,一切只为你发生,就像红色不仅仅包含激情、勇气与力量。而此刻,我只想说:“别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因为我只想寻找自由和快乐。”
在不断撕扯对峙的情绪中,花卉、枯枝、液体、燃烧后的人体图片,它们经由摄影台上的重组与分裂、灯光下的再造与创造,使我重新回到胶片的介质中。
胶片是一种柔软的,极其脆弱的材料,它同时也具有负像、正像,黑白与彩色影像特征。胶片统治摄影上百年了,也提供了基于材料属性的特殊美感,但是它也是易燃烧的材料,由此我发现了它脆弱的质感将给二次创作带来机会,如火药和色彩正片的相遇,产生新的色彩变化,如原有的影像在火药干預之下的再次诞生。对我来说,火药之下的干预就仿佛是脆弱的神经遭遇攻击,原有的影像将再次浸入我的想象与幻梦之中。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想做的就是刺痛观看者们的视网膜,那些胶片中隐隐约约仍然保留下来的人体形象原来具有古典美学的风格,也具有饱满的令人愉悦的美感,可是现在却通体疮痍,我期待着以溃败唤起人们对于生命易逝的不舍与思考。通过直接的形象破坏来实现观念的表达,也通过形象的再造实现生命的感知和情感的释放。它的平面也同时具有了全新且独特的肌理,繁复的色彩、紧密的光点,把摄影的情感书写带入了直观的场景之中,这是一种双重的表现,既是具象的挪用,也是对“形象”的解体,由此我也不再为追叙某种观念而犹豫不决。
我理解,“表现主义”大概也可以这样来做。
我发现在工作室里有着太多的可能性,那些火药,那些枯枝、落叶,液体、灯箱、复印机、照相机,随手可触的破碎影像,只要放置在光与黑暗之间就会产生出来异常丰富的图像。制造,再制造,它们慢慢地就成为了另外一个世界。突破照相机/胶片美学,通过重组、拼贴和施于实物等手段,让潜在的真实影像和枯枝,花瓣和其它实物等形成新的维度空间,我因此发现了影像艺术更多的创造空间。此刻的工作室,不再是实现经典胶片影像的传统暗室,而是成为了一个情感与心灵表达的全新的世界。它帮助我打破了固有的影像认知,特别是当我在胶片上反复烙烫线条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某种直接的快感,表达出我内心潜藏着的残酷和不安。在工作室里创造,我知道自己成为了一个行动的艺术家。
真实的影像记忆被化为多维的、错乱和复杂的生命记忆。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不断重复现场、回忆、幻想和恐惧,从而获得安慰和解放。这些原始的影像并非来自素材,而是有着独立的语言和表达的作品,但它已不能满足我最终创作的需要。于是它们在工作室里被重新释放,以不同方式,不同现象探索其可能性、未知性,这一过程让人着迷兴奋。在燃烧过后的空洞里施以颜色,在崩溃的形象中施予覆盖,在颜料和其他混合物的混合之时,我观看着那些气泡的侵染,仿佛就是在一点一点地让原本无生命的平面影像产生活跃的生命细胞,他们仿佛在酝酿着新的突破和再生,因此它们也产生出强烈的视觉差异。在工作室里,我由此也感到了自己的眼泪与呼吸前所未有地浸入在眼前的图像当中。
有意思的是,当代很多艺术家也喜欢工作室模式的影像创作、影像拼贴、算法虚拟、互联网截图、地理图像改造、装置化影像、观念摄影等等,都在冲击着传统的摄影美学,我似乎看到了一种新型的摄影美学缓慢却汹涌地到来。我把这样的工作方式称为“工作室美学”,它与所有的类型艺术家工作室异曲同工,它也是胶片时代暗室空间的承继,但是它是更加自由的空间。光,在这里面熔炼了所有事物,就如维利里奥说的那样,它会建构起一个异样的世界。
与很多工作室影像作品不同的是,我在工作室创作过程中更在意情感的自由抒发,也更在意真诚的心灵流露,我这些“再造”过的既是具象的,又具有强烈的构成性和抽象意味的图像,就是我所称的“工作室美学”的结果。它是独特的表达,自然也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和挑战性,因为它让我发现,工作室中产生的摄影艺术可以与我内心那些翻滚不息的涌动跳跃在同一个频道上面。
对于我来说,摄影总是在爱与恨的交织中进行,镜头中的爱,是何等的圣洁与高尚,又是何等的刻骨铭心与澎湃汹涌,摄影就像玫瑰或子弹,温暖而残酷。这时候,我想起了伟大的摄影家皮特·亚当斯说的那一句话,他说,“对于伟大的摄影作品,重要的是情深,而不是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