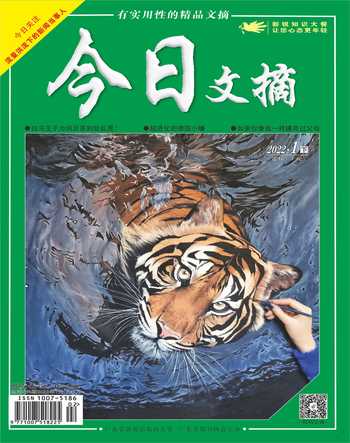哀乐中年
钱红丽
与多年未见的朋友重逢,她脱口而出:哎呀,你胖了。大约怕我难过,末了添一句:以前的你太瘦了,还是胖点好,不显老。
中年最显著的标识,无非发胖。
我这么克制的人,实在不应该啊。一见镜子里那张烧饼大脸,直想刮几耳光。
脸上肉多,格外蠢相些。
不服老?身体首先给个下马威,基础代谢功能刹车。小时,许许多多的美味,想而不得。如今,鲍翅飞龙,自由尽享,却要拼命节食。
生命两难,无非——得不到,已失去。尝试过各种减重,核心课题无非减少碳水摄入,谨慎而食。三四个月后,某日取快递,往菜鸟驿站磅秤上一站,静止的数字令人魂飞魄散,何以又重了三斤?
整日焦头烂额,操不尽的心,烦不完的神,应该消瘦才对呀?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过是人到中年,机体代谢缓慢。
这些都不算什么。不过是自身的囚笼,自困自解。最难以面对,是愈来愈糊涂的双亲。
前阵,回小城给老父做了八十寿辰。去年,老人开始旁敲侧击,装着无意间提起,谁家子女为父母做了寿,姐弟仨风尘仆仆,自北京、成都、合肥趕赴小城,就为了给老人摆一桌席,称他的心如他的意。电话沟通回芜行程时,隐约听见母亲在那头埋怨:他们上班那么忙,做什么寿喔。这回,这名老人又如此体恤开明。可是到我回家后,临离开,在她卧室窗台惊鸿一瞥,多瓶未撤包装的保健品猎猎一排。轰隆一声,我的脑子似被迫击炮击中,火自肝中来,到底忍住。
她送我下楼,我苦口婆心:保健品真不能吃,不仅不能让你的身体变好,其中的毒性反而伤肾。你明明可以活到九十岁,到时毒性导致肾衰竭,得不偿失,花冤枉钱事小。我话音未落,她蓄势待发反戈一击:可是的嚎,谁谁谁在电视上说,要大力发展中药。实在难以双盲实验等科学知识去说服一个奉电视为神明的母亲。
我这位母亲一辈子节衣缩食,如今采买食品,还都热衷于下脚料,隔日的叶类蔬菜,发臭的带鱼死虾。以她的理论:蔬菜蔫了水里泡一下,一样吃。死了的鱼虾也是鱼虾。她用这些节省下的钱,令人发指地买回保健品,上千上千地往外支付。
神将一根扁担压在我中年的肩,这头挑的是父母,那头挑的是孩子,不,是孩子的学业。有时,实在锥心。前年深秋,在小城正定拜访隆福寺,一尊高及屋顶的千手观音座下,压着四尊大力士,驼的是千万斤之累。寒风里,我摸摸这四尊佛,也是无言的体恤。
我这么一个孤弱身躯,何以敌得过力大无穷的佛?谁来渡我?简直悲不自胜。
去年,母亲动脉瘤手术,急急赶回,留孩子一人在家忙于功课,远程给他点外卖。等她推回ICU,已是夜深——这头老的,不省人事;那头小的,从未离开过大人独自过夜。
开车疾驰于芜合高速,打开家门,早已凌晨,一向怕黑的小人儿,亮着家里所有的灯,沉于酣眠。
苏轼有诗: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只有,唯有,活至中年,方能体悟这诗的悲意,遍地凌寒,雪满荒原。路还长,我就是那匹“蹇驴”,偶尔崩溃边缘嘶吼几声,家人赶忙起身关窗。前后左右邻居皆出自同一系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中年,真是挂霜的年龄,挺住了,就也不倒。一夜风紧,举目四望,无以御寒。
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耸耸我肥壮的双肩,投入至工作的鏖战搏杀中。
多年以后,忆及种种,也不过小事一桩桩,何哀之有?海子诗:亲人们呐/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一代代,都过来了,还有白发苍苍的晚年。
这一生,也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