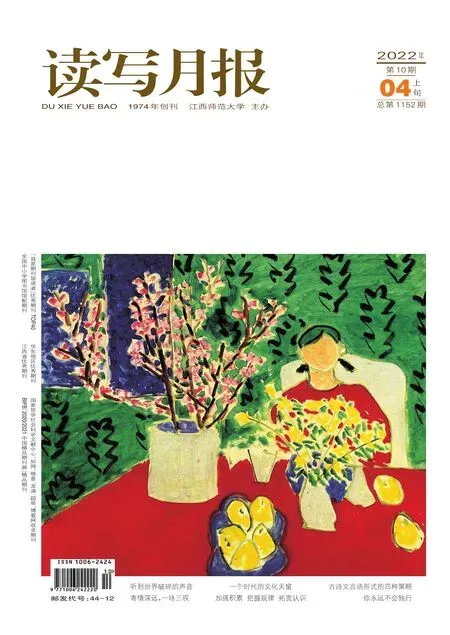一个时代的文化天窗
——《露天电影》导读
柴育斌
方心田的散文《露天电影》,留存的是一代人的记忆。露天电影让人们享受到了寂寞中的激动、静默中的呼啸,还有无边的憧憬……露天电影,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天窗。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向内的文化给予是多么重要。因为,一个人活着,除了必须吃喝住穿,精神方面需求的满足,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20 世纪70 年代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还是落后、封闭的。“发电,在农村可是个稀罕的活。那时,村里点的都是洋油灯,连蜡烛也少见,一般人家用不起。”这无疑是最真实的记录。那个时代是落后的,因而也是寂寞的,晚上家家户户都习惯早早地吃晚饭,为的是趁天黑之前打理完各自的事情,以免到晚上点灯多费煤油(洋油)。做完了手头上的事,即便要聊重要的事,也不愿点着油灯聊。如果是夏天天气好,会选择到院子里,借着月光或星星的光去聊。天气不好的时候,则在屋内黑灯瞎火地聊或者选择早睡,漫漫长夜就在寂寞中度过。
村里要放露天电影时,那当然是让精神寂寞的人们最激动、最期盼的时候:
“有电了,小竹竿上的灯泡就亮了,亮得刺人的眼,亮得眼前有一片黑压压的晃动的人头,亮得‘面前畈’里黑糊糊的啥也看不清,亮得天上的星星也不好意思地躲了起来。”
这份惊喜让人们“不安”起来,让星星害羞起来。因为相对于煤油灯光,电带来的光是灵光,它代表着先进的工业文明,而这只有在露天电影到村里来时才享受得到。这是露天电影打开的第一扇天窗。

露天电影未到村里来时是怎样的情况,方先生没有写,但是我们从放映前村民等待着的那段时间的表现可以想见:
“一脚踩住形似一头小黑猪的发动机,一手捏住转轮用的脏兮兮的油布带,猛然使劲一拉,那‘小黑猪'就‘突突’了两声。不行,再来。老放映员再踩住‘小黑猪’,缠好油布带,使劲一拉,‘小黑猪’又‘突突突’了三声。还是不行。我的心也随之‘突突突’起来,千万不要坏了呀!我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这时,老放映员猛抽了两口烟,鼻孔里喷出两团烟雾,然后将烟头扔掉,用衣袖抹了抹脑门上亮津津的汗珠,往右手心里吐了口唾沫,两手搓搓,再踩,再缠,再使劲一拉,终于,‘小黑猪’在众人的紧张期待中,‘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地叫个不停了。我们都长嘘了口气,立即欢跳着散开了。”
这段死去活来、起死回生的发电过程,就是众人从静默到呼啸的过程。对电的好奇、渴望正折射出平时乡村人们的生存状态:过着太过静默的生活,对外界一无所知。他们不懂发电机,不懂得除了传统农具、农作物和家畜之外的事物。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十分渴望新事物的降临。不仅是物质上的新鲜玩意儿,人们更渴望有一次精神的盛筵,能给他们提供释放、交流、宣泄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露天电影给他们开了又一扇窗:
“灯亮了,意味着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观众们显得更加喧闹、急切,各种噪声都有,找人的、寻位的、打情的、骂俏的,都蜂拥着挤一起了。”这打情骂俏的年轻人(也包含部分中老年人)太需要这样一个机会了,“电影放映时,不仅本村本寨的人会齐聚一堂,四乡八里的外村外乡人也会赶集似的潮涌而来,更有那些后生村姑,招蜂引蝶,乘机拉拉手、摸摸腿啥的”。
这些俊男靓女的这些有点“出格”的行为,谁说不是从露天电影里学到的呢?静默的血脉在呼啸中偾张,应该感谢露天电影给那个时代注入了人性的血清,让一个时代渐渐苏醒。在那个文化生活贫乏、外部传媒多半付诸阙如的年代,露天电影充当了孩子们的精神导师,也给其他不同年龄段的人提供憧憬的种子和精神指引。
“我们喜欢把电影中的人物分成好人与坏人两种,一有人物出场,我们就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而且基本能判断准确。因为影片里的好人一律浓眉大眼、高大英俊,坏人一律歪嘴斜目、凶神恶煞,就是三岁小孩也不会弄错。”
“从黑白到彩色,从单一的战争反特剧到古典现代剧,从本土片到进口片,从免费看到买票看,我们的露天电影生活,在那由白变黄的银幕上变化着、变化着,而我们这一代人也在这流水潺潺的变化里嬉戏着、成长着。”
诚如方先生所言,露天电影是物质严重匮乏、文化消费荒凉贫瘠年代的缩影,它留在那一代人心中的记忆,虽然不无温暖与欢乐,但在今天看来,也存在诸多缺失。孩子们从露天电影里开始道德和审美的启蒙,接受英雄主义的熏陶,学着区别好人坏人,自然有了基本的是非判断,打上了崇正抑邪的精神底色;但这样的教育无疑带有脸谱化、简单化的色彩,是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的。在岁月流淌的几十年间,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小康,正走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途上,露天电影也成了历史的记忆。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的发展不只是要修路架桥盖新房,还需要好的社会服务,需要全面提升教育、医疗、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质量。我们期盼,我们相信,上下同心,全力推进,“众手浇开幸福花”,乡村的明天会变得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江西省万年中学)
【原作】
露天电影
方心田
村前有块阔大的场地,类似城里的广场,我们叫它“面前”。场地过去,有口弯月形池塘,我们叫它“面前港”。池塘过去,是一马平川的田野,我们叫它“面前畈”。小时候,我最喜欢听到的消息就是今天夜里,“面前”演电影喽!放电影,我们叫作演电影。因为有人儿马儿在那白布上面跑啊跳啊,哭啊叫啊,难道不是演吗?下午早早地放学,挎上书包就往“面前”跑。干啥呢?电影还没开始呢。是没开始,我急着看大人埋电影杆子呢。“面前”早已聚了不少人,多是看热闹的小伙伴。有两三个大人在“面前”兴奋地忙活,一个用铁锹挖洞,洞边上堆有新鲜的土;一个用草绳绑扎摆成“门”字状的两根碗口粗的杉木和一根晒衣用的竹竿。扎好了,几个大人就“嗨”一声同步扛起两根木头,使它竖立洞中,再往洞里填上土,踩实了,摇摇,不动,一个两丈来高的“门”字就写在了场地上。在“面前畈”干活的人大老远看见这个“门”字,就知道晚上有好事儿了,会急急地收工;路过村子的外乡人看见这个“门”字,或听见演电影的消息,会把音信如禾种一样撒向四面八方。
杆子埋好了,我们就望眼欲穿地等待那个我们眼熟的秃顶放映员来。说实话,那时候我们的心里大都有个粉色的愿望——长大了当一个放映员,或者放映员的徒弟也行,这样就可以天天看电影。眼睛差不多被望穿时,那个秃顶的老放映员和他年轻的徒弟就一前一后骑着自行车来了,自行车的后架上分别载着一个木箱子和两个铁盒子。我们知道,铁盒子里装着电影片子。什么片子呢?我们挤上前一看,盒子外面用红漆或黑漆歪歪扭扭地写了“小兵张嘎”“黑三角”。打仗的、抓特务的,好看啊!没看过的人很期待,看过的人还想看。
来到“门”字下,老放映员不慌不忙,抽着大队干部发的香烟,寒暄着。他年轻的徒弟则从脏兮兮的木箱里端出一包床单样的白布和几根布带子,只见他将一根很长的带子朝“门”上的竹竿抛过去,可抛了几次也没搭上。这时,老放映员就会走过来,说一句“学着点,看我的”。他拿过带子,估估长短,退几步,倏地往上一抛,那带子的一头就稳稳地越过竹竿落下来。如此几次,几根带子都搭好了。徒弟赶紧配合师傅,用搭好的带子将白布上端的两角扎紧,一人拉一头,白布就徐徐上升且展开了。将长带子在木头上扎紧后,他们又分别拉着白布下端两角的短带子,同时扯紧,扎好,白布就石灰墙似的平展在大家面前。然后看他们挂喇叭。黑箱子样的喇叭被拉上去了,一切妥当,我的心才放下来,原先,我竟有点莫名的担心呢。空旷的“面前”,凭空挂起了一面藏了无数奥秘的银幕,小伙伴们都禁不住“喔喔”地欢呼起来。欢呼之后,赶紧回家搬凳子去,都要占个好位置。银幕弄妥了,放映员的事并没完。秃顶吩咐徒弟去附近人家借一张八仙桌,驮来,放在离银幕五六丈远的地方,再将喇叭上的电线拉过来,搭在和八仙桌腿绑扎在一起的一根小竹竿的杈上,杈上还吊个灯泡。弄完之后,他们就去安排好的社员家里吃派饭。
我也抓紧时间回家吃饭,洗好脸,洗好脚,换上干净衣服,和弟弟一起往衣兜里装满炒豆、炒花生或抓几截刨干净的甘蔗,就飞也似的穿巷过户往“面前”跑。这时,“面前”的人已很多了,大家都很兴奋、激动,喧闹不已。我们找到自己占位置的长凳,稳稳地坐上去,一边吃东西,一边看人流,看天色,看在晚风中微微飘动如波浪的银幕。放映员吃完饭,夜幕差不多就罩下来了。他们吸着香烟,打着饱嗝来到放发电机的地方,他们要发电了。发电,在农村可是个稀罕的活。那时,村里点的都是洋油灯,连蜡烛也少见——一般人家用不起。我赶紧从凳上跳下来,奔过去看热闹。在我们眼里,那个秃顶放映员一点也不丑,动作很是潇洒,只见他嘴角叼烟,一脚踩住形似一头小黑猪的发动机,一手捏住转轮用的脏兮兮的油布带,猛然使劲一拉,那“小黑猪”就“突突”了两声。不行,再来。老放映员再踩住“小黑猪”,缠好油布带,使劲一拉,“小黑猪”又“突突突”了三声。还是不行。我的心也随之“突突突”起来,千万不要坏了呀,我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这时,老放映员猛抽了两口烟,鼻孔里喷出两团烟雾,然后将烟头扔掉,用衣袖抹了抹脑门上亮津津的汗珠,往右手心里吐了口唾沫,两手搓搓,再踩,再缠,再使劲一拉,终于,“小黑猪”在众人的紧张期待中,“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地叫个不停了。我们都长嘘了口气,立即欢跳着散开了。有电了,小竹竿上的灯泡就亮了,亮得刺人的眼,亮得眼前有一片黑压压的晃动的人头,亮得“面前畈”里黑糊糊的啥也看不清,亮得天上的星星也不好意思地躲了起来。
灯亮了,意味着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观众们显得更加喧闹、急切,各种噪声都有,找人的、寻位的、打情的、骂俏的,都蜂拥着挤一起了。老放映员和他徒弟将放映机搬出来,摆在八仙桌上,套上片子,左弄右弄弄好了,一试机,片子吱吱地转动,还行。这时,做完家务的母亲也来了,她找到我们,和我们坐在一起。父亲一般是不和我们一起看的,他往往和别人的父亲们站一起,看电影的同时,聊聊生产队,聊聊农事;或者不来看,他有他的事情。
电影终于要开始时,喇叭里有人说话。“大家伙静一静,大家伙静一静——现在请大队书记讲话,大家伙欢迎。”这个固定环节,我们小伙伴是非常讨厌的,可是没办法,耐着头皮听呗。大队书记先清清嗓子,“喂喂”几声才用标准的土话说:“全村社员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俺们,要抓革命,要促生产……”讲了公社精神,再讲社员的生产生活,有时张家长李家短的鸡毛鸭屑也抖出来,时不时地惹出一片哄笑声。末了,他说:“哇完了,大家伙看电影吧。”电影终于开始了,喧闹声也终于慢慢退潮。小竹竿上的灯泡被掐灭了,一道强烈的光柱从我们头顶射过去,由小变大,直射到银幕上。
其实,年纪太小的时候,我是不在乎什么片子的,只要是电影就行。那时看电影就是赶个时髦,图个热闹,其实经常看到半途就打瞌睡。后来稍微大了点,看堂兄堂姐们谈论影片内容很起劲,也就注意起影片的内容来,这时电影片名和内容就成了我关注的重点。我最喜欢看打仗和反特的,像《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星》《侦察兵》《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钢铁战士》《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奇袭》等等,喜欢看解放军(八路军、红军、公安警察)怎么英勇机智地侦察情报、消灭敌人。我们管日本鬼子叫“日本佬”,管美国鬼子叫“美国佬”,管国民党叫“刮民党”,管蒋介石叫“蒋该死”。我们无不充满爱国心,无不向往当解放军或公安警察,无不想杀敌人抓特务当英雄,就是死了也觉得光荣。我们喜欢把电影中的人物分成好人坏人,一有人物出场,我们就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而且基本能判断准确。因为影片里的好人一律浓眉大眼、高大英俊,坏人一律歪嘴斜目、凶神恶煞,就是三岁小孩也不会弄错。所以,一看到八一电影制片厂那五角星片头金光四射,一听见那昂扬激奋的进行曲,我们就热血沸腾了。大概,我们那一代人浓重的阶级仇恨感及好战意识,就是这时形成的吧。后来,文化空气似乎活跃了点,影片内容也稍稍丰富了。我印象中看了不少古典戏曲和反映现代生活内容的片子,如《追鱼》《李慧娘》《天仙配》《小花》《神秘的大佛》《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苦恼人的笑》等。我们不知道,原来“四人帮”已被打倒了。
演电影,是那时乡村难得的盛大节日。开始,全县只有一两家放映队,轮到我们村,一年也许就只有那么一回;后来,公社有了放映队,一年也就有两三回。但还是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就追着放映员的屁股跑,他到哪放我们就到哪看,也不管新片老片,所以有的片子我们都看了五六遍,而且,我们不管路途远近、刮风下雨,都会兴致盎然地跑着去,兴致不减地摸黑回。我记忆中,跑去最远的地方是城关镇,离我村二十里。再后来,放映队多了,我们看电影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差不多一两个月就有一回。不仅公家会安排定期放映,而且村人自己也会想出多看电影的办法,如每年正月十五,除了舞龙灯唱老戏,还要前一年做了本村新姑爷的,合伙凑钱演电影,甚至连演几夜。后来遇婚庆寿诞上梁等大喜事,也都养成了演电影求热闹的风气。电影放映时,不仅本村本寨的人会齐聚一堂,四乡八里的外村外乡人也会赶集似的潮涌而来,更有那些后生村姑,招蜂引蝶,乘机拉拉手、摸摸腿啥的。所以,银幕正面的场地上注定是容纳不下全部观众的,就有一少部分观众要站到银幕的背面看。在本村做观众,我肯定可以在正面占个好位置,但去了外村,则十有七八站在背面看。在背面看也没啥,无非是左边的人头跑到了右边,右边的人头跑到了左边,不影响剧情,遗憾的一点就是字幕反了,不好看懂。好在那时我识字也不多,关系不大。
记忆的深海中,还有两回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公社放映《红楼梦》(越剧),冬天,在中心小学的操场上。我们四乡八里的外村人早早地就去了,操场上聚满了人。但等了很久也不见放映,一问,原来是在等片子来。片子还在另一个公社放,排队放呢,可见这是一部多受欢迎的电影。天气很冷,朔风凛冽,大人们却都在热乎乎地谈论宝哥哥、林妹妹,而我是不懂的,所以觉得很乏味,也很难挨。快到半夜了,我实在熬不住,正要缠着堂哥堂姐(我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他们去外村看电影)回家去,片子终于来了。操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打起精神一看,原来是老戏,咿咿呀呀地唱个不停。我很失望,所以很快就打瞌睡了,也不知道是怎样回的家。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红楼梦》是声名显赫的名著。还有一次是在公社机械厂的大院里。这时好像兴起了买票看电影,机械厂有现成的围墙、铁门,好把守,票价一般是五分钱或一两角钱,视影片的吸引力定价。那时人们没啥钱,更别说我们小孩子了,所以一般是不去看的,除非影片特别好看,仿佛现今的大片。那次放啥影片呢?好像是日本片《望乡》,也可能是《追捕》,票价不菲,但观众特别多,铁门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外面也是人海人山,很多年轻人想逃票挤进去,冲击着检票员和门岗,还有的索性翻爬有尖刺的铁门,像越狱暴动,可惜多数都被扯着脚拉了下来,只有个别幸运儿翻越成功。我在不远处看着这些不是电影的“电影”,真觉得有点惊心动魄。
从黑白到彩色,从单一的战争剧、反特剧到古典剧、现代剧,从本土片到进口片,从免费看到买票看,我们的露天电影生活,在那由白变黄的银幕上变化着、变化着,而我们这一代人也在这潺潺流水般的变化里嬉戏着、成长着。这种成长,虽然很贫瘠、很辛劳,却也很执着、很顽强,像田头地角的野草,坚持着、葳蕤着,蔓延到了今天。今天,电影杆子上那面发黄的银幕,早已在我们内心风化成了一块久远的化石,坚硬,无表情;但我想,只要我们需要,它肯定又会变得飘逸生动起来。
(选自散文集《平静的忧思》)
相关链接:
原作作者附言
露天电影是旧时代的风景。所谓旧时代,即农耕文明相对稳定的时期,其标志是生产力落后,劳动效率低下,社会财富增长缓慢,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处于半温饱或基本温饱状态,文化消费荒凉贫瘠,娱乐方式单一浅陋,人们思维素养相对简单,人际关系则相对丰富。那时候,方家村的孩子,比一些小村庄的孩子要多些优越感,因为文化生活略略活跃一点。比如露天电影经常有,草台班子演老戏经常有,村大人多,好干活、好聊天、好游玩。所以,外村的姑娘想嫁进来,本村的姑娘不想嫁出去,村里联姻的亲家倒有不少。如今,村里的文化生活依然贫瘠荒凉。平时打牌搓麻的从不间断,老老少少无一不好,逢年过节更是如此,这里一堆,那里一簇,站着看牌的比坐着打牌的还多,里三层外三层,好似拔地而起的幢幢楼房。自然,时下的年轻人都有手机,手机的式样也五花八门。玩游戏、听歌曲、看动画,个个玩得不亦乐乎,就连三岁伢崽也成了响当当的IT男。万年河并非亘古不变的河流。方家村明显有点变化的,不是号称新农村建设样板的洋房群扎人眼目,而是一些先富起来的村民已不声不响地进城安居了。平时周末,年节期间,他们会偶尔回村看看老屋,看看菜地,和老邻居唠唠嗑,话语间掩不住一丝丝自豪。岁月不居,人间沧桑。方家村,也已渐渐地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