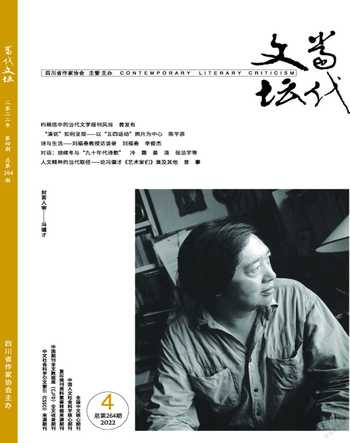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论李敬泽作品中的历史书写
王奕涵
摘要:文学是一种虚构的艺术,而历史是一种客观的真实,李敬泽却通过重新言说历史,将书写悬置于真实与虚构之间,诠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观与历史观。他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叙事策略,以实现自己的文学目标。首先,时间是叙事的基本维度,李敬泽作品中时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是并置的,呈现出兼具历史纵深感与当下延展感的叙事效果。其次,作为一种叙事目的,“总体性”是李敬泽一直以来的追求,他从话语层面对个体与总体进行了辩证统一,尝试观照历史中的每一位个体,并在文学中找到通往总体的路径。最后,任何一种策略最终都指向对真实、虚构问题的思考,李敬泽在书写中打破了虚与实之间绝对的二元对立,并反向重构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开放的关系中走向良性互动,以实现对抗巨大的现代性焦虑这一终极目的。
关键词:李敬泽;历史书写;总体性;真实与虚构
从2017年的《青鸟故事集》和《咏而归》到2018年的《会饮记》,以及新近的评论文集《会议室与山丘》和《跑步集》,李敬泽沉潜至中国文学传统之中,在全球性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化的视野下,不断梳理历史、文学、个体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创作实践,李敬泽并无意于纠结文体的划分,而是希望承袭先秦时代“广义的文”,恢复经史子集当中“子部”的传统,来超越文体和题材的局限。如果说“诗言志,歌咏言”,那么在李敬泽这里,应当是更为宽泛的“文以载道”,而他心中的“道”不妨理解为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传统所赋予我们所有的经验与集体潜意识,并将其置于活的、生动的、开放的状态之中。因此,李敬泽的创作可以被视作一种历史书写,对此,他有一种充分的自信:“两千年来,国人从未想到用这种言路来演绎、进入历史。请注意,我提供的是一个散文家如何进入历史叙事的角度和方法。”①虽然历史本身是客观的,但历史的叙述总是主观的,我们所看到的、被说出来的历史往往笼罩在迷雾之中,而李敬泽进入历史的方式就在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建立一种广义的书写,由此飞向更加空阔的意义空间。
一 叙事时间中历史与当下的并置
一般而言,历史叙述的时间是线性的、单一的,但在李敬泽的作品中,我们却常常可以看到叙述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是共存与并置的。不同向度的叙述时间在历史的纵深和当下的延展中为读者划定了一个坐标系,以便确定自己的位置,并跟随作者的目光,看到一幅宏大的历史图景。
在历时的时间线上,李敬泽沉潜至自先秦以来的经典作品,从中挖掘能够观照现实的精神养分,这一点在《咏而归》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部作品是根据2010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小春秋》修订而成,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补了《鱼与剑》《挑灯看剑》《哭秦庭》《江河及其方向——杜甫一千四百年》等十余篇文章。其中涉及的典籍作品主要有《论语》《诗经》《孟子》《战国策》等,顺历史长河而下,还包括了《离骚》《左传》等经典文献,以及《东京梦华录》《板桥杂记》等这样于历史微光之处悄然存在的作品。李敬泽并没有采取严肃的、刻板的史学话语体系,而是用一种亦庄亦谐的口吻重新讲述了典籍和历史,展示出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流动。如在修订时被提到开篇位置的《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作者开宗明义:“左传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吴国大举伐陈,楚国誓死救之;陈乃小国,长江上的二位老大决定在小陈身上比比谁的拳头更硬。”②文章的开头气势广阔,纵横捭阖,一瞬间将读者拉入春秋纷乱,而后笔锋一转,以今人的口吻为历史祛魅,让人不禁莞尔,营造出间离的叙事效果。但这绝不是为了调侃历史,而是意欲生动地诠释“气节”这一与日常生活距离较远的抽象概念。在他故事性的讲述中,分别展现了孔子及其门徒在关键时刻的反应,借由子路、子贡的价值观批判了当今“如果真理不能兑现为现世的成功那么真理就一钱不值”③的处事原则;反观孔子的凛然大义:“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这份庄重与决绝看似格格不入,李敬泽却直言“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因为正是这样一种气节,才能让我们能够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胜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④对真理的坚持、对“道”的信念不仅写在了书里,也印在了每一位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暗自迭代、传递,才使这精神永不消散。李敬泽还探讨了一些传统道德准则在历史中的演进和变化,如《勇》一文,通过列举三位古代勇者:北宫黝、孟施舍以及孔子,分析了不同性质的“勇敢”,并指出孔子所代表的“大勇”,因为“他使勇成为一个伦理问题:勇不仅体现一个人的力比多,它关乎正义,由正义获得力量和尊严”⑤。在他引经据典、又风趣幽默的讲述中,如今的“键盘侠”和“网络喷子”理当深感惭愧,“因为它是藏在人堆里的勇、免费的勇,它就是怯懦”⑥。李敬泽咏古人之志,也是在借古论今,希望今人能顺着历史的进程,在其厚重的意蕴中反思自己和历史传统的关系,正所谓“引古人之精神,接通此时之人的心与眼,使心有所安,使眼有所归”⑦,让我们总有可归之处。
另一方面,李敬泽立足于某个历史节点,延伸出另一条共时性的时间轴,营造出历史的“现场感”。从《青鸟故事集》开始,李敬泽就在《布谢的银树》中将读者拉进了蒙哥大汗的大帐中,看他如何接待那位来自法国的使者以及他想要传递的思想,为我们描绘出1254年的世界局势:“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正如秋风扫落叶般席卷亚欧,四分五裂的欧洲瑟缩于阴冷的中世纪末期,惊恐地谛听蒙古人的马蹄敲响大地。雪亮的刀锋即将落下,欧洲如案板上的鱼。”⑧他在共时的时间轴上确立了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化的视野,力争描绘“我们”的当下与“他们”的面貌,正是在这种比较中才能确定“我们”何以成为“我们”。“青鸟”原是《山海经》中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后来变为传信使者,承担起连接异域交流与往来的角色,由此足可窥见作者世界相连的全球性视野,以及书写“此地与云外异域之间的故事”⑨这一根本意图。
李敬泽以“物”作为串联时间、并联世界的线索,在物的流转中考察事物细节如何在生活方式起落、浮沉。在《沉水、龙诞与玫瑰》一篇中,作者“从各路史料中勾稽出了一个重要的西来品种:香料,讲述了一个香料如何进入中土的故事”⑩。沉水即如今所说的沉香,是沉于水中多年却不腐的木头,是古代中国的贵公子才能消费得起的雅好,它的背后确是一个长期被我们忽略、历史悠长的贸易体系:“从林邑的森林深处延伸出去,在每一个环节上分枝分叉,最终覆盖了古老的东方世界”11。而曾经迷倒整个长安的龙诞香却是因为“抹香鲸的肠内有一种病态分泌物,它被取出、凝結,状如灰色的琥珀”12,到了宋朝,这种香已经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半岛之间海上贸易的重要动力。“物”不仅承载了很多美好的想象,并且历经全球成为世界交流载体,“在这宏远的历史纵深中,我们才能看清‘龙诞’,这种域外名香悄然暗度,潜入了宋朝人的室内,它的袅绕青烟成为这个国度的经营阶层日常生活情境的一个重要细节,在来自索马里的龙诞香气中,中古世界最优雅、最精微的精神生活徐徐展开”13。文中最后一个香物——玫瑰,我们甚至分不清到底是贯穿整个欧洲文化、代表爱情、战争、宗教和艺术的文明之花,还是写在中国的诗歌中、文集中,从五代时期一直盛开至中国现代化城市之中的蔷薇。根据李敬泽对花的考古,我们所以为的蔷薇很可能就是欧洲的玫瑰,而欧洲的玫瑰也极有可能就是“原产自中国”的蔷薇。李敬泽将其置于世界贸易的密切交往中重新审视,玫瑰抑或是蔷薇成为某种代表性香气的重要商品,“不同种族的人们在这条路上交换着他们的嗅觉经验、他们对香的想象和发现”14,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人类交流史,悉为误读与和解的咏物史”15。独特的视角模糊了科学定义的边界,凸显其所具有的普遍性,于全世界最广泛的人类精神世界中吐露芬芳。
除了物的线索,不同文化之间的神交是另一条平行时空发生关联的路径。《会饮》原是柏拉图的《会饮篇》,李敬泽借用其中“对话”的概念,让诸子百家、酒神先哲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高屋建瓴地展现出不同文明的会通。就像《坐井》中的维特根斯坦和梁鸿,《杂剧》中临济和尚、卡夫卡、阿列克谢耶维奇、汤显祖和王国维,这一番奇景正如他最初的构想:“我们在这里同时想象中国和希腊的会饮,我们把真的变成了假的,在皇帝的宝座上谈论苏格拉底。”16得益于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我们才能看见罗素“正在一群洁净的、体面的、在后世的想象中如同诸神的中国人的簇拥下高弹阔论”,看见他“像个粗壮的金兵一样吃掉一枚汁水四溢的烤羊宝,同时谈论着中国文化的特性”17;才能回到丝绸之路的诞生之初,看不同民族的人民如何因为这个全新的命名被赋予全新的生活意义。李敬泽感谢了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拉铁摩尔及他提出的“丝绸之路”这个好词,“让我们以另外一种全球视野看待我们的历史,重新发现和整理我们的记忆和经验”18,而我们则应当感谢李敬泽拂去历史的尘埃,让那些微光重新照亮人们的双眸,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不仅仅是在扩展关于历史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历史的纵深里认识自己”19。
二 历史书写中个体与总体的统一
读过李敬泽的人都能感受到布罗代尔及其“总体性”原则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如他在《青鸟故事集》的跋中坦言:“感谢布罗代尔。在他的书之后,我写了这本书。”20“他的书”指的是《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李敬泽在其中发现了探究历史的另一种方式:在历史的无数细节中发现那些暗自运行的规律,这种“总体性”的视野不仅成为李敬泽的历史观,也成为他在创作实践中时刻谨记的文学观,对总体性的追索几乎已经成为他所有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重要议题。
李敬泽是在《会饮记》中正式采用了这一表述,他所说的总体性是指要穿越宏大叙事中看到其中的无数个体,以“微观史”的叙述方式将重心落在具体的人身上,表现他们宛如基本粒子在虚空中四下飘散的状态;而“更重要的是,反过来,看看能不能由这些粒子造出星来,能不能从碎片中为生活、为世界想象和书写某种整全感、某种普遍联系”21。一方面,李敬泽确信“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时间和人物其实并不重要,在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的涌动,是无数无名个人的平凡生活”22,他要重新打捞“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里的人,在重重阴影中辨认他的踪迹”23;另一方面,要开辟一条道路让个体走向总体、从“他”走向“他们”,通过具体的个人重建全新的、普遍的总体性。因此,对他而言,“写作,至少写《青鸟故事集》《会饮记》这样的文章,就是让我们碎片的、毫无关联的经验、思绪获得一种形式感,这种形式感不仅是问题,也是意义,也是某种总体性的闪烁”24。
个体是李敬泽历史书写关注的对象,他在宏大叙事之外着眼于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人,倾听那些被忽略的微弱声音。这些声音在《雷利亚》是明代正德年间曾在广东负责外事、外贸的官员顾应详,是受葡萄牙国王派遣初始中国的托梅·皮雷斯,是撰写《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的费尔南·门德斯·平托,他们的故事本来已经沉溺于厚重的过往之中,然而李敬泽却赋予他们庄重的历史意义。李敬泽梳理了这段能够反映中葡交流史的故事所具有的历史背景,认真分析了决定事件发展方向的种种原因:正德年间的政治氛围,顾应详个人的政策水平,皮雷斯的个人际遇,以及平托与皮雷斯女儿的巧遇,这些不再局限为史书记录中的一个墨点,而因为李敬泽的书写走到了历史的追光灯下被我们看见。正是因为一个个具体的人,因为他们每一个真实的抉择、微小的行动,最终构筑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历史。个体的生活就是历史的褶皱,在那其中有可能隐藏着具体而生动的历史时刻,在他的笔下,那些籍籍无名之辈显现出与我们接续相同的精神脉搏,因为“我们的面目,可能最终是由哪些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事物所塑造的”25,那些被我们认为最无关紧要的地方、在时间的裂缝中隐藏着时间的真相,对个体的观照指向中华文明精神资源与情感体验的构建。
然而,对个体的关注并不意味着作者要纠缠于历史的琐碎,个体只是历史叙事的基础,观察螺丝钉一般的存在如何组成、开动历史这台庞大的机器,而李敬泽的终极目标在于进入总体性。这种不仅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也不局限于恩格斯、卢卡奇式的纯理论,而是反映了李敬泽对文学的期待,特别是对于当今中国文学的期待。在他看来,“在文学中,整体性的关切、总体性的眼光,并非过去之事,它有九条命,它随时会活过来”26。今日之文学、今日之作家,有必要去面对并回应“一种中国之为中国的总体性、‘中国故事’的总体性,一种中国1840年以来现代性进程之中的总体性”,“而对这个总体性的把握,或者说,在这个新时代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总体性视野,这是对这个时代文学的根本考验”27。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李敬泽在《山海》中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丁玲家乡走出来的普通人现下的生活;他遥想班固留下的踪迹,想象在这条路上茅盾有过怎样的思绪,最终来到深厚壮阔的、如山一般的《子夜》。他希望能像茅盾那样在描绘人物命运浮沉的过程中,把握民族精神的脉搏,因为“茅盾所见不仅是琐碎的市民、炫目的景观,他探索一种全新的总体性结构,他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历史、在这大城之下运行”28。李敬泽将渺小和崇高交织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看那“万马奔腾,乌云在集结,远处,大城在铅灰色的乌云下静默如铁。树在翻滚,山在起伏喘息,山要站起来。”29风起云涌之间,那位丁玲的老乡开在山顶上的小店亮起了灯,平凡的人终于在文学的波澜壮阔中获得了平静。
总体性虽是对作家的要求、对文学的期望,但如你、如我一般具体的人终将从中得益,因为现实处于不断生成、不断发展當中,“人们不得不面对总体性。比如人工智能,一个围棋手在万众围观下的溃败被认为是人类溃败的开端”30。这不仅是作家的总体性焦虑,也是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都有可能面对的、巨大的现代性焦虑,居于其中的个体能够随时重返时间的洪流,能够在历史纵深感之中实现内化与成长,才有可能真正消解现代性日常对个体的钳制。而中国人理应在中国语境中寻找以中国古代经典文化为中心的话语场域,我们应当庆幸拥有杜甫,在李敬泽眼中,“我们之有杜甫,正如我们有祖国”,因为“杜甫之诗已经构成中国人最基本的美学眼光、人生情感和文化记忆”,想起杜甫“如同想起父亲,他始终伴随着我们,我们身上流淌着他的血液,我们的声音中蕴藏着他的声音,如大地般辽阔、沉厚的声音”31。只有作家具备了宽阔、深远的总体性视野,愿意并且能够深入到人类的困境和心灵的苦难中去,像杜甫那样“走进了大地上浩大的人群”,像他那样“如此真切、如此深情和诚挚地注视着人群、注视着一个个的百姓,注视吾土吾民”32,个体才能在精神的家园中实现个体与总体的和谐统一。
如今,整个世界正面临百年之未有大变局,而总体性在危机中往往更能得以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谁也不能独善其身。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着,城市化的进程、社会结构的更新,时间飞驰的不同速度在中国大地上以空间的形式得以具象,种种变化已经深入到我们最基本的生活经验当中。曾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体性被推翻,既有的“家国天下的总体性规划被打破了,这在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学中启动了一个激进进程,打开了全新的现代性空间,这个空间后来以极富想象力的方式建构了新的总体性”33。面对世间纷乱,李敬泽正是因为对我们的精神准则和文化传统抱有深深的信念,才“通过阐释经典重建具有现代意义的道德体系”34,并期待如今的文学承担起总体性的责任,把握社会之巨变,诞生能够与这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相匹配的作品,像杜甫一千余首诗歌一样为我们、为未来的中国人熨帖心灵的褶皱。
三 话语实践中虚构与真实的重塑
虚构与真实本就是文学中的基本题,二者的关系决定了叙事的形态与目的。但这一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处在开放、发展之中,现代虚构的内核已经脱离了模仿论的桎梏,其中的边界在不断位移、模糊。作为“非虚构”的主要发起人和重要推动者,虚构与真实可谓李敬泽反复思考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其中的关键在于争夺“真实”建构“真实”的问题:“虚”是手段、是策略,文學所写依然是真实。非虚构、虚构、历史、现场诸种概念各自运行一套抵达 “真实感”的机制,但若要重塑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还是要靠对真实事件和任务的深入理解和详尽把握,一种深度的还原能力”35,这不仅符合李敬泽总体性的基本原则,也是他通过历史书写从技术层面做出的有益探索。
李敬泽首先从文章的形式上对虚与实的问题作出回应。读李敬泽的时候常常为其文体的归类煞费脑筋,他游走于虚实之间的笔触并置了宏大的历史事件与微型的感性事件,融合了亲历、现场与人心,而这常常令习惯了现代专业化分类的人感到茫然。受西方文学分类方法规训多年,读者已经养成了以虚实作为判断文类的标准,习惯小说类别下的虚构和散文类别下的真实,并以此为基点对阅读作出预设和期待。然而,李敬泽有感于“中国散文的这一脉,现代以来早已丢失殆尽,如今居然有人告诫你散文不能虚构,他们没读过《庄子》吗?”36,他推崇中国文脉中“广义的文”,带有混沌的、未凿的大巧不工和包罗万象,希望能够借此撇开欧美的现代分类方法,建构中国的文章理论。在他看来“文与章,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根本发意”37,而他的历史书写正是一种恢复“经史子集”中子部传统、先秦传统的实践和尝试。基于这一认识,李敬泽打破了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之间的壁垒,文体的混用使得他不再拘泥于小说要以虚构故事为基础、历史散文应以客观事实为标准的种种规定,从形式上模糊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将评论、记叙、描写等通通纳入广泛的书写当中,这使他的文章具有了一种浩然气象。
其次,在李敬泽的书写中,虚构不再局限为一种文类性质,真实也不再囿于客观存在,原有的叙事标记的所指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作者、叙述者抑或是旁观者的身份地位游移不定。在《咏而归》中,“今夜偷偷打开苏洵的行李,你发现一部《战国策》,你愕然、茫然,然后冷笑:《战国策》还用读?江湖之上水人不是胸中早有一部《战国策》,才下心头又上口头?”38“在某一个清晨,我停下,让那支箭呼啸着穿过我的身体,我的前胸和后背传出一个直径三厘米的洞,风从中吹过,发出哨音”39,作者居于中间,用这些奇异的句子将历史与当下、虚构与真实、可能与不可能勾连了起来,这一点在《会饮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坐井》中,一句“我已经记不起徽宗皇帝临死前的表情了”将读者引入一种不可能的真实之中,“起风了”三个字为他构建的真实更增几分实在的触感。接下来一段难以辨别叙事还是描写的文字直接反向重塑了虚与实的关系:“现在,我仍然能够记起那一幕,那片阳光照射下覆雪的坡地,寂静如宇宙洪荒,但是,起风了。你其实不知道那是风,你只是看到你的脚踏破贞静的雪,细小的粉尘仓皇地在雪上拂动,奔赴而去,渐渐飞扬,在阳光中旋转,直到腾空而起,如一只威严的、芒羽闪烁的巨鸟。他沉重的袍襟在风中轻摆,他顽劣地笑了,笑得像汴京街头的一个泼皮:这风是咱们两个惹起来的”。40宋徽宗仿佛穿越历史而来,“我”“你”“他”身处同一个时空,叙述的视点和主体变动不居,根本无法确定谁是说话者谁是观察者。虚构话语与非虚构话语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在虚与实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叙事效果。最后那句极富奇幻色彩的结尾:“我摘下我的头颅,缓缓地,把它放进冰冷的井底”41,无疑将语言能够触及的边界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再次,除去技术层面的语言因素,李敬泽还尝试将其历史书写带离 “再现”“模仿”等传统的虚构逻辑,而是在“总体性”原则的指导下,对原本客观的历史重新进行叙述。虽然被言说的历史会丧失它的客观性,被赋予感性的主观色彩,但正是那些普通个体所具有的主观性,才使那于天地间默默运行的“大力”得以具象,可以说,只有进入并超然于个体的普遍生活才能真正窥见整体的力量。因此,李敬泽试图穿越历史的迷雾去挖掘历史上那些不引人注意的副段落,目的是为了观照现代无名的大多数以及他们的生活,从而无限地逼近历史的真相。《青鸟故事集》中篇幅最长的《飞鸟的谱系》,李敬泽不仅写到了道光皇帝、李鸿章、林则徐,还花费了更多的笔墨去记述历史角落里的广州总通事蔡懋,美国人威廉·亨特、英国使者马戛尔尼,以及大概最早到达英国的中国人:覃纪华和黄阿东。这些真实存在过的人在历史的记录中可能只占据一个墨点,李敬泽在钩沉史料之间,以文学性的笔调将他们推至前台,我们才能发现他们在中外交流之初所担负起的沟通之责,以及他们微不足道、却又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历史深厚的意蕴中,虚构成为李敬泽的书写中的深层结构,令那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事与物得以再次被理解,他于二者之间悬设的隐性逻辑关联,重新获得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到了《夜奔》中,有一个名为“他”的主角,一个全知全在却又不见踪迹的“我”,还有不具名的出租车司机、老周、老马和“女人”。我们不仅无法确定叙事的视点,甚至无法确定故事发生的地点:从烧烤摊,到飞机场,再到出租车内,以及会议现场,加上穿插其中、不断闪现的老马的传奇故事和神秘的拼车“女人”,整个故事充满了奇幻的色彩。这些不能算作有名字的人物并不具名,正因如此,那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隐藏于虚构之中的无主话语亦可以成为任何人的感受,可以被任何一个人表达,从而达及一种无人称性与超越的普遍性。于是,“他”和“马哥”拱手作揖,“如在宋朝。铁塔的宋朝,范仲淹和苏轼的宋朝,林冲和鲁智深的宋朝。然后,各走各的路。马哥融入茫茫人海”。42马哥、“女人”“他”和范仲淹、苏轼,以及林冲、鲁智深,那些真实的、虚构的中国人一同被卷入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而去。
总之,若是一定要追究李敬泽的笔下常常出现的“我”“他”或是“李老师”、《咏而归》的作者,这些称谓中的主体究竟为何人,则很有可能浪费了李敬泽的一番苦心。正如他在《大樹》中评论《会饮》的开篇,论及“‘你们’是谁,却不曾说‘你们’就是我们,我们这些读者、听众、看客”43,在层层的转述当中,任何讲述都将“介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它是个人‘意见’,它必是‘小说’”44。在他的书写中,称谓回归到语言功能层面的意指符号,真正的主体性已经消隐于能指链的滑动中。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这些书写既是超验的,又是具体的,在虚构的话语和历史的真实之间,飘散着成千上万不断运动着的微尘,无数的我最终成为我们、你们还有他们,所谓虚与实在李敬泽的延宕中得以交融,不复痕迹。
结 语
李敬泽的历史书写不仅继承了“文”的话语传统,同时也在语言实践上呈现出先锋的意味,但这种实验性质的风格并非是对西方标准的迎合,而是通过沉潜至典籍海洋深处寻觅根本性的破解方案。现代、后现代带来的意义的消解与坍塌急需重建容身之所。回望并不总是惆怅的,故乡理应成为我们的力量源泉,经典,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整一性,完全可以医治后现代虚妄的颓势,“中国故事同时指向人类的共同境遇和共同命运”45。这正是李敬泽所期待的“文学上的中国道路”:从自身挖掘精神养分,应对世界秩序的剧变,逃离既定的西方标准,也逃离广泛的现代性焦虑。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所谓‘世界文学’的经验去套,你得在世界背景下去辨析、确认中国经验”46。历史并未终结,至少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如此,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的是一个敞开的、形成中的、不断变化的未来,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可能性。而当代作家的责任就是要去直面、去回应历史巨变带来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确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形象、命运和责任,探讨自己是谁,和将要成为谁”47。在这个意义上,李敬泽的历史书写正是树立文化自信、构建文学上的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尝试,他对于历史与当下、个体与总体、虚构与现实无不显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气势,他打碎既有的框架,将所有的碎片重拾、杂糅在一起,从而飞向中国语境下的、更加广阔的文学空间。
注释:
①⑩李敬泽、蒋兰:《〈青鸟故事集〉,元写作的尝试》,《创意写作》2019年第3期。
②③④⑤⑥⑦3132363839李敬泽:《咏而归》,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第5页,第5页,第41页,第43页,第255页,第167页,第168-169页,第176页,第64页,第221-222页。
⑧⑨11121314202223李敬泽:《青鸟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61页,第263页,第16页,第26页,第27页,第38页,第359页,第360页,第360页。
15葛亮:《物外之境——〈青鸟故事集〉与东西文化之辩》,《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
161718252829304041424344李敬泽:《会饮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页,第25页,第60页,第70页,第179页,第181页,第158页,第21页,第37页,第150页,第107页,第108页。
192124李敬泽:《飞于空阔》,《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2期。
26333547李敬泽:《会议室与山丘》,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29页,第140页,第224-225页,第203页。
27李敬泽:《历史之维中的文学及现实的内涵——对话李敬泽》,《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
34卓今:《〈咏而归〉的阐释与重建》,《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
37李敬泽、李蔚超:《杂的文学,及向现在与未来敞开的文学史——对话李敬泽》,《小说评论》2018年第7期。
4546李敬泽:《文学中的新中国故事》,载李敬泽《跑步集》,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125页,第115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罗曼·罗兰的诗学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K2018A0241)
责任编辑:伍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