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聚
萨莉·鲁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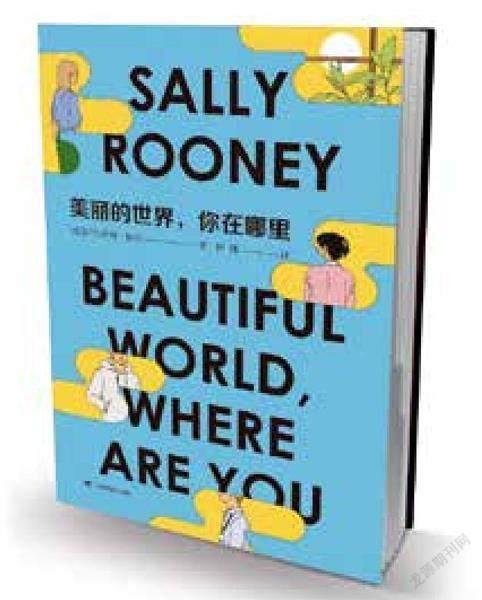
六 月初的这天,中午将近,火车站台上,两个女人在分别数月后相拥。她们身后,一个浅色头发的高个男人正在下车,提着两只行李箱。两个女人没有说话,双目紧闭,手臂环抱对方,持续了一秒,两秒,三秒。深情相拥的她们是否意识到,这幅画面有些许荒谬,几近滑稽?旁边站着一个人,正对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巾猛烈地打喷嚏;一只被人丢弃的脏塑料瓶在微风吹拂下沿着站台骨碌碌地滚过;站台墙上的滚动式广告牌正从美发产品切到汽车保险;平凡甚至陋俗的生活,侵占了她们周遭的一切。还是说此刻的她们意识不到——或者说不是意识不到,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受这些庸俗和丑陋的侵扰,不被它们污染,因为她们在这一刹那窥见了某種更深刻的东西,隐藏在生活表面之下的东西,它不是非现实,而是隐秘的现实:一个存在于所有时空的美丽世界?
当晚,费利克斯下班后在艾丽丝家门外停好车,看见窗户亮着灯。七点已过,外面天还没暗,但气温降了,海隐于树林之后,绿中泛银。他单肩挂着背包,步履悠闲地来到前门,在黄铜片上轻快地叩了两次门环。咸咸的凉风在他周围搅动,他双手冰凉。门开了,屋里站着的不是艾丽丝,而是另一个女人,年纪相仿,更高,头发颜色更深,深色眼睛。你好,她说,你是费利克斯吧,我是艾琳。进来吧。他走进来,她在他身后把门关上。他有点恍惚地微笑着。对,我是费利克斯,他说,我听说过你,艾琳。她抬头扫了他一眼,说,希望都是好话。她说艾丽丝正在做晚饭,他跟着她穿过门厅,望着她的后脑勺和优美的窄肩,一路往前,来到厨房门口。厨房里,一个男人坐在桌边,艾丽丝站在灶前,腰间系了一条脏脏的白围裙。你好,她说,我正在沥意面。你见过艾琳了,这是西蒙。西蒙向费利克斯问好,费利克斯点点头,手指抚摸着背包带。厨房有点暗,只开了操作台的灯,桌上点了蜡烛。蒸汽让后窗起了雾,玻璃透出丝绒般的蓝色。费利克斯问,要我给你搭把手吗?艾丽丝用手腕正面碰了碰额头,似乎在给自己降温。她说,应该都弄好了。谢谢你。艾琳正在跟我们讲她姐姐的婚礼。费利克斯犹豫片刻,在桌边坐下。他问,上周末,是吧?艾琳愉快地向他投来注意,又开始讲起婚礼的事。她很风趣,手部动作很多。她时不时会让西蒙发表意见,他的声音很松弛,似乎看什么都觉得有趣。他对费利克斯也很留意,时不时会迎上他的目光,带着密谋般的微笑,仿佛很高兴还有另一个男人在场,或者很高兴女人们在场,但想和费利克斯一同分享或确认这种愉悦。他很帅,穿着棉麻衬衫,艾丽丝给他倒酒时,他会非常自然地低声道谢。桌上摆着带花纹的小碟子,银色刀具,白布餐巾,一只黄色大沙拉碗,里面拌了油的叶子闪闪发光。艾丽丝端着一盘意面来到桌边,把它放在艾琳面前。她说,费利克斯,我最后上你的面,因为这两位是我尊贵的客人。他们四目相对。他有点紧张地朝她微笑,说,没关系,我有自知之明。她摆出讽刺的表情,回到灶边。他注视着她。


电视剧《聊天记录》剧照。
饭后,艾丽丝起身清理桌上的餐盘。餐具咔哒作响,彼此摩擦,水龙头哗哗地流。西蒙在问费利克斯的工作。艾琳疲倦而满足地静静坐着,双眼半闭。烤箱里热着一盘水果奶酥。餐桌上只剩下食物碎屑,一条脏餐巾,沙拉碗里粘着湿哒哒的叶子,桌布上残留着柔软的蓝白蜡滴。艾丽丝问有没有人想喝咖啡。西蒙说,请给我来一杯。一大盒冰激凌在料理台上慢慢融化,沿着边细细流下来。艾丽丝拧开一只银咖啡壶的底座。费利克斯在问,那你是干什么的?艾丽丝跟我说你是从政还是什么的。水槽里有一只脏的酱料锅,一块木头菜板。灶头发出嘶鸣,散出火星,艾丽丝问,你还是喝黑咖啡吗?艾琳睁开眼,只看见西蒙半侧过身朝向灶边的艾丽丝,回头说,没错,谢谢。不用加糖,谢了。他的注意力重新回到费利克斯,再次聚焦,艾琳的眼皮颤动着,又快要闭上了。他洁白的脖颈。他在她身上颤抖,涨红着脸,低声问,那样可以吗,抱歉。烤箱门咔嗒一声打开,散发出黄油和苹果的芬芳。艾丽丝的白围裙被弃在椅背上,系带向下悬垂。西蒙在说,对,我们去年和他共事过。我和他不熟,但他的工作人员对他评价很高。在他们四周,房子安静结实,上了钉的木地板,烛光下光洁可鉴的瓷砖。昏暗宁静的花园。海平和地呼吸着,将带咸味的风送入窗内。想象艾丽丝住在这里。一个人,或许不是一个人。她站在灶边,用勺子把奶酥盛到碗里。一切各居其位。今晚,人生的一切都和这座房子系在了一起,像抽屉里一条打了结的项链。
晚餐后,费利克斯出去抽烟,艾琳上楼去打电话。西蒙和艾丽丝在厨房里洗碗。透过水槽上方的窗户,他们能看见费利克斯瘦小的身影,在越来越暗的花园里走动,时隐时现。香烟的一头亮着。艾丽丝一面留意他的身影,一面用方格茶巾把盘子擦干,放回碗橱。西蒙问她工作如何,她摇摇头。哦,我不能说,她答道。这是个秘密。对,我退休了。再也不写书了。他把滴着水的湿沙拉碗递给她,她用茶巾轻轻擦拭。他说,这话我很难相信。此时窗外已不见费利克斯的身影,他已经走到房子的另一侧,或者走到更远处的树林里。她说,你不信也得信,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就只有两个好的构思。不对,是写作太痛苦了。而且你知道的,我现在有钱了。我应该比你都有钱。西蒙把沙拉钳面朝下放在水槽边的网架上,说,我想也是。艾丽丝放好碗,合上碗橱门。她说,我去年帮我妈把贷款还了。我跟你说过吗?我钱太多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会做其他事,我有计划,但我非常不会规划。西蒙看向她,但她看向别处,把沙拉钳从架子上取下来,包在茶巾里擦干。他说,你这么做很慷慨。她有点难为情。好吧,我告诉你就是为了让你觉得我是个好人,她答道。你知道我非常渴望获得你的认可。她把夹子放进装餐具的抽屉。他说,我非常认可你。她的肩摇摆起来,她半开玩笑地答道,哦,不,你不能毫无保留地认可我。但你可以有点认可我。他沉默片刻,用海绵擦洗着一只烤盘。她焦躁起来,又向窗外扫了一眼,但一无所获。天光开始消逝。只剩下树的轮廓。她说,反正她现在也不跟我说话了。他俩都是。西蒙顿了顿,把烤盘放在架子上。他说,你妈妈和你弟弟吗?她拿起烤盘,用毛巾去按它,又快又狠地摁上去,说,或者是我不跟他们说话了,我不记得怎么回事了。我住院的时候和他们闹掰了。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又住在一起了。他看着海绵顺着洗碗水流到水槽底部。听你这么说我很难过,他说,听起来太惨了。她不加掩饰地笑了一声,感到笑声灼烧着喉咙,继续拿毛巾去按烤盘。可悲的是,不用去见他们反而让我心里更舒服,她说,这不符合基督教义,我知道。我希望他们幸福。但我宁愿和喜欢我的人在一起。她能感到他在注视自己,于是弯下腰,把烤盘哗啦作响地塞进碗橱深处。他说,我不觉得这违背了基督教义。她发出颤抖的笑声。哦,听你这么说太好了,她答道。谢谢你。我感觉好多了。他从水槽底部拿起海绵。她问,你呢,最近怎么样?他对着洗碗水微笑,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我还行。她继续注视着他。他扫了她一眼,幽默地说,干嘛?她温和地扬起眉毛。我拿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我是说,你和艾琳之间。他将注意力重新放在水槽上。我也不知道,他说。
她用手拧着茶巾,若有所思。你们现在只是朋友,她说。他点着头,把铲子放在沥干架上,说没错。她继续说道,而你很快乐。他笑了出来。快乐谈不上,他说,还是老样子,静静地绝望罢了。后门开了,费利克斯走进来,在垫子上跺脚,关上身后的门。今晚外面很美,他说。楼上传来嘎吱的脚步声,艾琳轻轻地走下楼。艾丽丝将拧干的湿茶巾叠好。他们都是来看她的。为了她他们此刻在她家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理由,只要他们人在,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所谓。费利克斯问西蒙抽不抽烟。我猜你没抽过。你看起来太健康了。我敢打赌你肯定喝很多水,是不是?聊天与欢笑,这些不过是愉悦地组合在一起的声响,悬在空中。艾琳站在门边,艾丽丝起身给她续酒,问她工作的事。她来看她了,她们又在一起了,她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所谓了。
凌晨一点稍过,他们上楼睡觉。灯开了又关,水龙头开着,马桶水箱重新接上水,门开开合合。
海慢慢吸气,将海浪从岸边吸走,只剩下平坦的沙滩在星光下闪烁。潮湿的海草纠缠在一起,昆虫在其间爬行。沙丘静谧地聚集,凉风抚平沙丘上的草。沙滩前面的人行道悄无声息,上面铺着一层白沙,房车的拱檐闪烁着微光,黑暗中车紧挨着车停在草地上。接着是游乐设施,门帘紧闭的冰激凌小亭,沿着街往镇里走去,有邮局、酒店、餐馆。水手之友关着门,窗上的贴纸难辨字迹。过去一辆车,前照灯一扫而过,尾灯红得像煤。再往上走是一座联排住宅,空白的窗反射着街灯,屋外垃圾箱排成一列。出城的沿海公路,寂静,空荡荡的,树木在夜色中升起。西面,海如同一块深色布料。东面,往上走,穿过大门,来到教区神父的旧居,幽蓝似牛奶。里面有四个人在睡觉,醒来,再次入睡。他们侧卧,仰躺,踢被子,无声地在梦里穿行。屋后,太阳已经开始升起。晨光打在后墙上,透过树枝,斑斓的树叶,潮湿的青草,洒了下来。夏日清晨。掌心上清凉的水。
(责编:栗月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