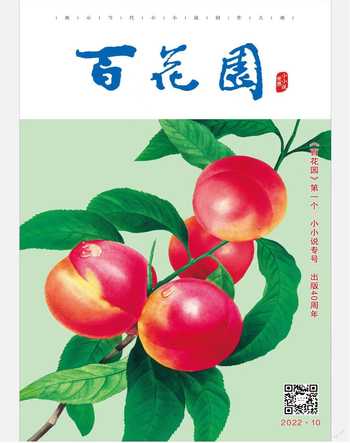鞋皮生
岑燮钧

所谓“鞋皮生”,是梨园界的一句行话,就是戏里的落拓书生。因这类人物脚下趿拉着踏倒了后跟的鞋——在江南叫作“拖鞋皮”,所以叫“鞋皮生”。剡剧当中,就数孙怡香演的鞋皮生最出名,人称一绝。
孙怡香的这门绝技,得自她的开蒙师父仇龙生。仇龙生是演小丑的,但却是个全科,样样都会,是个教戏师父。孙怡香的父亲与他有点儿小交情,就让她去学戏,有口饭吃。他对仇龙生说:“老仇,我阿囡交给你了,让她多伺候伺候你,拜师礼你多担待。”他双手一摊:“实在没铜钿啊!”仇龙生也不计较,让她磕个头就算数了。
大清早的,孙怡香就起床了,她去给师父倒尿盆。这是父亲教她的规矩。仇龙生说:“阿香,你放着,让阿小来倒。”他说的是他小儿子。阿小没办法,就噘着嘴拎出去了。孙怡香跟出去,然后从阿小手中接过尿盆。等她回来,她听见师父在骂阿小:“你看看人家阿香多勤快!就你,烂手的,什么都不想干!”
师父教的开蒙戏是《彩楼记》,里面的吕蒙正就是个鞋皮生。师父示范给她看,趿拉着鞋皮,一步三摇,却又不能演成官生,得有穷酸气,但光有穷酸气也不行,还得有几分傲气,因为吕蒙正是个读书人。师父一边唱,一边教她怎样穿着拖鞋皮走台步——
我穿一双破烂鞋,
走遍长街与短街。
乌纱帽儿挡不得蒙尘态,
身上单寒事怎挨……
孙怡香一看就明白了,她骨子里也有几分穷傲气。师父看她一点就通,很开心。
有一天,来了师父的大师兄,他是一个戏班的班主。师父说:“阿香,你跟着我这个讨饭师父,怕是很难出头了。要不,你拜师伯为师吧,他路子广,你跟着他才能唱出名堂来。”孙怡香一听要把她送给师伯就急了,她红着眼睛说:“师父,我不要别的师父,我只认你这个师父!”
“那为啥呢?”
“你待我好,不打我不骂我,又教我本事!”
师父尴尬地看了看师兄,然后一脸皱纹地笑了起来:“阿香,你是个有良心的小囡!”
后來,男班唱男调,女班唱女调,孙怡香就跟师父分开了。她唱《彩楼记》比其他演员都好,渐渐红了起来。孙怡香去看望仇龙生,仇龙生就高兴地跟大家说:“这是我的寿头徒弟,一门心思地跟着我这个讨饭师父!”寿头者,傻瓜也,师父说来,特亲热。孙怡香偷偷地塞给他钱,师父推了推,收下了。只是有一回,孙怡香又要给他钱的时候,一旁的大花脸开玩笑道:“孙怡香,你不要再给你师父钱了,你上次给他的钱,他一个晚上输了个精光!”师父说着“去去”,连骂大花脸,但是,从此看见孙怡香,总是感到有点儿难为情。孙怡香再给他钱,他说什么都不肯收了。
比起女班来,男班唱得像黄牛叫,很快就衰落了。一九四九年后,剡剧几乎已找不到男班,仇龙生也回家种田去了。而孙怡香越唱越红,成了省团的一根台柱。每逢重阳节,她总要备一份礼,早早地托熟人给师父送去。
有一件事,让孙怡香抱憾终身。那时,她已被“打倒”,刚刚从八一窑厂回来,行动还受里弄监视。有一天,一个瘦弱的老头儿找上门来,身边一个人扶着他。孙怡香看了半天,突然喊了一声:“师父!”原来是阿小扶着他来省城看病的。她又是高兴又是难过,心里慌得很。果然,一会儿,里弄干部来查问了。她有意让师父留下来,住一夜,但是里弄干部说啥也不答应。师父摆摆手说:“阿香,你别为难,师父难得上省城来,也是顺路来看看你,你的心意师父领了……”她看着师父离去的背影,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回身在家里翻了半天,翻出一斤红糖、一封挂面,又追上去,送给师父。师父硬是不要,孙怡香急了,不由冲口而出:“师父,你不要嫌少……”师父心里一震,也不由得老泪纵横:“阿香,你也要保重!”师父收下了。
三个月后,师父死了。孙怡香没去奔丧,她是事后才知道的。
孙怡香最后一次去“看望”师父,已是很多年之后了。因为女儿在美国,她晚年也定居在那里,很少回来。八十八岁米寿的时候,她回来了一趟,觉得往后大概是不可能再回来了,特地多待了几天。当时,她的头发已全白,像一树梨花。电视台特地为她做了一期节目,她说到了自己的艺术特长:鞋皮生。
下了节目,孙怡香回了一趟剡县老家,找到了师父的小儿子,让他带着她去看了师父。师父的坟茔已荒草萋萋,墓碑非常小,快陷入土里了。她把一双自己亲手缝制的布鞋祭在了师父的坟前,心里默默地说:“师父,你穿了一辈子拖鞋皮,你穿一双新鞋吧!”
临走时,她拿出五万元,让阿小把师父的坟墓修一修,换一块大碑。
[责任编辑 冬 至]
——上海里弄居住功能更新方式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