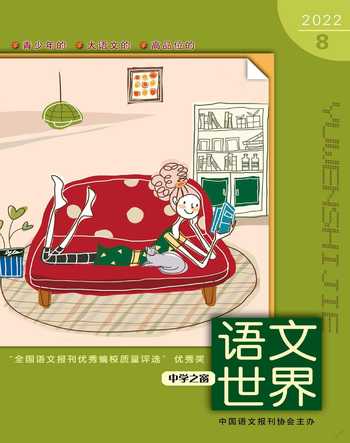高中时代的野蛮阅读
陈俊江
高中时代,好大一个词。不过,高中三年对我个人而言,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就说读书吧,高中时的阅读引领了我,提升了我,一定意义上说,重塑了我。
刚上高中时,我茫然无措,是老师们的教诲让我静下心来,让我有了方向感。语文老师封如楼先生说,语文无他,读书而已。这句话,我受用至今。是阅读,帮我寻到了知识的桃源,帮我找到了心灵的港湾。
其实,想读书却不一定就有书读。这话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而在我读高中时,却并不奇怪。那时,谁要是有一本课外习题集,谁都要被同学高看一眼。我们一批从农村考到城里来的住校生,资源就更为贫乏。书店里自然有书,不过那是要花银子的,所以,书并非唾手可得。转念一想,教科书不也是书吗?而且应当是最好的书啊。那,先读“破”教科书再说。
高中语文第一课,《荷塘月色》,课后练习要求背诵文中写景的三段。读着读着,我发现文章开篇的那些“叨咕”和写景之后的“宕开一笔”,一样精彩啊。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园的荷塘月色中想到了江南,想到了采莲,千里之外的江南,千年之前的风流,还有比这更妙的笔墨吗?好吧,一起背了,那就全文背诵。直到如今,我还是认为,读《荷塘月色》,如果只是盯着月下荷塘、塘上月色、荷塘四周那三段华彩写景,那可就低看这个名篇了。
《荷塘月色》多读读,以至背诵全文,还是容易理解的。说《记念刘和珍君》也能背诵,可信吗?但真的熟读成诵了,理由是被震到了。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太震撼了,那么冷峻又那么温情,那么犀利又那么悲悯。读这样的文字,我说不出话;读这样的文字,就是在“读人”。文章所写的人,写文章的人,都是大写的人,他们肩上有担,他们心中有爱。
阅读中,我慢慢悟到,所谓“读书破万卷”,“万卷”固然重要,“破”更为重要,不仅要追求量的扩张,也要追求质的深化。如果能像揉面一样的把一篇文章“揉”熟,或可胜过囫囵吞枣好多篇。
老师说,学语文要多做有心人,哪怕是一个报纸旮旯也能读出学问。读《语文报》,功课做得扎扎实实。一般来说,读报,多是泛泛浏览。而当时我们读《语文报》,是当语文拓展教材来读的,从报头到报尾,从文章到习题,一直到中缝的“零打碎敲”,哪怕是一则征稿启事,都细细读来,圈点勾画做笔记,气力那是舍得花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学校组织的读报比赛中,我拿了第一,奖品是个硬纸板讲义夹。讲义夹一打开,左边赫然写着某人在高一年级《语文报》读报比赛中荣获一等奖,特发此奖,以资鼓励。这获奖词的毛笔字真是漂亮,我照着临写了好久。这个讲义夹,是我的一份荣光,随我走南闯北,一直用到工作以后好多年。

报纸可以精读,字典自然也可读。我有一本《新华词典》(不是《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的版本。1982年8月底,接到考上县中的消息后,家里给我5块钱,让我去买个热水瓶,到了镇上以后,我没能抵御住书店的诱惑,买了一本《新华词典》,花了3块8毛钱。这本词典默默记录了我高中时代的语文学习,也顺带记录了我的野蛮阅读。所谓读词典,本来是为了查一个字,结果连带看了不少相关内容,比如这个字有许多词条,查其中一个顺带学了其他。还有一种情况是,作业做完了,拿起词典,随手翻到哪一页,读到什么是什么,读到哪儿算哪儿。读到特别有兴趣的,还会动笔做一些圈画。久之,积累了不少词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
许多年以后,我把这段经历当个故事讲给一个小学生听,并且给她看了这本还一直收在书橱里、模样比较“沧桑”的词典,以表明我此言不虚,小朋友微笑着表示相信,但她眼里明显地写着费解。读词典这事儿,是不太容易理解啊。
慢慢地,新环境适应了,读书渠道多起来了。可以借书,也可以买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那时是正当红的纯文学期刊。我在这本杂志上读了不少后来名气很大的作品,比如铁凝的成名作《哦,香雪》,对这篇标题像诗歌一样的小說,印象很深。17岁的山村少女香雪对大山以外世界的好奇与向往,大概正契合一个刚跑到城里来读书的15岁乡下少年的心理,用如今的时尚词来说,叫共情。生活是不一样的,但对新生活的向往,其理相通。还记得一个细节,当时看了《哦,香雪》以后,我有点不服气地想,小说中写台儿沟那地方偏僻闭塞,那我们盐城说起来是东部沿海地区,可还没通火车呢。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在1983年第1期《青年文学》上读到的,标题也很诗意,但插队知青的生活是艰苦的,小说中纯朴的情感、坚韧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很是打动人。王蒙就夸奖这篇小说“是诗,是涓涓的流水,是醇酒”。确实,《哦,香雪》《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都是不一般的小说,后来都获奖了。记忆中的80年代,经常有小说散文诗歌的各种评奖,奖项公布也是令人瞩目的新闻。如今很少听闻文学奖,是类似的评奖少了呢,还是当年人们的目光更容易聚焦文学?
后来,我自己也预订期刊来读,北京的《诗刊》,百花文艺的《散文》,山西的《名作欣赏》,好文章如源头活水,汩汩,滔滔,为我带来了丰沛的润泽。这些杂志打开了一扇窗,文学之窗,窗外的新风景让我应接不暇。我不但透过窗看风景,有时干脆跑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到学校斜对门的市图书馆去借书,到校外不远的工人文化宫阅览室去读现刊,到仅有里把路之遥的建军路新华书店去“蹭书”或者买书。渐行渐远渐无穷,我的阅读视界渐渐开阔起来。
到了文科班以后,读书用功更勤。我们念念不忘的80年代,是文学的年代,空气里洋溢着理想主义。班级里一拨文艺青年,囊中羞涩却眼里有光。学校里还经常有征文、朗诵、演讲比赛,这些活动也促进了我们的阅读。
其时,班主任邵鸿翥先生不拘囿于教材,经常补充些课本之外的学习内容,拓宽了我们的视野。邵老师古文功底深厚,他给我们讲八大家散文和唐宋古文运动的缘起沿革,溯源至先秦诸子、两汉文章,一高兴就成段背诵《孟子》,我听得目瞪口呆。因了这缘,我买来《三苏文选》和《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认真地读。比如《留侯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阅读这些文章,本意希望提高语文水平,没想到的是这些文章还能帮我遮风挡雨,直到如今仍然给予我心灵滋养。
老师喜欢抄一个文言段子在黑板上,让我们练“句读”,加标点,或者解释字词。司马迁《史记》的段子居多。我有幸经常面聆謦欬,才知道老师爱读《史记》。他说鲁迅评价《史记》为“无韵之离骚”,眼光绝对老到;《史记》是最好的古文,也是真文言,唐宋以后的文章是仿文言;要学好文言文,就要多读读《史记》。老师还送了我一本《史记选》,王伯祥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最权威的。我很珍视这本书,专门用好看的画报包了书皮,在其后的辗转中这本书不知所之,甚是可惜。
跟着老师的节奏,我还学会了随季节的流转而做一些主题性的阅读。比如说元宵节要到了,邵老师把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抄在黑板上,推一推他那厚厚的满是圆圈的眼镜,微仰着头说,这是写元宵节最好的诗词,最好能背诵。“最好能背诵”相当于“一定要背上”,于是也就背上了。中秋节要到了,老师便补充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说东坡中秋词一出,余词尽废。只一句话,我们便知道了这首词的厉害,于是在中秋月色里诵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像这样读书,很有意味,很容易入情入境。慢慢地,这样的阅读竟成了习惯,到如今依然喜欢跟着四季去读书,或者说,去读岁月,读人生。
還有一种阅读方式也颇令我得益,就是跟课本相关的阅读,学了课本内容之后,去读与此相关的文章,我称之为“延伸阅读”。比如说,课本里学了《花城》,就去看看秦牧散文集《花城》。课本里学了《威尼斯》,就去读读朱自清《欧游杂记》,进而去读读《你我》,甚至去翻翻《经典常谈》。有意思的是,我1985年参加高考,语文试卷的现代文阅读题,素材就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中的“《史记》《汉书》第九”。读书当然不是为考试押题,但多读自然是好的,开卷有益。而且,这样的阅读一定意义上带有了研究的性质。多年后我在《古典文学知识》上发表一篇《文言文的延伸阅读》,文中的阐述有教书的思考,也有我读书的认知。
这些阅读经历,我曾写过一篇《“前大学时代”的野蛮阅读》。友人见了就笑我,说你要多交学费的,读高中还顺带读了个中文的大学预科。我明白这不是夸奖,这是揶揄,因为我明显跑偏了。
事实上,在当时,班主任邵老师就严肃地指出了问题,他生气地问我,你就靠一门语文去高考吗;又苦口婆心开导我,说现在不要多看,是为了将来能更好地看。我估摸着老师这样批评我的时候,他的内心也是纠结的,他是不是也如我一样在想,天下为何要有高考呢。我不是不听老师的话,我明白学科要平衡,可是我的外语水平就是温吞水,六十颇有余,七十尚不足。我知道这很不理想,但一想到自己在乡村小学的“戴帽”初中班仅学过一册英语就参加中考,我就一次次地原谅自己,不是我不用功,是底子薄。老师问这是理由吗。是啊,这是理由吗。
于是我下决心调整,想办法提高,我把拼搏的脚步交给煤渣跑道的操场,我把瞌睡的黎明交给比诗词难学的英语,我给自己加一节英语早读课。不但认真地背书,背课本里的How Marx Learned Foreign Languages(高中英语第一课“马克思是如何学外语的”),背Albert Einstein(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还去读课外的段子,比如安徒生的童话The Ugly Duckling(丑小鸭)。我甚至还学唱英语歌,饶有兴味地去琢磨那些印在年历片上或者杂志封三的英文歌曲。“当那曙光渐渐明朗,这是一个新希望。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Paloma Blanca(白兰鸽),多么欢快的旋律,跟着唱起来,满满青春朝气。
定神一想,我这哪是学外语,这不还是在学文艺。不好意思,那时怎么就那么喜欢课本以外的东西呢,真是不务正业。好在英语高考差强人意,聊以慰风尘。只是道行还是不够深,英语学着学着就学丢了,“丑小鸭”晃悠晃悠就晃成了丑老鸭,“白天鹅”的梦随风缥缈,成了遥远的一曲歌。
都已经丑老鸭了,不妨坦白一下,那时虽然发了狠,功课上却还是未能“火力全开”。高考前的紧张日子里,我还经常读一读图文并茂的《历代题画诗选注》,还悄悄地“了解”了一下《射雕英雄传》。这算不听话吗?算不用功吗?
如今想来,亦谈不上懊恼,反而感念那时的宽松与自由,好让年少的阅读“野蛮”了一回。
要是不任性,青春,她怎么就叫青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