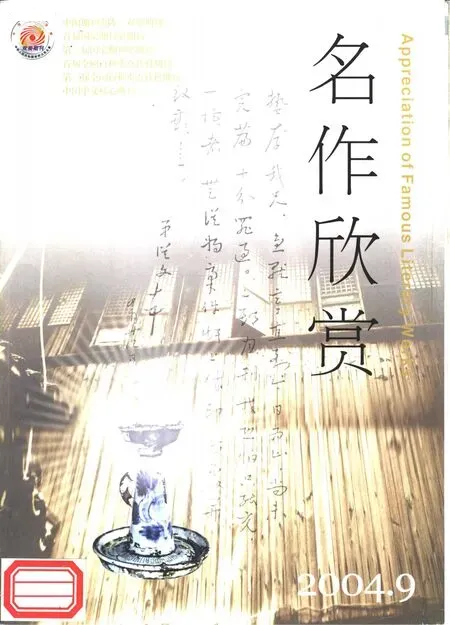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前世与今生(下)
六
宋代发达的商业文化,促使女性文学繁荣,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两位重要的女诗人——李清照和朱淑真。她们的诗,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艺术高度,都可以与同时代的男性著名诗人比肩,甚至更胜一筹。
社会变迁是直接影响文学兴衰的因素。宋朝因外族入侵而移都江南,政治中心的转移带来经济与文化教育中心的转移,也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变迁。宋代——北宋219年,南宋152年,从“北”到“南”,这使江浙一带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又直接影响到人文素质的变化。
首先,就文化而言,自孔子以降,公元前134年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开始变质,到了宋明,社会变迁致使“宋明理学”将儒家思想彻底演化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陆九渊,他们或强调“性即理”“理”或“天理”乃是世界的本源,或强调天地万物在我心中,心为本体,“心即理”,心乃是宇宙的本源。总之,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尽管后世在哲学层面给予许多褒扬,但是,当其偏离原来儒学的真谛,发展为愚民的封建伦理以及与原儒学背道而驰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三纲五常”,就真正把女人打到了十八层地狱。那么,在这种专制文化的压迫下,为何能产生李清照、朱淑真这样的优秀诗人?我以为,“人之初,性本善”,人灵魂里的“真”“善”“美”“圣”都是生而有之,对于“恶”的反抗也是生而有之。这种天性,尤其对知识者,无论男女,无不如此。另外,金兵攻陷汴梁(开封),入主中原,北宋亡;徽宗九子赵构偏安临安(杭州),称南宋。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经济与文化都是空前繁荣的时代,商业贸易繁荣,教育与科技都有很大发展。陈寅恪甚至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清明上河图》再现的是北宋汴梁“锦绣芙蓉国”的一派繁华景象。可以说,那时的宋朝,很有些欧洲“文艺复兴”之势。
强势的程朱理学没有淹没文学的蓬勃之势,宋王朝南迁的伤痛对当时的文人伤害尤深,这些影响都给李清照、朱淑真这样的女诗人在创作上增加了思想和感情的新因素,给女性文学的成熟与发展带来了新前景。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山东齐州章丘人。早年生活优裕,诗词风格闲适。金兵入主中原后,流寓江南,丈夫病故,境遇凄惨悲苦,诗词风格由悠闲而沉郁伤感,悲叹身世,怀念中原。她的诗词语言清丽,善用白描,艺术上别是一家,是中国诗词的一座高峰;所著《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皆散佚。后人辑《漱玉词》,今有《李清照集校注》和《金石录》。
她的作品总是自辟蹊径,独出心裁。早期代表作有《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平淡、自然、清丽、和谐,呼之欲出。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心境、意境,两境契合,优美怡人,展示了人间一派和平境界。《点绛唇》:
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
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诗人以花自喻,伤春,惜春,慨叹易逝的青春。她写闲愁和闺房里的“寸肠千缕愁”,写闲花、闲草和闲情,绝妙工巧,意味隽永。
当金兵横扫中原,李清照移居江南后,生活大变,心情大变,诗词大变。尤其晚年,虽然她还写花写草,但其闲情逸致则完全变了味道;她写愁,再也不是闺房之愁,愁情变成了国恨家仇。“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写的是乡愁。逃难中写下《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1134年,李清照流亡金华,国运维艰,愁压心头,游双溪写下那首著名的《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还有《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声声慢》浓缩了诗人一生的情愁、国愁、家愁,诗写物便是写人。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无论是身邊小事还是家国大事,李清照都能妙笔传神,含蓄隽永,风韵、神韵、情感、思想,浑然一体,写出别人难以企及的作品。李清照的诗词以柔美著称,写尽了孤独、悲凉、凄苦。但她笔下也有豪情万丈的阳刚之气,其家国情怀涤荡着一部中国文学史。
除了写词,李清照也写诗。感时咏史,情辞慷慨,是她诗歌的风格。她的诗有《咏史》《乌江》《晓梦》《春残》《夜发严滩》《题八咏楼》等。1131年即南渡第二年,赵明诚任京城建康知府时,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他用绳子缒城逃走。丈夫的行为使她深感羞愧,为此夫妇失和。在他们沿长江漂流至乌江镇时,李清照留下千古绝唱《乌江》(又题《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她在充满爱国激情的《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二首)序中言其身世,也诉说晚年的苍凉情怀:“……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落,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她虽贫病交加,心里想的还是国家,诗中之愁依然是政治之忧和民族之痛。她歌颂韩肖胄的凛然大义:“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她最后的临别赠言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她还写过一篇歌颂木兰横戈挥师疆场的《打马赋》,谴责宋室的无能,抒发暮年之志。
李清照生于乱世,“以心抗世,以笔唤天”,“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行,爱情之尊”。这位被封建社会“役使”的歌者,在秋风苦雨的悲剧中,最后以寂寞、哀愁和坚毅的个性,“集国难、家难、婚难和学业之难于一身,凡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婚姻、人格方面的冲突、磨难”,都在她的诗词文里得到了展现。
中国文学史历来视李清照为婉约派,但她的诗词从一开始就有大气如虹,不让李白、辛弃疾之豪放。早年尚未出闺阁之时,因闻“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文潜的诗而和之:“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俸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则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记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此诗传出,即令文场骚动,她的诗词富有情思,倾诉了对生命的感悟,饱含着温暖撼人的力量。
李清照后半生颠沛流离,孤身江南。1129年赵明诚病故后,不久她嫁给了只有贪欲之心的张汝舟。他们同床异梦,此公对她时有拳脚相加。心存高洁的李清照,宁可下狱,也要告倒张汝舟,与之分手。在程朱理学的笼罩下,宋朝是中国专制社会男尊女卑最为残酷的一个时代,男人可以妻妾成群,女人却不可再嫁,再嫁就是“不终晚节”。依照法律,妻告夫,不管输赢,都要坐牢两年。李清照以其“欺君之罪”告倒了张汝舟,在她大名的护佑下,只坐了九天牢狱;面对专制礼教,她却成为最早冲破黑暗闸门获得婚姻自由的胜利者。
李清照改嫁又离婚一事,这在专制社会是件大事;如果从“女性意识”来评论那更是了不得的大事,尤其在程朱理学极盛的时代。但是,不可思议或不可能的事实发生了,她坚毅地追求自由,这是专制制度下少有的胜利者。
李清照漂泊的晚年,直至客死江南,再也没有“少年的欢乐,中年的幽怨”,情愁家愁早已化入云烟,唯国破家亡之愁苦附身,她含蓄蕴藉、悲切哀婉的诗词虽为说愁,实为写志,执着的阳刚之气,成为她的心态、心志和心声。李清照的诗词倾吐、抒发的情怀,早已远超古代一般知识女性的“女性意识”。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她是独创一格的,她是独立于一群词人之中的。她不受别的词人的什么影响,别的词人也似乎受不到她的影响。她是太高绝一时了,庸才作家是绝不能追得上的。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之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
七
在中国文学史上,另一位与李清照齐名的女诗人是南宋多情才女朱淑真,其凄怨哀美的诗词艺术高度,常被史家与李清照相提并论。
朱淑真(约1135—约1180),号幽栖居士,生于仕宦家庭,祖籍安徽歙州。《四库全书》说她是“浙中海宁人”,另一说她是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唐宋时期留下作品最丰盛的女诗人之一。
朱淑真天生灵秀,博通经史,琴棋书画皆精,尤工诗词,风流蕴藉。十九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志趣相异的市井俗吏为妻。婚后,“巧妻常伴拙夫眠”是她爱情生活的写照。她曾随丈夫宦游吴越,但是这个俗夫不仅爱寻花问柳,还纳小妾,迫使朱淑真离他而去,甚至她还尝试皈依佛门。不幸的婚嫁,无聊的生活,令她红颜薄命,抑郁而终。
朱淑真曾自编诗词集,死后被父母付之一炬。但她的诗词流播甚广,宋代魏仲恭(即魏端礼)因常听街谈巷议,惋惜这位含恨离世的才女,1182年便将其流布于文朋诗友间的作品缉为《断肠集》(共十卷370首诗,现存310多首)、《断肠词》(原八卷约200多首词,现存一卷32首)和《璇玑图记》传世。
魏仲恭在序中说:“比在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颂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说到她的死,则说:“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聊以慰其芳魂于九泉寂寞之滨,未为不遇也。”魏仲恭与朱淑真为同代人,此序所云,应是真实记录。其后,明代田汝成说:“淑真抑郁不得志,抱恚而死。父母复以佛法并其平生著作荼毗之。”(《西湖游览志》)
尽管女诗人的作品受到文人和百姓的激赏,但因有悖于传统伦理,便受到卫道士的挞伐,指责她的诗词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但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文人都是“卫道士”,明代大画家杜琼为朱淑真的《梅竹图》题词曰:“观其笔意词语皆清婉……诚闺中之秀,女流之杰者也。”
虽然,临安唐佐为之立传,但关于她的婚姻、爱情、创作,甚至死亡,人们所知甚少,认为朱淑真是一位谜一样的女子。时空茫茫,她留给人们的凄婉诗词,远比其模糊的背影要清晰真实得多。我們可以从其清丽的诗词中,真实地听到一位女性的心声。
因朱淑真抒写不幸的婚姻和爱情的痛苦,后世称她“红艳诗人”。她的诗词“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婚后诗词颇多幽怨之音,且表现大胆。
南宋诗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评论朱淑真与李清照诗词之差异时说:“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沉博,下开南宋风气。”其实,作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之差异,不仅与作者所处时代和地域不同有关,更与作者自身的不同处境相关。
朱淑真的诗词总是独出心裁,《生查子·元夕》就是她的杰作之一: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尽管这首断肠名作与其许多诗词风格一致,但卫道者却说此词为朱熹所改,又说朱熹所作,后来干脆将其编入苏轼的集子中,连《四库提要》都说此作“非”朱淑真之作,理由是:女人怎么可以“人约黄昏后”?怎么可以“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如此“出格”的词,不该是女人所为。
朱淑真关于元宵的诗词不止一首,《元夜诗》就是她关于“元夕”的一首绝妙之作:“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吹鼓斗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赏灯那待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人称此诗与《生查子·元夕》有着同工异曲之妙。
爱情之苦无处倾吐,她便借诗词表达自己的心情。《减字木兰花·春怨》就是一首名作: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这首词以五个“独”字,写其孤独、痛苦得坐卧不安的情状,“泪洗残妆”,愁梦不成,写尽了人生之苦。她的另一首名作《菩萨蛮》,也将一位深受专制重压的女诗人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位断肠诗人诗词创作上的主要成就即表现在此类作品之中。不妨再举数首诗词,以示这位女诗人的思想、情怀和诗美的高度。
《谒金门·春半》:
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十二阑干闲倚遍,愁来天不管。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
《蝶恋花》:
楼外垂杨千万缕。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独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绿满山川闻杜宇。便做无情,莫也愁人苦。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
这两阕词,前写愁,后惜春,都是意境清幽,尤其后者,抒发春之眷恋,实则是借多情杨柳、声声杜鹃、潇潇暮雨,深沉含蓄地抒发怀春伤春之情和对人生的眷恋。
据黄嫣梨《朱淑真研究》考证,朱淑真的丈夫纳妾远宦,她回到娘家,没有断过与少女时代的情人幽会,这说明她不认命,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冯梦龙在《情史》里根据朱淑真的两首元宵诗词结论说“淑真殆不贞也”。这意味着什么?丈夫纳妾,她不贞!不贞,意味着反叛。朱淑真的诗词有八十处用“愁”,二十处用“恨”,这都是泪水和断肠写就的。这“愁”字多了,“愁”变成了“仇”!
宋代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第一座高峰,除了李清照、朱淑真,还有张玉娘、吴淑姬、魏夫人、苏小妹、唐婉等众多的女诗人、女词人。她们的诗词都有个性,无论是“断肠”的呐喊,还是以“梅”“菊”自比自怜,或是惜春伤时,相思怀远,都是借意象“自吐肝胆”,除了一定的忧患意识和咏物言志,最多的还是表现女性“断肠”的生活状态,“断肠”的“芳草”生生不息,此种对真爱的渴望与追求,便是她们那个时代女性的心声和生而有之的生命意识,也就是女性意识的觉醒。
八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改朝换代只是新的复兴起点。岁月流转,世事变迁,文学总是踏过前朝的脚印,不断延续和发展自己的精神。
文学的繁荣,总是与经济相依为命。宋元明清,接续发展,为中国文学添加辉煌。宋代以降,闺秀文学和青楼文学作为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主体,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繁荣,到了明末清初,开始呈现真正的繁荣。
宋元相续,喜好文墨、擅长诗词的张玉娘(1250—1276)是连接两代的著名女诗人,人称其文才可与李清照、朱淑贞、吴淑姬比肩,著有《兰雪集》(二卷),被誉为“宋代四大女词人之一”。《山之高》是她的名诗:“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采苦采苦,于山之南。忡忡忧心,其何以堪。汝心金石坚,我操冰雪洁。拟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暮雨心去来,千里相思共明月。”除了寄托哀思、情愁与爱情悲歌的《山之高》《拜新月》《卜归》《古离别》,也有抒发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的《凯歌乐府》《塞上曲》《咏史·谢东山》《从军行》等。
元代除了来自宋末的张玉娘,还有孙淑(字蕙兰,约1304—约1328),著有《绿窗遗稿》,其诗作“闲雅可颂”;生于儒学世家的郑允端(1327—1356)著有《肃庸集》(一卷);贾蓬莱(?—1362),著有《絮雪集诗》《闽杂记》;曾手书《金刚经》的著名女书画家、诗词作家管仲姬(管道昇,1262-1319),著有《梅花诗集》,有一首《我侬词》:“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这就是女性维护爱情与尊严的呼吁书!
明清女性作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各有差异,但作品就是她们“倾诉”的“镜子”。她们的断肠诗、哀怨词,或情致缠绵,或幽怨伤感,或激烈悲壮,皆是面对现实的有感而发。
明末以降,尤其清代二百多年,温婉灵秀、能诗善文的江南女作家多如天上的星星,光明灿烂,江浙则是女性文学的摇篮。这些女性作者只是历史和文献留下来的一个部分,而因战乱和岁月流逝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的女性作者则是一个未知数。中国以大家闺秀为主体的家族群体形式的女性写作,是世界文学的一个奇迹,有著作或编著传世的女性作家多达四千余人。这些女性作者,几乎都是出身于书香门第,有着优渥的生活,诗书画从小就是她们人生的组成部分。
沈氏元末迁居吴江,历时四百年,这个家族共诞生文学家近一百四十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这样赞颂沈氏家族:“门才之盛,甲于平江,而子姓继之,文采风流,代各有集。”沈氏文采风流当然包括女性,沈素瑛、沈大荣、沈倩君、沈宛君、沈静蒪、沈媛、沈关关、沈宪英、沈华曼、沈少君、沈蕙端及嫁入沈家的张倩倩、李玉照、顾孺人等,都是有著作的闺秀女诗人。
叶氏文学家族也是久负文名,叶绍袁与著名曲作家沈憬之女沈宜修结婚后,使叶氏女性文学代代相传,以沈宜修及其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叶小繁为中心,还有与叶氏联姻的沈智瑶、沈蕙端、周慧贞、沈华鬘、沈树荣、颜绣琴等,组成了明清江浙灿若群星的两大女性诗群。
沈宜修之妹、才情不在李清照之下的沈静蒪(字曼君)著有《适适草》,极善小词:“春未盈,蝶睡轻,柳外东风吹恨生,日长花气清。瘦魂惊,一声莺,羁住愁魔不放行,遥山翠半醒。”沈宜修之女,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戏曲家叶小纨(字蕙绸,1613—1657)著有雜剧《鸳鸯梦》,还有诗集《存余草》。自幼聪慧、怀志高远的叶小鸾(字琼章,1616—1632),十三岁填词赋诗、能琴擅画,十七岁夭折,著有《返生香》,她的深沉之作如《九日》:“风雨重阳日,登高漫上楼。庭梧争坠冷,篱菊尽惊秋。陶令一樽酒,难消万古愁。满空云影乱,时共雁声流。”不涉世事的她,其诗心确有“末世”的气氛。
除了江南家族的女性作家群体,山东孔氏历代女性诗人群体也不可小觑。孔氏家族的女性诗人包括孔丽贞、孔素瑛、孔传莲、孔继孟等孔家女孙,以及颜小来、叶粲英、蒋玉媛、叶俊杰等孔家女媳各二十余人,每人均有诗词专集或诗作行世,共计刊刻诗词专集三十余部。
明代除了这些文学世家的女性作家,还有马守贞(1548—1604),著有《湘兰子集》及传奇《三生传》;涉猎群书、博学善文的名妓梁小玉,著有《嫏嬛集》《千家记事珠》《咏史录》《诸史白卷》《山海群国志》《草木鸟兽经》《古今女史》《古诗集句》《乐府骊龙珠》和传奇《合元记》;诗人兼剧作家梁孟昭(1560—1640),著有《墨绣轩吟草》《山水吟》《山水忆》和传奇《相思砚》;被称为“一代作手”,诗作清新幽异,又长于作曲的江南才女阮丽珍(1607—1653),著有传奇《燕子传笺》和杂剧《梦虎缘》《鸾帕血》;沈静蒪(字曼君),所著《适适草》包括诗、曲、文、赋,不仅“清新卓颖,真情自适”,还颇具竟陵学派之风;“诗巧慧俊冷,不作浅浮小语”的彭琬(字玉映),著有《挺秀堂集》(又名《梦月轩集》);“忙里不知秋色老”“才情两足”“名句络绎”“意境英气而阔大”,与其姊彭琬“时称双璧”的彭琰,著有《闲窗集》。
这里要提及一位从中国古代诗坛走失的女诗人倪仁吉(1607—1685),她是“绣、画、诗、书”四艺俱绝的才女,尤工于诗,著有妙入秋毫的《凝香阁诗稿》(即《凝香阁集》,1665年刊印,辑诗300余首)。她的农家诗被誉为“千古一绝”,“语言通俗、生动、朴素,似乎随手拈来,不事雕琢,却显出意境的深远”。她以对农村生活的真情,从一个农村普通女子的角度,分“春”“夏”“秋”“冬”四季,专写“纺纱”“织布”“刺绣”“樵夫”“渔夫”“牧童”“割麦”“耘秧”“车水”“灌水”“种豆”“栽芋”“浇瓜”“剥枣”“种麦”“翻耕”等,系统记录农事活动、民俗民风及山川风物,抒发了对农村生活、劳动和祖国河山的热爱,为历代女诗人所少有,“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此举《即景之一》为例:“露冷池莲晓更愁,折来聊向胆瓶留。小楼又有霞光入,妆点红衣一段秋。”这种心境和意境,可谓光彩照人!再如《凝香阁诗稿》中的《题画诗》,“设意中之景,想景中之人,写人中之画,作画中之诗,对其景而其人呼之欲出,而其人之才与情亦无不毕出”,可谓构思独特,立意高远。
倪仁吉是一位“好媳妇”“好妻子”“好母亲”,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人生的创痛和悲苦、人性的扭曲与压抑,在其人格自我完善和塑造中,人性的挣扎和解脱,才使她成为诗人。
朱光潜说:“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是人格的焕发。”诗、词、文、赋、题跋皆工的清代才女沈彩(1772—1837),著有《春雨楼集》(十四卷,其中诗词七卷),收录其诗、词、文、赋、序、题跋480余首(篇),作品私人化、纪实性强,“还原了侍妾心灵世界的婉曲与幽妙”,是清代侍妾生活与传统家庭夫、妻、妾关系的极佳个案文本,真实再现了传统家庭中的夫妾关系,也是底层女性生存状态和日常生存的一面镜子。“我本青云侣,失足堕尘寰。飘颻鸾凤群,逸兴不可删。拾翠弄蔻茞,采香佩兰蕳。麻姑向我笑,手挽双髻鬟。”“簪花妙格几曾悭,万里鲸波到海山。不似唐宫一片叶,只随沟水向人间。”诗作浅而不俗,其作品虽多为闺阁生活实录,但也不乏底层的凄苦哀怨!袁枚有闺中三大知己女诗人:其一,严蕊珠,著有《露香阁诗稿》(1803年刻本,诗89首),其诗清新妩媚,多为自然山水的抒写;其二,席佩兰(1760—1829),著有《长真阁诗稿》(七卷)、《傍杏楼调琴草》,其诗“天机清妙,音节琮琤;其三,金纤纤(名金逸,1770—1794),著有《瘦吟楼诗》《虎山唱和诗》。另外,袁枚对著有《湘筠馆诗》的孙云凤(1764—1814)也是美语相加,他在《二闺秀诗》中云:“扫眉才子少,吾得二贤难。鹫岭孙云凤,虞山席佩兰。”袁枚对著有《香奁诗话》的金燕也是评论甚高:“字字出于性灵,不拾古人牙慧”,还称“似此诗才,不独闺中罕有其俪也”。
心性豪侠的女诗人沈善宝(1802—1862),不仅有《鸿雪楼诗选初集》《鸿雪楼词》传世,还以十余年之精力,编辑了《名媛诗话》(12卷),对千余清代女诗人多有翔实的梳理与记述,奠定了道光与咸丰时期(1821-1860)清代女性文学的实绩。
清代有无数才女作家,除了著有《天雨花》的弹词女作家陶贞怀及著有《再生缘》的陈端生(1751—1796),重要的女诗人还有王贞仪、吴琼仙、季娴、王端淑、蔡琬、江珠、恽珠、许禧身、许之雯、苏慕亚、杨芸、施淑仪、薛绍徽、陈芸等。
晚明以降至清季,不仅有血亲姻亲家族式的女性写作族群崛起,就连女性诗社也以家族化、地域化现身,诸如蕉园诗社、清溪吟社、秋红吟社、泰州仲氏女子社、常州张氏四女社、建安荔乡九女社、湘潭梅花诗社、成都浣花诗社等,还有与文士关系密切的青楼文学,那些女性作家,尽管她们多出身于书香门第富庶之家,但她们熟悉底层女性的生活,其作品不仅再现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不少作品也揭示了底层女性的思想感情。除了诗词,还有戏曲创作,都促进了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九
一种新的文化思想不一定非得是已有文化的全部“遗传”,一般说来,经济才是文化生长的沃土。当历史走过晚明踏入清朝的大门,始自晚唐与宋代的东南沿海商业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社会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文化人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异化出新的思想,文化也就在这些新的色彩中绽放出从未有过的崭新花朵。
孔孟与程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颜元曾说“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是明末清初的大儒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之新前所未有:消解和反对“理学”“心学”,批判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理学”“心学”都违背了孔孟旨意,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甚远;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神化孔子和独尊孔孟之道,认为孔孟之言也绝非“万世之至论”,反对封建礼教,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婚姻自主,追求平等与个性,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李贽:《焚书》)。黄宗羲提倡民主思想,“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萬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顾炎武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提倡“利国富民”、明道救世,怀疑君权,还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提出均天下、反专制、反禁欲主义。他们离经叛道,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先驱和“异见者”,他们的哲学与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诉求,是儒学发展史上第一次生发出的“民主”元素,对中国近代新思潮的到来有所启蒙。
当儒学行走至清末民初及“五四”时期,“叛逆”思想发展到了巅峰,以鲁迅为首的知识界对孔子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无情讨伐。我们研究者多以为“五四”新文化思想是受了西方思潮的陶冶,其实也深受清代那几位大儒思想的影响。这是儒学命运遭遇严厉考验的一个时代,孔子从“圣人”被贬为“孔老二”。现在回头仔细研讨鲁迅那一干人马“打倒孔家店”之因,实际上所反的主要就是“独尊儒术”和宋明“理学”和“心学”对于儒学的利用与误读所演绎的那些偷梁换柱、贻害无穷的封建礼教。
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学,长期不被史家重视,他们不自觉地受传统意识钳制,面对文学,只知有男而不知有女,不能一视同仁,或是没有以足够的激情和理性认知女性文学之于中国文学史的贡献,这就造成了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蔡琰、李清照等数人之外,大多数女性作者都被淹没在中国文学的深海里。这些被“缺席”的古代女性作者,正是中国文学应该发掘的财富。
清末民初,风雨如晦,那是中国历史记忆中的一个非常时代,或者说是中国由此走向光明的开始。那时由于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华大地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和改良派的变法维新。知识界的觉醒缔造了“救亡图存”的意识,中国社会思潮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动荡,文学上便出现了一个“秋瑾时代”。秋瑾是中国女性文学转型期的一个关键的代表人物。这个时代,秋瑾向死而捐躯,文学上的激昂慷慨,预示着中国女性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代的到来。
秋瑾于光绪元年出生于厦门一个官宦之家,从小在家塾攻读经史诗词,十余岁就能作诗填词。1900年,秋瑾在北京目睹八国联军抢劫烧杀,这给了她极大的刺激,开始读新书新报,关心时事,又因与丈夫不和,她要冲出家庭牢笼,谋求自立,立志与男子共同负起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责任,以达到“驱胡兴汉、男女平权”。1904年她到日本留学,先后与陶成章等人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大业,组织“共爱会”“十人会”“洪门天地会”。她自号“鉴湖女侠”,另号“竞雄”,其意是要与男性竞争英雄。秋瑾主张民族革命与女权运动齐头并进,在东京创办《白话报》月刊,宣传推翻清廷、男女平权,关心女子教育,反对缠足。1905年秋瑾加入“光复会”和孙中山的“同盟会”,翌年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为唤醒妇女创办白话《中国女报》。1907年,她与徐锡麟策划的皖浙起义失败,决心用自己的头颅撞击“警钟”,以殉难唤醒国人。秋瑾被捕后,在酷刑审讯时,回首长夜三千年,她长叹一声,只写了七个流传至今的大字“秋风秋雨愁杀人”。当年,农历六月六日(1907年7月15日),年仅32岁的秋瑾,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秋瑾代表了女性的真正觉醒。
“秋风秋雨愁杀人”是秋瑾对“革命”未能成功的万般无奈和失望,其中蕴藏着她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巨大关怀。这一点,可从她的《致徐小淑绝命词》中得到印证:
痛通报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未酬,雄心未渝,中原回收肠堪断!
秋瑾一生短暂,其伟大精神,就在于追求国家独立自主。她的“新亭口之泪”的大气象,就是留给未来的曙光。她一生不仅为民族家国,也为女性的解放、自由平等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努力,被誉为中华女性解放的第一位精神导师!这一点,可从她的诗文中得到充分证明。她的许多信笺都流露了革命心声,《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和《中国女报发刊词》等都是她伟大精神的深刻昭示。
虽然太平天国洪秀全时期就提倡白话文,颁布了《戒浮文巧言谕》,提倡“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诗界革新导师”黄遵宪(1848—1905)也提倡“我手写我口”、俗语入诗;编辑《白话丛书》和创办《无锡白话报》的裘廷梁(1857—1943)发出“白话为维新之本……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但都没有得以实践。秋瑾是近代以白话写作的第一人。1905年她到日本后开始以白话写文章,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要早十多年。
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当初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话,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听晨钟之初动,宿醉未醒;睹东方之乍明,睡觉不远……然则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非报纸而何?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升级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中国女报发刊词》)
这就是秋瑾的声音!
从清季民初到“五四”时期,追求光明的女作家,叛逆,反抗,是她们作品精神的核心。秋瑾、徐自华等人,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
秋瑾的结拜姐妹徐自华在秋瑾就义后写下了《满江红》,其爱国之心、忧民之意溢于言表:“……亡国恨,终当雪;奴隶性,行看灭。叹江山已是,金瓯碎缺。蒿目苍生挥热泪,感怀时事喷心血。愿吾侪,炼石效娲皇,补天阙。”
秋瑾豪爽雄健的性格、为国为民的大仁大义之精神,成为中国女界第一面昭示解放的旗帜。在文学上,她的诗文所体现的女性意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位列前沿。因此,秋瑾是中国女性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代表。她的诗文褪去了传统的哀婉色彩,代之以剑拔弩张风格。
清末民初的女性文学,其思想和艺术有异于以往的女性诗文,是中国女性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期。这时期除了秋瑾,还有郭筠、徐自华、吕碧城、张默君、崔震华、杨步伟、尹锐志、沈慧蓮、吕云章、钟明志、曾宝荪、冼玉清、沈亦云等女性作者。她们多数都具有一定的新思想,热诚参与拯民救国,反抗压迫,争取自由平等和国家富强。她们也许不清楚儒家“经世致用”和法家“富国强兵”的含义,但她们心里都有一个并不清晰的“民国”或“共和”。从她们的诗文中,我们既可体认到新思潮和革命对于女性的影响,亦可窥视到女性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贡献。
起自“五四”时期,至20世纪末,中国文学界迎来了陈衡哲、冰心、凌叔华、庐隐、石评梅、袁昌英、冯沅君、丁玲、陈学昭、沉樱、谢冰莹、苏雪林、白薇、冯铿、陆晶清、濮舜卿、萧红、赵清阁、方令孺、安娥、罗淑、罗洪、关露、葛琴、彭慧、林徽因、张爱玲、苏青、梅娘、杨刚、田琳、白朗、草明、李伯钊、颜一烟、王莹、凤子、曾克、杨绛、林海音、琦君、艾雯、徐钟珮、胡品清、罗兰、张秀亚、孟瑶、郭良蕙、繁露、毕璞、华严、严友梅、童真、刘枋、张晓风、林文月、萧丽红、袁琼琼、曾心仪、廖辉英、萧飒、三毛、欧阳子、蓉子、林泠、席慕容、张香华、李昂、施叔青、季季、苏伟贞、朱秀娟、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琼瑶、赵淑侠、林佩芬、朱天文、龙应台、黄庆云、亦舒、西西、程乃珊、林燕妮、周洁茹、周桐、林中英、懿灵、严歌苓、虹影、林湄、张翎、吕大明、卢岚、九丹、郑敏、菡子、陈敬容、李纳、林蓝、柳溪、宗璞、茹志鹃、刘真、柯岩、黄宗英、韦君宜,以及谌容、张洁、叶文玲、张抗抗、霍达、舒婷、戴厚英、王安忆、王小鹰、王小妮、陈染、林白、方方、池莉、张烨、张真、叶梦、斯妤、张辛欣、张雅文、凌力、马瑞芳、航鹰、陆星儿、竹林、赵玫、唐敏、黄蓓佳、乔雪竹、陈祖芬、张欣、胡辛、徐小斌、蒋子丹、毕淑敏、铁凝、徐坤、迟子建、残雪、叶广岑、马丽华、刘索拉、蒋韵、田珍颖、王英琦、斯妤、须兰、王旭烽、马晓丽、马秋芬、皮皮、素素、孙惠芬、萨仁图娅、韩小蕙、万方、张悦然、周晓枫、冯秋子、袁敏、遇罗锦、林子、伊蕾、翟永明、唐亚平、海男、傅天琳、陆忆敏、萨玛(崔卫平)、蓝蓝、林雪、李小雨、李琦、康桥、虹影、张曼菱、路也、冯晏、空林子、王妍丁、潇潇、朱文颖、林娜北、冷梦、叶梅、林湄、张翎、周洁茹、金仁顺、安如意、盛可以、任晓雯、周瑄璞、魏微、鲁敏、乔叶、戴来、葛水平、姚鄂梅、付秀莹、马小淘、滕肖澜、霍艳、七堇年、毛竹、毛尖、苏瓷瓷、娜夜、廖一梅、纳兰妙殊等。至今中国作家协会的女会员,大约有三千人。她们高举“解放”的旗帜,撘乘文学春潮,乘风破浪,集结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广场。
清代至今,女性诗文作品的集辑刊印和出版也是一个奇观,重要的文献研究著作有《名媛汇诗》(郑文昂编,20卷)、《名媛诗归》(钟惺与谭元春合编,36卷)、《名姝文灿》(张嘉和辑,10卷)、《妇考》(收录明清女诗人女作家4000余人,作品4000余种)、《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徐乃昌编撰,10集100家107卷;光绪二十四年校刊,20册)、《闺秀诗抄》(16卷,宣统元年刊本,8册)、《中国妇女文学史》(谢无量著,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版)、《玉栖述雅》(况周颐著,1921年,1940年出版)、《闺秀词话》(雷瑨、雷瑊著,1925年出版)、《清代妇女文学史》(梁乙真著,中华书局1921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谭正璧著,光明书局1930年版)、《中国现代女作家》(贺玉波著,现代书局1932年版)、《中国女性文学史》(谭正璧著,此书系作者对《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修改润色与订正版;光明书局1935年版)、《历代妇女著作考》(胡文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女性文学史话》(谭正璧著,天津百花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古代妇女史》(刘士圣著,青岛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二十世紀中国女性文学史》(盛英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林丹娅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树明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双调夜行船——90年代的女性文学》(徐坤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女性词史》(邓红梅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女性文学新探》(盛英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阎纯德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孟悦、戴锦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女性文学教程》(乔以钢、林丹娅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任一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曹新伟、顾玮、张宗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古代文学简史》(苏艳霞、李静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
文人墨客无意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女性作者的宝贵文献,尤其清末至民国和“五四”时代,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于传统女性文学的关注,似有停滞,1976年之后,对于传统女性文学之研究之风又渐渐吹起,到了21世纪,此风才又吹遍了大江南北。而20世纪新文学之女性文学研究,除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及其属下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委员会常开学术会议,各个大学开设的“女性文学研究”“女作家研究”课程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研究课题也很多,数百家杂志也都在刊发此类研究论文。
1976年后缘于英国维尼吉亚·沃尔夫的《自己的房间》和法国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学界乘女性创作之风,其研究也繁荣起来。一时间,关于女性文学、女性解放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争论不休。关于“妇女文学”与“女性文学”,谭正璧先生说:相比之下,“后者更强调了女性的独立与自尊”。何为女性文学?我一直认为: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女性文学”!“女性意识”既包含女性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也包含耳濡目染的社会属性,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精神,小视野,温柔温情儿女情长,大视野,豪迈的国家前途与命运,都属于女性文学内容。
从传统到现代,说不尽的中国女性文学的前世与今生。这个大课题,期待年轻学者写出中国女性文学独一无二的辉煌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纪念。
2022年4月29日于神州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