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之见”新论
何心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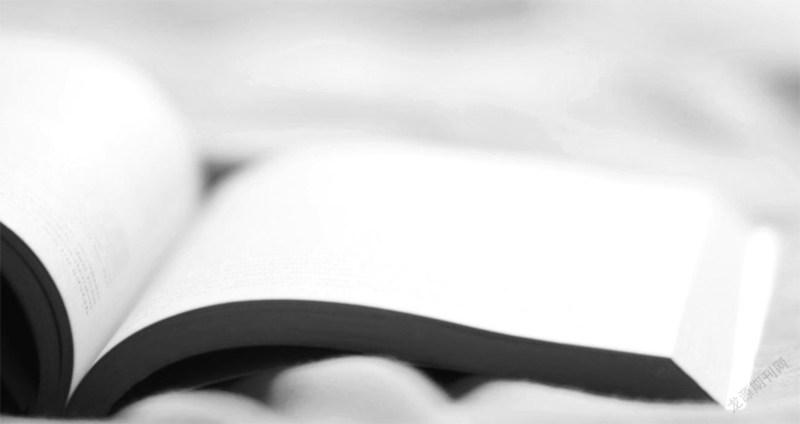
宋代邵博在《聞见后录》中说:“书生之见,可言而不可用者哉!”这是说,书生的见解说着好听,实际却没有可行性,因此将“书生之见”作为贬义词,来驳斥一些只重理论而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言论。然而,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新时代的新“书生”,有能力也有必要发一发切合时宜的“新书生之见”,来推动时代前进了。
邵博对书生之见“可言而不可用”的评价着实有些偏激,他未曾见过天下所有书生,也未曾听过天下所有的“书生之见”就下此定论,其理由之充分性令人存疑。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邵博这话说得却也不无道理。在生产力水平尚低,交通闭塞的古代,人们的实践经验极其有限:农民固着于土地,工匠只精通单一的技术。而随着科举制的完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更是常见,他们有“读万卷书”的学识,却难有“行万里路”的经验,因此发出“可言而不可用”的书生之见在所难免。
“见”可以是对时事的评判,也可以是对文学的创作。在古代,书生们常常因为生不逢时、不受重用而消极避世,不愿“见”;现如今,书生“不见”或“无见”却反而更是普遍。使得当今书生之“不见”现象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实用主义日益盛行,浮躁之风愈甚,人们更偏爱“快餐文学”。地铁、公交车上,埋头刷娱乐新闻的上班族数不胜数;而图书馆里,愿意沉下心来去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却少之又少。知音难觅,听者难寻,这就让越来越多的书生不愿“见”了;而“键盘侠”“网络喷子”们的恶语相向,更让许多书生不敢“见”了。
难道,书生就真的可以 “不见”或“无见”吗?显然,并非如此。发“见”正是书生们的责任和使命,“不见”或“无见”则是书生倡导“躺平”理念,不再思考针砭时事,逃避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如此,我们又如何期望他们扛起时代大梁,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呢?
在我看来,新时代要有“新书生之见”。这就要求新书生们看到自己的价值,认同与勇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上下求索中形成“见”,在觉知中深入“见”,并自觉地大胆地表达“见”。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的“认识”也包括了见解,我们的见解是不是真理,必须靠实践来检验。在发表见解之前,我们可以通过实践验证,这样能使见解更具说服力。那么,发出了狭隘的、错误的见解怎么办?我们是在不断的试错中成长的,只要能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及时修正,并从错误中总结经验,这不也是“新书生之见”所蕴含的一种敢闯敢为、勇于改错的态度吗?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青年的期盼。希望所有中国青年,不只是书生,都能敢于又乐于发出“新书生之见”,推动时代前行!
评点
古语有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说的正是那些与现实脱节、与生活脱轨的知识分子。当今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越发重要,正如作者所呼吁的那样:我们需要新时代有理想、有担当、有见解的新书生。文章构思严谨,论证充分有条理,用词考究。
(指导教师:何文魁/编辑:李跃)035B5837-464F-41AE-AE62-D6581FBF4E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