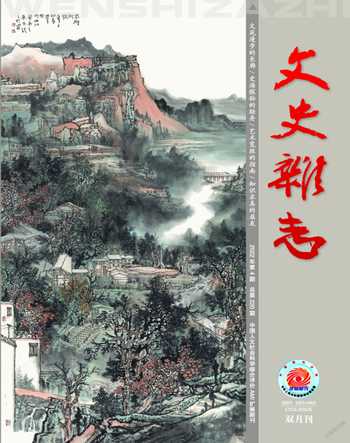《今注本二十四史·汉书》指瑕一则
梁英旭
孙晓先生主持修注的《今注本二十四史·汉书》是近年来《汉书》研究的重要收获,其“今注”部分广泛吸收今人研究成果,注文力求“准确、质朴、简练、严谨、规范”,立意颇高。然个中仍有可待商榷之处。《律历志·上》:“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其状似爵,以縻爵禄”,原书“其状似爵”一语颜师古无注,今注本在“爵”字后加注“爵:商周时的酒器”,恐非。按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新莽时期的铜嘉量,其形状绝不似商周酒器三足爵,颜师古此处缺而不注,未必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今注于此将“爵”释为商周酒器,不知其据何在,宜可再酌。事实上,注释中提到的商周酒器三足爵,至迟到西周末期在考古发掘中就绝少见到了,且其是否作为饮酒器,在学界仍有很大分歧。《说文》释爵:“爵,礼器也。”这里的爵当然指的是三足爵,但为何说它是礼器而不直言酒器,值得注意。对此学界已有坚实的论述,此不赘言。朱凤瀚先生指出东周文献所言之爵,“或是饮酒器总称,或是酒器专称,但皆不会是指上述商、西周时期的铜爵”[1]。既然东周之爵已非商西周之爵,那么汉代常用的“进酒行爵”之爵便很难理解为商周三足爵。换言之,汉代当另有一种爵,且该爵状似当时的容器“量”,上引《汉书·律历志》中所载之爵即就此而言。《仪礼·士虞礼》将爵分为“足爵”“废爵”两种,郑玄注“废爵”为“爵无足”者。孙机先生将这里的足爵视为三足爵,无足爵释为瓒形爵。[2]从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瓒形爵实物来看,其外形已距三足爵甚远,与汉代容器“量”则更为接近。阎步克先生认为爵的器名“曾三次由一种器物迁移或拓展到另一器物上去”,因而产生了四种外形不同的爵,它们分别是商西周的三足爵、继起的斗形爵、春秋以来饮酒礼上使用的筒形爵以及宋代《三礼图》中描绘的雀杯爵。至于汉人所言之爵具体何指,阎步克将其与汉代常用的饮酒器“卮”联系起来,该说甚为有力,“其状似爵”恰为其证。[3]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筒形杯多件,伴出物疏简上写有“髹布小卮”“斗卮”等字样,为汉卮无疑。只需将其与现存汉代嘉量齐观,一目了然,合若符契,則“其状似爵”之爵所指为何,也就不辨自明了。综上所述,《律历志》此处所载之爵,并非商周酒器之三足爵,而是汉代的“卮杯爵”。这也提示我们,“爵”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不同时代名物关系或有变动,读史至此当有所用心。
注释:
[1]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2]孙机:《说爵》,《文物》2015年第5期。
[3]阎步克:《由〈三礼图〉中的雀杯爵推论“爵名三迁,爵有四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作者: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