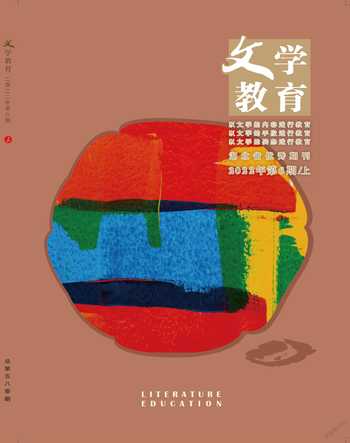汪曾祺《聊斋新义》中女性形象的现代性
乔乔
内容摘要:汪曾祺以全新书写角度,对经典小说《聊斋志异》作了“现代性”改写。在改写的部分篇目中,他按照自己独有的美学经验和审美旨趣,为传统两性关系注入平等、自由现代意识,赋予了传统封建桎梏中的女性以健康、自由的人性和情爱观,重塑了与蒲松龄笔下完全不同的、具有现代性意识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汪曾祺 《聊斋新义》 女性形象 现代性
20世纪80年代,经过三十年的漫长沉淀和文学思索,长期搁笔的汪曾祺重回文坛。虽岁值花甲,但创作激情和才能却蓬勃爆发,这期间他佳作迭出、好评如潮,为中国当代文坛添补了许多独属于汪曾祺审美旨趣的精良作品。1986年至1991年间,汪曾祺在蒲松龄《聊斋志异》原作的基础上,对《聊斋志异》部分篇目进行重新改写,创作完成《聊斋新义》。他在《〈聊斋新义〉后记》中说:“我想做一点实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对于改写,汪曾祺有一套自己确立的原则:“小改而大动”,即尽量保存传统作品的情节,而在关键地方加以变动,注入现代意识。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从六朝志怪到《聊斋》,都值得重新处理,从哲学的高度,从审美的视角。可以说,汪曾祺改写《聊斋》的初衷和目的就是把“现代意识”融入“古典传奇”之中,让旧故事言说新思想,从而完成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性改写。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加之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汪曾祺对自由、对美、对人性颇为关照,作为“抒情人道主义者”的汪曾祺一向关心、尊重女性,甚至有一种膜拜女性的心理,女性是他心中最纯真最美丽的象征。诸如《受戒》中的小英子、《大淖记事》中的巧云、《薛大娘》中的薛大娘、《小姨娘》中的小姨娘等等,她们不受任何外在事物和世俗的拘束,活得自由,爱的也自由,汪曾祺总是尽可能的让这些女性们展示出最为完整的生命力和最为健康的人性,因此在下笔改写《聊斋志异》时,汪曾祺不可能不受到他自有的审美旨趣和审美理想的牵引,他以现代人的眼光、现代性的思考,重新对这部经典作品加以审视、忖度,他的改写绝不是在蒲松龄给出的既定圈子里作毫无创新的改写,他的创新是要跳出原作者的思想和主题,舍弃原作的旧思想,把自己的思想灌入其中,尤其对《聊斋》里涉及情爱及两性关系的篇目和章节进行改写时,汪曾祺更是对原作思想主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并沿着他惯有的书写传统和审美经验,饱含对女性的热爱,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灵动的女性新形象。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是当代作家与古代作家的博弈,是现代性思想和旧封建思想的博弈。与其说汪曾祺是完成了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改写,不如说他是在充分借用吸纳原作的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对自己审美经验的又一次尝试,他真正要写的是属于他自己的《聊斋》。
汪朗曾说,父亲汪曾祺对原著小改而大动,故事和人物的描绘变得清晰明了,从现代人的哲学观念、审美视角,注入更多的生命意义和人性的幽微曲折,即便是细致微小的情节也能引人深思。原作中,蒲松龄对魏运旺身份建构照循其固有的落魄文人书写模式:昔日显赫家族+当下落魄失意——
魏运旺,青州之盆泉人,故世族也。后式微,年二十余废学,就岳家,业酤。
封建男权社会有严格的等级秩序,这让许多像魏运旺一样丧失话语权利和社会地位的落魄文人试图以一种易得且代价极低的方式,寻找一个可控的话语世界,从而实现自身话语权力的转移,而这样的世界一定是由比自己地位还要低、几乎失语的女性所建构。于是那些花鬼狐妖幻化的女子成了男子们摆脱“阉割”焦虑的有效途径,这些异类女子不可能具有主体性和话语权。“狐妖美女”极形象地概括了男性或男性文化对女性意识上的排斥和无意识上的欲望这样一种矛盾状态的最终解决,那就在狐化女、女化狐的过程中,去尽异己的野性妖氛。
在蒲松龄所架构的双性关系里,狐女被充分物化成一件几乎没有自主性的物品,被赐予谁皆由前因和命定,她自己不需要决定也不可能决定。被宿命裹挟,这段情爱中几乎没有爱情的因素存在,如同《聊斋志异》中许多或妖或仙的异类女性一样,狐女出现只是为了宽慰落魄文人,让他们重新拾得丧失的话语权力。不再有野性和妖氛的狐女,既保留了异己特征,又成为欲望对象,而且还是一种不必绳之以“父法”(譬如)婚姻的欲望对象。在何时需要出现,何时又该离去的棋盘上,狐女俨然一颗被操纵的棋子,操纵者不是魏运旺,也不是书生,而是“命数”。这是蒲松龄给予像魏运旺这样落魄文人的补偿和安慰,魏运旺与狐女的的结合与交欢空洞且毫无价值。
面对这样空洞且无意义的两性关系,汪曾祺自是不敢苟同。他重新忖度考量,首先让二小从男权社会被阉割的心理焦虑中摆脱出来,从有妻的丈夫变成因家寒而未說亲的少年。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魏二小与狐女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被赏赐的轻佻艳遇。狐女也不再是蒲松龄笔下因“舍妹与有前因,便合奉事”而被赠予他人的礼物。汪曾祺为这对小儿女的关系注入自由、平等的现代意识,使无法把控的陈腐宿命意识“命数”经他之手转化为完全自主、可把控的“爱情”,狐女来是因为爱,走也是因为爱,爱的时候潇洒、自然,不爱的时候也够坦荡、率真——
“你今天来的早?”
“我要走了,你送送我。”
“要走?为什么要走?”
“缘尽了。”
“什么叫‘缘’?”
“缘就是爱。”
“……”
“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你忍心?”
“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活。”
来的时候因为喜欢,走的时候因为不那么喜欢,来去都因为自由且不受约束的爱,这与汪曾祺一贯主张男女情爱自由是相一致的。《薛大娘》中的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薛大娘为男女拉纤,讲的是一个有情,一个愿意,和吕三在一起也仅图个喜欢。这是汪曾祺的理想,是其对女性的独特关照,对健康人性的独特关照。这种超越世俗、完全自由的爱情观,即使在当下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和超越性。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的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女性只有完全隐藏自身,成为男性的依附时(比如“某某的母亲”“某某的妻子”等),才具有身份标识,往往没有独立的身份,被记住姓名的女性是很少的。女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被历史遗忘,而是根本就没有历史。《聊斋志异》里多数女性没有明确的身份和名字,她们最主要的身份角色也只是某氏、某妻。妻性被强制赋予,自主性剥夺殆尽,作为无意义符号,她们参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基本没有话语权。
蒲松龄《陆判》的主题思想意在表现陆判与朱尔旦的人神友情,朱氏和吴女作为简单的行动元参与其中,不构成故事的主题和中心,朱氏在两性关系中被强行赋予的妻性也基本被消解,沦为一个不需要任何情感的器物。来看蒲作《陆判》是如何描写朱氏早晨醒来发现换头这一故事情节——
朱妻醒,觉颈间微麻,面颊甲错......夫人引镜自照,错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细视,则长眉掩鬓,笑靥承颧,画中人也。
移花接木,作者借由朱尔旦视角描述朱氏换头后的娇好容貌,从而完成换头的最终意义,取悦朱尔旦,满足一个丈夫的低等审美需求,朱尔旦满意则意味朱氏换头的成功。这不仅仅是朱氏个人的悲哀,也是封建社会女性无法回避的悲哀。即使是试图揭露封建统治黑暗,抨击封建礼教束缚的蒲松龄,其作品仍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
汪曾祺对《陆判》进行颠覆性的意义重构,他把更多笔墨放在对朱氏换头后一系列对话及换头后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描写充分体现出汪曾祺的现代性思考——
第二天,朱尔旦的老婆起来,梳洗照镜。脑袋看看身子:“这是谁?”双手摸摸脸蛋:“这是我?”这是朱氏第一次在身体变化后对自我身份认知产生的疑惑和焦虑。接下来由换头产生的一系列尴尬事件,让朱氏再一次思考自己究竟是谁这个问题——
朱尔旦的老婆换了脑袋,也带来了一些别扭。朱尔旦的老婆原来食量颇大,爱吃辛辣葱蒜。可是这个脑袋吃的少,又爱吃清淡东西,喝两口鸡丝雪笋汤就够了,因此下面的肚子就老是不饱。 晚上,这下半身非常热情,可是脖颈上这张雪白粉嫩的脸却十分冷淡。吴家姑娘爱弄乐器,笙箫管笛,无所不晓。有一天,在西厢房找到一管玉屏洞箫,高兴极了,想吹吹。嘬细了樱唇,倒是吹出了音,可是下面的十个指头不会捏眼!
吴女的头拼接到朱氏的身体上,导致吴女不是吴女,朱氏也不再是朱氏,成为拼凑起来的角色,一个发生内在分裂的异体。
“你现在贵姓?姓周,还是姓吴?”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么你是?”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我,还是不是我。”这张挺好看的面孔上的挺好看的眼睛看看朱尔旦,下面一双挺粗挺黑的手比比划划,问朱尔旦:“我是我?还是她?”
小说以朱氏对自我身份的质询作结,极具开放性和荒诞感,我们亦不禁沉思,朱氏到底是谁?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汪曾祺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饱含对女性的极度关怀,完成对封建旧女性的现代性塑造,让她们在异化、压制的逼仄世界里,拥有对自我身份思考的可能。“我是谁”是女性开始关注自身的开始。这种不断追问自我、反观自我的身份追寻,正是汪曾祺改写的目的所在。
为传统小说注入现代意识,汪曾祺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完成了对《聊斋志异》的颠覆、重构和升华。汪曾祺笔触始终流淌在美和人性的河流里,他爱这些鲜活的生命,笔也总是尽可能的去放开,让人物自己去呼吸,去表达。在处理《聊斋志异》里这些封建女性形象时,汪曾祺的热爱也丝毫未减,他不愿意,也不舍得让笔下的女性身处男权话语的囚牢里,他用自己的笔为她们放生,让瑞云、狐女、朱氏等等这些封建女性拥有自由的生命、健康的人格,让她们拥有自由、平等的现代男女情爱关系。汪曾祺的改写是在自己的志趣里拿自己的东西,是其对自己审美志趣的又一次实践,这些美好的女性同小英子、巧云等共同构成了汪曾祺女性形象人序列,经由现代意识过滤,散发出更多的时代新义。
参考文献
[1]汪曾祺.后十年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2]汪曾祺著梁由之编.后十年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3]高丹《聊齋新义》:汪曾祺是如何改写《聊斋》的[EB/OL].澎湃.2020-01-21,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
_5585119,2021-01-27.
[4]汪曾祺.后十年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汪曾祺.后十年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8]徐先智,范伟.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论晚清小说中女性的社会规训及其逻辑[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8(3):107-110.
[9]蒲松龄,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汪曾祺.后十年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11]汪曾祺.后十年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12]汪曾祺.后十年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13]汪曾祺.后十年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